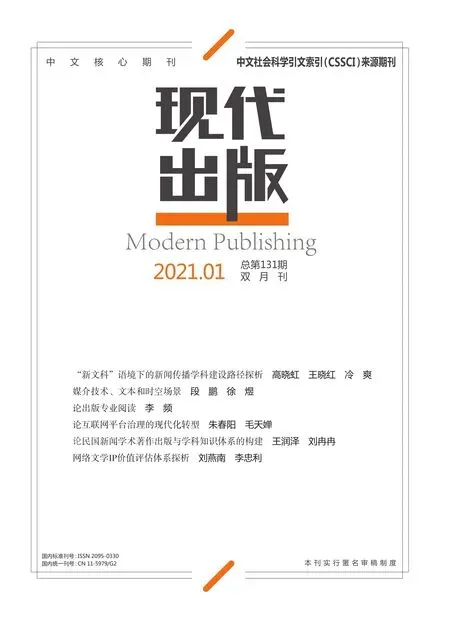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研究
——兼论国民党战时出版管理工作之得失
国民政府首都西迁重庆后,国民党中央为向各地特别是前线和沦陷区军民迅速传递宣传书刊,加强政治宣传,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从1939年1月成立到1945年7月被裁撤,共存续6年半时间,虽然对抗战时期书刊运输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未能缓解前线和沦陷区“文化食粮”短缺的情况,也未能塑造战时文化认同。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考察:第一,考察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设立背景、机构变迁、运作情形及在战时宣传品运输方面之成效;第二,以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存废及组织运作为个案,考察国民党战时党政机构工作效能低下之成因。
一、抗战初期战地书报工作之背景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沦陷区不断扩大,战事消息总是令人沮丧,为了振奋人心,激励士气,国民党中央要求加强对各地的政治宣传和文化鼓动工作。然而,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和交通线因战事中断,许多书报宣传品积压在后方,不能及时送达前线将士和民众手中。一名读者写信给著名出版家邹韬奋抱怨说,重庆出版的报刊寄到西安要费时两个月,与大后方接壤的晋东南地区也竟至一年半看不到后方报纸杂志。曾赴徐州前线采访的范长江说,在淮河南岸作战的青年军官告诉他,经常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前方军民亟感精神食粮缺乏,偶获来自后方之只字片纸,莫不争读传观,虽陈旧破烂之书籍,明日黄花之报纸,亦爱不忍释。”1938年3月,甫从前线采访归来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和《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目睹前线苏皖豫鲁各战区缺乏书报的情形,在大后方多方奔走,呼吁加强战地文化宣传工作,组织力量向前线输送文化印刷品。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蜜月期,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倡导呼吁下,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在1938年3月和7月先后成立了“战时书报供应所”和“战地文化服务处”两个机构来负责征集和输送书报。
战时书报供应所是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到第五战区去做统战工作的钱俊瑞多方奔走下成立的,曾得到国民政府相关文化机关的补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捐款两千圆。该所1938年3月26日开始对外办公,钱俊瑞任所长,全部工作人员仅有14人,地址设在汉口铭新街福新里八号(武汉沦陷后迁重庆王爷石堡五号)。战时书报供应所积极在后方募集书报刊物,大量供应前方。其第一期工作即征集到社会科学常识读物12种,抗战建国理论读物32种,国际与外交读物13种,日本研究读物12种,军事读物17种,政治读物13种,经济读物11种,史地读物14种,生活修养读物5种,文艺读物22种,抗战救亡记载读物11种,抗战实用知识读物14种,等等。
战地文化服务处成立于1938年7月1日,名义上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等13个机关共同发起组织,但实际运行则依托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展开。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统一战线的产物,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因此战地文化服务处的成立及运行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和支持。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洛阳、长沙、宜昌、上饶、西安、桂林等地设有14个总处,每个总处又根据情况设立分处共33处、代发处数百处,有的分处还将触角伸进了沦陷区,初步组织起了一个全国性的发行网。通过这些“服务处”“服务站”,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把征集到的书报杂志和各处编写的宣传品及时输送到前线,同时散发到广大中小县城。除公开征集外,战地文化服务处还在重庆、桂林、西安、金华四地设立印刷所,翻印《前敌周报》《士兵周报》等军中读物,专供前线士兵阅读,以上两种读物每期每种印量都在十万份以上。成立后五个月的时间里,战地文化服务处就出版及征集书报七百余万份。因为背靠国民党军委会和政治部,其在运输方面得到了军委会的优待和沿途兵站的帮助,经其运输的读物一概受到军用品待遇,其散发的读物数量很多、流传很广。
虽然战时书报供应所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在征集、印刷和输送抗战宣传印刷品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猜忌和不安,因为这两个机构从创设到运作,中国共产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担心这两个机构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大开方便之门。早在1938年3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组织了一次对武汉出版物的秘密调查,其调查报告认为:“无论书籍与刊物,皆共党及左倾色彩占绝大多数,类多诋毁本党之词,尤以书籍为最,计共审查二百五十八册,有关共党者有一百十册。若将左倾及人民阵线者加在一起,则有一百六十一册,已超过总出版量二分之一以上,影响所及,亦殊骇人。”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机关所发行之书报之所以能“到处流布”,是因为充分利用了“本党统治下之交通机关”。1939年1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传达了特种谈话会所制定的《禁止或减少共产党书籍邮运办法》,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宣传活动的限制和破坏。
为此,他们先是下令不准军队接受共产党方面的宣传品,也不准许邮局受理邮寄,后又借口战地文化服务处走私物资而无理搜查其堆栈,最终找借口在1939年3月31日将其撤销。而对战时书报供应所,国民党当局也采取了监视和限制政策。在1939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发给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一封密函中,他们指责战时书报供应所昆明分所等文化机构“或则公开发售违禁书刊,或则暗中从事异党活动,对于抗战建国之前途殊有不利之影响,亟应切实注意,严密防范”,要求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应严予取缔,并策动党员多设书店从事斗争,建立本党在当地文化界之核心暨外围组织,随时相机运用”。各地的战时书报供应所,自成立起就遭到了国民党当局不同程度的阻挠和破坏,如信阳分所在1938年6月和9月先后两次遭到国民党右派和驻军的查抄,其中第二次更是将书报全部没收。在国民党的蓄意破坏下,各地书报供应所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自1939年底起被迫陆续关停。
二、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设立过程及组织变迁
战地文化服务处和战时书报供应所等进步文化运输机关工作的相继停摆,于国民党而言,虽然暂时在表面上消除了共产党宣传品“蛊惑青年”的潜在风险,但是前线宣传和文化印刷品供应短缺的问题却也越发突出,特别是随着战事扩大和抗战大后方的进一步西移,情况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因为缺乏书报杂志,前线官兵没有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影响到了官兵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激励,也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抗战士气和战斗力。这势必要求国民党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全面受其掌控的新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邀集文化、交通、教育、军政等各有关部门的代表举行了三次会商,决定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协调调度文化品运输的机构,定名为“中央文化驿站管理委员会”,并商定了《中央文化驿站设置办法》和《中央文化驿站组织大纲》。根据组织大纲,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由国民党之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中央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委员长行营交通处,国民政府之行政院、交通部、教育部,以及四川省公路管理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共同指导,专门办理阐扬国民党理论及有利抗战建国书刊之传递与散布事宜。驿站设管理委员若干人,各部门各派一名代表担任,组成管理委员会,主持驿站一切工作事宜。管委会设常务委员五人,办理驿站一切日常事务。
1939年1月3日,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推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表窦培恩、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温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代表柳靖宇三人为常务委员。中央文化驿站在重庆设立总站,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代表施裕寿任站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表詹世清任副站长,总站设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内,1月16日开始对外正式办公。
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设立之初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管,至于其为何不由负责全国宣传文化工作事宜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目前尚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但可以确定,这一制度安排有违机构设置初衷,带来权责错位问题以及互相推诿等现象。机构设置之初,只有工作人员三四名,其中仅有一名专职人员,开办经费也不过750圆,后又减至600圆,而总站每月只有100圆办公费,但就是这些经费各部会也不愿落实到位,机构成立后,除了象征性组织各机关开会,商讨制定一些组织规程外,各项业务并无实质推进。1939年5月17日,总站在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本站自一月间奉命筹设以来,迄今已四月,因经费短绌,人员缺少,交通工具率无,以致不仅展布无由,即日常工作亦为之濡滞。”然而大量文化宣传品积压后方,不能及时运往前线和战区的局面,却引起了蒋介石的焦虑。1939年6月21日,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达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手令:“关于宣传品之分发办法,与线路及沿途各处传达之办法,必须确实设立,而其传达方法,应设军邮。请与交通部、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切实协商。……以传递中央宣传品为中心工作。”接到命令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迅即召集国民政府交通部、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政治部、国民党后方勤务部、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五个机关会商宣传品运输问题,决定:(1)改组扩充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管理处改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另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交通部、国民党后方勤务部、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七个机关组织理事会协商工作。(2)根据交通部所绘交通运输图另行划定分站14个,支站56个,以与现行军邮发生密切联系。(3)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草拟总管理处组织章程。(4)由国民政府交通部草拟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与军邮联系办法。7月中上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先后召集上述机构多次商讨,草拟了《中央文化驿站设置办法》《中央文化驿站理事会组织办法》《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组织办法》《中央文化驿站各地分支站与军邮联系办法》,并呈递蒋介石核定。1939年9月起,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管理权限和业务划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直接负责。后来还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罗的“全国文化交通站”,合并到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之中。
1939年11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文教会,通过了《战地书报供应办法草案》,其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工作指导和组织原则。根据该办法,战地书报供应统筹由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办理。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除了在重庆设有总站之外,在每个战区都设立分站一处,负责所在战区地域范围内的书报供应;在前线每一个游击区设立支站,负责本游击区内的书刊分发、递送。总站还在战地的每一个县设立办事处,县以下各个乡镇的驿站由当地的中心小学兼办;乡镇以下则以“保”为单位,由本保的国民学校(包括乡村学校、民众学校、短期小学、流动施教团等)负责。其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组织系统表
1940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38次会议通过了此前经蒋介石认可的《中央文化驿站设置办法》《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组织规程》及经费预算等件,并送请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追加预算。“中央文化驿站管理委员会”自2月1日起更名为“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总管理处在各战区设立14个分站,各分站下总计设立58个支站。后来随着战线推移及交通情况的变化,各分支站时有增设、迁移或撤废,然大体维持了这一规模,甚至一度有在南洋地区设立分站的计划。
至此,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作为一个统筹负责战区文化宣传品运输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下设指导科、运输科、总务科三科。指导科主管各分支站、办事处工作之设计、指导和考核,以及散发书刊的审查、分配等事务;运输科主管书刊的运输、散布以及运输工具的调查、接洽、管理等事务;总务科主管文书、庶务、会计及书刊之保管、统计、包装等事宜。此后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归属权几度变更,但其基本组织架构、组织规模和业务职能都得以延续下来,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机构被撤销为止。
三、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工作成效及困境
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成立后,其便担负起将后方出版印刷品运往各战区、基层部队和沦陷区的重任。其日常业务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是书刊征集、翻印审查和书刊宣传品运输,其中翻印和运输工作是其核心业务。此外,其还兼营一部分战地阅览室、流动书报室、书报代订业务。
征集工作。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等机关商定或由文教机关会报决定经常供给书报的数量和品类,然后由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登报或用其他办法,向各文化团体及私人征求所需书刊。在地方,则由各分支站与当地的文教机关商定经常供给的书报数量和品类,然后用同样办法向社会各界征募。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统计,1941年文化驿站共征集到书籍10 474册,杂志8 996册,报纸63 720份;1942年共征集到图书58 201册,杂志40 881册,报纸68 400份。但通过此办法征集到的读物,多数并非专门为战区实际需要而编著的,加之种类繁复,难易程度不一,有相当部分读物并不适宜前线官兵或沦陷区民众阅读。而且,其中部分读物,在国民党方面看来,难免有掺杂“异党宣传”或“激进内容”之虞。因此到1943年以后,征集工作已不再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
翻印工作。为了保证运输到前线的书刊品类、数量、内容符合要求,书报以官方翻印为主。所谓翻印,就是为了克服战地交通困难、减少运输负担,而在各战区、前线就地印刷所需书刊的办法。当时除了尽量利用各战区自身的印刷机构外,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还在江南(含浙西皖南)、苏北(包括鲁南)、皖北、鄂东(包括豫南)、湘鄂赣边区、河北鲁西、冀西北、鲁东北、晋东南、晋西十地设置印刷所十所,负责翻印各种教科书、一般读物、报纸和宣传品。仅1941年1月至3月就翻印各种书刊22种,共计80余万册,而1942年全年则翻印42种200余万册。
运输工作。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主要工作职能是在交运机关和承运机关之间进项联络、沟通、统筹协调。为保证运输工作的顺利实施,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先后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制定了《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递运各机关书店出版社交运书刊办法》等5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军政公私交通机关低价甚至无偿承运各类书刊宣传品,运输手段包括专车、兵车、航空、邮寄、军邮、客车、舟轮,甚至是畜力驼运和人背手提。其采用逐级分段运输的方式。所谓逐级,即由总管理处负责运输至各战区分站,然后由分站运输至支站,再由各支站分发到各国民学校,最后由各学校分发至区域内机关和民众手中。所谓分段就是在通铁路、公路、水路之处,尽先使用舟车交通工具;在不通水陆交通之处,则利用畜力或人力驮运。总之,穷尽一切手段和办法,将书刊宣传品运送至读者手中。
虽然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直辖机构,可以以中央的名义要求各地公私交通机关“义务”附运,而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也三令五申要求各地予以便利和配合,甚至对拒绝附运的公商车辆“扣发车辆准行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影响了工作效能的发挥。这其中既有现实环境造成的困难,也有普遍存在于国民党党政机关中的顽固性的体制弊端带来的困难。
首先,从现实环境看,自抗战爆发后,铁路、公路、水运常因战事中断,而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短缺,有限的运力都被优先用于军事目的,书报印刷品常被视作不急之务。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对于经济报告之决议案》中,关于交通问题第二款规定:“货物运输宜辨别性质,权宜轻重,以定先后……凡非军需建设器材及民生日用必需之品,应予严格限制,俾得先其所急。”从轻重缓急来看,显然军需用品、民生用品、伤兵的运输,都优先于宣传品的运输。正如当时一位观察者所言,在很多人看来,“精神食粮问题是吃饱了饭以后的事。饭是非吃不可的,人人都是一样,吃饱饭后有没有书读的问题好像并不严重”。虽然在宣传部门的措辞中对“精神食粮”的重要性不惜溢美之词,然而揆诸实际,则不免曲高和寡,现实中经常发生延误现象。
其次,从文化驿站的组织性质看,其不过是一个协调机关,既无事权,又无财权,也缺少自己独立的运输工具,其运输量的大小、运输效能的强弱,端赖两头的运输机关和交运机关是否有积极性。在运输机关方面看来,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以“中央”之名,硬性规定各公私交通工具低价甚至无偿代运书报宣传品,有些是“断人财路”,有些是“于理无据”。如按照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0次会议通过的《全国各地公私交通工具附运本党书刊暂行办法》的规定:官方或公营背景的军车每辆每月应义务运送100公斤宣传品,各公路局客车每辆每月应义务运送20公斤,各铁路每路每月5 000公斤,各轮船公司每月每船200公斤。众所周知,在战时后方,物资短缺、物价腾贵,一些运输车辆的司乘人员“或私带客商,或包运货物,或密贩鸦片毒品,或倒卖零件汽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每载一车人货,计算所得,轻者数百元”。不难想象,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硬性规定自然会遭到有形的或无形的抵制。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统计,1941年通过空军接转所、军运管理所、军运车辆指导所输送的书刊仅有两万余公斤,仅占其全年运输总量的1/7;而由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商车辆管制所运输的书刊,全年更是只有区区79公斤,船舶管理所也只有137公斤。到了1943年12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45次会议将先行办法修改为《全国各地公私交通工具附运文化驿站书刊办法》,其中除了铁路增加为1万公斤外,其他官方或公营交通机关的规定运输量都有大幅下调,尤以军车和各公路局运营车辆下调幅度最大,从原来的100公斤降为20公斤,下调了80%,事实上等于放弃了此一途径。而私营的运输汽车和轮船公司,也分别被安排了20公斤和50公斤的任务,虽然数量不大,但因属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单位,因此每多运1公斤书刊宣传品,就意味着少一份收入,强迫他们“代运”,于情于理都无依据。因此,各交通机关“常以汽油缺乏、运输困难为词”予以拒绝。
在其他途径都困难重重的情形下,邮局就几乎成为唯一可靠的运输机关。1941年邮局承担了全年运量的64.9%,1942年承担了75.2%,1943年因为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开通了“特约文化专车”而分流了少部分运量,但仍达到67.3%。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挤占了邮局大多数的印刷品邮寄业务,不但引起民营出版业者的不满,在战时运力紧张、运费高涨的前提下,也给邮政方面带来极大的运力负担和经营压力。中华邮政虽属公营,但也是营业性质,也需要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按照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与中华邮政最初商定的《中央文化驿站宣传书刊优待办法》,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一律按八五折计费,到后期已“不敷运夫力资”。1941年10月21日,中华邮政以“运输工具缺乏,邮运极端困难”为由,“对于若干地之印刷书籍,均奉命停止收寄,以免妨碍真正信函之运输”。后虽经各方面居间协调,仍给予一定便利和优惠,但邮政方面迭有不满,允为事实,因此就出现了前文提到的漏送和遗失也不愿意负责的情况。
从交运机关看,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推出的服务,本可为其解决战时运输困难问题,并且可节省相当一部分运费,理应十分踊跃才是,然而实际情况是很多交运机关并不积极。根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历年统计汇编的《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记载,除与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存在统属关系和指导关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外,其他部会或出版机构,多未积极利用该系统提供的运输渠道。考其缘由,大概不外乎如下三点:第一,各部会一般均有独立的出版和发行系统,如待运书刊系在本系统内部输送,径可通过系统内部已有交通系统或便利条件便可达成目标,求助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反而是多出一道中间环节,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迁延和损毁等风险也不可控。如在各战区,军方报纸就多利用“军邮和政工系统,除供给驻在地军队以外,并利用游击区的交通站,把报纸的发行深入敌后,供敌后的游击部队与政府工作人员阅读”。第二,不少出版机构自身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发行系统,如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全国建立了三级共600多个分支机构,比之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更多更发达,便无托求后者之必要。第三,各出版机构有盈利和生存之需要,除非中央有经费补助的“党义”“总理遗训”“总裁言论”一类的出版物,欲要其不顾成本而大量印刷和廉价供应一般书刊和宣传品,恐亦不可能。
鉴于以上原因,虽然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试图让国民党的宣传书刊能“传递迅速与散布广远且能深入战地”,但最后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首先从运量上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成立的数年内,其每年的实际输运量都远远未达到计划输运量:1941年仅运送14万公斤;1942年原计划运送153万公斤,实际只运送了13万公斤;鉴于上年度实际运量与计划运量之巨大差异,1943年将计划运量降低为40万公斤,但是实际只完成19.3万公斤;1944年计划仍为40万公斤,到当年11月仍只完成13.3万公斤。从实际到达率来看,则更乏善可陈。以1941年为例,本年共运送84 219包书刊,实际到达者仅29 598包,实际到达率只有35%。以如此少的运量、如此低的到达率,要应付全国20余万单位之需求,可谓杯水车薪。此外,由于担心违禁书刊会随其运输系统扩散,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绝不代运党外书刊,就是对党内交运的印刷品也实施严格的审查,“以免混入敌伪及共党有关宣传书刊”。这导致经由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寄往前方的书刊总体上品类单一、内容枯燥、缺乏新鲜感,并不能引起广大官兵和沦陷区民众的阅读兴趣。
而从人事方面看,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工作也存在着许多国民党官方机构的通病:在中央,人浮于事;在地方,无差可办。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在国民党的战时党政军机构中,类属临时增设的事务性机构,业务相对简单,重庆总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工作清闲、薪酬微薄,有很多人在外面做“兼职”贴补家用,“一直请的是事假。人不露面,还照领工资”。而在地方各分支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除了日常分发宣传书刊外,实际上也无事可做,因此可能还兼领一部分情报搜集工作。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曾给各分支站发密函,要求后者“蒐集共党宣传书报,径寄密存,所需费用先行代垫,再由中央拨还,或酌予津贴”。而在地方分支站的报告中,许多都是关于共产党军事动态、政治概况、经济设施等的机密内容,如在一份情报中详细开列了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和第五大队的人员和装备情况,甚至连指导员、中队长、办事处主任姓名都有详列。而如果考虑到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在重庆的办公地点川东师范学校也是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的所在,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怀疑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也无怪乎一些人将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在各地的分支站直接视作“中统”特务组织。实际上其基层网点虽众多,但是主要工作已不是服务抗战宣传,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了防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上。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其设立初衷,把宝贵的资源用在了内争问题上。
连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自己都承认,因为工作性质“被动”,其成立以后的几年间,实际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前方将士和沦陷区民众的“精神食量”短缺问题,如1944年豫湘桂会战失败后,粤汉铁路以东地区各省书刊运输几乎完全停顿。而随着1943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议“机构缩编”,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这样业务不多、成绩不彰的机构,就面临随时可能被裁撤的命运了。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CC系的陈立夫互换组织部长和教育部长职位,进而引发两大系统的人事洗牌。朱家骅先自组织部长去职后,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组织部长陈立夫所汰。而当时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系由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CC系以“紧缩机构”名义,欲将其并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1944年的工作检讨报告里甚至透露出国民党中央一度有裁撤之议,以至于报告不得不一再阐释其机构存在之必要。然而,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到1945年7月,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终于“奉命结束”。
四、从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看国民党战时出版管理工作
如果我们将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置于国民党整个战时出版管理工作中来考察,更可见国民党战时出版管理工作之混乱低效,进而管窥国民党党政机构设置和运作中长官意志带来的各种弊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即已注意到出版问题对抗战前途影响甚大,蒋介石甚至有“宣传重于作战”的训示。为此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出版管理政策,成立了众多出版管理机构和具体的出版、发行、运输机构,然而效果却极为有限,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首先,从管理层面看,政出多头,权责混乱。早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就针对新闻和出版管理工作改组扩大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职能,在其内部分设新闻处和出版处,分别主管新闻和出版工作。后来为了应付日益扩张的检查、管理职能,又在其下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管理职能上多有重叠之处,彼此之间经常争夺对出版业的领导权。仅从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成立后的归属看,就可见国民党出版管理工作之混乱。最初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归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管,后来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管辖。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党务改进案》决议扩充、加强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职能,将其定为统一管理党内出版事业之机构,一般出版管理重要原则应由该委员会负责拟定,其他党内类似组织一并裁并。1943年8月9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36次会议决议,将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划归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管辖,其所属之印刷所因非出版机构,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管辖。1944年3月20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51次会议决议,将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改组为事业机构,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被重新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存续期间竟然四易其主,在组织人事上还深陷派系斗争漩涡中,国民党出版管理系统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对此,国民党内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叶秀峰、苗培成、雷震和贺衷寒等9人连署《加强出版事业管制,以促进文化动员案》提案,痛陈国民党的出版管理乱象:“现有党政机关,管制出版事业者,在党则有中央新成立之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及中央宣传部之出版事业处;在政则有内政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组织既分歧,职权又颇混淆,管制政策既难一致,管制方法,自易疏漏,工作无由开展,效果无由显著,遂使出版事业,浪费人力物力,而日渐萎缩,精神食粮未能补充,而日渐缺乏。”
其次,从执行层面看,出版管理机构职能重叠,效率低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事业处职员屠义方批评道:“把一种事业弄得太复杂,太纷歧了,就难收整齐一致的功效,叠床架屋,不仅力量分散,且亦深感重复之弊。不幸本党所办之出版事业即深中此病。我们试将党内出版工作检讨一下,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出版事业多少是有点做得不统一,如中央宣传部就其业务的需要,有其单独的出版机构外,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训练委员会,亦各有其单独的出版组织。在中央党部一个机关内,就各有各的出版机构,他如三民主义青年团、教育部、政治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对于出版事业,亦各自为政,彼此之间,既无一贯之出版方针,更无统一之出版计划,工作没有联系,意志不能齐一,隔阂重复之弊,在所难免。各方在此种事业本身上所花的经费,确属不少,而所获的成效反而有限,未能集中精力,发挥效能,当然也就难得有很好的成绩。”而发行运输机构之设置,亦存在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本为解决战时后方宣传品向前方运输迟滞之问题而设立,然国民党内负此职责的机构还有很多。如“文化用品联合运输委员会”“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在推广发行业务上实际上也多有重合。1941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在部内另设“各地书刊供应处”,其职能包括“办理书刊之印刷分配及发行等事宜;办理书刊运输之联络事宜;办理民众小报之编印或翻印中央报纸分发战地事宜”。其三项职能,与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中国文化服务社职责几乎完全重合。
这不禁让我们心生疑窦:国民党何以要浪费如此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重复设置如此多职能相似的出版管理和执行部门?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战时国民党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框架中来。1939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它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五院和军事委员会之上,融党政军大权于一体。它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战时体制的最终形成,从法律上和制度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也从法制上确立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将国民党一党专政推向极端。因此,这一时期很多党政军政策的制定,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立、改组、裁撤,都出于蒋介石的个人意志,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设立也不例外。
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设立以后,日常行政上陷入“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怪圈。原来,在战时,无论党政军各机关及各种民众团体都喜采取“联席会议”之办事方法,遇有问题即召集所有有关方面集体讨论,由各部门成员共同成立一专门委员会,推动问题解决。政策制定者初衷是要通过集体决策的形式制定相关政策,集思广益、虑而后动,然后在实际执行上,相关部门为了分散自身工作负担和问责压力,时常会互相推诿扯皮。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成立时,也遵循了这样的工作程式,其结局是成立四个月,不但实际工作毫无推进,而且各部门允诺分摊的经费亦无着。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再三过问,恐怕其业务推进将遥遥无期。而后来在国民党中央文化驿站的运作过程中,虽然国民党中央再三传令各地“切实协助”书刊运输工作,各有关部门也转发命令如仪,但逾时就不免松懈,不得不一再“重申前令”。
国民党战时出版管理工作之无序混乱,正是整个国民党党政机器运转失灵的一个典型侧影。国民党的教训就是:若抛弃正常的民主决策渠道,妄图“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决策”,遇有问题不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途径而另设机构,就可能陷入机构臃肿、权责不清、扯皮推诿的陷阱中。
注释
① 文化食粮的供应问题[J].全民抗战,1939(83):1216-1217.
② 长江.战区文化供应问题[J].抗战三日刊,1938(54):3-4.
③ 金功辉.携手援义战: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经济动员概述[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40.
④ 江陵.一个文化供应机关——关于战时书报供应所[J].中苏文化,1938,2(1):53-54.
⑤ 勾适生.访问战时书报供应所[N].新华日报,1938-04-27.
⑥ 朱剑侬.关于战地文化食粮的供应[J].战地,1938,4(1):3-5.
⑦ 战地文化服务处近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3):24.
⑧ 储安平.战地的文化服务[N].中央日报,1938-10-07,1938-10-08,1938-10-09.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45.
⑩⑮⑯(55) 文化驿站工作报告:三十八年一至四月[A].台北: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数位典藏号014-000400-0012).
⑪ 刘晓滇.抗战时期的“战地文化服务处”[J].文史春秋,2011(11):11-13.
⑫ 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6 文化工作[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423.
⑬ 方继远.信阳战时书报供应所[M]//信阳地区文化局文化志编辑室.河南省文化志资料选编(第12辑),开封:1988:35-36.
⑭ 异云.前线需要书报[J].战时生活,1938(11/12):5.
⑰ 云南省政府训令秘缉字第336号[J].云南省政府公报,1940,12(18):9-10.
⑱⑲ 会商宣传品运输问题[J].中央党务公报,1939,1(1):21,33-34.
⑳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协调前线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及解决战区出现的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3月9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兼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
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8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3.
㉒ 中央文化驿站发展海外业务[J].中央党务公报,1940,3(5):19.
㉓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年度)[M].重庆:中央调查统计局,1942:31,34.
㉔㉖㉛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一年度)[M].重庆:中央调查统计局,1943:36,36,33.
㉕ 中央文化驿站大量翻印士兵读物[N].中央日报,1941-04-10.
㉗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党务报告[R].重庆:中央常务委员会,1943.
㉘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3册[M].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53.
㉙ 独孤迂.略谈军中文化设备[J].革命军人,1942(29):2-5.
㉚ 取缔军车搭客带货盗卖公物[J].广东省政府公报,1939(442):100-102.
㉜ 军事委员会训令办二通渝字第3555号[M]//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中央文化驿站法规汇编.重庆: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1941:80.
㉝ 此处各项百分比数据是笔者根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1941、1942和1943年历年统计数据换算得来的。
㉞ 魏中天参加文化运输问题等谈话会报告[A].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一般496/48.21).
㉟ 呈请修订中央文化驿站宣传书刊优待办法[J].驿运月刊,1942,3(1):32.
㊱ 广西邮政管理局启事[N].广西日报,1941-11-12(4).
㊲ 张煦本.记者生涯四十年[M].台北:自立晚报社,1982:61-62.
㊳㊻㊽ 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三十三年度工作检讨报告[R].重庆: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1944.
㊵ 20余万单位之数字是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工作检讨报告中所言。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三十三年度工作检讨报告[R].重庆: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1944.
㊶ 袁风华,林宇梅.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设立“中央文化驿站”有关史料选[J].民国档案,1987(1):45.
㊷ 朱传荣.朱家溍口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1.
㊸ 中秘处致王延龄函[A].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特9/20.1).
㊹ 伪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及第五大队姓名实力调查表[A].台北: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特9/20.13).
㊺ 马甫平.晋城抗战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192.
㊼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9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2001:317,319.
㊾ 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致教育部函[J].民国档案史料,1987(1):47.
㊿ 徐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51)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792.
(52)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纪录[R].重庆:中央常务委员会,1942:180.
(53) 屠义方.对于统筹本党出版事业之拟议[J].出版通讯,1942(4):2-3.
(54) 汪耀华.中国近现代出版法规章则大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285.
(56) 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中央文化驿站法规汇编[M].重庆: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1941: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