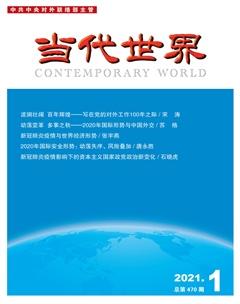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
孙德刚 韩睿鼎

【内容提要】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阿拉伯民族主义历经百年兴衰。二战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武器”,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矛盾。然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从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到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安全挑战和身份认同日益多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在海湾地区应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东地中海地区应对土耳其的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多极化的“新中东”格局已现端倪。
【关键词】阿拉伯民族主义;巴以问题;阿以关系;阿拉伯国家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1.007
阿拉伯世界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从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成为连通欧洲与亚太两大经济区的桥梁和纽带。奥斯曼帝国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风生水起,民族独立、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成为阿拉伯国家精英的奋斗目标。为削弱奥斯曼帝国,英国承诺支持阿拉伯人在肥沃的新月地带(沙姆地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又与法国秘密签订了瓜分中东的《塞克斯-皮科协定》。在诸多此类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了由盛到衰的百年变局,对当前大国关系和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地方民族主义
1945年,埃及、沙特、伊拉克等已获得独立的7个阿拉伯国家宣布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旨在促进西亚、东非和北非阿拉伯人的团结,像苏联一样构建统一的“阿联”。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制定了阿拉伯统一的“宏伟蓝图”。伊拉克时任首相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提出,阿拉伯统一应分“两步走”,即先实现阿拉伯次区域的一体化,再实现阿拉伯世界整体的统一。作为第一步,沙姆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先合并成一个国家,接着非洲的埃及、苏丹和利比亚统一,然后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和也门统一,最后上述3个次区域再组成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独立后再加入到统一进程中,最终形成大一统的“阿拉伯联邦”。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主张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和伊斯兰教为纽带,强化民族认同。为增强民族凝聚力,阿盟呼吁各国阿拉伯政府和人民支持民族解放,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法殖民主义。在共同的任务面前,阿拉伯民族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追求以团结与统一实现民族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阿拉伯世界的共同斗争下,法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英国于1971年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军、结束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委任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阶段性成就。不仅如此,埃及纳赛尔高举泛阿拉伯主义旗号,于1958年宣布埃及同叙利亚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同年伊拉克和约旦宣布组成阿拉伯联邦;1974年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宣布与突尼斯合并为伊斯兰阿拉伯共和国;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和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提出“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大目标;其他阿拉伯国家也积极研究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方式。1981年5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旨在促进海湾阿拉伯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一体化、遏制伊朗;1989年,埃及、伊拉克、约旦、阿拉伯也门共和国4国成立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同年,北非5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1]然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统一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者主张世俗化和现代化,反对君主世袭制;而以沙特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主张伊斯兰教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基础作用,反对世俗化和共和政体。纳赛尔推行的阿拉伯统一事业以及阿拉伯民族革命,招致了以沙特为首的君主制国家的反对和指责。1962年,沙特组织召开国际伊斯兰会议,讨论对付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策略。[2] 1969年,沙特高举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发起成立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埃及作为世俗主义的代表,沙特作为伊斯兰主义的代表,其意识形态争论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无疑是致命一击,两国在也门发动的代理人战争削弱了阿拉伯世界联合抗击以色列的能力。
其次,在冷战大背景下,无论是美苏还是英法均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阿拉伯世界统一为一个国家既不具有可操作性,又充满危险,故采取了培养代理人、分而治之等措施。早在1955年,英国就和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北层国家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成为西方遏制苏联向中东扩张的屏障;苏联则与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等“进步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制衡亲西方的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认为两个或多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对美国弊大于利,认为一个更大更自信的阿拉伯国家会持强硬政策,难以相处;阿拉伯民族主义会被共产主义所利用,统一后的阿拉伯国家如果持反美立场,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3]
最后,在四次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连连失利,对阿拉伯民族主义造成严重打击。纳赛尔将以色列视为“卡在阿拉伯世界咽喉的一根刺”,认为其阻断了西亚和非洲的阿拉伯世界连为一体。1948、1956、1967和1973年,阿以之間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多次败北,无力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遥遥无期,甚至1973年阿拉伯世界长期的政治中心——埃及首都开罗一度处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威胁之下。
经过30年的抗争,阿拉伯各国政府和民众出现了沮丧和失望情绪,将纳赛尔主义的失败归咎于“阿拉伯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已不在少数。[4]萨达特把埃及从纳赛尔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他明确规划了“埃及优先”的外交战略,强调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巴以问题。1978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埃及签订《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退潮;埃以单独媾和体现了埃及坚持国家利益优先原则,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埃及民族主义。
埃以媾和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思想混乱,激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愤,造成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削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5]1979年,埃及被阿盟扫地出门,阿盟总部也从开罗迁往突尼斯。随着埃以撇开巴勒斯坦、开启阿以和平的先河,阿盟群龙无首,沙特、埃及等倒向美国,伊拉克、叙利亚等倒向苏联,利比亚特立独行,各方激烈争夺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构成的威胁增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凝聚力,延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弱的进程。
因此,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到冷战结束,阿拉伯民族主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前30年以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为大旗,将以色列视为主要威胁,后20年是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共存时期,以以色列和伊朗为主要威胁,阿拉伯民族团结进程受挫。
冷战结束后,由于阿拉伯世界长期未能解决内部政治制度、经济诉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等问题,加上领导权之争和外部力量的推波助澜,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中东地区格局从美苏两极变成了美国一超独霸,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联合苏联制衡美以的策略走到了尽头。1993年,以色列巩固外交成果,与巴勒斯坦签订《奥斯陆协议》;1994年又与约旦签订《华盛顿宣言》,约旦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自此,处于抗以前线的两个国家——埃及和约旦相继与以色列媾和。1999年,毛里塔尼亚宣布与以色列建交,后因以色列发动加沙战争于2009年宣布断交。到21世纪初,阿拉伯国家身份、利益和价值观进一步多元化,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取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6]
阿拉伯民族主义从应对以色列威胁到应对多重挑战
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又一转折点。阿拉伯国家政权安全受到的内部威胁,超过了以色列等外部威胁。阿拉伯世界从应对以色列威胁转变为应对多重挑战。
首先是社会抗议的频发。从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到西亚的也门、巴林、叙利亚,“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街头政治体现出下层民众“求民生”“反腐败”的强烈诉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发生政权更迭,巴林爆发街头政治,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陷入代理人战争的泥潭。2018—2019年,“阿拉伯之春”第二波再度冲击阿拉伯国家,导致阿尔及利亚、伊拉克、苏丹、黎巴嫩政府改组,阿拉伯国家被迫将注意力从国际转向国内。维护政权安全、回应民众对社会变革与经济改革的诉求,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大国中东战略调整的冲击。21世纪初,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却未能像二战后在德国和日本那样,通过政权更迭和民主改造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打造“民主样板”。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厌战情绪上升,不愿意投入过多军事和外交资源,对解决巴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等热点问题丧失热情。与此同时,俄罗斯以叙利亚和利比亚代理人战争为契机,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俄进美退”的战略新态势迫使广大阿拉伯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寻求再平衡。
再次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基地”组织以及2014年后的“伊斯兰国”对阿拉伯国家政权安全构成了新挑战。极端组织借助高科技手段,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当中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宣扬民族、宗教和教派仇恨,构筑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不仅对西方主导的中东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而且阿拉伯现政权首当其冲,成为其打击的“近敌”。叙利亚“胜利阵线”、“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机构、索马里青年党、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残余力量蓄谋东山再起、实施破坏活动,迫使众多阿拉伯国家将反恐、去极端化视为国家的重要任务。
最后是伊朗和土耳其的地区挑战。“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来,教派矛盾升级,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民族认同和教派认同稀释了国家认同。教派主义的兴起不仅影响了战乱阿拉伯国家,而且在非战乱国家如伊拉克、黎巴嫩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选举政治打上了教派争夺的烙印,强化了教派、族群和部落认同。[7]伊朗积极组建“什叶派抵抗联盟”,联合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和沙特实施“反包围”,以缓解周边地区受到的压力。土耳其高举“维护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大旗,通过政治伊斯兰与卡塔尔、巴勒斯坦哈马斯、叙利亚土库曼旅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等形成“亲穆兄会联盟”。2016年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伊朗断交;2017年沙特、阿聯酋、巴林、埃及等国与卡塔尔断交,这意味着伊朗、土耳其、穆兄会等内部挑战上升为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首要威胁。
在敌友换位、中东地区治理退潮、多极化初现端倪、地缘政治强势回归的“新中东”,阿拉伯世界迎来了新的百年变局。威胁复杂化、利益多元化和身份多重化,迫使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战略上寻求“再平衡”,包括缓和与以色列的矛盾。2015年也门冲突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对阿联酋来说是重大安全问题;[8]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代表——伊朗和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的代表——穆兄会对阿联酋构成了双重挑战。2020年8月,阿联酋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宣布关系正常化,表明阿拉伯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和新一届政府对以色列安全认知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印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判断,即随着阿拉伯世界面临多重任务,阿拉伯国家不再坚持“先巴以、后阿以”的和谈顺序,而是在巴以和平前,率先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9]协议用“亚伯拉罕”作为名称意味深长,暗示双方认可亚伯拉罕是共同祖先。阿以建交带动了巴林、苏丹、摩洛哥与以色列邦交正常化,阿以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准盟友”,更多阿拉伯国家或将在对以关系上实现重大转变。
如果说阿以通过和解实现了“连横”,土耳其与伊朗则在捍卫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坚持政治伊斯兰、反对以色列霸凌主义方面成为存在互补利益的“合纵”。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积极参加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进程;在利比亚,土耳其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制衡埃及、阿联酋、沙特、以色列等支持下的利比亚国民军;在东地中海,土耳其成为以色列、埃及和阿联酋遏制的对象。2019年1月,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决定设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随后,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2020年9月,埃及、以色列等6国能源部长举行视频会议,签署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章程,宣告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正式成立,矛头直指土耳其。

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带动了巴林、苏丹、摩洛哥与以色列邦交正常化,阿以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准盟友”,更多阿拉伯国家或将在对以关系上实现重大转变。图为2020年9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从左至右)出席协议签署仪式。
在海湾地区,伊朗成为阿以的共同对手。2019年伊朗总统鲁哈尼提出“霍尔木兹和平倡议”,呼吁外部大国停止对波斯湾安全和政治事务的干预,后将“倡议”提交多个阿拉伯国家和机构,但应者寥寥。沙特指责伊朗构建“什叶派新月地带”,操纵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颠覆巴林等阿拉伯国家政权;伊朗指责沙特等国充当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拼凑“中东战略联盟”,遏制伊朗。2020年11月底,有媒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沙特秘密会晤。[10]不久便发生了伊朗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遇袭身亡事件,更加重了伊朗对沙特、以色列和美国勾结、破坏伊核计划的猜疑。
阿拉伯民族主义缘何式微
纵观阿拉伯民族主义百年兴衰历史,可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孕育了阿盟,阿盟体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阿盟提出民族独立、政治统一、政治民主化、经济文化发展和世俗化五大目标,并于2002年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然而,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哈马斯与法塔赫分庭抗礼,使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有恃无恐,不断扩大战果。随着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相继与以色列媾和,“新中东”格局浮出水面。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已使阿盟降格为一个仅仅将阿拉伯国家在形式上团结起来和充当重新定义泛阿拉伯主义的论坛性平台。[11]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背后有诸多主客观、内外部原因。
第一,阿拉伯国家始终未处理好“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阿拉伯民族团结与统一既是理想,又是现实。阿拉伯世界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文明板块。然而,阿拉伯民族不是直接由血缘组合发展到地缘组合的原始民族,而是以阿拉伯半岛已有的阿拉伯民族为核心, 由若干民族融合而成的新型民族。[12]阿拉伯国家资源禀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存在“一族多国”和“一国多族”的现象。国家认同、次国家认同和超国家认同之间竞争激烈,泛阿拉伯民族认同、泛伊斯兰宗教认同相互交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彼此影响,宗教、民族、国家三种群体认同的张力贯穿始终;宗教性、整体性、地方性构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三大特点。[13]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了远大理想,却在实践中未能解决多元诉求的问题,最终偃旗息鼓。
第二,阿拉伯世界未能摆脱形而上层面的意识形态争论。阿拉伯民族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复兴和统一,但其内部意识形态争论从未停止过,世俗与宗教、温和与激进、分权与集权、传统与现代、左翼与右翼、君主制与共和制是内部争论的焦点。如何求同存异、避免意识形态纷争,成为过去、当前和未来阿拉伯国家走向团结的前提。在争取民族解放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这就决定了当时民族主义的具体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斗争、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等方式来颠覆西方的统治秩序。而到了国家建设阶段,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设国家,因而体现到操作层面,便是以“问题解决”代替“意识形态争论”,以“国家意识”代替“民族意识”,以维护现状代替对政治秩序的破坏。[14]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阿拉伯世界迎来了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穆兄会趁机扩大活动范围,引起君主制和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恐慌。阿拉伯国家在君主制模式、政治伊斯兰模式、世俗威权政治模式等不同模式之间相互转换,至今未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
第三,阿拉伯国家普遍未能处理好民生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西亚到北非,多个阿拉伯国家开始实行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在经济社会治理中未能培养了解本国国情的技术官僚,大多是照搬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将民众推向市场,提供社会支持和福利的能力下降,导致基层群众生活贫困,社会腐败现象严重。[15]阿拉伯国家人口自然增長率较高,经济增长率低,导致贫困和失业问题长期困扰各国政府。不仅如此,以海合会六国、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为代表的产油国依赖地租经济,缺乏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科技产业,高等教育不发达,高科技人才匮乏,中长期规划好高骛远,可操作性不强。为争夺地区主导权和维护政权安全,阿拉伯国家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向了国防与安全,经济停滞不前。中东阿拉伯国家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后,执政者没有实现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转型。无论是主张世俗主义的泛阿拉伯主义,还是主张回归传统的泛伊斯兰主义,都未能真正实现经济振兴。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宏伟蓝图主要体现的是阿拉伯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抱负,政府未能满足社会中下阶层的经济和发展需要,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宏伟构想难以在中下层民众当中产生共鸣。
第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倡议未能顾及中小国家的关切。二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因内部矛盾而导致的断交事件屡见不鲜,包括利比亚与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卡塔尔至今未恢复与埃及、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等国的外交关系。阿拉伯世界长期未能形成妥善解决内部分歧的规范,也未能就未来民族统一的方式进行充分讨论,其整合阿拉伯国家的力量缺乏先进的制度和创新手段。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世界的侵略,而自己却在内部推行类似的强权政治;他们在理论上反对地方主义,而在实践中又奉行地方主义。[16]如埃及与叙利亚合并后,纳赛尔将埃及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移植给了后者;利比亚与突尼斯合并后,卡扎菲将利比亚的体制移植到了突尼斯。同样,老阿萨德总统将黎巴嫩视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萨达姆将科威特作为伊拉克的一个省,并打着“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号,将阿拉伯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打了8年的两伊战争。中小国家担心的是:民族统一进程实际上是大国吞并小国的过程。海湾阿拉伯国家担心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掩护,伺机推翻君主制政权,故民族统一被阿拉伯小国视为洪水猛兽,这种威胁甚至超过了以色列。
第五,阿拉伯世界内部族群、教派和部落构成因素复杂,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又一障碍。以北非阿拉伯国家为例,马格里布地区诸国的认同呈现多元性与模糊性特征,存在柏柏尔、古罗马、阿拉伯、法国及非洲等多元异质文化,缺乏统一的身份认同。除了主体民族外,阿拉伯世界的庫尔德人、科普特人、柏柏尔人等人数比例较高,他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持保留意见;加上伊拉克、黎巴嫩、索马里、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中央政府主导能力下降,无法将各民族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民族分裂势力在外部大国的影响下潜滋暗长,南苏丹独立就是其中一例。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和阿拉伯国家内部族群的“颗粒化”相互促进,严重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
第六,阿拉伯世界区域一体化步履蹒跚。与欧盟、东盟和非盟相比,阿拉伯国家从未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阿盟下设阿拉伯经济理事会,成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阿拉伯货币基金,但是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同质化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经济的“内循环”。1957年6月,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成立;1964年,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成立阿拉伯共同市场。但是到1973年,上述4国相互间贸易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3.4%和1.9%。[17]近年来,东亚国家相互贸易依存度高达51%,拉美国家为19%,非洲国家为16%,而阿拉伯国家仅为10%,其中马格里布国家仅为4.8%。阿拉伯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等,而不是域内国家。[18]没有利益共同体,就难以建立阿拉伯政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结语
《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并不是中东和平的序幕,而是阿拉伯世界分化的标志。从《戴维营协议》到《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到今天的地方民族主义,各国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安全和利益进行再定义,阿以掀起建交浪潮体现出双方在“新中东”背景下的战略再平衡。[19]2020年8—12月,以色列在短短5个月内增加了4个阿拉伯邦交国,可谓建国史上的重大外交胜利。尤其是苏丹曾经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与埃及并肩作战,向来是阿拉伯世界坚定反以的左翼国家。[20]其与以色列建交,意义深远,表明阿拉伯国家内部、阿盟和中东形势都处于转型之中。
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式微,阿拉伯国家整体影响力下降。美、欧、俄等域外力量以及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这3个非阿拉伯国家成为“棋手”,阿拉伯国家沦为“棋子”,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索马里等动荡国家所在的广大地区则沦为大国政治的“棋盘”。美国打造的中东战略联盟(海合会六国、约旦、埃及),俄罗斯围绕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进程打造的“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角”,伊朗主导的什叶派抵抗联盟,土耳其主导的亲穆兄会联盟,以色列与亲西方阿拉伯国家组建的“温和联盟”等等,把阿拉伯世界撕成了碎片,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岌岌可危。地缘政治的回归和大国在阿拉伯世界构筑的代理人网络,使阿拉伯世界距离民族复兴和统一的“初心”渐行渐远。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外交研究”(项目批准号:19AGJ010)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第二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苏童)
[1] 黄民兴:《阿拉伯民族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载《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2日,第8版。
[2] 刘中民、薄国旗:《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77-78页。
[3] 白云天:《美国应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超冷战考量(1955-1960)》,载《阿拉伯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第92页;R. Thomas Bobal, “‘A Puppet, Even Though He Probably Doesnt Know So: Racial Identity and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Encounter with Gamal Abdel Nasser and the 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5, 2013, p.943。
[4] 殷之光:《“全球六十年代”与“全球治理”话语的局限——以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为视角》,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3期,第13页。
[5] 何志龙:《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63页。
[6] 韩志斌:《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评析》,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期,第58页。
[7]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Vol. 56,No. 1, 2014, p.95.
[8] Ebtesam Al Ketbi, “Contemporary Shifts in UA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Liberation of Kuwait to the Abraham Accord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2020, p.4.
[9] Hassan A. Bararim, The Abraham Accord: The Israeli-Emirati Love Affairs Impact on Jordan, Amma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20, p.7.
[10] Summer Said, Stephen Kalin and Dion Nissenbaum, “Secret Meeting in Desert Between Israeli, Saudi Leaders Failed to Reach Normalization Agreement,” November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cret-meeting-in-desert-between-israeli-saudi-leaders-failed-to-reach-normalization-agreement-11606508754.
[11] 趙军、陈万里:《阿盟视角下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实践》,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第30页。
[12] 王彤:《阿拉伯民族为何难以统一——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第46页。
[13] 刘中民:《阿拉伯民族的三大特点及其对阿拉伯政治思潮的影响——以民族与宗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10-11页。
[14] 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的自我转型: 表现、原因及影响》,载《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9页。
[15] 程东金:《阿拉伯变局:新旧秩序的十字路口》,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第11页。
[16] 王彤:《阿拉伯民族为何难以统一——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统一理论与实践》,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6期,第51页。
[17] 黄民兴:《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载《中国民族报》2011年8月12日,第8版。
[18] Tom Bayes, “Chinas Emerging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ence in North Africa,” February 27, 2019, https://atlantic-community.org/chinas-emerging-diplomatic-and-economic-presence-in-north-africa/.
[19] Yoel Guzansky & Zachary A. Marshall, “The Abraham Accords: Immediate Significance and Long-Term Implications,”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2020, p.8.
[20] Ehud Yaari, “The Sudan Agreement: Implications of Another Arab-Israel Milestone,” October 26, 202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udan-agreement-implications-of-another-arab-israel-miles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