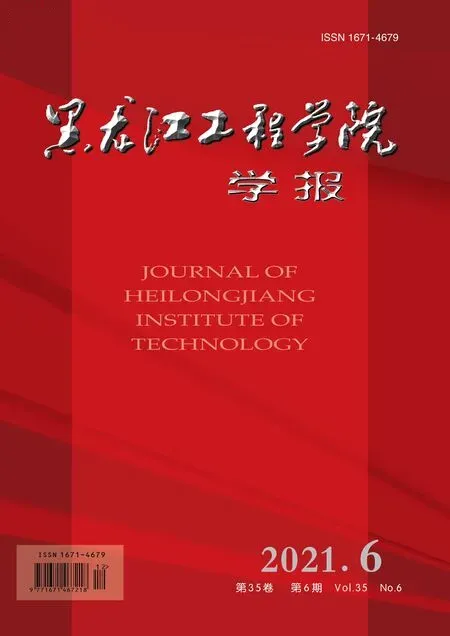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周继舟,曾瑞明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00)
恩格斯晚年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做法常常遭到误解,这一切肇始于恩格斯的“爱徒”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具有“公信力”,伯恩施坦将晚年恩格斯拉扯到修正主义理论阵营为其理论“站台”。从这开始至今,恩格斯晚年思想一直是后人广泛讨论和研究的课题,这其中有许多讨论是沿着伯恩施坦的理论路径进行考察并最终将恩格斯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为了说明恩格斯晚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还原恩格斯晚年真实形象,文中首先梳理历史上对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讨论,探求争议的本质,然后以恩格斯的文本为依据,建立“历史—文本”之间的本质联系,阐明恩格斯晚年根据西欧社会变化的现实情况提出革命方式变化的客观性,最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代背景阐明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对于我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时代价值。
1 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争议
恩格斯根据社会新形势所提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从它问世到现在的百年历史中饱受争议并不断引发后人广泛讨论。对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而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一直是后人不断争论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的现实背景,伯恩施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引发第二国际内部一片哗然,为维护恩格斯思想的思想遗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愤怒并对这种思想进行反驳。即便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仍将恩格斯晚年文本进行片段式的解读,曲解恩格斯的原旨。一些西方国家学者出于自身的目的将恩格斯晚年思想进行切片化的解释,这种做法无疑走向失真性;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同样处于相对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的阶段,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风潮,并渗透在社会各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思想似乎在中国重新上演,这激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议论。
1.1 第二国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争议
对恩格斯晚年革命思想的讨论与争议始发于第二国际内部,而第二国际内部纷争的高潮又滥觞于伯恩施坦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误解。当伯恩施坦面临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双重困境后,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修正,同时对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下文简称《导言》)中关于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民主合法斗争给予了高度赞扬,他指出:“他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恐怕可以正当地把它成为他的政治遗嘱)为社会主义运动立下的功绩,是无论怎样高地评价都绝不会过分的。”[1]并以片面化和主观性的特点将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策略的思想为自己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撑腰”。针对伯恩施坦的此种做法,第二国际成员卢森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中指出:“当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审查当前工人运动的策略并把合法斗争同街垒对立起来时,从导言的每一行都看得很清楚,他论述的不是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当前日常斗争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框内它的态度问题。一句话,恩格斯对被统治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做了指示。”并认为“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为,而立法则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维持生存的手段。”[2]考茨基在面对伯恩施坦误解恩格斯的这个问题上,他指明恩格斯是一个老革命家,并指出恩格斯认为是可耻的东西却被伯恩施坦当作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功绩”[3]。
1.2 西方学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讨论
恩格斯逝世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对恩格斯也发起了责难。而责难的推动者之一诺曼·莱文教授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指出:“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也导致了欧洲劳工运动在科学意义上的合法化……对于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变化的不可避免性这一规律只能解释为它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合法性。”[4]他把恩格斯晚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想打上了教条主义的烙印,同时这种认识也印证了他所推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并将马克思视为“辩证法学者”,将恩格斯视为“机械唯物论者”。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价。美国学者曼弗德雷·B.斯特格认为恩格斯晚年所提出来的革命新策略是根据他晚年所生活的社会新环境而进行的新的思考,他认为把恩格斯与修正主义划上等号是对恩格斯晚年著作的抽象理解。
1.3 中国学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纷争
把视野聚焦到中国,中国学者对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也进行了激烈地讨论。民主社会主义信奉者从自身理论需求出发,将恩格斯指认为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典型案例就是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的问世激起了无数争议与反对,此文作者认为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否定了自身壮年时期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同时也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而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5]而面对这种极具误导性的思想,大多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发表了相关文章进行批驳。陈学明教授通过史实考察和文本分析指出恩格斯不仅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还是坚定的守护者,他指出:“认为恩格斯后期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仍然坚持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导师、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他们从未‘拿原则作交易’。”[6]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者也借此次机会梳理了关于恩格斯晚年争议的起源、过程及其走向,主要代表就是高放先生发表的《恩格斯“政治遗嘱”百年八次争议》,这篇文章对恩格斯晚年思想起到了正本清源、消除误解的作用,高放先生认为《导言》肯定了议会民主的合法斗争的作用,这是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他还指出:“和平过渡与暴力革命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各国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的策略。”[7]
2 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恩格斯生前对《导言》的误读就做出了澄清和回应,他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好处的。”[8]之后在给朋友的多次回信中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即便如此,后人仍对《导言》进行切片化的处理,走向文本的思想原旨的对立面进行错误解读,而这种做法的本质无疑是缺乏对恩格斯晚年著作及其思想进行整体性思考的表现。对恩格斯晚年思想进行全面性和整体性地把握必须要立足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从恩格斯晚年的文本出发,还原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首先,通过欧洲社会的发展研判欧洲社会新形势,肯定无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积极作用。恩格斯通过对世界新形势和阶级斗争新发展的判断,并结合对社会发展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明确了暴力革命和和平方式都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和手段,都是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而服务的。但是社会现实条件决定了社会革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形势高涨,现实社会并不具备合法斗争的条件,因此,暴力革命的手段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显得具有唯一性。随着社会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各国的实践表明和平夺取政权的方式又显得有其合理性。因此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合法斗争表示了肯定态度,认为这个手段是当前形势下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武器,他指出:“他们(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9]从中也可以发现,恩格斯认为普选权是进行合法斗争的核心,因为社会发展条件和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了运用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普选权的手段不断扩大阵营,加之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在普选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恩格斯对此毫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发展。”[9]不难发现,恩格斯认为利用普选权而开展合法斗争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一件伟大且新式的武器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其次,坚决不放弃暴力革命这一原则性的革命策略。恩格斯晚年对议会斗争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或者放弃暴力革命的手段。相反,恩格斯强调“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的这么远,竟让你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8]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以革命者的个人意志为出发点,要以革命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行动指南,所以他强调在革命形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必须拿起暴力革命这个武器。同时要认清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统治人民的暴力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在利用合法的手段夺取政权时,资产阶级会先采取暴力手段对无产阶级实行镇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手段进行反抗斗争。他在1892年回答伯维奥时就指出:“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9]这说明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暴力革命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再次,强化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恩格斯早在1871年就指出:“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10]恩格斯何出此种见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各种新的现象以及工人阶级自身发展的不充分等原因,主要表现在:其一,认为当前工人阶级还不成熟,部分人思想具有落后性、对社会的洞察不够充分、无法领悟到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容易被社会错误思想误导;其二,19世纪末,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成立了无产阶级组织,但是这些组织的指导思想都存在一定的空洞性,无法实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进而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应有的效果;其三,在议会斗争特别是在普选权中加强政党建设可以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恩格斯认为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以指引工人阶级进行正确行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拥有先进的思想引领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工人运动中,不能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必须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积蓄力量提供有力保障。
最后,坚定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必将胜利的信念。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极速增长并加速了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改善了工人阶级生产和生活环境并使其拥有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最为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随着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状况的深入研究,他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给出的“好处”和两大阶级之间矛盾暂时缓和都是“假象”,这并没有“蒙蔽”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想法。因为恩格斯明确指出即便资本主义通过调控手段抵抗住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巨大风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旷日持久地维持下去。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被消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会一直存在并不断激化,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难以调和,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命运也就成为了不可改变的结果。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何时崩溃的具体时间恩格斯并没有指明,因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1]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极端激化,生产力不断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现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就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1]
3 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新思想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晚年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教条,而是指导行动的科学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引实践,实践必然会走向与结果相反的方向。所以恩格斯晚年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已有的理论之内,而是通过观察社会发展新现象和新形势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为新时代不断深化自我革命进而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对于新时代继续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3.1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夯实理论基础
纵使与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相去甚远,但是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晚年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对于当前新时代深化伟大社会革命仍然具有实践价值。恩格斯在风潮云涌的19世纪末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议会斗争”“街垒巷战过时”的新见解和新看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边界,指引着20世纪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始终影响着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自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一条死路。”[12]中国在“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成功的背后,究其原因是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根据新形势制定方针政策、调整改革策略、完善发展方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仍然坚持“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出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复兴之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也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增强忧患意识,完善和发展自我革命的制度体系,根据新时代的发展特点、社会环境,不断调整改革的手段和策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进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向社会革命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
3.2 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初心和使命依据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中,我国也面临境外势力的挑衅和挑战,境外势力不断干预中国发展,国际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局面,然而在此种国际局势中,党坚定自我革命的信心来源何处?一方面是理论自信,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进行深刻剖析并对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全面把握的前提下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无产阶级必然取得胜利[11]。另一方面是现实信心,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使用各种手段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作用甚微,反倒是全球化主义、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右翼”势力抬头,而这背后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固有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之前的苦苦挣扎。只有认清了这两方面内容,我国继续进行新时代“伟大革命”才能坚定信心,才不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打乱阵脚。所以在此种环境之下,新时代继续进行自我革命进而推进党的伟大革命,一方面要知己更要知彼,认清国际局势,深刻把握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认真总结各方面利弊因素;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社会革命保驾护航。
3.3 为人类继续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坚定理想信念
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归宿并不仅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终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10]恩格斯晚年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取得胜利,最终社会历史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并指出人之为人就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城乡、工农以及脑力与体力的分工的对立关系会逐渐消失进而使劳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革,人在这个意义上才摆脱了动物的某些特征,“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0]“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0]这意味着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是走向自由人全面发展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