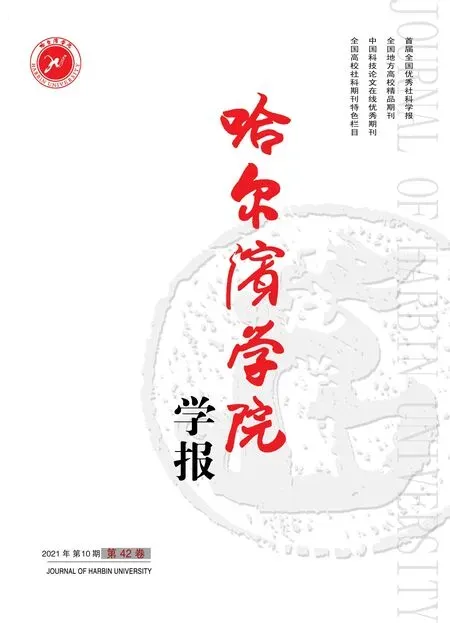文化·宗教·人性:莫里耶小说《特丽尔比》中的焦虑书写
潘玉立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也译作杜穆里埃),1834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童年辗转在伦敦、巴黎和比利时等地。[1](Pvii)早年在异国他乡漂泊的经历使得他对国家、种族、性别、宗教、文化等问题格外关注。他的第二部小说《特丽尔比》(Trilby)在19世纪红极一时。小说以其巴黎求学生活为原型,以催眠为分界线,分别讲述了催眠前身为模特的特丽尔比和英国画家小比利(Little Billee)之间的故事,以及催眠后化身知名歌唱家的“斯文加利小姐”(La-Svengali)和犹太音乐家斯文加利(Svengali)之间的纠葛。小说一经出版就掀起了一股“特丽尔比狂热”(Trilby-mania)。社会名流纷纷模仿小说中女主人公的造型,剧作家争先将小说改编为舞台剧,制造商竞相生产小说的周边产品。
目前,学界关于《特丽尔比》的研究主要分为种族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催眠术研究等。由于斯文加利犹太族裔身份的特殊性,很多学者倾向于从种族主义和民族身份等角度进行研究,如:Pick,Gracombe,Mendelssohn和Peak等学者从种族主义分析了小说中的艺术、堕落和反犹太主义等主题。[2-5]此外,由于19世纪特殊的背景,一是维多利亚中后期“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使得女性主义成为研究《特丽尔比》的一个视角;同时,19世纪英美文坛涌现出很多关于催眠术的小说,因此,催眠术也成为研究《特丽尔比》的切入点。基于此,本文从心理学的焦虑理论出发,对《特丽尔比》进行一次跨学科的研究尝试,以期为《特丽尔比》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焦虑书写研究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罗洛·梅看来,焦虑是人们视为存在之根本的某种价值受到威胁和挑战时所引发的无助和不安的情绪体验。《特丽尔比》中的人物因为其原本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出现各种不同的焦虑,主要表现为文化焦虑、宗教焦虑和人性焦虑。这既是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焦虑意识的文本投射。
一、文化焦虑
小说中的文化焦虑主要表现在对维多利亚社会传统“英国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文化“他者”的包容和肯定。“英国性”(Englishness)泛指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特色,是英国人的身份象征和民族文化特性。[6]“英国性”的衰落和“他者”的崛起无疑是民族文化焦虑的表现形式。莫里耶建构的“英国性”不再是文化优越和社会文明的绝对象征,“他者”也并非荒蛮落后和阴险邪恶的化身。恰恰相反,莫里耶正是通过“他者”来讽刺英国文化的墨守成规,也希望通过“他者”来弥补英国国民性中的固有缺陷,去创造性地重构“英国性”的历史内涵。[7]因此,小说中“英国性”和“他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莫里耶文化焦虑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英国性”的衰落
《特丽尔比》中的大部分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巴黎不仅是小说中艺术家们的艺术活动中心,更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女主人公特丽尔比是爱尔兰和苏格兰混血儿,但作者却赋予特丽尔比明显的“法国性”。[7]特丽尔比刚出现时,穿着法国步兵的大衣,说着不太文雅的英语,其中还夹杂着很多法语单词。她嘴里嚼着法国大兵吃的面包,吃完以后还抽了一根烟。[1](P12-17)显然,特丽尔比和维多利亚社会的“家中天使”形象大相径庭,言行举止之间透露着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Bohemian)。而小比利和他的朋友塔菲(Taffy)、莱尔德(Larid)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们共同的记忆、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对形成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具有持久的作用,时刻提醒着他们是英国人。[8]他们吃的、喝的、聊的都与英国相关的,如:小说中在圣诞节期间,小比利和塔菲特别怀念家乡的美食、狩猎、射击、冰山溜石游戏等,为了缓解思乡之苦,他们特地让远在伦敦的朋友寄来火鸡、葡萄干布丁、肉馅饼和香肠等特产。[1](P108)
“英国性”不仅仅是民族特性,也是那些自己认同或渴望拥有英国身份的人所持有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的联结体。[8]《特丽尔比》中的英国艺术家们不仅认同自己的英国身份,而且也希望身为英国人的特丽尔比能形成这样的民族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特丽尔比逐渐把她的巴黎狂欢曲置之脑后,越来越渴望拥有英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身份认同。她扔掉了法国军大衣,戒了烟,开始尝试英国食物,连说话的方式也更加文雅了。[1](P88-90)但特丽尔比的文化皈依最终以失败告终,[7]不仅未能如愿以偿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家中天使”,嫁给心爱的小比利,而且还被犹太艺术家斯文加利催眠而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傀儡,最终郁郁而终。特丽尔比的香消玉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传统“英国性”的没落。苟延残喘的“英国病人”终将被朝气蓬勃的“他者”所吞噬。
(二)“他者”的重构
小说中的文化焦虑也体现在莫里耶创作性地塑造犹太“他者”形象中。传统犹太“他者”往往是邪恶的化身,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臭名昭著的犹太商人夏洛克以及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教唆孩子偷窃的犹太恶棍费金。斯文加利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犹太艺术家。“Svengali”一词甚至被收入字典,用来指代控制别人思想而不择手段的恶人。[7]该小说也一度因为反犹太主义而被学界所诟病,但莫里耶在赋予斯文加利犹太族裔身份的同时,更加凸显犹太族裔在艺术创作上的天赋。小说中斯文加利在音乐上的造诣登峰造极、无人能及。
斯文加利并非《特丽尔比》中唯一的犹太“他者”形象,而小比利“英国+犹太”的混杂血统具有更重要的比喻和象征意义。[7]小说中,莫里耶曾多次嘲笑塔菲和莱尔德的假现实主义绘画方式。莱尔德把西班牙斗牛士画得“栩栩如生”,却没有去过西班牙,也没看过斗牛。[1](P5)而小比利才是真正的艺术家。[1](P9)莫里耶还刻意把小比利的绘画天赋和斯文加利的音乐天赋进行了对比:“小比利的手触及画布的一瞬间就如同斯文加利的手碰到键盘一样。”[1](P55)这一形象的对比,将两人的艺术才能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犹太血统”联系起来。[7]“他者”的新鲜血液给小比利带来了艺术灵感和天赋,让他得以摆脱“英国性”中的刻板和迂腐。[7]
除了斯文加利和小比利,作者赋予被催眠后的特丽尔比犹太“他者”的特性。被催眠后,特丽尔比以“斯文加利小姐”(La-Svengali)的艺名示人,摇身变为举世闻名的歌唱家,她的歌声如天籁一般,令人无法抗拒,让观众为之倾倒。而被催眠前,特丽尔比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小说中对其歌声有详尽的描述,但斯文加利认为特丽尔比的“上颚就像万神殿的穹顶一样”,因而也认定她拥有常人所没有的音乐天赋。[1](P50)被斯文加利催眠后,她变成了斯文加利小姐。由此可见,一方面作者试图凸显催眠前后特丽尔比身份的转变,另一方面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她犹太“他者”的特性。特丽尔比的“英国性”是在小比利的影响下有意识的建构的,而她犹太“他者”身份则是在催眠后被斯文加利赋予的。犹太“他者”的身份不仅治愈了特丽尔比的五音不全,而且还赋予她特殊的音乐天赋。从特丽尔比到斯文加利小姐,从五音不全到天籁之声,这既是毁灭也是重生。因此,创造性地塑造犹太“他者”形象不仅是莫里耶批判传统“英国性”的重要手段,也是莫里耶书写文化焦虑的有效形式。
二、宗教焦虑
小说中的宗教焦虑主要表现为对宗教救赎的质疑和对宗教权威的讽刺。虽然莫里耶并没有从正面解答他对宗教的看法,但从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中不难发现他对上帝和宗教的态度。
(一)对宗教救赎的质疑
起初,特丽尔比是一个模特。在热情奔放的法国,做裸体模特对她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7]小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小比利看到她在工作室里为一群学生当裸体模特后很多天不理她。但特丽尔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她皈依基督教之后,她的羞耻心和罪恶感瞬间被唤醒,她才理解小比利生气的原因。于是,她开始像基督徒一样虔诚的忏悔,并下定决心改过自新。[1](P84-87)
Gracombe认为,精神信仰的顿悟往往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杜穆里埃用有着“当代英国文化世俗圣经”之称的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小说来取代福音派的《新约》,让特丽尔比皈依基督教。[3]的确,特丽尔比的顿悟是在世俗圣经的影响下完成的。小比利的母亲巴格特太太给她带来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约翰·里奇的漫画,试图通过这些世俗圣经来开化她、改造她、规范她。在它们的影响下,特丽尔比的精神信仰一点点的建构起来。
然而,皈依基督教并未改变特丽尔比的悲惨命运。在小比利母亲的强烈反对下,特丽尔比意识到自己配不上小比利,也认识到自己这些年的罪过。所以,她带着弟弟远离巴黎,到乡下以洗衣和缝补衣服为生。故事并未以特丽尔比的皈依而结束。弟弟简诺特(Jeannot)的死让她明白忏悔和祷告救不了她弟弟,也救不了她自己。对上帝和宗教彻底失望的特丽尔比又一次回到了巴黎。然而,这一次回归将她从人间地狱推向了另外一个深渊。
(二)对宗教权威的讽刺
小说中的宗教焦虑还体现在小比利对宗教的态度上。特丽尔比离开后,小比利爱上了牧师的女儿爱丽丝。但两人的信仰截然不同,小比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追随者,而爱丽丝和她的父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牧师还曾因此怒斥小比利:“你是个小偷!休想夺走我的救世主!你以后再也别在我家门口出现了!”[1](P188-189)而讽刺的是,很多年后牧师开始经营爱尔兰啤酒,而且生财有道,变得非常富有。他开始像商人一样思考问题,慢慢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仅和主教以及乡村主任牧师闹翻了,还脱离了他原来的教堂,搬到伦敦开始了新的生活。[1](P190-191)显然,这是莫里耶对宗教权威的最大讽刺。莫里耶笔下的宗教不再是拥有绝对公信力和威严的存在,而是一种可以被随意摒弃、任人评价的个人信仰。
三、人性焦虑
小说中的人性焦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维多利亚社会男性把女性当作物品;另一方面,19世纪工业革命后人类的主体性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人沦落成机器。
(一)被物化的女性
正如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歌《我已故的公爵夫人》(My Last Duchess)中的公爵夫人一样,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意愿和声音,她们只是男性的物品或附属品。
小说中,特丽尔比被催眠前就已然是一个物品。作为模特的她,身体部位被不同的男性艺术家拆解和迷恋。在他们眼中,她只是身体的某个器官,一个完美的脚、喉咙或嘴巴。[1](Pxiv)特丽尔比的脚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被物化的社会现状,莫里耶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这双脚。当特丽尔比向小比利作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一个模特。我在隔壁给雕塑家杜里安当模特。几乎身体的所有部位我都要展示,从头到手再到脚,尤其是脚。这就是我的脚……这是全巴黎最漂亮的脚。”[1](P15)小比利除了惊叹“那确实是一双美得惊人的脚,只有在图画和雕像中才能看到这么美的脚……人类的脚竟然也可以是如此充满魅力的物体”外,还有悲悯:“可怜的特丽尔比!那么可爱而纤细的脚,却只能被雕塑家用巴黎灰白色的熟石膏捏成雕塑,保存在世界各地画室的架子和墙上。”[1](P15)然而被催眠后的特丽尔比,变成了一个器官,一个没有意识的唱歌机器。
(二)沦为机器的人
Pick在《斯文加利的网:现代文化中的异国巫师》一书中,运用小说中“蜘蛛网”和“网上的苍蝇”的比喻作为标题,形象描述了催眠师斯文加利和被催眠者特丽尔比之间的关系,凸显了斯文加利作为犹太催眠师的邪恶和黑暗。[2]特丽尔比无疑是斯文加利的受害者,斯文加利的声音像施了魔法的咒语一样,萦绕在特丽尔比的脑海里——“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想,除了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把她变成了一个唱歌机器,一个无意识的傀儡。[1](P298)
一直以来,学界看到的是特丽尔比受害者的身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和斯文加利一样,也是一个催眠师:就像斯文加利用他神秘的眼睛和咒语迷惑特丽尔比一样,斯文加利小姐用歌声迷惑了她的观众。她的歌声有一种魔力,让人抓狂,让人着迷。这种魔力与催眠很相似。催眠师会让你做任何他们想让你做的任何事情,包括撒谎、谋杀、偷窃等。[1](P52)特丽尔比也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到处都是关于她的报道、她的照片和她的周边产品。因此,特丽尔比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Coll认为,特丽尔比的命运与该时期整个社会充斥的人性丧失的现象有关。人性丧失的过程粉碎了她的自主意识,使她沦为最原始的人。[9]莫里耶的小说充满了对维多利亚晚期人类意志和行为的焦虑,这与该时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益合理化、系统化的世界,一个机械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历史时期。[9]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人类的主体性受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人沦落成机器。小说中的特丽尔比和她的听众无疑是莫里耶人性焦虑意识的文本投射。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涉及种族、性别、阶级、宗教、文化等当下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业已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族裔文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莫里耶是一个对国民性、社会现象和时代问题有着敏锐洞察的作家。他的第二部小说《特丽尔比》对焦虑有着多重解读和深刻反思,主要表现为文化焦虑、宗教焦虑和人性焦虑。通过研究莫里耶小说中的焦虑书写,一方面有利于读者深刻理解作品的精神内涵,探究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动机;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发公众对当代人心理问题的关注和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凸显小说创作的时代价值、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
——贯穿建筑的连续上升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