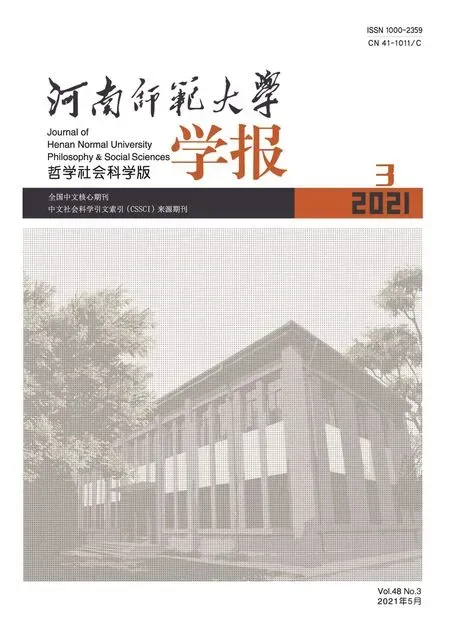伦理精神的哲学意蕴及其基本特征
杜 灵 来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人(类)正是在精神力量的牵引下,在急迫地追寻与外在世界持续互动时的平衡感和主动性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着作为“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存在”的类本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的进化史,在激发精神、凝聚精神、锤炼精神、崇尚精神的进程中走向未来。然而,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化”过程中,出于自我救赎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类精神的光芒有时如萤火虫般漫天飞舞,让人眼花缭乱而变得心猿意马;有时又似聚变的亮光在头顶炸裂,令人瞠目结舌甚至痴迷癫狂。客观上,只要涉及“人(类)”的问题,必然与精神关联,无人不精神,无精神则无人。人的世界里,精神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另一方面,泛在的精神又常常会引发精神的“泛化”,而泛化的精神却可能带来精神的“极化”或“奴化”。要给予精神这一非常熟知的范畴一个具有普遍共识性和历史穿透力的说明与界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正如黑格尔所言:“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1)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对于这样一个与人的本质和本性息息相关的“存在”,如果不廓清形象,让它眉清目秀起来,既会影响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会影响我们对生活和时代的感受与理解。在以情理结构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场域内,精神与伦理之间存在着“电磁感应”般的一体两面性,伦理是精神的“电”,精神是伦理的“磁”,伦理是精神的筋骨,精神是伦理的血脉。只有厘清“精神”的本质,才能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探寻“伦理精神”的哲学意蕴,把握其基本特征,进而通过“精神—伦理—伦理精神”的递进分析,在彰显“精神”和守望“伦理”中回归“伦理精神”,迈上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路,找寻到民族精神与文化自觉的起点、自信的支点和自立的平衡点。
一、“精神”的本质及其中西意象
从宇宙学和心理学的层面来看,外界的“事”和“物”通过人的神经系统以感觉、知觉、意识等方式记录入人的体内并重演于体外,便成了人的“精神”。这种解构式的阐发似乎充满了“科学性”和“真理性”,但是生活经验和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精神”的本质和形态并非一种如此简单的“反映论”过程。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对存在的反映,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理或生理过程。精神“被反映”,同时又参与反映过程,左右反映的状态,决定反映的结果。因此,不摆脱机械唯物论的思想束缚,走出自然主义的逻辑窠臼,走向“主客一体”和“主客同构”,就无法看清人类“精神”的真实面貌,也无法深刻理解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准确把握精神的哲学本质。“‘精神’的本质特征, 是具有观念化的外物,并在此过程中将自身展现为诸‘最具体、最发展的形态’的品质和力量。一方面,‘精神’观念化一切外在的东西, 使其成为‘人’的内在性; 另一方面,‘精神’ 具有客观性的力量将自己实现出来, 成为世界或‘文明’的种种形态”(2)樊浩:《精神如何与文明在一起》,《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精神在中西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哲学意象,如果说精神的西方意象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和“理性(智)”的话,那么精神的中国意象则是内在于人的“价值追求”和“感性(情)”。
在“以德配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人感应”“动心忍性”“尽心知性”“至诚尽性”等观念的引领之下,“精神”在国人的认识和理念中早就充满了神秘且巨大的能量。精神范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对它的意蕴的解读还需要立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沿着从“字解”到“词解”再到“意解”的路径,层层剥茧地破解深藏其中的文化密码。在传统文化看来,“精”是构成和维持生命体的基本物质,是天地的造化,是生命的源泉和供给。《黄帝内经·灵枢》阐释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黄帝内经》将“精神”与人的养生和健康长寿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云:“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精”被描述和界定为天地在孕育人时所赋予人的自然造化之精髓,是人能成为万物之灵长的根本前提,是人之成为人的内在决定。“神”作为一个会意字,从“示”从“申”,“示”为昭示之意,“申”乃天空中闪电之形。古人以为闪电神秘莫测,威力无穷,故称之为“神”。儒家认为“阳之精气曰神”(《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汉·王符《潜夫论·卜列》)在传统文化的视域下,“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神”则是观念、意志、行为等一切生命活动的统帅。人的生命起源于“精”,维持于“气”,展现于“神”。“精”充则“气”足,“气”足则“神”旺。所谓天有三光之宝日、月、星,地有三柔之宝水、火、风,人有三品之宝神、气、精。人通过“精、气、神”观照自己与万物。“精神”翻译成英语时所对应的单词有很多:spirit(精神,心灵,情绪,心境), mind(思考能力,智慧,思维方式),consciousness(知觉,意识,观念),essence(本质,实质,精髓),Vigour(活力,精力),Will(意志)。说明在中文语境下的“精神”寓意是比较广大的,但是“主体性”和“能动性”是其两个鲜明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伦理”品质和“精神”走向。道家的“清静虚无”是“精神”,儒家的“三纲五常”是“精神”,佛教的“慈悲觉悟”也是“精神”。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为要义的传统文化中充满着“精神”的张力。孟子将人格修养的境界描绘为六个层级:“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孟子·尽心下》)层层递进的境界中都饱含着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感召与引领。心学大师王阳明通过“精(气)神”解读他的“致良知”思想:“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为之神,以其流行而言为之气,以其凝聚而言为之精。”(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 上) 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4页。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良知”,即为“精、气、神”各自的“凝聚”“流行”“妙用”的和谐统一,而“致良知”的唯一方法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过程和展现过程。一直到我们生活的今天,“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依然还是普遍的人生共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从一定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种谋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精神哲学,追求的是在理想与信念引导下,通过知行合一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此岸通达,追求的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奥古斯丁的“真理是上帝之光”,再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一直到其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历了透过“现象”构建“理念”,进而突破“神性”走向“人性”的过程,走出了一条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精神论”的道路。黑格尔之后的“非理性主义”以及“分析学”“现象学”等哲学走向都将认识的触角延伸到了主体的精神世界,形而上学向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转向变成了基本的趋势。精神哲学大师黑格尔指出:“人作为精神是一种自由的本质,他具有不受自然冲动所规定的地位。”(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 9页。“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 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 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 让他享受。”(6)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页。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巨著中将人类意识发展史描述为五个渐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即客观精神)—绝对精神,而且,对“精神”的本质也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揭示,认为“精神的一切活动无非外在东西回复到内在性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而这种内在性就是精神本身,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回复,通过这种外在东西的观念化或同化,精神才成为而且是精神”(7)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页。。黑格尔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将世界“精神化”。在黑格尔那里,“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伦理”与“道德”不仅具有“精神”的本性,而且就是“精神”。“精神”经历了从“伦理”到“教化”再到“道德”的螺旋上升的辩证过程。黑格尔关于“精神”的思想,不但克服了康德“实践理性”范畴的局限性,而且得到了之后哲学家的普遍认同。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精神”出于“自然”而又与“自然”相对峙,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以及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的统一。“精神”的最大魅力不仅在于守望信念并追求超越,更在于它是信念生发和实现超越的内在力量。樊浩教授认为,“西方精神史的总体图式是伦理与道德分离,从古希腊的伦理,演绎为古罗马的道德,进一步抽象化为近代康德‘完全没有伦理’的道德哲学或实践理性,至黑格尔虽然达到伦理与道德的统一,但现代西方哲学故意冷落黑格尔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伦理与道德关系的摇摆状态或中间状态,导致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现代性矛盾。中国则相反,从孔子《论语》到老子《道德经》的共生互动开始,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取向便是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一以贯之的传统,只是具有不同的时代话语和历史表达,从‘克己复礼为仁’、‘五伦四德’,到‘三纲五常’,最后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8)樊浩:《伦理道德为何精神》,《哲学分析》,2016年第 2期。。 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在天人合一且相互感应的思想支配下,通过“克己复礼”与“感性”方式建构人的内在价值尺度与外在追求范畴的话, 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则是在天人相对的视域下,以“绝对精神”的理念,通过张扬人的“理性(智)”的方式无节制地释放人的物理力量。
一般动物界的感觉系统只能停留在表象、欲望和情绪这三个层次上,唯有人因为有了自我意识,才会将动物的这三个心理活动提升到认知、意志和情感的层级,从而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人”。而 “精神”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知、意、情”领域所建构起来的“真、善、美”。如果说文明是文化精粹的积淀与发展,那么“精神”则是文明的集中表达和核心内涵。“精神”既是文化自信的立足点,也是文明发展的支撑点。“在哲学意义上,‘精神’具有三个基本规定。‘精神’的对立面是‘自然’,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精神’的本性是自由;‘精神’的本质和力量,在于将人从‘小体’的自然存在者,提升为‘大体’的伦理存在者,达到黑格尔所谓‘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精神’是思维与意志的统一,用中国道德哲学话语表述,‘精神’是‘知行合一’。”(9)樊浩:《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其实,精神就是精神,既不应该作为物质的奴婢而亦步亦趋地俯首跟从,也不应该因傲视存在、自大轻浮而变得虚假和狂妄。精神的本性是自由,就是从外在的控制下获得解放,同时也从内在的情欲的束缚下获得解放。检审精神的过往,还原精神的本真,才能实现精神在物质基础上的引领价值,保持精神在现实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张力,让精神在“适应”的基础上保障其存在的稳定与持续,在“超越”的过程中彰显自身存在的真实意义和本来价值。
二、伦理精神的哲学意蕴
哲学发展史表明,中西方均将“精神”锚定为各自哲学的核心范畴,标注为各自思想的灵魂。那么,“精神”与“伦理”又何以联姻而孕育出“伦理精神”呢?“伦理精神”的本质和形态又如何呢?在古希腊,“伦理”指称的是灵长类生物长期生存的居留地,是为人的生存提供的可靠的空间。没有伦理的存在,就没有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精神的存在。伦理为人的精神生长提供着稳定的条件。“伦理”与“精神”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伦理与精神的关系,就好比物体与重量的关系一样。黑格尔认为,“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从实体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3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以标题的显著形式明确展现了他对精神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真实的精神:伦理”“对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道德”“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并进一步指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而且它只有当为精神本质时才是伦理的”(1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页。。在这里,“精神”被黑格尔当作“包含着人的整个心灵的和道德的存在”(12)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伦理即精神,精神即伦理,不存在无伦理的精神,也不存在无精神的伦理。伦理是精神的实体,精神是伦理的本质。
在中国,伦理的精神要义从隐含着文化密码的汉字中即可看出端倪。许慎在《说文解字·人部》中讲道:“伦,辈也。” “伦”的繁体为“倫”,源于“侖”,会意字,从亼(表聚集),从册(编竹简),会集简牍编排次序之意。本义指次序、条理。“侖”另加义符“亻”写作“倫”,现在简化作“伦”。伦,从亻从仑,本义指人际关系有次序条理。“理”,从王(玉),里声。本义指治玉,引申为治理、办理、处理,又引申为一般事物的内在机理、秩序、条理、道理等。伦理二字连用,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在此指“事物之伦类各有其理也”。孟子曾生动地为我们诠释了伦理的发生机制:“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后人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要义的探寻、总结和提炼尽管见仁见智,但是将其要义归结为“精神”却是不争的事实和一致的取向。王阳明以“精神”来诠释作为他的道德哲学核心概念的“良知”:“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如果说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才走出了一条精神哲学之路的话,中国人从思想发端的源头上便将“精神”的桩基牢牢夯筑进了“伦理”的土壤。以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1910)为肇始,关于“伦理”与“精神”的现代诠释和意义追求的研究即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现阶段国内就“伦理精神”范畴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当首推樊浩教授,他通过发掘伦理型中国文化的独特资源优势,试图建构当代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提出了“精神回归战略”和“走向伦理精神”的时代命题。他认为,“伦理道德不仅是伦理型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而且在‘有伦理,不宗教’的五千年中国文明中一直担负着特殊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在西方文明中宗教主导着人的精神世界,那么在中国文明中伦理道德便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所以,中国哲学对伦理道德从一开始便进行‘精神’的而不是‘意识’、‘理性’或‘物质’的把握”(13)樊浩:《伦理道德为何精神》,《哲学分析》,2016 年第2期。。“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必须确立三大关键概念:伦理、精神、伦理精神。准确地说,必须确立三大优先战略: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战略,精神之于理性的优先战略,伦理精神之于道德理性的优先战略。三大关键概念,三大优先战略,呼唤三大回归: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一言以蔽之,走向伦理精神!”(14)樊浩:《走向伦理精神》,《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3期。他认为,“‘伦理’之中,‘伦’是体,‘理’是用;‘精神’之中,‘精’是体,‘神’是用。伦理是自在状态,精神是自为状态,‘伦理精神’是既自在又自为的状态。所以,伦理与精神之间具有相互期待、相互诠释的关系。伦理,只有通过精神才能达到和建构”(15)樊浩:《走向伦理精神》,《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3期。。假如说“伦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轴”的话,那么“精神”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间轴”。“伦理”与“精神”的关系就好比“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一样。“精神”与“伦理”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精神”是“伦理”的内容与本质,“伦理”是“精神”的发展与表达。没有脱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的伦理,也没有脱离伦理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伦理是精神的土壤,精神是伦理的生长。无“精神”不“伦理”,无“伦理”不“精神”。伦理是“持存”,表达的是对合理性的肯定与维护,是精神的“生长地”; 精神是“超越”,展现的是对现实性的否定与发展,是伦理的“引路人”。离开伦理,精神无法生长;离开精神,伦理必然迷茫。“伦理”与“精神”的结合,就好比是人的灵与肉的结合,自然的天与地的结合,宇宙的时与空的结合,互为表里,共生共存。“伦理精神”既是人类认识自我、理解社会、把握时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引导人类不断走出自我困境、持续走向美好生活的支撑点和平衡点。所以,“伦理精神”范畴的存在不但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历史上的必然性,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自然结果。
那么,何谓“伦理精神”呢?当我们探寻了“伦理”和“精神”的各自轨迹与融通理路之后,“伦理精神”的本来面目就呼之欲出了。樊浩教授认为:“伦理精神是社会内在生命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是民族伦理的内聚力与外张力的表现。”(1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页。“精神”是主体的自我意识和意志的更新与生长,是主体真实性和普遍性的获得,而这一过程必须依托于“伦理”这一特定的场域,亦即特定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结合各家所论,我们可以尝试对“伦理精神”作出如下一个界定:伦理精神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的自我更新与生长的样态,是主体在建构意义世界时引领知、意、情持续走向真、善、美的知行合一的动力过程。对伦理精神范畴的这样一个界定,表明伦理精神的本质应该从辩证统一的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伦理精神是人的“伦理实体”(存在场域)与“精神本质”(发展场域)的内在辩证统一。伦理与精神互为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伦理是精神的土壤,精神是伦理的生长。离开伦理谈精神,就好比离开肉体谈灵魂,成无源之流;离开精神谈伦理,则好比离开灵魂说肉体,乃无本之木。其次,伦理精神范畴的存在是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人类意识梯次推进、不断上升的过程,必然会凝聚并发展为“精神”,而“精神(磁力线)”围绕“伦理(电流)”主线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发展史画卷展开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是在人的伦理精神运动变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之中才得以展现的。人类的自我意识在探求外在自然奥秘的过程中造就了人类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在探求内在自然生命秩序的过程中造就了人类的“民主精神”,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形成了人类伦理精神的基本结构单元。再次,伦理精神的存在价值与发展指向使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有机统一得以实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有机统一是伦理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也是伦理实践的发展瓶颈和困惑所在。伦理精神的存在,使得精神的个体化取向和伦理的整体化取向在此刻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独立与自由”的个体发展诉求因为有了“整体与稳定”的社会发展现实获得了实现的基础,而“整体与稳定”的社会发展也因为有了“独立与自由”的个体发展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价值。“至善”当然不是一个预期的固型的标准,而是一个理想的努力的方向。因为伦理精神的存在,个体至善和社会至善因此而实现了同向同行与风雨同舟。“‘伦理精神’既是个体与整体相同一的共体理性,也是共体意志,是共体的‘精神’。以‘伦理精神’为对象,才能更充分、更准确地体现道德形而上学的时代精神特质和它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17)樊浩:《“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整个伦理精神辩证运动的本质,是个体扬弃自己的个别性而获得实体性,是个体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迈向普遍性,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运动”(18)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2页。。张康之教授在其专著《论伦理精神》中提出,近代以来建立在法的精神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得到解构,伦理精神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伦理精神将替代法的精神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已有地位,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第三次启蒙——“伦理精神启蒙”(19)张康之:《论伦理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如何在一起”(伦理)的问题比“如何生活”(道德)的问题越来越具有了先在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时至今日,伦理之觉悟依然是国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伦理之问题依然是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伦理精神”的认知提升和实践自觉必然是化解当代纷繁迭出的社会矛盾和个体困惑的不二法则。上个世纪中期,思想家罗素就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到达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20)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无疑需要跨越“轴心时代”遗留的傲慢与隔阂,通过“对话”与“协商”走向 “共建”与“共享”,回归生命本真和生活本身。这就需要全人类具有整合“理”的纷扰、搁置“法”的争辩、走上“共情”与“尚义”大道的哲学智慧,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胸怀和卓识,开启一场伦理启蒙和精神洗礼之旅。当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从主体、客体两个层面都与人的伦理精神密切相关,对制度的高度认同、治理主体能力的提升、治理体系的建构与有效运行,都离不开“人”这个最终的决定因素,离不开人对关系建构与维护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这些都需要最终通过对全体国民伦理精神的陶养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国民伦理精神陶养问题研究,理应成为走进新时代的当代中国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伦理精神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伦理精神是人在认知基础上所形成的情感和意志的结合体,是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其本质是实践的、能动的和发展的。它是一种集结起来的强大的内在性本质力量,因其所具有的特殊的“意志性”而产生着强大而恒久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也是在“伦理”的积淀和推动之下所自然焕发出的一种坚韧的实践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特性,伦理精神才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相伴而行,成为决定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同时,伦理精神也是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有机统一,而科学与民主就是人的伦理精神的外在张力与内在积淀的显现,就是人的认识实践性和意识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正是因为有了实践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的基本特质,伦理精神才成为人类生命和谐的根本建构力量。
(二)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颉颃。伦理精神所内含的是人伦关系、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诉求,决定着民族生活的内在秩序的设计原理,以及民族性格生长发育的样式和状态。黑格尔在自己的精神哲学研究中认为,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民族是在伦理精神基础上按照其内在发展规律而生成的现实形态,伦理是民族个体所赖以存在的公共精神本质。伦理精神是民族伦理的深层结构,是民族精神的合理生发,是民族伦理的内聚力与外张力的集中表现。没有伦理精神的民族,就像是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上的神的庙宇一样。同时,任何伦理精神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深度表达。“以‘伦理精神’为对象,才能更充分、更准确地体现道德形而上学的时代精神特质和它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21)樊浩:《“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伦理精神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历史传承,是时间维度上的民族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是空间维度上的时代精神的凝练与生发。它既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交汇点与聚变点,同时也孕育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聚力与外张力。
(三)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同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属性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界定。这一界定,也为我们认识人的伦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奠定了唯物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基点,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谈伦理精神。社会为个体提供了彼此合作的机会,编制着联结的纽带,满足着人的情感和信仰的需要,也是个体伦理精神生长唯一的土壤。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决定了人的精神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品质,由此决定了伦理精神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精神固然有它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但是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制约作用是客观必然的。伦理精神是伦理主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由意识到意志再到精神的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受着社会条件的制约,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成长。因此,社会历史性是伦理精神自身重要的特征之一。社会是伦理生长的基地,伦理是社会发展的支柱,而历史就是人的伦理精神的成长史。伦理精神是维系社会和谐以及创造持久历史意义的人类生命纽带。
(四)激励性与导向性的协同。作为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存在,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样态只能是“精神”。而“精神”是人的“自我意识”在“知、意、情”领域所建构起来的“真、善、美”,是人的意识的冲动性所凝结成的意志的自主表达,既需要个体的内在激发,也需要共体的外在导向。伦理精神是个体与共体实现有机统一的实在,而这一“有机统一”只有通过扬弃共体精神的抽象性和个体精神的主观性才能完成。此处“扬弃”的过程,离不开个体精神世界的激励,也离不开共体精神家园的的导引。个体精神的自由需要保护和激励,共体精神的持存需要引导。由此,激励与导向便自然成为伦理精神的鲜明特征之一。通过调节内在生命秩序以安顿人生,是伦理精神的存在原点和发展支点,而人的生命的内在秩序,显然不是内在独自生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内、外在秩序互动、协同的产物,这个互动和协同的过程就是内在激励与外在导向的统一。实现社会至善与个体至善的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内在标尺,“至善”之维在于“社会善治”的达成和“个体美德”的普遍呈现,而这一普遍呈现则在于国民对伦理精神的自觉践行,在于伦理精神激励和导向作用的持续产生。
四、结语
我们在这里探究 “精神”“伦理”“伦理精神”的内在辩证关系与发展理路,论证“伦理精神”范畴的哲学意蕴及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阐发“伦理精神”的历史意义和基本特征,彰显伦理精神的哲学价值,并非要以“伦理精神”覆盖人类全部的精神形态,囊括精神的一切品质,凸显伦理精神的一枝独秀以遮盖人类精神世界的满园春色,而是要通过论证和分析来进一步确立伦理精神在我国思想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本来地位与价值,深耕我们传统思想中所固有的肥沃的伦理土壤,唤醒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提振文化自信,凝聚行为意志,跨越我们走向未来有可能遭遇的一切所谓“现代化的陷阱”,让民族复兴的梦想多一重前行的自信和力量。因为只有伦理精神才能将精神的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特质高度融为一体,让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跌宕起伏间能够始终保持不忘本来的定力、吸收外来的活力和面向未来的张力。在守望“伦理”中回归“伦理精神”,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走进新时代的国人找寻到精神与文化自觉的起点、自信的支点和自立的平衡点。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孕育积淀出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也是处处洋溢着“精神”品质,充满着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期望和要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的沃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由重关系、重人情的情理结构系统所生成的传统伦理型文化,在人欲横流的市场价值魅惑中想必能发挥出解毒和纠偏的作用。对当代中国而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培育,都需要从以安“伦”尽“分”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精神中汲取滋养,获得稳定恒久的支撑力量,进而在实现传统伦理精神的历史转化与时代建构过程中,走出一条革故鼎新、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新时代国民伦理精神的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