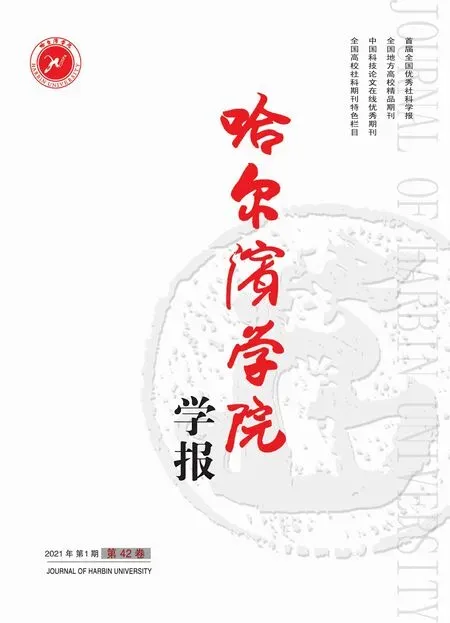“上官体”诗歌之生成与流变探微
杨丽花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初唐宫廷诗坛,继虞世南、李百药之后,上官仪凭借出类拔萃的诗歌才华卓然名家,成为宫廷诗坛的领袖人物。高宗龙朔年间(661—663),上官仪“绮错婉媚”的宫廷诗艺术风格广受文士追捧,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这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个以诗人名字命名的风格称号,[1](P59)更是初唐诗歌发展史上一道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
关于“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载:“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2](P2743)《新唐书·上官仪传》云:“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3](P4035)新、旧两唐书在论及“上官体”生成时,似完全归因于上官仪政治身份的“贵显”。关于“贵显”的具体时限,两唐书都未作明确定论。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高宗龙朔元年至麟德元年间(661—664)。这一时期上官仪进入朝廷中枢,位极人臣,官运亨通,由为宦生涯的显达带动其文学创作大放异彩,进而造就“上官体”的形成,不能不说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仅凭此一点来解释“上官体”形成的全部动因未免显得孤立。本文拟从初唐政治文化思潮、诗歌发展脉络入手,结合上官仪宫廷诗歌创作的崭新因素和自觉的诗学理论建构,对“上官体”的成因和流行做系统地探究。
一
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约、规范着个体人生图景的绘制。上官仪的为宦生涯和文学生涯始于太宗贞观初期,《旧唐书·上官仪传》云:
上官仪,本陕州陕人也。父弘,隋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大业末,弘为将军陈稜所杀,仪时幼,藏匿获免。因私度为沙门,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兼涉猎经史,善属文。贞观初,杨仁恭为都督,深礼待之。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俄又预撰晋书成,转起居郎,加级赐帛。[2](P2743)
上官仪生于隋朝,其父在隋末政治动乱中被杀,幼年即遭受父难,匿迹沙门,苦难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促使他游情释典,博览经史,加之过人的文学禀赋,于贞观初年举进士,踏入文人荟萃的宫廷文学圈。他的才华深受太宗欣赏,多次参加宫廷宴游赋诗活动,并亲自帮太宗润色文稿,深受恩遇。但上官仪在太宗朝的政治声名,远不能与其在高宗朝的“贵显”相提并论。
考其原因,源于太宗时期的政治统治思想。依陈寅恪先生所论,唐初基本延续了西魏宇文泰所创立的关中本位系统,这一政治体现在用人政策上,最为注重门阀士族和尊经崇儒。“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代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4](P202)太宗朝重视门阀的风气相当严重,《旧唐书·李义府传》曰:“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2](P2769)官修《氏族志》,正是这一时期门第观念盛行的产物。因此,能够进入太宗朝权力中枢的人物若非出身于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便出身于世代显贵之家,在当时都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如上官仪般无显赫家庭背景之士人很难与之分庭抗礼。
高宗统治时期,永徽六年(655)发生“废王立武”事件,武氏在宫廷斗争中取得胜利,攫取政权。为巩固自身统治,武氏极力压制和削减关陇贵族,同时通过科举考试从平民阶层中大量选拔人材。“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5](P279)这一政策直接造成传统贵族与寒族之间势力的此消彼长,新进文士迅速崛起,并开始在政治上掌握话语权,“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的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6](P247)上官仪的“贵显”适逢其时,于高宗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
科举取士逐渐兴起,具有文人气质的文士阶层逐渐取代此前具有贵族气质的儒生一统的局面。同时由于武后对文学的特殊喜好,“颇涉文史,好用雕虫之艺”,导致高宗显庆以后,社会政教衰弛,崇尚浮华之风竞相蔓延。《旧唐书·儒学传》云:“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于是醇浓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2](P4942)社会文化思潮由尚儒向尚文转型,为“上官体”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土壤,上官仪“词彩以自达”的华丽人生曲线更是对当时文士形成巨大的吸引。中国古代传统士人向来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作为人生最圆满的出路,上官仪的“贵显”使他们看到虽无显赫的家世亦非功勋旧臣,依然可以凭借文学以自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的情势便不难理解。
二
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样式,宫廷诗歌的历史使命是欣颂盛世太平,润色帝王弘业。因此,宫廷诗歌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与帝王的推崇和国运昌盛密切相关。如邓绎《藻穿堂谭艺·唐虞篇》所云:“一代文辞之极盛,必待其时君之鼓舞与国运之昌皇,然后炳蔚当时,垂光万世。”[7](P6146)以上文字虽就文学繁荣的整体情况而言,然用来形容宫廷文学尤为合适不过。
一代雄杰唐太宗开创了唐初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盛的局面,诗歌作为贞观文治的重要内容,太宗更是特别关注并身体力行。《旧唐书·邓世隆传》:“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政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2](P2600)太宗存世六十余首诗作,除少数作品雄伟不群、规模宏远、具有帝王气象,绝大多数带有南朝诗歌的特质,以至闻一多先生说太宗是双层人格:“事功=北人;文艺=南人”。[8](P189)帝王的文学喜好,往往会带动大量朝臣进行创作,甚至重塑一个时代的文学轨迹。上官仪即是在这种南朝诗风浓厚的环境里,在君臣宴集酬唱中,形成了“绮错婉媚”的宫廷诗艺术风格。“绮错”着眼于诗歌的外在形式,指自觉追求诗歌声律和对偶而产生的声律和谐、色彩华丽、声色交错纵横的美感;“婉媚”着眼于上官仪诗歌柔婉流转、清新妩媚的审美内涵。杜晓勤认为,“绮错婉媚”乃是“对诗歌表现技巧和艺术形式研磨得甚为精致后方可达到的诗美境界”,[9]这是上官仪立足宫廷诗坛而又超越传统宫廷诗人的地方。
宫廷诗歌因其独特的历史承载,是一种规范化、类型化的写作。书写内容大体以奉和应制、君臣酬唱、宫廷咏物为主,创作视角“向外转”,对富丽的宫殿、华美的庙宇、曼妙的佳人等外在意象进行精雕细琢,无需灌注诗人的个性和情感。语言运用上讲求错彩镂金与铺锦列绣,同时大量使用典故,表现出一种穷极雕饰、华贵秾艳的特色,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所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10](P28)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是很难摆脱这种传统的宫廷写作套路的。《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集一卷,存诗二十首。今人新辑佚出十一题十二首。因长期行走于宫廷的特殊生命历程和特殊的文学创作环境,上官仪诗歌存在无法避免的御用性和依附性品格,无法完全超越宫廷诗的写作路数,但对其作品加以细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个诗人的感悟笔触和思想情绪,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传统宫廷诗写作的突破,尽管这种突破传统的努力是有限的。
首先,上官仪诗歌有意摆脱宫廷诗歌大量堆积华美辞藻的传统习惯,继之以洗净铅华、省净雅洁的语言构成情隐于内而秀发于外的诗境。其诗歌名篇《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躁野风秋。”此诗作于高宗龙朔元年。诗中没有“金龙玉凤”的繁复意象,没有华丽的辞藻堆彻,力图写的清新自然,以平易晓畅、宁静洗练的语言描绘出上朝途中的玲珑风物,雍容闲雅的气度隐然其中。《大唐新语》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躁野风秋。’音韵凄响,群公望之犹神仙焉。”[11](P123)另《奉和山夜临秋》中诗句:“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诗人以细腻敏感的内心关照外物,以省净疏朗的文字勾勒出朦胧凄清的诗境,诗句景象颇具层次,动静、高低、远近完美结合,浑然流利,不着痕迹,可以说盛唐王维、孟浩然宁静秀逸、清雅空灵的诗作与之一脉相承。再如《奉和秋日即目应诏》中的名句:“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诗人敏锐地捕捉了秋季的代表性景物,以表现季节流转、时序变迁、生命凋零的主题。意象组合新奇雅致,有种纵横交错的美感。“秋天的两种象征蝉和落叶,被混合起来,互相成为对方的潜在隐喻。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落叶(或它们的影子)的飘动像蝉影,或是蝉(或它们的影子)的飞动像落叶,或者是真正的树叶飘过蝉影。潜在的相互隐喻和直接的描绘强调了两种事物之间的一致性,表现了秋天景象的微小无助与无可挽回。对句的第二句袭用了流水与南飞的大雁转瞬即逝的主题。”[1](P61)
其次,上官仪在传统宫廷诗歌只注重表现外在美感的基础上,尽可能融入自己的情感和志趣,在实现声色与性情渐趋统一的融合中自觉努力,使传统宫廷诗呈现出一种新的转机。如《王昭君》诗:“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干。”此诗语言平易自然,近乎白话,有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人以景造情的手法相当纯熟,将自然界原本无生命的“琴”“笛”“雾”“风”等外在物象,通过拟人的修辞,赋予其悲凉哀怨的情感,十分传神。读之哀婉动人,悲切生动,显著增强了诗歌的内在情绪感染力。
上官仪凭借卓越的诗歌才华,在传统宫廷诗歌的规范之外,力求一种新的突破和探索,使宫廷诗写作不再僵化,呈现出一种新鲜的活力,也为宫廷诗歌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如罗宗强所言:“‘上官体’的流行,说明在龙朔初年,绮艳文风有一次高潮,不过它已达到更好的层次。”[12](P29)
三
“上官体”的生成,除却时代机遇及其宫廷诗创作的卓越才华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官仪自觉的诗学理论建构。通过对作诗法则的总结,为广大文士提供了一种教程式的规范,对“上官体”的流行有推波助澜之效。
上官仪撰有诗学理论著作《笔札华梁》二卷,原书已佚。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认为:“《日本国见在书目》‘小学家’类著录《笔札华梁》二卷,未提撰人。《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文史类’著录有上官仪《笔九花梁》二卷,“九”当为“札”之误。”[13](P54)《文镜秘府论》引用此书若干节。今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基本勾勒出《笔札华梁》全貌。
现存于《文镜秘府论·地卷》中有上官仪“八阶”“六志”理论,均为初学者而作,由浅入深探讨了学诗入门的途径。其中“八阶”为“咏物阶”“赠物阶”“述志阶”“写心阶”“返酬阶”“赞毁阶”“援寡阶”“和诗阶”等,分析八种不同题材内容的诗歌所呈现出的不同体貌;“六志”为“直言志”“比附志”“寄怀志”“起赋志”“贬毁志”“赞誉志”等六种诗歌中咏志的具体方法。在每种门类之后,以假作某诗形象展示,再加以解释,包含对艺术表现形式的细致分类。如“六志”中的“直言志”“比附志”“寄怀志”直接继承了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形成的“赋、比、兴”等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在重视诗歌形式之余,寻找一条抒发思想情韵的合适途径。上官仪《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诗前四句:“奕奕九成台,窈窕绝尘埃。苍苍万年树,玲珑下冥雾。”描画出黄昏时分万年宫清肃邈远的景象,“奕奕”与“苍苍”、“窈窕”与“玲珑”等精妙词句又增加了诗歌抑扬起伏、连绵不绝的音乐美,声色俱茂的图景为全诗“怀友”主题营造了氛围。
上官仪还提出了著名的“六对”“八对”理论,对于推广、普及新体诗的声律影响非常大。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曰:
唐上官仪曰: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中水,虫穿叶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连绵对,“残河河若带,初月月如梅”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隋亲因意得,意得逐情亲”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不归”是也。[14](P165)
对偶是诗歌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早在齐梁时期,刘勰曾将对偶的种类分为四种:“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15](P588)上官仪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六对”“八对”之说,分类更为多样准确,技巧更为细密清晰,各种“对”不仅在词义上两两相对,更在调声上轻重、缓急相对。以《早春桂林殿应诏》诗为例:“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暧将夕。”此诗颔联、颈联对属精密,描写出清新明丽的初春景致,“晓树”与“春堤”、“流莺”与“芳草”两组意象并置,造成视境的开合与感觉的挪移,“满”与“积”使静止的景物顿生光辉,意象新奇;听觉、视觉、嗅觉的交叉转换,色彩与景物的有机搭配,使全诗流淌着春意融融的情韵之美,表现出诗人所具有的细腻观察力和以虚实相间的空间营构、创造诗境的能力。另外,“远气犹标剑,浮云尚写冠”(《故北平公挽歌》)、“花轻蝶乱仙人杏,叶密莺啼帝女桑”(《春日》)等句亦属对精工。
上官仪诗学理论的广泛传播,使初学者有法可循,易于效仿,成为推动“上官体”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当然,上官仪诗学理论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在齐梁声律理论的基础上,对诗歌声韵、病犯、对偶及体式深入探讨,对五言律诗的形成具有无法忽视的贡献,对稍后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在律诗最后定型上的努力导夫先路。
四
“上官体”在龙朔年间成为宫廷诗歌发展的高潮。后世论者着眼于文学的政教作用和现实情怀,对于其过分追求诗歌结构、声律和辞藻的形式之美予以激烈批评。如闻一多称“上官体”为“病态的唯美主义”,[8](P242)认为“靠近那五十年的尾巴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收束了。”[8](P1)诚然,“上官体”诗歌有非常重视形式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无论上官仪对传统宫廷诗歌创作的有限突破,还是对诗歌声律和结构的深刻认识,都对盛唐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且,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也并未随诗人肉体生命的终结而骤然消歇。
麟德元年(664),上官仪因草拟废武后诏而被诬伏诛。上官仪谢世后,“上官体”继续以正、反两种力量存在。从正面力量来讲,其突出表现是上官仪孙女上官婉儿继承祖父衣钵,在武后、中宗朝挟宫廷势力,光大祖父遗风。上官仪死时,婉儿尚在襁褓,随母配掖庭。史载其“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即受宠于武后,“内掌诏命,掞丽可观”。中宗即位后,“大被信任”,以其文学才华引领宫廷诗坛。《新唐书》卷七十六“上官昭容传”云:“婉儿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庚和,婉儿尝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3](P3488)“上官体”经由婉儿之手得以继承发扬,婉儿诗句“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等,清丽婉约,颇有其祖之风。从反面力量来讲,此时诗坛另一种更为声势浩大的风尚是以批判“上官体”为使命、试图重建新的诗美标准,主要以陈子昂、“四杰”等中下层文人为代表。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曰:“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16](P3611)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购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17](P36)卢、杨从文学承载的“风雅”精神出发,对“上官体”提出抗议和批评。然而,即使他们在理论上尖锐攻击“上官体”,但在创作实践中却未能完全避免其美学吸引力。略举王勃两首诗作,如《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接字》诗:“帝里寒光尽,神皋春望浃。梅郊落晚英,柳甸惊初叶。流水抽奇弄,崩云洒芳牒。清尊湛不空,暂喜平生接。”再如《咏风》诗:“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驱烟寻磵户。卷雾出山楹,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这两首诗从题材上来讲,是宫廷诗歌常见的酬唱、咏物之作,对风光景物描摹细腻,风格纤巧,措辞精致,很难说没有受到“上官体”的影响。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发展进程中,文人才逐渐探索出唐诗发展的健康道路,实现如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所言“声律风骨始备”的诗歌美学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