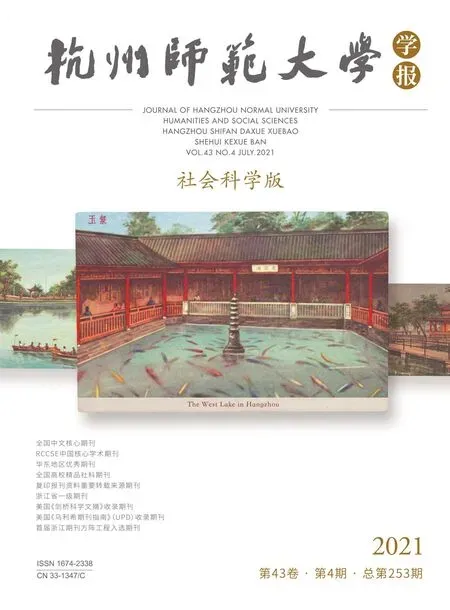比较伦理学:意义与方法
——黄勇教授访谈
黄 勇,陈乔见
上篇: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陈乔见(以下简称“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策划了“21世纪前20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展开与前景”专题,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通过访谈的方式,来对21世纪前20年各自所在的领域做一个回顾和前瞻。他们委托我对您做一场有关“比较伦理学”的专访。确实,21世纪已经走过了五分之一,回首20世纪的前20年,那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来自西洋的坚船利炮和思想学术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主掌的《新青年》,对东西方伦理都有不少比较,比如“中国重私德轻公德”“中国重义务轻权利”“中国重家族轻个人”等等一些观点,都是在与西方相互比较的视野下得出的结论。不过,由于“救亡压倒启蒙”,那时的东西方比较更多地指向社会改造,对中国传统伦理批判和否定居多。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大为不同,如果说上世纪前20年是中西“伦理比较”,那么我们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则更加回归学理,确属“比较伦理学”了。在此方面,黄老师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注意到您在世纪之交(1999-2001)担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主席时,于2001年在美国创办了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我们就从这个协会和期刊谈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当初创办这份杂志的初衷是什么?
黄勇(以下简称“黄”):先说协会,最早的时候是一些中国大陆到美国读书的学生成立了一些留学生协会,学历史的成立了“中国留学生历史协会”,学政治的成立了“中国留学生政治协会”,等等。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学哲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协会,不过我们协会用的名字比他们更专业,叫“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虽然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时间相对晚点,大概是在1995年美国东部哲学学会年会上成立的。当初最早去美国读哲学博士的一些中国学生已经毕业,开始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任教,包括李晨阳、倪培民、姜新艳等,他们是第一届理事会的成员。我自己是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出去的,而且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再在美国读书,只是阴差阳错又在哈佛大学神学院读了一个学位(因我在复旦做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中世纪哲学家阿奎那,所以在神学院旁听了一些课,其中的一位教授鼓励我再读一个神学博士),所以当初还在写论文找教职(我是1996年开始在美国正式任教的,但事实上当初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论文是在1997年夏天完成并在秋天答辩,不过聘任我的学校说我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所以一开始就以正式的助理教授职位聘我)。我记得当初选协会第一届主席时,李晨阳和倪培民获得同样的最高票,后来是用扔硬币的方式决定由李晨阳任第一任主席,两年后换届时倪培民被选为第二任主席,而我是第三任主席。“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的英文名称是“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North America”(ACPA),这里的“中国哲学家”指的不是做中国哲学的学者而是研究哲学的中国人,因为至少在当初,我们中的大多人主要做的都是西方哲学。当然后来由于我们这批人的研究兴趣大多转向中国哲学,这个协会的性质也不知不觉中逐渐有了变化,看起来更像是做中国哲学的学者的协会。一方面,它开始吸收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非中国人,而另一方面,后来有些国内来美国读哲学博士的学生由于做的完全是西方哲学,他们也就并没有太强的愿望加入我们这个协会。
陈:看来这个协会起先是“在北美的中国哲学家”协会,似乎有点海外游子抱团取暖的意思,后来逐渐走向了“中国哲学在北美”的协会,更接近关于中国哲学的协会,较之于种族认同更为侧重文化认同。这份杂志跟这个协会有关系吗?
黄:有。这份杂志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挂着“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说起来,创办这份杂志有些偶然。在任协会主席时,我当初认识的一位朋友,叫Parviz Morewedge,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Binghamton)校区任教,主要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传统中的神秘主义哲学,但同时又热心出版事业,成立了一个小型出版社,叫全球出版社(Global Publications),附属于他所在的学校。后来他离开了这所大学,便将它重新注册为全球学术出版社(Global Scholar Publications)。有次开会时跟他见面,他知道我在负责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就说他愿意为我们协会出一套丛书。我就跟我们协会理事会的其他两位成员倪培民和王蓉蓉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可以顺便增加我们这个年轻协会的曝光率,所以马上决定了下来,将该套丛书命名为ACPA Series ofChineseandComparativePhilosophy,并马上准备该丛书的第一卷,即由姜新艳主编的《经由省察的生活:中国的视野》(TheExaminedLife:ChinesePerspectives)。
就在这第一卷出版之前,我的这位喜欢出版事业的朋友又建议我为我们的协会出版一份中西比较哲学的杂志。由于我们当初协会的规模不大,会员不多,而且在中西比较哲学方面已经有《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West)、《中国哲学杂志》(JournalofChinesePhilosophy)和《亚洲哲学》(AsianPhilosophy)等成熟刊物,担心我们新办一个刊物可能没有优质的稿源,甚至担心我们的会员也不愿意将最好的文章给我们自己的杂志,于是我发电邮征询会员意见,虽然有个别的有我上述的担心,但绝大部分认为应该办一份杂志。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负责这个刊物,我就让倪培民负责那套丛书。在他负责下,这套丛书迄今出了大概有近十本书。除了姜新艳编的一书外,还有Ewing Chinn和Henry Rosemont, Jr.编的《元哲学与中国思想:解释郝大卫》(MetaphilosophyandChineseThought:InterpretingDavidHall),Marthe Chandler 和 Ronnie Littlejohn编的《擦亮中国之镜:祝贺罗思文》(PolishingtheChineseMirror:EssaysinHonorofHenryRosemont),伍安祖(On-Cho Ng)编的《理解的命令: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和本体解释学》(ImperativeofUnderstanding:ChinesePhilosophy,ComparativePhilosophy,andOnto-hermeneutics),Jay Goulding 编的《中西跨文化:走向世界整合的哲学》(China-WestInterculture:TowardthePhilosophyofWorldIntegration)以及安延明的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诚的概念》(TheIdeaofChenginthe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等。
这样我就开始筹办这个新的中西比较哲学的刊物。首先是要确定刊物的名称。我们在协会会员的电邮群中展开讨论,最后觉得商戈令提出的 Dao 比较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涵括整个中国哲学,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对不知道中国哲学的西方人听起来有点神秘主义味道,我就坚持加了一个副标题,这样我们的刊物的完整名称就是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道:比较哲学杂志》)。在一开始,我们邀请了一些名人写稿子,比如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黄百锐(David Wong)、柯雄文(A.S.Cua)、安乐哲(Roger Ames)等,都曾经为我们供稿。过了两年,我们的稿子就很多了,我自此开始也不再邀稿了,而所有的稿子都需要经过匿名评审(在此之前邀稿不送外审),每篇两个评审,即使来自有名的作者也是一样。这样我们这个刊物逐渐成熟,特别是在第六卷(2007年)由比较正规的Springer出版(不久便收入A&HCI)以后,成为与上述几家中西比较哲学的成名刊物不相上下、并驾齐驱、甚至有所领先的刊物。例如在2019年的刊物影响因子的排名中,在收录的528种哲学刊物中,我们刊物是进入第一区(最高的25%)的刊物中唯一一种非西方哲学刊物。
陈:这份杂志不到十年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成绩,实属不易。想必您也知道,这份杂志现在国内也很吃香,因为很多大学激励老师英文写作,在海外刊物尤其是在收入A&HCI的刊物上发文。您之前也曾私下说起,因为坚持匿名评审,有可能为此“得罪”了国内一些学者。能否谈谈您办这份杂志所坚持的原则。
黄:在编这个杂志的过程中,我坚持几点。第一,我非常尊重匿名评审的意见。如果他们建议不录用一个稿子,即使我自己认为这个稿子不错,我也都不会录用。一方面,经常不尊重评审的意见,以后就很难有人愿意为我们的刊物作评审(你可能知道,在英语世界为刊物评审文章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这会让我自己在面临熟人、朋友的被评审者拒绝的稿子时很为难,因为他们知道我可以推翻评审者的看法。当然这样做的一个可能弊端是一些真的优质稿件也会流失,但我觉得如果一篇稿子真的是优质的,作者可以将其投给其他刊物,而迟早会有其他刊物的评审者推荐发表的。第二,我决定不在自己编的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因为我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匿名评审,而很显然我作为主编无法为我自己的文章安排匿名评审。与此相关,我让两位书评编辑全权负责书评,一个负责英文著作的书评,一个负责中文著作的书评(我们的刊物从很早开始就每期发表三篇中文著作的书评,三篇英文著作的书评,在有规律地发表中文著作的书评方面,我们这个刊物是非常独特的)。尽管如此,我要求两位编辑不要安排发表我自己所写、所编的书的书评。第三,自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后,培养和接受了不少博士生。我鼓励他们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经常帮助他们修改文章,一直到我认为可以发表为止。这时我就会让他们投到别的刊物上。我跟他们说,至少他们开始的四、五篇英文文章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以后才可以考虑投到我编的刊物上。结果由于他们在别的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表过我自己的学生的一篇文章。
陈:确实,要办好一件事,甫一开始就要把基本原则或者说某种类似“宪法”的东西确定下来,而且,重要的是主事者以身作则,率先遵守。学术刊物乃天下公器,在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人情大国,主事者确实需要把“宪法”写在心中。以我的观察,国内一些重要哲学刊物也愈来愈走向和信赖匿名评审制度了。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黄:后来我又做了一套丛书,现在还是很有影响的。你知道,国外有很多出版社出版有指南(Companions)系列丛书,其中包括的题目会很具体。例如不仅会有《亚里士多德指南》(CompaniontoAristotle),还有《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南》(CompaniontoNicomacheanEthics)等,但往往不包括任何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家的指南,或者最多是笼统的《中国哲学指南》一本。因此我就跟Springer出版社说,我们能不能做一套丛书,叫SpringerCompanionstoChinesePhilosophy,整套书的每一卷都是关于中国哲学的,他们很乐意,并说这套书也不用出版社的名字,就叫DaoCompanionstoChinesePhilosophy,以便与已有的同名杂志相配套,相互促进。这是所有英语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众多指南丛书中唯一一套关于中国哲学的指南丛书。我的计划是,这套书可以包括一些比较广的题目,也可以包括一些比较具体的题目,希望在若干年后能够为中国哲学中每一个哲学流派、每一部哲学经典、每一个重要哲学家都出一本,基本采取成熟一本出一本。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了十五卷,包括有沈清松编的先秦儒家哲学、梅约翰(John Makeham)编的宋明儒家哲学、David Esltein编的当代儒家哲学、刘笑敢编的先秦道家哲学、David Chai编的魏晋玄学、王友如编的中国佛教哲学、冯耀明编的中国逻辑哲学、黄俊杰和John Tucker编的日本儒学、Ro Youngchan 编的韩国儒学、Gereon Kopf 编的日本佛教哲学等。这些都是较为一般的指南丛书,还有一些则比较具体,如有Amy Olberding编的《论语》、陈慧编的郭店楚简、Paul Goldin编的韩非子、Eric Hutton编的荀子和我跟吴启超合编的朱熹等。另外庄子和孟子两卷很快会出版,还有老子卷、梁漱溟卷、易经卷、法家卷都在编辑过程中。我觉得细水长流,每年出一到三本,长期下来应该比较有规模。
陈:做这个“Dao”系列的中国哲学指南丛书确实很有必要,很有意义。我到牛津大学访学一年,就发现他们那边类似的丛书非常多,有TheCambridgeCompanionstoPhilosophy,BlackwellCompanionstoPhilosophy,RoutledgePhilosophyCompanions,OxfordHandbook等系列,还有几年前您给我介绍的SEP(StanfordEncyclopediaofPhilosophy,斯坦福哲学百科)网站,后来我经常使用这个哲学百科查询一些自己感兴趣、想了解的哲学概念或理论等,很方便,也很权威,也曾多次向学生推介。我就在想,中国大陆现在不缺钱,也应该来做类似的事业,由某几个名校哲学系及其出版社来推进,当然,主事者非常重要。现在反而是在您的主事下,凭一己之力,用英文先做了,很有必要向大陆学者推广这套以海外学者为主撰写的中国哲学指南丛书,它应该成为研究相关人物或领域的必备参考书。
黄:是的,现在复旦大学已经开始着手将我编的这套中国哲学指南丛书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一直在想,以你上面提到的《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为样板,中国学者可以至少做两件事情:一是出一套类似的包罗万象的中文版的哲学百科全书;另一个是出一套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虽然《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也收一些中国哲学的条目,但毕竟有限)。因是网络版,不受字数限制,每一个条目可以有上万字甚至数万字长。而且如你注意到,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对于重要的哲学家,不仅有一个全面的条目,而且还对这个哲学家的哲学的各个重要方面另安排独立的条目。以康德为例,除了“康德”这个条目外,还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的哲学发展”“康德与休谟论道德”“康德的超验唯心论”“康德与休谟论因果”“康德的超验论证”“康德的数学哲学”“康德的科学哲学”“康德的宗教哲学”等,差不多有20个独立条目(很可惜的是,里面没有一个中国哲学家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也说明我们有必要出一套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百科全书》)。另外,这个百科全书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这些条目的作者都是这个领域公认的学者,而且虽然条目的作者都是邀请的,但写好的每个条目跟杂志文章一样都要经过匿名评审,一般都需要修改以后才能发表。不过,如你所说的,虽然中国现在不缺钱,但我无法想象谁会发起做这样的事,而且即使有人发起做这样的事,国内顶尖的学者是否愿意为它写条目都是一个问题。
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文化要走出去,这项工作确实很有必要。但是,想必您也有所了解,国内现在都是“项目化生存”,果真有一天国家开始出资推动此项工作,我担心研究很可能陈陈相因,东拼西凑,即便做出来也很难有公信力和权威性。而且,如果撰写类似词条不在各种评价体系之内,有多少人愿意为之努力确实很难说,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对培养学者的学术荣誉感似乎并不有利。就此而言,有时候一人主事反而办得好,就像您一二十年来所坚持的那样。
黄:最近还策划了一套丛书,因得到复旦大学哲学院的支持,起名为FudanStudiesin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由Bloomsbury 出版。这套书中的每一本都以某个重要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为焦点,我会邀请十来位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要求他们去读这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然后试图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方面提出挑战、批评,然后再邀请这位西方哲学家对这样的挑战做出回应。虽然这样的西方哲学家一般不懂中国哲学,但由于我们是用中国哲学的资源来讨论他们自己哲学中的问题,因此也可以从理论角度作出恰当的回应。我们一般先开一个讨论会,然后再要求会议的参与者回家修改论文,再将它们连同西方哲学家的回应一起编辑出版。到现在,该丛书的第一卷,MichaelSlote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已经出版, 第二卷ErnestSosaEncounteringChinesePhilosophy将在年内出版。第三卷讨论英国哲学家Simon Blackburn,但由于疫情,会议几经延迟,到现在还没有开成。很多在英语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抱怨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不感兴趣,但如果他们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他们怎么可能对中国哲学感兴趣呢?所以本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西方哲学家知道,中国哲学中有很多资源直接涉及他们所关心的西方哲学问题,从而使他们对中国哲学产生一定的兴趣。而且由于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当代西方哲学家,其他一些受这些哲学家影响或者研究这些哲学家的学者也可能因此产生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则是通过要求每一卷的参与者认真阅读有关西方哲学家的著作,鼓励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把自己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当代西方哲学中所关心的问题挂钩起来,看看前者是否能够对后者作出重要的贡献,而这就涉及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中国哲学或者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陈:经由您的引介,斯洛特于十年前就多次来国内开会,并且于2013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系列讲座,这些年他与中国学界的交往交流比较频繁。据我所知,国内做美德伦理学或情感主义的几乎言必称斯洛特,而他自己也很乐意从中国哲学比如孟子、王阳明和阴阳思维中汲取思想资源。我对于索萨的“美德知识论”略有所知,布莱克本的书也略有翻阅,但都了解不深。当您邀请当代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参加这种比较特别的哲学对话时,他们有何反应,事后他们觉得如何?
黄:如你所说,斯洛特在我们开会讨论他的著作之前,已经关心中国哲学了。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最早应该是他有一个中国学生跟他写博士论文,用他的道德情感论解释孔子的思想。我跟他最早认识大概是在2009年温哥华召开的美国哲学学会西部分会的年会上。当初我参与组织了“宋明理学与道德心理学”的会议,得到美国哲学学会的支持和资助,作为这次年会上的小型会议,记得有三场讨论。我们做宋明理学的学者发表宋明儒学中涉及当代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文章,由西方的道德心理学家做回应。虽然我的文章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霍卡(Thomas Hurka)回应的,而斯洛特回应的是另外一位学者的文章,但我们在会上做了比较多的交流。你上面提到的他在华东师大的系列演讲也是我安排的,当初的设想是做一个系列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每次请一个西方哲学的名家做三到四个讲座,然后请一些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对这些讲座做评论,再请这个哲学家做回应,并最后将这些讲座、评论和回应结集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斯洛特的讲座成了这个设想的系列中的独唱,书也没有出版,有点遗憾。所以我那次组织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讨论他的哲学,他当然非常乐意,事后也开始花更多的精力研究中国哲学。相对来说,我们第二次会议、丛书第二卷的主角索萨事先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不是太多,不过他也曾经在我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通过对《论语》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的解释来阐发他的美德知识论思想,或者说用他的美德知识论对《论语》中的这句话做出了一种独特、有启发性而又不无道理的解释。因此,当我跟他谈起我的这个计划时,他也欣然接受。后来在读了我们从中国哲学对他的美德知识论提出的各种挑战的论文后,他说看来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庄子、荀子和王阳明(因这三个哲学家在我们的论文中出现得最多)确实在美德知识论方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回应我们从这些哲学家的角度对他的美德知识论提出的批评,他说他不得不要超出甚至修改他在已经发表的著作中的观点。他非常支持我将这个计划做下去,并说如果我在联系西方哲学家时遇到困难,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切身经历给他们做说明。至于我们计划中的第三次会议、丛书第三卷的主角布莱克本应该对中国哲学也有些了解,因为他自己单独编写过一本哲学词典,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哲学的条目。因会议还没有开始,我当然不知道他对我们这个计划的反应,但当我跟他联系时,他也是马上答应的。当然并不是我所联系的西方哲学家都愿意参与我的计划,我曾经联系过好几位这样的哲学家,但他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婉言相拒。不过,另一方面,当我邀请一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参与我的这个计划时,也有不少人婉拒。尽管如此,我看到,两方面还是有不少的学者愿意参与这个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因此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目前只希望疫情赶快过去,让我们把这个计划中的第三个项目尽快完成。
下篇:比较伦理学的意义与方法
陈:您说当初办《道:比较哲学杂志》事出偶然,但是后来做“道”系列指南和西方哲学家遭遇中国哲学系列丛书时,恐怕更多地是出于计划,我相信在您内心深处,一定是有某种雄心和抱负,认为这是一桩值得付出的事业,一旦认准了,不急不躁,持之以恒,“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三年一小成,九年一大成。相信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界的尴尬处境一定会因黄老师的努力而有所改观。让我们转到比较伦理学的话题。说到比较伦理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提起,即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孔汉思(Hans Küng)起草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自此后,“全球伦理”的提法日渐增多,而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则是有关“道德金律”的讨论火了一阵子。在2000年前后,国内很多有分量的学者都对此有所讨论,而我第一次知道您,也与此有关。2004年7月,您和理查德·罗蒂造访复旦大学,罗蒂做了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您做了关于“道德铜律”的讲座。您于2010年在台大出版社出版了“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政治三部曲,对以往有关“全球化”的研究算是一个阶段性汇集。能否介绍一下“全球化伦理”在西方的一些情形?
黄:“全球化时代”三部曲的出版跟台湾大学的黄俊杰有关系。当初他邀请我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并希望我为他们高研院所编的丛书供稿。我就将我那段时间发表的有关全球化的论文汇编成一册叫《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宗教和政治》,但因篇幅太大,他就决定将其分为三册:《全球化的伦理》《全球化的宗教》《全球化的政治》(后来上海交大出版社用了别的书名出了这三本书的简体字版),并专门搞了一套“全球-在地化”丛书,我的这三本成了这个系列的前三本。说起全球化,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全球化的食物如麦当劳、全球化的饮料如可口可乐等。但是,我想真正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应该是最有地方性的。就此来说,越是全球化,越是要讲地方性。
你上面提到的1993年的全球伦理大会,西方学者都强调“己所欲,施于人”的所谓金律,而认为儒家讲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能是银律。但以杜维明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坚持消极表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金律,在全球化时代更有价值,因为它强调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但是,对儒家“金律”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不用做任何事,就能遵守此规则。但在我看来,无论是道德金律还是银律,无论是肯定表述还是否定表述,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定我与人是相同的:我所欲一定也是人所欲、我所不欲一定也是人所不欲。所以,我提出“道德铜律”这一概念,其积极表达是“人所欲,施于人”,消极表达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英文版2005年发表在《东西方哲学》。我的提法主要是受了庄子的启发,比如他所讲的“混沌”的寓言,以及鲁侯养鸟是“以己养养鸟”而非“以鸟养养鸟”的寓言。这两则寓言充分表明,我之所欲不一定为他人之所欲,因而也隐含着我之所不欲不一定是人所不欲。我的“道德铜律”跟“道德金律”或“道德银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关注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行为对象之间的差异。我认为道德铜律古往今来都是适用的,但其意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显突出。
陈:从主体视角向他者视角的转化,以及人们有各自的善观念,除了庄子的启发外,是否还有罗尔斯的影响。我知道您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罗尔斯的课,彼时正是罗尔斯由《正义论》走向《政治自由主义》。晚期罗尔斯有个基本看法,现代民主社会中存在大量合理而又整全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他称之为“多元论的事实”,道德或政治规范不能建立在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的基础上,否则就会造成对其他整全性学说的排挤和打压。
黄:我刚到哈佛时是访问学者,旁听了罗尔斯的两个课:一个是他给本科生开的课,记得是近代伦理学史;另一个是他和斯坎隆(Thomas Scanlon)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三个人为哲学系和政府系合办的一个博士项目开的课,每次其中一个人主讲,其他两个人做评论。但说实话,去这些课堂有点追星的味道,我真正对罗尔斯思想的理解还是通过读他的著作而获得的。我的道德铜律思想跟罗尔斯对宗教、文化和形而上学多元性(在他看来多元性不只是个事实,而且也是一个价值)有关,但至少在两个方面也有不一样:一个是关注点不同。他主要是在政治哲学角度讨论多元性这个事实和价值。由于存在着宗教、文化和形而上学关于好生活的多元看法,罗尔斯就认为,一个社会在确定其政治原则时,不能用其中的任何一种看法作为理由,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对在好生活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公民不公。而我的道德铜律则主要是从伦理学角度关注多元性这个事实和价值;更重要的一个差别是我们对这个事实和价值的关注程度不同。在罗尔斯那里,在我们讨论政治问题时,要表示我们对在好生活问题持与我们不同看法的公民的尊重,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有争议的好生活观作为理由,我们唯一能用的就是他所谓的公共理由,即我们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教会成员、家长、工会成员等等)提出的、为所有公民能够接受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政治哲学范围内,如我在后来出版(先是英文版后是中文版)的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政治之公正与宗教之善:超越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所表明的,我也不同意罗尔斯的看法。由于为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所谓公共理由(如科学、数学、逻辑的理由)往往不足以解决大多数政治问题,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不同公民伙伴的、与我们不同的好生活观中是否有我们能够接受的、同时又可以支持我们所倡导的政治原则的理由。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真正显现了我们对自己的公民伙伴的尊重。要尊重我们的公民伙伴,光是不把我们的好生活观强加到他们身上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力图了解、理解且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他们的好生活观。这一点在伦理学方面就显得更加重要。我的道德铜律要求我们的行动必须适合我们的行动对象的独特性,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首先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行动对象的这种独特性。这种了解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特定的行动对象作出恰当的行动,而另一方面它本身就表示了对我们的行动对象的尊重。
陈:确实,了解他人才能真正尊重他人。在此方面,您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观点,比如Ethics of Difference(差异伦理学)、Patient-Centered Relativism(对象为中心的相对主义),以及庄子是 patient-centered relativist等,极富启发意义。2004年作为硕士生的我第一次聆听了您的相关讲座后颇不以为然,后来阅读您的文章多了,也比较了解您的思路和想法,对此越来越赞赏。我相信您提出的“差异伦理学”一定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我认为这是对庄子思想的一个极好的阐释和现代发展,中国哲学真正要对现代世界贡献思想与观念的力量,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研究,而不是困在历代浩如烟海的注疏中。不过,我也一直有点疑惑,道德铜律似乎不再相信儒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伦理观念。我们能感受到庄子“以人养养鸟”的寓言就是冲着解构儒家道德原则的,在孟子的心学普遍主义与庄子的以对象为中心的相对主义之间,您似乎更倾向认同庄子?人与人之间真的无法达成道德共识吗?这也是庄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黄:我们也可以说,“道德铜律”就是一种道德共识,可以说人人相同的“心”和“理”就是要根据我们的行动对象的独特性来行动。当然你也可以说儒家讲的这个人人相同的“心”“理”是仁,但这也与我讲的道德铜律不矛盾。仁者爱人,但如何去爱一个人则取决于我们的爱的对象的独特性。我们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对妻子丈夫的爱是不同的,我们对好人与坏人的爱也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对父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与在他们年迈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爱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程颐用“理一分殊”来说明张载《西铭》中讲到的不同种类的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子认为,虽然我们这里所谓的道德金律或银律是“近于仁”,是“入仁之门”,是“仁之方”,“然未至于仁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以己之好恶处人而已,未至于无我也”。相反,如果我们能够“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所以,虽然我的道德铜律主要源于庄子的思想,但与儒家的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
陈:很受教益。我相信程子的“以物待物”或“物各付物”可能吸收了庄子的一些思想。让我们转向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比较哲学方法论的问题。您最近20年来主要从事美德伦理学的研究,我知道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的斯洛特、赫斯特豪斯等美德伦理学家及其著作,最早都是从您那里获悉的。庄子之外,近十余年来,您更多地还是做一些儒家与美德伦理学相互发明的工作。记得2018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做了几场关于二程和王阳明的讲座,我发了一条微信广而告之,提前“剧透”了您的思路,名之曰“西方伦理学的问题,理学家更好的回答”。确实,有人会认为您的比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取径是“西方的问题,中国的回答”。国内有不少人对此做法颇有异议,认为问题是西方哲学设定的,而我们不能总是跟着西方哲学设定的议程或问题走。这貌似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因为它暗含了某种“原罪”,意味着这样做本质上就是错的。您新近出版的《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2019年)和即将出版的《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两部书名都表现了这一取径,而且书名也颇有意味,比如您不是从美德伦理学的视域来看宋明理学,而是从儒家(包括宋明理学)的观点来看美德伦理学。能否借此机会详细谈谈您做比较伦理学的方法。
黄:事实上,我并不是在先确定如何做中国哲学以后、或者说对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一个明确意识以后才开始做中国哲学的,可以说我做中国哲学的方法是在做中国哲学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你知道,无论是在华东师大、在复旦还是在哈佛的学生时代,我虽然也学中国哲学,但主要学习的都是西方哲学,前后加起来四个学位论文都是西方哲学。而且我在美国教书时教的主要也是西方哲学课(我当初应聘的职位是政治哲学),最初发表的五六篇英文期刊文章也都是关于西方哲学的,另外我在美国的哲学系的所有同事也都是做西方哲学的。所以当我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到中国哲学后,很自然地,跟很多国内的中国哲学的学者不同,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一种比较独特的中西比较的视野:一方面,在思考中国哲学问题时,我就在想西方哲学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在思考西方哲学问题时,我就会考虑中国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持什么看法。如果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发觉,西方哲学家在其中的某个问题上的看法存在着缺陷,而中国哲学家的观点恰好可以克服这样的缺陷,我就开始构思论文,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家如何可以比西方哲学家更好地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陈:这种意识会不会跟您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有关。您上面提到您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有关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聚焦宗教之善与政治正义展开论述,您既不是单边地赞同自由主义,也不是单边地赞同社群主义,而是看看“两造”各有什么好的观点,还存在什么问题,然后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您对此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只不过那种比较主要是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内部,而后来关于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比较则扩展到两种文化和两种思想传统之间,但基本方式似乎还是一样。
黄:顺便提一下我在别的地方说起过的,事实上,我在构思博士论文时,也在上杜维明先生的几个研究生讨论班,其中一个是关于朱子的。当时我觉得朱子的一些思想可以用来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各自的偏颇,但后来我的指导老师认为这样一个题目太大,鼓励我博士论文集中在当代西方语境中讨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而在博士论文写完后可以再研究朱熹,这事实上也确实就是我后来的大致研究路向。关于你讲到的我讨论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系的方式与讨论中西哲学关系的方式,是有一点类似,可以说都是广义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哲学一般是以问题为出发点的。写一篇论文就要在这个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说明你的看法与其他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人家的看法有问题,你自己的看法如何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而且你还要设想人家对你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你如何回应这样的反对意见。分析哲学要求你的论证一定要清楚,如果你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写清楚,大概是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将自己的观点想清楚,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观点有什么深不可测。但在我的这两个研究之间也有一点不同:我在做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问题时力图提出一种超越两者的立场,而在做中西比较哲学时我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古代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贡献。当然有时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发现,在中国哲学家讨论的一些问题上,西方哲学家的解决思路更独特,或者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提出了一些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家无法很好回答的问题,或者我发现西方哲学家的某些看法有问题,但中国哲学家也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就放弃这样的研究计划。为什么这样做呢?还是因为我当初在英语世界以英文写作写给西方哲学家看。有些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我觉得对这种看法的最好回答不是抽象地、一般地去论证中国有哲学,而是去论证即使是在西方哲学家最关心的一些哲学问题上,中国哲学家也有可能提出比他们更有道理的看法。而这样的做法同样也适合对中国哲学有同感或者好奇心但由于语言的限制而无法自己去做中国哲学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因为他们对中国哲学感兴趣,很显然不是要证明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高明,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中国哲学家是否持一些与西方哲学家类似的立场,而是想知道中国哲学家对于他们解决他们自己的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是否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因此如果你的研究只是表明,(例如)孔子有很多与亚里士多德类似的美德伦理思想,那么这些西方哲学家就不会有动机去读《论语》,因为他们已经熟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而孔子只是有些类似的思想而已。
陈:确实,如果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关注和讨论一些西方哲学家(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所关注和讨论的一些哲学问题,这较之诉诸philosophy或ontology等词源学或概念的比较来确证中国古代有无哲学更为有效,也更为实质。在我看来,西方哲学上讨论的很多问题是普遍性的,中国古人也讨论这些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您的比较伦理学研究主要不是意在寻求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而是探讨哪一方对相关问题解决得更好。
黄:是的。由于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做中国哲学研究,很自然地我跟国内中国哲学学者的一些做法会有明显不同,尽管我当初对自己的这种方法论没有明确的意识。我真正有意识地思考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的方法论问题与刘笑敢教授有关。刘笑敢认为虽然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众多,但主要有两种,一种以历史的客观性研究为主的导向,一种是以理论发展创新为导向。后来他看到了我写的一些文章,觉得有些特别,不太容易归入这两种方法之中。我记得他问我是否可以用一段话说明我的这种做法。当初我思考了一下,写了一段话电邮给他,但现在找不到这个电邮了。不过我看到他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发表的《中国哲学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一文中就这样描述我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两种导向的说法反映的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现状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并非要将所有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律纳入两种导向之中。纯粹客观的哲学观点的比较式研究就不必列入两种导向之中, 纯粹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兼及中国和西方哲学内容,也不一定要纳入两种导向中的某一方。中国哲学的研究大可在扎实深入的思考探索中开拓新的方法和角度。比如黄勇讨论意志软弱是否可能以及讨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课题时都以二程的资料为主, 却摆脱了平行比较、或以西释中、或援西入中的既有模式, 完全集中于对哲学问题本身的讨论。这既不是纯粹将二程当作研究对象,又不是利用二程的资料建构自己新的思想体系, 而是不分中西的哲学理论的探讨。这应该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模式, 或许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模式。”在该页的注释中他又说:“或许有人认为黄勇的做法是援中入西,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未必恰当, 因为他是以程颐的思想资料回答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并不是将程颐的思想纳入某个西方哲学的体系或框架之中。”我觉得他对我的做法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
刘笑敢在讨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反向格义”。大家知道“格义”主要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上当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用大家熟悉的中国本土哲学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的概念来解释当初大家不熟悉的外来的佛教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格义这种方式还是有其肯定意义的。而刘笑敢说的反向格义主要是指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讨论中一些学者用外来的特别是西方的(因而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家不熟悉的)概念来解释大家熟悉的中国哲学概念,这就有些奇怪。由于我自己做的工作主要不是解释工作,而是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去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语境中还是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都没有反向格义(或者格义)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语境中,我不是在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所以对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来说,我不是在做反向格义;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语境中,我不是在用中国哲学概念来解释西方哲学,所以对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来说,我也不是在做反向格义。
由刘笑敢的问题激起的我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因为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关于二程哲学的专著(WhyBeMoral:LearningfromtheNeo-ConfucianChengBrothers)各章的写作,正需要写一篇导言,而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要说明我在该书各章中体现的方法论。所以你看,我并不是预先确定了某种方法论,然后再根据这种方法论来撰写全书各章。相反我是在撰写全书各章的过程中,由于我所处的环境(在西方哲学界)中所设想的主要读者群(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而是对中国哲学不甚了解甚至不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而自然形成的。顺便说一下,该书的中文版已经由华东政法大学的崔雅琴翻译成中文,年内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中文书名现在暂定为《为什么要有道德:二程道德哲学的当代启示》。
关于我在该书的导言中所归纳的我从事中国哲学或者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些主要思想,实际上已经在你帮我翻译的《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以儒学研究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一文中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了。虽然上述刘笑敢讲的两种导向主要是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本身而言的,而我做的应该算是比较哲学,但在比较哲学领域,就方法论而言,主要也是这两种导向。一方面,有些从事比较哲学的学者之所以从事比较,主要是为了通过比较对所比较的哲学家获得更好的理解。例如通过跟孔子的比较,可以看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我们原先看不到的方面,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有些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在从事比较研究时主要关心的不是他们在比较的哲学家(如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本身,而是想在这样的比较中得到某些启发,为他们自己的哲学构造服务。南乐山在我所编的刊物(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第一卷的第一期上所发的文章《比较哲学的两种形式》(“Two Forms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就详细阐明了这两种比较哲学方式的不同。大多数比较哲学学者认为他们在从事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比较哲学,南乐山则明确承认自己在做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比较哲学。相对而言,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安乐哲所从事的也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比较哲学,但安乐哲自己并不认同,认为他所讲的是真正的中国哲学。
陈:诚然,大概很少有作者写一本书或研究一个主题,会先把方法论写好,然后按部就班做研究,一般都是在写完后觉得有必要再来一个方法论的总结作为导论,当然一开始必定也有某种未曾明言或概念化的方法论在其中。我在这里要为您的“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辩护和扩展一下。首先我认为方法随主题和对象而定,讨论不同的主题,面对不同的对象,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也认为一些看似比较特殊的方法也有其普遍性。比如您所讲到的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如何做中国哲学的方法,其中一些同样适用于在中国语境中做中国哲学,没有这些方法论的自觉,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很难走出陈陈相因、浮泛空疏的困境。
黄:是的。我自己所从事的比较哲学跟南乐山讲的这两种都不同,或者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哲学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哲学对重大哲学问题的贡献,而且由于我在英语世界从事这样的工作,很自然地我会选择那些历史上和当今西方哲学家在我看来存在缺陷的重大哲学问题上的有关观点,然后看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何能在这些问题上提出更为合理的看法。所以我有点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研究是让西方哲学家确定(他们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让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所以很显然这不是南乐山所讲的第一种比较哲学研究方式。但同时,由于我要向西方哲学家所表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不是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一定是我认为是恰当的因而也是我所接受的看法),我的研究也不同于南乐山讲的第二种比较哲学研究方式。因为我需要表明我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确实是这个古代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而这就要求我对有关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本做仔细的客观的研究。
在这种意义上,你将我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概括为“西方的问题,中国的回答”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也可能引起误解(就像我自己关于这种方法论的说法会引起误解一样),而如果有人进而认为我实际上在做的不是中国哲学,而是西方哲学则更有问题。当然我也不会反过来辩护说,我在做的是中国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实际上我在做的既是中国哲学,也是西方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西哲学家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当然我迄今的研究还是单向度的,还没有反过来做,即选择中国历史上哲学家讨论的、其代表性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的问题,然后再看西方哲学家在这样的问题上如何能提出更有道理的看法,即让中国哲学家设定(他们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让西方哲学家提出定论(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有人认为我在做的不是西方哲学而是中国哲学呢?)。不过,无论是在中国哲学研究的语境中,还是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语境中,这种相反向度的研究,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没有很强的迫切性。
陈:我记得您曾私下谈论过,当您谈论这种双向度的比较研究时,国内一些学者建议您不要做后面那一种研究,即中国哲学家设定问题,西方哲学家更好的回答。因为中国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弱势,近代一百多年来大家都说中国传统思想不行,一直处于被否定的状态。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否定很多时候是成见偏见所致,并无多少学理性。如果有人真心诚意从学理上研究中国哲学的不足,我以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做中国哲学也是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做中国哲学。虽然跟美国大学不一样,中国大学的所有哲学系都会有人做中国哲学,但还是西方哲学占主导。不仅做狭义上的西方哲学的人往往比做中国哲学的人多,而且做逻辑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等的基本上都是在做西方哲学,如果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算作是西方哲学的话,那做中国哲学的人在一个哲学系中真的是少数派。现在回到我上面的话题。在何种意义上,我从事的这种比较哲学研究也是一种中国哲学研究呢?表面上看起来,我用中国哲学资源来解决西方哲学的问题,很显然我真正关心的是西方哲学而不是中国哲学。但其实不然。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看。首先,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中国哲学资源来解决西方哲学问题呢?这不正表明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吗?这里,很显然我不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他们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因此绝对不能与西方哲学挂钩;但我也并不假定,所有中国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也都是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或者只有西方哲学家也讨论的问题才算是哲学问题,反之亦然。我认为不要作这样的一般的事先假设。相反,我们应该从我们关心的具体问题出发。如果我们首先关心到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某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去看看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什么看法,特别是有启发性的看法,反之亦然。我自己的比较哲学研究经验告诉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中看到关于相应问题的讨论。
这就涉及我的做法与其他比较哲学的不同,我的比较侧重的是问题,而不是概念。当然中西哲学中有些类似的哲学概念可以比较,但这样的比较可能性比较狭小。中西哲学中可能缺乏相应的概念,但可能有相应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哲学中从苏格拉底到戴维森都讨论意志软弱这个问题,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呢?如果我们为此而在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去找“意志软弱”这个概念,则要么根本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但跟西方哲学中的“意志软弱”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按照戴维森的看法,意志软弱就是:你经过综合考虑知道你应该做一件事情,而且也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还是没去做。这实际上就是知行问题(比如,知而不行),而关于知行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广泛的讨论,因此很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不只是西方哲学的问题。
陈: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一是质疑所谓中国哲学独特性,我完全赞同。讲中国哲学特殊性的一些学者,往往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理解),然后说中国哲学是另一套。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其实较之通常所谓“以西释中”还更加变相西化,因为你逃避不了人家的阴影,虽然你明面上可能有意地避免使用一些西方哲学的词汇。
黄:我的看法是,也许中国哲学确实具有他们所说的独特性,但这应该是大家深入广泛地研究以后得到的结论(如果真会有这样的结论的话),而不应该是我们从事这样的研究的前提。现在我要讲一下在何种意义上我所做的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点。虽然我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资源去解决那些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家没有很好解决的哲学问题,但在此过程中,我也始终从西方哲学家的角度对我阐述的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发问,看他们是否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而这会促使我们看到我们之前往往会忽视的中国哲学家的一些洞见。例如宋明儒承袭先秦儒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但西方哲学家就会问,你有什么根据认为人性善呢?我们都知道程朱的回答是由恻隐而知仁,或者说由情知性。性是形而上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情是形而下的,是可以经验到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可经验到的善的情来知道经验不到的善的性;这里善的性是用来解释善的情的:没有善的性怎么能有善的情呢,就好像没有根怎么会有苗呢?但是站在西方哲学家的角度,我们又不能不进一步发问,既然程朱也承认人的情不总是善的,也有不好的情,那么为了解释这些不好的情,我们是否也必须假定人一定也有不好的性呢?当然我们可以回应说,好的情一定要有好的性来说明,但坏的情不一定来自坏的性,就好像从好的苗我们可以推知一定有好的根,但从坏的苗却不能断定其根一定不好,因为苗之不好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但这样的回应无法完全排除坏的情来自坏的性这种可能性,就好像我们无法排除坏的苗是由于坏的根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程朱的由情知性无法证明人之性善。但这是否就表明儒家性善论有问题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进一步阅读朱子的文本发现,他的这个由情知性论证是跟另一个论证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人禽之辨。当人做了伤人的事情以后,我们会说这个人不应该伤人,但当一只老虎伤人时,我们不说老虎不应该伤人。为什么呢?因为应当隐含着能够。我们从经验的观察和研究可以知道老虎不能不伤人,而人可以不伤人。我们可以让伤人的人不去伤人,但无法让伤人的老虎不去伤人。从这样的观察我们可以知道,伤人不属于人的本性但属于老虎的本性。当然这样的论证也不一定就对人性论做了完美的证明,但这个事实说明,我们做中国哲学的学者时刻想着西方哲学家对我们讨论的观点的可能挑战,有助于我们关注我们没有关注的方面。我这里不是说我们先前忽略了程朱哲学中关于人禽之辨的讨论,而是说我们没有把它与由情知性一起来论证性善论。
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我们上面谈到了宋明儒讲人性是形而上的。事实上宋明儒在西方一般被称为新儒学,而宋明儒较之先秦儒之“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许就是其形而上学,但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特别是英美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反形而上学潮流,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如罗蒂所指出的,“宗教和形上学共有的律令——给思想找一种非历史、超文化、跨时空而无物不适的基质——已经死去,不复存在。在后形上学的文化中,人们会认为,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对上帝或‘实在的本性’负责,不是由上帝或‘实在的本性’告诉我们生活·世界是什么”。因此用宋明儒学来帮助当代西方哲学家解决他们的哲学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回应他们对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倾向的可能批评。在此过程中,我就发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反对的是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我称之为基础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认为,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超经验、非历史的真理作为基础,它独立于我们的经验信念与实践信念,并可以推导出我们的经验信念与实践信念或者确定这些经验信念或实践信念之真假。但如我们上面看到,宋明儒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首先假定了一些经验事实,人有恻隐之心,恶人能变善而动物则不能,等等,然后试图解释这样的事实,认为如果不存在由仁义礼智构成的人性,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经验现象。这里,虽然在本体论上,形而上的人性是在先的(没有作为性的仁就不可能有作为情的恻隐),但在认识论上,这些经验现象是在先的(离开了恻隐这样的情就无法知道仁这样的性)。我称宋明儒的这样一种形而上学为解释性的形而上学,它可以避免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评。
陈:确实,儒家人性论的研究和当代发展,如果没有源自外来思想的批判或援助,我觉得很难讲出新意,也不太具有说服力。
黄:现在我再讲第三点。虽然我的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解释中国哲学,但由于我强调用中国古代哲学家本来的思想来解决西方哲学家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研读文本,从而对中国哲学的某些方面可以提出一些独到的解释。例如为了说明程颐对西方哲学中讨论的意志软弱问题的贡献,我们不能不关注他在由张载提出的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问题上的看法。学界一般都认为,闻见之知是像关于雷鸣电闪这样的经验知识,而德性之知是一种理性的道德知识。可是我做了仔细的研究,发现张载、程颐讲的闻见之知主要也是指道德知识,只是这些知识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或者从儒家经典中看到的,因此是一种间接知识,而不是一个人通过自己内心体验而获得的知识,而后者才是德性知识。因此,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往往具有相同的形式,如我们对父母要孝。如果一个人只是从书本上或从老师那里知道应该对父母孝,甚至理解为什么应该对父母孝,但没有从内心体验到这一点,这个人并不会有动机去对父母孝,而这就是闻见之知。而如果这是一种通过内心体验而获得的知识,是一个人的自得之知,这个人就自然会有孝父母的动机,而这就是德性之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你可以说闻见之知是间接知识(从别人那里获得的),而德性之知则是直接(自得)之知;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你甚至可以说闻见之知是理智之知,而德性之知反而是经验之知(只是通过内在经验而不是外在经验获得的知识),即杜维明所谓的体知,虽然它也包含了理智的成分。关于对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这样一种理解,我在去年发表于《哲学分析》第3期上的《作为动力之知的儒家“体知”论:杜维明对当代道德认识论的贡献》一文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陈:黄老师关于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这个发现,很受教益。可见,当我们试图从中国哲学资源中寻求对西方哲学问题的解答时,不只是对一些观念做一些去脉络化的大而化之地提取,也需要我们从中国哲学固有的脉络中认真研读中国哲学家的文本,准确理解他们所讲一些概念的涵义。总之,从西方哲学问题出发,也能加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而且往往能发人所未发。就此而言,所谓“以中释中”未必比“以西释中”(姑且如此名之)对理解中国哲学家的文本更准确。不过,是否也存在这样的情形,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也构成了严肃的挑战?
黄:当然。上面提到,虽然我试图用中国哲学中的资源来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我也始终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对我所用的中国哲学中的观点立场提出责疑和挑战,而为了回应这样的责疑和挑战,我往往会在中国哲学中发掘出以前不太为人关注的方面。但并不是在所有场合我都能对西方哲学的责疑和挑战提出令人满意的回应。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儒家中的人性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事实上,我在试图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提出儒家的解决方案时也往往使用儒家的人性概念。但我们如何规定人性概念呢?我们从儒家的角度也许会说,人性并非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把人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即人性就是人所独有的特性。上面提到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家霍卡认为这样的观点有问题。他说把人性理解为人所独有的特性会把人类与其他存在者共有的所有东西排除在人性之外,不管它对于人来说多么重要,同时也会把人所特有的东西都视为人性,不管它对于人来说多么微不足道。另外,当我们说某种(些)性质是人所独有的时,事实上我们不光是在说人,而且是在说人以外的存在物:这些别的存在物没有人所有的这种(些)性质。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无法断定什么是人性,除非我们已经考察了迄今存在的所有别的存在物并确定它们都没有人所有的这些性质。即使这种工作实际上是可能的,但如果一百年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存在物也具有人所特有的东西,我们是否就必须否定这些性质属于人性呢? 那么我们把人性理解为人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即无之不足以成为人的东西是否可行呢?这种观点的一个好处是,要了解什么是人性,我们只需要研究人,看什么是人所必不可少的性质,而无需研究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但他认为这也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人性概念就太泛了。像自我同一、占有空间这样的特性对于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对于与人很不相同的其他存在物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人性的第三种理解是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即人性是人所特有的而且是人必不可少的性质。霍卡认为,虽然这种人性观可以克服上述两种观点的一些弊病,但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第一种观点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例如,说人性是人所特有(并且必要)的特性,我们还是得研究人以外的存在物,这使我们的人性概念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关于所有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本性的概念。他自己提出了他认为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一种人性观,我这里就不加讨论,但我认为既然人性概念对儒家哲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学这么重要,儒家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人性概念,并使这样的人性概念避免霍卡提出的问题。
陈:这确实是一个在儒家人性论传统中不曾留意的问题,值得认真对待,好好思考。您特别强调,您运用中国哲学资源来解决西方哲学问题,要对中国哲学有细致深入的理解,您可能对它们做出了某种独到的解释,但仍然是其原意,并不是在做一种所谓“创造性的诠释”。这涉及到文本解释学的问题。我在翻译您的论文时学到两个原则:一个是principle of charity(厚道原则或宽厚原则),大致是说解释者对被解释者要尽力做出最厚道的解释;一个是principle of humanity(人性原则),大致是说解释者也应该认识到,被解释者哪怕古代的圣贤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犯错,因此对其明显的矛盾之处或有问题的观点不能一味回护。这两个原则对我很受用,也经常会给我的学生讲。我以为如果我们很多研究者都怀有这两个基本原则,我们的研究会大为改观。我想问的是,这两个原则有没有一种优先关系,比如厚道原则优先于人性原则;关于厚道原则,有没有钱穆先生所谓“温情的敬意”或“同情的理解”的意思。人性原则,有没有最近几年哲学界很喜欢讲的“批判性思维”在里面?
黄:事实上,这两个原则差别没有这么大。奎因和早期戴维森的厚道原则要求我们在解释他人(特别是古人和其他文化中的人)的文本时,要尽可能假定这个人的讲话是合理的甚至是真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古人和其他文化中的人与我们的背景很不相同,因此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他们讲话的背景和假定,我们可能将其讲的许多话看作是假的甚至非理性的。后期戴维森接受的、最初由葛然蒂(Richard Grandy)提出的人性原则实际上差不多,只是他试图纠正在使用厚道原则时可能有的极端化现象,即把古人和异文化的人讲的明明是错误的话也看成是真的。之所以被称为人性原则是因为它假定人是理性的,因此我们在解释他人的话时,也要假定这是理性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也许还没有真正理解他讲的话,这与厚道原则没有什么两样。但人性原则也假定人是人,而人是有可能犯错的,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古人或异文化的人讲的话有可能是错的甚至不合理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性原则包含了厚道原则并试图避免其误用。同样,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类似于你上面提到的 “温情的敬意”或“同情的理解”。人性原则可能没有批判性思维那么强,批评性思维可能与左派或女权主义所倡导的怀疑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类似,解释者往往怀疑古人的著作讲的是不是真的,例如有些女权主义《圣经》学者认为《圣经》中关于妇女在早期基督教中的地位的描述是不对的,受到了男权至上主义的影响。左派和女权主义喜欢用“怀疑解释学”,比如左派会说某某经典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等。
陈:我想我大致理解“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是怎么回事了。我想这个概念可用来形容国内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儒学的解释心态和方法,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更准确地说是“批”),在一本名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的著作中,一位老一代的学人得出孔子“为少数恶人之师表、集片面谬说之大成”的结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心态和方法至今在国内学界并不少见,这愈发突显厚道原则和人性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您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到,歌德说:只懂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不懂语言。宗教学研究之父德国学者缪勒(Max Mueller,1823-1900)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宗教: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不懂宗教(He who knows one[religion],knows none)。您自己进而说:只懂一种哲学的人其实不懂哲学,只懂一种伦理学的人其实不懂伦理学。王国维说“学无中西古今”,现在国内有不少学者从事比较伦理学或更一般而言的比较哲学研究,您能否对这些博士生或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和良言,作为本次访谈的结束语。
黄:首先我想说的是,虽然我认为我所采取的这种研究中国哲学或者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具有它的独特意义,但很显然它只是而且应该只是研究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因此我并不主张大家都采取这种方法。事实上,可能很多人认为这种方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很少有人愿意采取这样的方法。对于想用这样一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或者中西比较哲学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如博士生,虽然没有良言,但我会鼓励他们去做。我听到一些博士生说,要用我这种方式做研究、写论文,需要有扎实的中西哲学的训练,而这不是在博士阶段可以完成的。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是选题,这方面确实需要导师的建议或者把关,确定这样一个题目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做得出来的。而一旦题目确定,即使这个学生先前的中西哲学训练不是很全面,问题也不会很大,只要他愿意花力气。例如,你的题目是王阳明如何可以帮助美德伦理学回应来自情景主义(situationism)的批评,你要阅读研究的主要就是这两项,当代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中情景主义对美德伦理学的批评和王阳明哲学的有关内容,而即使你以前对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深入研究,在博士生的几年中还是可以完成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好几位博士生都在这方面有成功的尝试。在博士毕业之后再做几个题目,那么你在中西哲学两方面的训练就更加扎实。所以这里似乎也存在一个类似循环的解释学的东西:你在中西哲学方面的训练越扎实,你就越能做中西比较哲学;而你的中西比较哲学做得越多,你在中西哲学方面得到的训练就越扎实。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新作选:董春雷《无尘(三联画)》(2021年)、许建春《日暮结局村》(2021年)、孙尔、郑怡艳《痕》(2017年)、朱珺《绝学之路·中国壁画艺术展》(2020年)、徐清《沙孟海先生集易林联》(2021年)、斯泓《霓裳羽衣曲(系列之一)》(2017年)
- 杭州师范大学名贤篆刻录:乐石社社刊《乐石第二集》篆刻选刊:陈兼善/邱志贞/陈伟(1914年)
- 杭州师范大学名贤书画录:孙智敏《阆苑画屏行书七言联》(约1940年代中期)
- 张涌泉《<金瓶梅>词语校释》手稿
- 苏元老撰并楷书《龙洞记碑》
- 基于文化遗产的“结构—功能”变迁,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