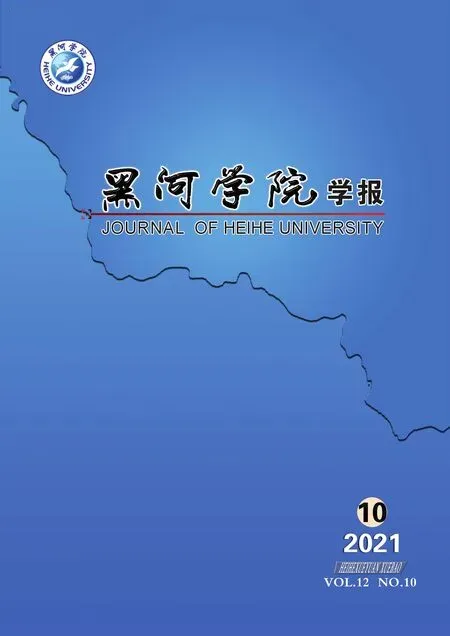当代大自然文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照
——以刘先平作品为例
楼 枫
(安徽开放大学 教务处,安徽 合肥 230022)
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进程加快,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物种消亡等问题凸显,人们不得不将目光从自身的发展转向外界的变化,开始怀念曾经静美和谐的自然。作家生性敏感,率先关注土地伦理和自然生态。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在《散步》一文中表达了“我想为自然代言。”(I wish to speak a word for Nature.)[1]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坛上兴起了讲述土地故事的“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e writing)。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坛,皖籍作家刘先平发起和倡导了中国大自然文学,从《云海探奇》开始,先后创作5部大自然小说,以及多部纪实性探险作品,打开了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大门。
有关自然的书写古已有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不乏对自然的描写,孔子认为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虫鱼。①《论语·阳货》中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诗经》中的动植物多为“比兴”之用,及至唐诗宋词中的春花秋月,散文八大家的山水小品,或托物言志,或寄情山水,对自然的描写实际上还是“人类中心”的体现。而大自然文学的出现,描写焦点从人类移向了大自然,开始通过对大自然的描绘来呈现人的精神与自然地理的交融与对抗。大自然文学这一当代文学形态,以当代生态观为指导,以较高的文学品位为读者描绘了丰富有趣的野生动物公民,展现了瑰丽多彩的自然画卷,以生态道德观敲响人们保护脚下这片土地的警钟。这是文学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的融合,所以,对大自然文学的研究,不能只在文学性上加以审视,还应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究其社会性和文化价值[2]。刘先平为自然国立传,其写作的语言和表达的观念虽然都是现代化的,但他却积极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创作理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相契合的部分,可以在古代思想精粹中找到映射。
一、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核心思想,其玄妙之处在于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智慧。简而言之,“道”是客观规律,“自然”是指世间万物存在的方式与形态。“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即要尊重世间事物自我运行的客观规律,要顺应而不要忤逆,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朴素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大自然文学以自然为书写对象,描绘了自然王国中野生动植物等生命主体的生存面貌。叙事者以客观公正的笔调,揭示了大自然的运行法则,感叹于生命对自然宪法的顺服。在《夜探红树林》一文中,刘先平讲述了自己二月从海南带回几颗红树林种子,将其插在水石清华的盆中,经过整个春天的等待都未见动静。然而就在六月盛夏的某一次赴京归来后发现,才短短几天的工夫,几颗种子在盆中便欣欣然长成了郁郁葱葱的红树林。见此情景作者猛然醒悟,红树林是热带水生林木,当生长温度不达标时,红树林便休养积蓄;而一旦气温上升,红树林便生机勃发,于是不禁感叹:
生命的底蕴、内涵,太奇妙!太神秘了![3]69
作者在这里道出了自然界生命的奥秘:不到萌发的时候,哪怕营造再舒适的环境,也无法迎来生命的演进。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时节到来的那一刻。但身处当代快节奏社会,人们已经无法放慢脚步积蓄能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即生命。人们迫切希望压缩事物运转的周期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乃至培育出速生林、速生鸡、速生菜等违背自然生长规律的新物种。人看似成为凌驾于造物者之上的万物灵长,实则沦为了自然宪法的破坏者。刘先平在作品中重提自然法则,试图唤醒人们对于生命客体的尊重和对自然规律的敬畏。
而这种尊重与敬畏不仅体现于美好的生命成长,还体现于现实的优胜劣汰。刘先平并没有回避残酷的自然世界,他作为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旁观者,告诉读者这就是大自然,大自然有自己的竞争机制,作为人不要也不应去干涉。他在《大漠寻鹤》中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苇丛中的黑颈鹤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的一对幼鸟不被麝鼠猎食,勇敢地与之搏斗。在击退了猎食者后,却冷漠地任由自己的孩子自相残杀,最终一只幼鸟被更为强壮的同胞所杀。在震惊地目睹这一切之后,作者回想起了两件事:一件是曾经的学生记叙自家屋梁上的雏燕会为了争夺父母捕来的食物,而互相将对方蹬落燕窝;一件是研究专家发现大熊猫这种极其温顺的动物,熊猫妈妈如果一胎两仔,便会遗弃其中一只,专心喂养另一只。对于自然界种种让人费解的现象,作者试图去理解并接受:
大自然有大自然的“人格”,有自己的法规,所有的生物都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正是在这种悲壮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焕发出了生命的灿烂,生命的壮美[3]222!
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讯息:大自然的法则并不都是美好的,有的很残酷,甚至背离人性。而我们需要跳脱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将自己放到更为宏观的视野中去面对真实的自然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是适者生存,种群活力维系着生态平衡。刘先平如实地再现了自然界的生命景象,让我们的灵魂经受强烈震撼的同时,领悟到无论是应时而生,还是淘汰至死,都是生命的灿烂与壮美,都是客观规律的体现。所谓“道法自然”便是不破坏、不干涉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懂得理解、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轮回轨迹,心中常怀对自然的敬畏与顺应。
二、天人合一——讲究和谐共生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儒家和道家都对“天人合一”有阐述。儒家学说认为“人无有不善”,①《孟子·告子上》中记载:“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天”即崇高的道德本体,而人生来就具有道德观,此谓“天人合一”。道家学说则认为人和天本就是合一的,②《庄子·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中记载:“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与天同属自然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基本正确且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可以总结为,人是属于自然界的,因此,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生的终极要义便是要实现天人和谐[4]。当代关于“天人合一”的认识,更多的是偏重于热爱生命、尊重自然,与自然交融共存,与万物和谐共生,实现彼此信任和完美结合。
大自然文学的书写并没有刻意规避人类,人与自然是互联相通的。其他物种并不是人类思想的象征或附庸,人类也不仅仅只是观察的眼睛和叙事的旁白。在山间、在密林、在荒漠、在海洋,人类与万物是平等的关系,相互融合、彼此倚赖。在《童年·故乡》一文中,刘先平回忆了家乡巢湖岸边渔家人怡然惬意的农作与生活,其中有一段湖滩牧场的描写:
冬天,湖水退下去了,褐色的湖滩裸露了出来,成了一群群大雁的居留地。翌年,经过几场软软的风,细细的雨,蓼叶吐红,柳条发青,芦笋冒尖了,平展展的湖滩铺了层茵茵绿草。永远是那样悠然自得的放牛伢子,骑着牛来了;扎着红头绳的小丫头,举着竹竿把鹅群赶来了……[3]3
这是一段生灵和谐的特写镜头。冬日,湖退滩露,使得大雁有了栖居之地。春天,在和风细雨的浸润下,蓼叶、柳条、芦笋便纷纷展叶萌发。好一派闲适恬淡的湖滩风光!这时候,人类出场了,因为湖滩染绿,吸引来了放牛伢、小丫头,他们的牛和鹅可以在这生机勃勃的湖滩牧场吃个够。这段近似工笔画的细描中,动物、植物、人类,乃至没有生命的湖、风、雨都是互相依存的有机统一体,没有主角与配角,没有核心与边缘,只有永恒的时序和轮回。在平权的自然国度里,人类不再是宇宙的焦点,而是融入其中,互为因果。作者用优美的笔触告诉我们,人类放弃主宰权并不意味着万劫不复,将自身置于自然的伊甸园才能享有和谐的永生。面对人与自然的琴瑟和鸣,刘先平不禁在作品中赞叹道:“人与自然绘出了一幅天人合一的感人图画。是一首人与自然的颂歌。”[3]146
在刘先平的作品中还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天人”关系。《寻找大树杜鹃王》中关于“大地母亲”[5]152“母亲河”[5]153“大地的乳汁”[5]154的描写,将自然比作生命的母体,孕育出人类与万物,揭示了人类与自然母亲休戚与共,命运合一的关系。《东海有飞蟹》中,作者在描写小兄弟俩于普陀山千步沙戏水时,对生命有了如下思考:
据说生命诞生于大海,人类的始祖是从海洋中逐渐走向陆地。生命在水中孕育,婴儿在水的包裹中成长[3]39。
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对立,人类更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大自然文学将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更进一步,人类在自然中孕育,置身于自然就仿佛安睡于母亲的怀抱,一切世间纷扰都归于冲淡平和:
小早起身,躺到了海边,半边枕着沙滩,半边在海浪的触及处,于是,他的身躯就随着海浪起伏,陶醉于大地的摇篮——海的晃动中……[3]39-40
沉浸在自然的怀抱,海洋作床,大地为摇篮,海浪的起伏是母亲温婉的轻抚、低吟的哼唱。人在融入自然的同时觅得了心灵的归宿,更有了亲近自然的理由。
除了揭示人与自然的亲子关系,大自然文学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还体现在不仅讲求人物“合一”,还讲求物物“合一”。刘先平在作品中非常注重表现在人类之外,自然万物间的同生共荣。物种之间并非只有竞争关系,还有唇亡齿寒。《寻访白海豚》中海鸥与白海豚共同配合捕鱼的场面,《藏羚羊大迁徙》中鸟鼠同穴协作巡逻的奇景,都反映出物物之间的超种族联系,对此作者作出如下评论:
动物间的互惠,动植物之间的互惠共生,是颇有哲学的意蕴。……生命之间互惠的关系,在对立的生存竞争中,营造了和谐与繁荣[5]46。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之间默契地结成这种自发且井然的合作关系,通过彼此的信任达成生存协议,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为自己增添生存砝码。“合一”便生和谐,和谐便使自然界的每一部分都运转协调,每一分子都尽己之职,每一个元素都配合精妙。天、人、物合而为一,和平共处,遵循自然法则与生命平等,不讲征服与被征服,只谈互利共赢,由“天人合一”走向“天下大同”。
三、兼爱非攻——追求博爱和睦
“兼爱”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它由儒家的“仁爱”思想脱胎而来,在墨家的提倡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兼爱”去除了儒家的宗法等级制的内容,相较于儒家有等级差别的爱,墨家的“使天下兼相爱”则是平等的。“非攻”则倡导天下人不要互相攻击,要互敬互爱,睦邻友好,体现了世界和平的愿望。“兼爱”与“非攻”作为墨家思想的核心,对于平衡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人类作为曾经狂热的自然改造者,在“大自然属于我们”的误区中走了太久。自然万物在人类面前并非平等,而是可以驯服和奴役的,人类恣意享受着攫取和征服自然的快感。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类将自身的利益放在考量的首位。如果山川河流挡住了去路,那就开山断流,哪管是不是人类闯入了自然涵养的领地;如果飞禽走兽伤害了人类,那就赶尽杀绝,不问是不是人类掠夺了生灵栖息的家园。刘先平通过作品呼唤生态道德时,首先对人类导致的生态恶果进行批判。《寻访白海豚》中因围海造田、电鱼炸鱼、环境污染而濒临灭绝的白海豚;《海上鸬鹚堡》中因贪婪者频繁盗取燕窝而累到唾液腺破裂吐血的金丝燕;《大漠黑颈鹤》中因人类偷取镇巢的接骨石而惨遭巢窝被毁的黑颈鹤,无一不是因为人类的自私与自利而遭受无妄之灾。究其原因,是人类忽略了自然的生命性,剥夺其平等地位,对其只存索取之意,没有“兼爱”之心,以至于作者在作品中奋起疾呼,人类的贪婪与私欲是大自然的恶果之源!大自然文学不惜以血淋淋的现实和直白的控诉敲响警钟,试图唤醒人类对自然的爱护与善待。
当然,在刘先平的作品中并不都是对暗黑的批判,还有对明亮的宣扬。《蓝色天鹅湖》中,牧民与天鹅比邻而居,牧民绝不会猎杀天鹅,还会给天鹅宝宝喂食,天鹅与人相处得融洽和睦,每年春天都会飞回来生儿育女。“那顶蒙古包中一家人,与天鹅一家的相亲相爱,也是一种反思和醒悟吗?”[3]165-166大自然文学在反思人类的自然“暴政”的同时,将人类社会的“兼爱非攻”延伸到了自然社会,试图以中国传统思想来对抗人类的生态伦理丧失。在刘先平看来,人对自然界生物应饱含兄弟般的深情,不论是温顺的梅花鹿、憨厚的大熊猫,还是狡猾的沙漠狐、凶猛的草原狼,抑或是静美的珊瑚、狂野的风暴,都应被无差等的温柔以待。人类不应以自身的喜好和利益对万物生灵划分三六九等,而应当报以同等的尊重与爱护。刘先平在作品中时刻秉持着无私的生态观,人类不能为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而恣意破坏生态的平衡,甚至应该为了保护生态而做出让步。在《蓝色的天鹅湖》一文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尤尔都斯盆地还是个理想的修筑水库的地区,不仅蓄水,还可发电,在这西部干旱地区,水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论证中,得知这将破坏天鹅的栖息、繁殖地之后,蒙古族自治州果断地决定另选他址。在当时,这是我国为了保护一个物种而否定大型建设的第一例[3]166。
人类以让步来换取生态和谐,这是生态意识的一大进步,人类对自然的爱上升为博爱。爱所有动物、植物,爱整个自然界,其实就是爱人类自己。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之间都存在着普遍联系,人类并不是独立于自然之外,而与自然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意识到,施以自然的恶,将会成为炙烤周身的野火;而报以自然的爱,终会化为滋润肌肤的甘霖。所幸的是,大自然文学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未来——孩子,已经自觉地对自然萌发爱与护,“兼爱”这粒小小的种子,已经悄然在人类下一代的幼小心灵生根发芽。在《东海有飞蟹》中,小兄弟俩在沙滩上捉到了三只小沙蟹,当父亲问他们准备怎么处置时,小兄弟俩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放回大海!”[3]44大自然文学在教化下一代的同时,对下一代也满怀希望。多一分爱护,少一分攻掠,人类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就是在善待自己。爱满星球,共筑家园,对自然的和睦博爱会让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地球更加长久地繁衍生息下去,由“兼相爱”获得“交相利”。
四、结语
文学应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当代大自然文学以培养和树立生态道德的重要意识和紧迫感为己任。刘先平在谈到大自然文学的主旨时认为,“其实质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保护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3]9有作家在谈到刘先平作品的美学风格时总结为“奇”和“趣”[6],笔者认为还可以加上“思”。刘先平在践行创作主旨时,为更好地维护生态伦理,唤醒生态道德,通过关照中国传统思想,在古代哲学中找寻答案。其笔下闪现的思想光华为作品增添了厚重感,使生态书写具有了文化内涵和思想指引,让读者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下,享受阅读喜悦的同时,更激发内心深处对地球家园的热爱,产生震颤人心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