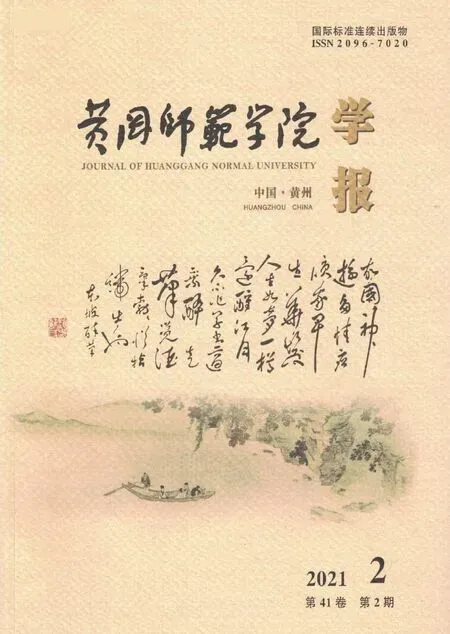明代锦衣卫都指挥使刘守有生平考论
余劲东,陈雅丽
(长江大学 历史系,湖北 荆州 4340231;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2)
锦衣卫作为明代皇帝的亲军卫队,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锦衣卫作为军事机构在明朝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锦衣卫通常身处幕后来履行有关职能,因此对他们履职情况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吴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由于发表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锦衣卫的评价趋向消极,认为锦衣卫实质是无恶不作的特务机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锦衣卫的评价渐趋客观,更多地关注到其监察职能的行使、权势的变化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对锦衣卫的研究日渐增多①,但这些研究仍集中于对锦衣卫机构和职能的有关探讨,对任职锦衣卫系内的官员个体关注相对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明代万历年间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入手,来讨论作为锦衣卫个体官员的家族、仕宦和交游问题。刘守有是嘉靖时名臣刘天和(1479—1546)之孙,自万历初年到万历十六年前后一直在锦衣卫系统内部担任排名第一、二位的长官,更与当时权重一时的朝臣如徐阶(1503—1583)、张居正(1525—1582)、冯保(?—1583)、申时行(1535—1614)、王锡爵(1534—1611)等都有过交集。通过对刘守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锦衣卫个体的了解,也有助于了解锦衣卫长官在政局变迁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及其制约因素。
一、刘守有的家世背景
刘守有出身于明代麻城四大望族之一的锁口河刘氏家族,其家族兴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的洪武年间。刘氏祖先“南昌人讳(刘)梦者,从高皇帝起义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赐田麻城,遂为麻城人。”[1]406由于有从龙之军功,刘梦由一介庶民晋身为朝廷命官,并由南昌徙家至麻城,从此南昌刘氏便在麻城生根开花。洪武晚期,刘梦长子刘从政(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成为明代麻城历史上第一位进士,自刘从政开始,明代麻城刘氏一族先后有17人举乡试,有14人中文、武进士。因为科举成绩的显赫,锁口河刘家因之被誉为“荆湖鼎族”②。
刘守有的高祖刘仲輢,景泰四年(1453)中举人,官至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令[1]406。刘守有的曾祖刘璲,弘治三年(1490)高中庚戌科进士,其为官行政颇受上级认可,被评为“江右有司第一”③,但不久后病死于江西丰城知县任上[1]406。刘守有的祖父刘天和官至兵部尚书,谥庄襄,为有明一代名臣,《明史》卷200有传。刘守有的父亲刘澯,嘉靖十一年(1532)中进士,任官郎中。以上是刘守有高、曾、祖、考的有关情况。不难看出刘守有出身于地位显赫的官宦世家,且其家庭内部有着“诗书传家”的传统,这为刘守有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进而培养相对健全的人格提供了助力。通过对刘守有家世及成长背景的了解,也有助于了解其在为官之后的行政作为。
二、刘守有的仕宦履历
由于祖辈和父辈的荫庇,刘守有进入仕途的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嘉靖十五年(1536)刘天和因为战功卓著,“加太子太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2]5293,但是刘天和的四个儿子当中,三个很早就已经去世[1]406;仅存的刘澯早先已中进士并出任官职,不需要再享受荫叙的恩遇④。因此,刘澯的长子、亦即刘天和的长孙刘守有很自然的获得了荫叙,成为锦衣卫千户⑤。目前难以查知刘守有确切的出生年份,但他的祖父刘天和出生于1479年,且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出生于1560年。亦即在1479—1560的81年之间,先后有刘天和、刘澯、刘守有、刘承禧四代人出生。据此推算,刘家的代际间隔平均为27年,这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据此推算,刘守有的生年当在1533年左右,尽管这一生卒年肯定存在一些误差,但可以确定的是:刘守有在孩提时代便已经具有锦衣卫千户的身份。
在诗书传家、父祖皆为进士的良好家庭氛围熏陶下,刘守有显然具备了良好的政治素养,加之又早早具有锦衣卫千户(正五品)这样的仕途起点,因此在他步入政坛后很快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关于刘守有的快速升迁,沈德符(1578—1642)认为这和当时的权相张居正(1525—1582)不无关系。其称:“今上,江陵在事,以同乡麻城刘太傅守有领锦衣,寄以心膂”[3]535;“刘故大司马谥庄襄天和之孙,为江陵牙爪,故特擢之。”[3]536
沈德符作此论断并非没有根据。第一、麻城刘氏与荆州张氏的籍贯同属湖广行省,在颇为看重乡谊的明代,难免让旁观者对两人的关系有所联想。第二、嘉靖朝内阁首辅徐阶(1503—1583)的长孙徐元春(1547—1596)“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3]284从此刘家与徐家成为姻亲,刘守有也籍此成为徐阶的家人。而徐阶对张居正又有知遇之恩⑥,张居正对此颇为感怀,即使是在其日后身居首辅时,仍对早已致仕的徐阶保持应有的尊崇⑦,即使张居正对刘守有没有过关照,但至少没有理由对老上级的姻亲加以为难。第三、刘守有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异常谦卑,时人称“(张)居正广制吴妆绮绣,奇器宝玩,以进上及慈宁宫,所费颇巨。而锦衣缇帅刘守有受役如奴客,为之收敛织作矣。”[4]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刘守有对张居正的百般迎合至少不会让张居正过分厌烦。第四、刘守有对张居正的政治盟友冯保(1543—1583)也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尊重。据时人称:“缇帅体甚隆,与东厂并重……而并列共事,无低昂也。刘守有每谒首珰,必叩头。”[3]537对此,冯保作为司礼监太监,也很是受用。
尽管刘守有与张居正有如此之多的联系,但目前并未发现张居正对刘守有给予过分关照的直接证据。万历二年(1574)刘守有巡视会试时,其职衔是“昭勇将军、锦衣卫管卫事署指挥使”,以正三品的散阶,排名锦衣卫长官的第二位。但这种陞擢却很难跟张居正扯上关系。因为从刘守有荫叙锦衣卫的身份开始到万历初年巡视会试时,时间跨度已达30年左右,这种升迁速度并不算格外离奇。可供参考的样本是徐元春的儿子徐有庆,“未冠,袭世职,积资至三品”[5],可见通过荫叙入仕的官员经过长期的年资积累,享有三品散阶的情况在当时不足为奇。万历五年(1577),刘守有再次巡视会试,其职衔和在锦衣卫系统内的排名一如三年之前,并未取得任何仕途上的“进步”。直到万历八年(1580),刘守有的老上级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余荫卸任之后,刘守有才循资升任“昭毅将军、锦衣卫掌卫事署都指挥佥事”,排名锦衣卫长官的第一位,这与沈德符所说的“特擢”相去甚远。然而同属锦衣卫长官,余荫的官至是“都指挥使”、刘守有不过是“署都指挥佥事”,其中的差别仍然深可玩味。
尽管刘守有很难说受到过张居正实质性的关照,但在张居正倒台后却仍被朝臣目为张居正的余党而时常遭到牵连。沈德符即认为:“时掌锦衣麻城刘守有,故江陵所卵翼,驯致贵显,惴惴虑株连波及。”[3]464张居正去世后不久,刘守有奉旨前去抄家。很快御史毛在(万历二年,1574进士)便弹劾刘守有在奉旨抄家的过程中“搬运鼠窃,报官者十一二耳。至房屋、田产,公行欺隐。各犯家属浼张照等,转为方便。党恶欺君,何以自解?”[6]2556在接到御史对刘守有、张照等人的指控后,万历皇帝的处分明显有轻重之别。对于给各犯家属提供方便的张照等人,一概革任闲住;而对刘守有却不过是诘责称:“逆犯财产,还著尽心稽查。如再有容隐脱漏,定行重治。”[6]2556一般而言,大臣受到弹劾,理当主动请求避事待勘,然而万历皇帝丝毫不以为意⑧,继续让刘守有原任管事,从圣谕中不难看出万历帝对刘守有的眷顾正隆。7天后,御史陈性学(1546—1613)继续“陈(刘)守有通赂、卖法七大罪”,皇帝仍不过是责令“刘守有著痛加省改,遵前旨供职。”[6]2561而且在稍后的春闱之中,刘守有以“荣禄将军、锦衣卫掌卫事、左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的身份巡视会试,此时已经跻身从一品的大员[7]。
次年7月,御史刘一相(1542—1624)继续弹劾刘守有在抄家过程中藏匿张居正家产之事。在御史锲而不舍的弹劾下,尤其是将刘守有和张居正捆绑在一起的情况下,万历帝对刘守有的态度终于有些许改观,并谕令内阁拟旨罢黜刘守有。当时的内阁辅臣申时行(1535—1614)等人抗奏称:“窃见(刘)守有敬慎无过。张简修擕金宝潜匿其家,事属风影。……守有遽难议罢。”[6]2937据清人的说法是万历帝“重违大臣意”[2]6143,因此刘守有在当时并未受追究。但实际恐怕却并非如此简单。其时,与刘守有一并因张居正之事而受到弹劾的还有刑部尚书潘季驯(1521—1595)、吏部侍郎陆光祖(1521—1597),其结果是潘季驯削籍[2]6145,陆光祖调任南京[2]5892。然而刘守有不但未受冲击,反倒在5个月后升任左都督并提督巡捕[6]3016,成为正一品的高官;又过6个月,“加太子少保”衔[6]3099,最终位极人臣。可见在张居正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刘守有仍然极受万历皇帝的信任。其原因应当在于刘守有“与政府及厂珰张鲸交结用事”[3]536,申时行作为首辅、张鲸作为司礼监太监时常在皇帝左右进言,为刘守有营造了非常宽松的政治环境。早先弹劾刘守有的御史刘一相就是因此事而遭“执政者”所忌,被排挤出任陇右佥事,最后死在陕西副使任上,断送了大好的政治前途。
万历十六年(1588),刘守有已经在锦衣卫都指挥使的任上做到了第六个年头。这年11月,御史何出光(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上疏弹劾司礼监太监张鲸和锦衣卫都督刘守有“相倚为奸,专擅威福,罪当死者八,赃私未易缕指。”[6]3987然而,这一次刘守有却未能继续延续之前在仕途上的好运。神宗下令:“张鲸策励供事,刘守有革任。”[6]3987张鲸是早在万历帝尚在东宫时便已鞍前马后服侍的旧臣,又在扳倒冯保的过程中出谋划策⑨,因此神宗对其深信不疑,不忍将其罢黜。如果张鲸继续掌权,尚有庇护刘守有的可能。然而张鲸在当权时的作为并未受到当时朝臣群体的认可,因此在神宗做出“策励供事”的决定后,“九卿大臣科道等官,联章论劾。”[8]就连内阁首辅申时行也加入到反对张鲸的行列中来[6]3992。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最后不得不罢免张鲸,而刘守有的仕途也随之走到尽头。
不难看出,刘守有虽然长期在锦衣卫系统内任职且享有极高的政治待遇,但究其本身而言,却对朝中包括皇帝、权相、权宦的强权势力有着极强的依附性。尽管刘守有善于利用在锦衣卫系统内任职的特殊身份与朝中其他大臣的建立广泛联系,而且也曾一度左右逢源的游走与内宦和外臣之间,但锦衣卫官员乃至首领的职能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可替代性,如果丧失了皇帝的信任或是权臣的关照,便很难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在张居正时期,刘守有可以平流进取;在张鲸和申时行的关照和皇帝的宠信下,刘守有得以平步青云;而在圣眷日淡和所依附的权臣失势后,刘守有尽管身居一品、身处近密,也难以经受得住言官的弹劾,不得已退出政治舞台。
然而刘守有在仕途上的一度成功,竟使得时人对锦衣卫职官的看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守有之前,世家子弟如果能够考上进士,经常会愿意主动放弃业已取得的荫叙身份[9],诚如清人所论“锦衣卫(官)……文臣子弟多不屑就。”[2]2339例如于谦(1398—1457)之子于冕“荫授副千户”,尽管曾因于谦的冤狱而受到牵连,但是在获得平反并有了复官机会后,却“自陈不愿武职”[2]4551,⑩。但在刘守有之后,这种情况为之一改:“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其后皆乐居之。”[2]2339锦衣卫职衔的职衔从此被视为官场升迁的终南捷径,“世家子孙,求绾卫篆……以至明攻暗击,蔑人闺门”[3]536,为争夺锦衣卫的身份而无所不用其极,得之便如一步登天。后来的世家子弟将刘守有的成功经历视为官场上奋斗的目标,认为是锦衣卫的身份促成了刘守有的成功。但明代任职锦衣卫的官员也并不稀见,为何刘守有却可以成为其中的翘楚?除了对权臣的依附外,刘守有的成功是否有其他的踪迹可寻?
三、刘守有在锦衣卫任上的行政作为
锦衣卫兼具执法与司法的双重职能,“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2]1862尽管清人对明代锦衣卫的评价趋向消极,认为“(明锦衣卫狱)幽系惨酷,害无甚于此者。”[2]2335但难以否认的是:锦衣卫作为维护明代皇帝独尊地位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皇帝意图的坚决执行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刘守有在任职锦衣卫期间,也大体按照既有的制度规定来履行职能。
就缉捕言之。“锦衣旧例有功赏,惟缉不轨者当之。”[2]2340可见锦衣卫官员的封赏与是否有效执行皇帝的缉捕意图密切相关。在张居正和冯保先后倒台后,刘守有作为锦衣卫都指挥使两度奉旨前去抄家,《实录》记载:“锦衣卫都督同知刘守有等,抄没犯人冯保并伊弟侄冯佑等及张大受、徐爵等家财,金银睛碌、珠石帽顶、玉带书画等件,并新旧钱,各色蟒衣、纻丝、绢无筭。”[6]2575而在抄家之后,也确实步步高升。
就刑狱言之。在对冯保进行抄家时,惜薪司太监姚忠贪占冯保之侄冯邦定的财产,其表侄邓勋知晓此事并要求均分贪墨财物,姚忠指令锦衣校尉马禄将邓勋殴打致死。事情败露后,“南城黄御史关行锦衣卫拘提”[6]2561,可见锦衣卫有权对内廷一般罪犯进行拘捕传讯。但锦衣卫享有的这种三法司之外的刑讯权却一直遭受到广泛质疑。嘉靖时期,刑部尚书林俊(1452—1527)便上疏称:“内臣所犯,宜下法司,明正其罪,不当废祖宗法。”[2]2341但嘉靖帝不予采取。
关于刘守有侍卫皇帝的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但可以确认的是,除了履行制度既定的职责之外,锦衣卫也需要完成其他皇帝临时交付的其他事务性工作。刘守有在任期间,先后协助工部修建了武英殿、慈宁宫,并由此得到赏赐。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刘守有协助武英殿修缮工成,得到银币的奖赏[6]2731。万历十三年(1585)六月,历时两年的慈宁宫重建工程竣工,但花费不及往年修建的一半。万历帝因之龙颜大悦,加封刘守有太子少保并对其赐币奖励[6]3099。此外,从万历二年(1574)到十一年(1583)连续四届会试,刘守有每次都担任巡绰官。
然而,锦衣卫的身份颇为微妙。在日常履职时,他们以皇帝爪牙的面貌出现,因为直接服务于皇帝,所以经常会受到奖擢;但如果锦衣卫在执行皇帝意图时过于严苛而激起朝臣的强烈反抗,也很可能被作为皇帝“壮士断腕”的牺牲品。因此,如何在贯彻皇帝意图和实现自我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不少锦衣卫官考虑的问题。这就导致任职锦衣卫指挥使的官员“在处理一些政治案件中,对皇帝的旨意多是有保留地去执行,以至于在普通官僚阶层中保有较好的口碑。”[10]
刘守有也不例外。在他担任锦衣卫长官时有不少士大夫因事而遭到廷杖处罚,但刘守有在主持行刑时往往留下余地,使很多受到杖责的大臣性命得以保全。早在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适台臣傅应桢、刘台等,以劾江陵逮问,赖刘(守有)调护得全。”[3]535张居正因为“夺情”事件而遭受多次弹劾,“五君子先后抗疏拜,杖阙下。亦赖其(刘守有)加意省视,且预戒行杖者,得不死箠楚。”[3]535时任上林丞洪某因为给其父洪朝选(1516—1582)诉冤而遭受廷杖,但洪朝选先前与张居正修隙,因此张居正希望借此机会将上林丞洪某杖毙。刘守有明言“杀人以媚人,我不为”[11],借故迁延行刑,使洪某得以保全。
刘守有的周急救困不仅保全了朝中大臣,也为自己赢得了美誉。在申时行之后担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1534—1611)盛赞刘守有称:“自门下典握禁兵,用儒饰将,府中不闻急步、疾呼……豪杰当事,作用断与书生不同”[12];时代稍晚的沈德符认为刘家“子孙贵盛不绝”[3]535正是刘守有宽松用刑的福报;即使是百年之后的清代人,也不得不称赞“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刘守有)力。”[2]2339尽管清人对明代厂卫的评价并不为高,但“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2]2329的情况并未在刘守有执掌锦衣卫时出现,时人对锦衣卫的态度也一度有所改观,以致出现了上节所论的那种功臣子弟争相求去锦衣职位的情况。毫不夸张的说:刘守有以一己之力,一度在短期内扭转了时人对锦衣卫凶残贪酷的刻板印象。
四、刘守有的仕宦交游
麻城刘氏之所以能够在明代成为当地望族,固然得益于刘家历代先祖的积累,但也离不开刘守有在京城为官多年构筑的交际网络。刘守有的社会关系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广泛与朝臣进行联姻,这种联系最为稳固;二是在锦衣卫任上时利用公务便利与朝中大员产生交集并加强联系;三是重视维护湖广乡谊的关系。
刘家的姻亲范围十分广泛,刘守有的岳父是曾经担任福建左参议的曾烶(嘉靖二年,1523进士),曾烶与刘守有的父亲刘燦结成儿女亲家,曾烶的长子曾梦麟娶刘燦之女为妻,而刘守有则娶曾烶的三女为妻,曾、刘两家可称是亲上加亲。而曾烶的另外两位儿子亦即刘守有的表兄,一位娶黄冈籍的金华知府汪文渊(嘉靖八年,1529进士)之女,一位娶麻城籍的琼州知府周思久(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之女[13]。刘守有又与前任首辅徐阶的长孙徐元春结成儿女亲家,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于兹不赘。除徐元春之外,刘守有之子刘承禧,还与麻城另一望族的成员梅国祯(1542—1605)之女定下婚约。梅国桢每到京师,作为亲家的刘守有“辄以羽林卫士给之,因得纵游狎邪。”[3]449梅国祯和他的亲兄弟梅国楼考上进士的万历十一年(1583),刘守有担任排名第一的会试巡绰官,尽管难以知晓刘守有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梅氏兄弟谋取便利,但刘、梅两家的交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刘守有去世后六年后,梅国楼还专门撰诗纪念并在诗前小识中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14],言辞极其恳切。此外,据冯梦龙称:“刘金吾(守有)有姻家为云间司李(松江府推事)”[15]186,可见刘守有利用姻亲关系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从中央到地方的巨大关系网。
刘守有尽管作为皇帝的侍卫之臣,但与朝臣也过从甚密。如前所述,先后在朝担任内阁辅臣的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等与刘守有都有过交往,沈德符即称:“(刘守有)与江陵、吴门(申时行)二相相昵,而好文下士”[3]449,如前所述,申时行在刘守有遭遇弹劾时对其伸出过援手,王锡爵更是对其褒奖有加。刘守有不仅在对朝臣进行廷杖时手下留情,在同僚遇到麻烦时也经常扮演周急济困的角色。吏部尚书王国光(1512—1594)欲为其子觅一经师却久而未得,转向刘守有求助,刘守有随即安排梅国祯与其宴见,王国光之后在公开场合声称:“梅大(国桢)将来名位,未易涯也”[16],可见其对刘守有引荐的老师非常满意。兵部尚书凌云翼(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受到弹劾时,其长子凌廷年在锦衣卫系统内任官,刘守有作为部门长官“以僚谊贷之数千”,而在不久之后,仅仅因为凌氏父子的一次招待,“刘为(之)焚券而去”[15]185,这些行为毫无疑问为其在同僚中积累了口碑。
除了与姻亲和朝中大员密切联络,刘守有还特别注重“好文下士”[3]449,王世贞(1526—1590)、屠隆(1541—1605)、冯梦龙(1547—1646)、汤显祖(1550—1616)等当时名重一时的文化官员,也都与刘守有有过交集,甚至私交甚笃。
王世贞在文集里回忆了一件往事。当其为官京华担任郎中时,“颇思寓目林泉园圃,以一畅其悰,而官贫薄,不能治游具。”[17]尽管如此,却一直对京城的韦园恋恋不忘。其后,王世贞外出任官长达20年才重回京城任职,而此时韦园也转归刘守有名下。在王世贞甫回京城之时,刘守有立刻邀请王世贞兄弟游览韦园,令其多年的夙愿得偿。此外,王世贞的胞弟王世懋(1536—1588)与刘守有也常有书信往还。王世懋仕途发展一直不太顺遂,而在刘守有得势后一再援引王世懋入京为官,尽管王世懋已无意于仕途,但却使用《易经》中“断金如兰”的典故来形容与刘守有的感情,对其畅述乡居生活和儿子的成长情况,并且鼓励刘守有“勉力善事圣君”,以书信内容言之,二者的关系应当不局限于官场上的客套。
刘守有与屠隆结交于京师。屠隆在写给学生周叔南的祭文中明言:“叔南丈人刘金吾亦与余厚善”[18]378。但二人的“厚善”绝非屠隆的学生同时也是刘守有的女婿这么简单。从屠隆写给刘守有的书信中可以知道,在屠隆初遭弹劾时,“明公(刘守有)一日三造不侫邸中,对长安诸公冲冠扼腕,义形于色”[18]546,其情况激烈到连屠隆都害怕拖累刘守有,而劝其不要再为自己争执。在屠隆离开京城时,正值其二子生病,刘守有将屠隆妻儿8口留在自己家中照顾;而屠隆冬日出京,受阻与潞河一带,刘守有更是“馈饷不絶,又为治千里装。”[18]546刘守有对士人的关照一至如此。
刘守有与汤显祖同样过从甚密。汤氏在《答陈偶愚》中称:“弟孝廉两都时,交知唯贵郡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昆季,即思云(刘守有字思云)爱客,亦自难得。”[19]可见早在汤显祖声名未显时,便已与刘守有结交。而在汤显祖初入仕途时,刘守有也给予他极大的帮助。汤氏在其诗中称:“灸肉行觞深夜留,锦衣重复敝貂裘。新丰满市无人识,欲傍常何问马周。”[20]903可见刘守有对他的关照,绝不是吐哺食之,推衣衣之这么简单,更是常向其介绍京城人脉,便于汤显祖快速融入当时的士人群体。无怪乎在刘守有去世后多年,汤显祖仍写信怀念称:“幕府才华千古尽,锦衣人地一时无。曾同吊屈今埀老,犹自招魂楚大夫。”[20]741结合刘守有与王世贞兄弟、屠隆、汤显祖等人的交际,可以发现刘守有不光是“好文下士”,而且还实实在在的给予了当时众多官员、文人以帮助,无论这种行为是发自内心抑或是沽名钓誉,但给当时诸多文化官僚提供了便利却是不争的事实。无怪乎时人对刘守有的评价颇高。
同乡之谊也是明代士人构建社交网络时非常看重的因素,尽管与前述的姻亲和僚友之谊而言,对官员的帮助可能并非那么直接。如前所述,同属楚人的张居正,似乎对刘守有仅仅只是不过分为难,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二者的交好,但张居正的江陵后进“公安三袁”与刘氏家族的交谊却常见与三袁的文集之中。此外,王世贞在为刘天和撰写的墓志中明言:“公有子四,其三皆先卒,最后澯,最贤,而又继卒。诸孙幼,以故公殁十六年,而门人大司马刘公采,始克具状。”[1]406可见即使在刘天和去世后16年,子亡孙幼之时,同乡后进担任南京参与机务兵部尚书的刘采(1500-1573)仍不忍其功绩湮没,亲自为其求取墓志铭。可见同乡之谊对刘守有的仕途帮助虽不直接,但也让刘守有在政务之余感受到一丝温情。
总的来看,尽管在《实录》寥寥数条的记载中,刘守有更多是循规蹈矩的完成皇帝抄家、缉捕的指令,给人所谓“朝廷鹰犬”之感,但这本就是制度规定的锦衣卫职责所在;出于职掌的原因,刘守有不可能离开所处的职位而肆意妄为。但结合与刘守有有过切身交集者的记载来看,刘守有的形象绝不至于恶劣,甚至可以说是明辨是非、气节高尚的名门贵胄。作为理当只对皇帝负责的锦衣卫,刘守有却能在皇帝、宦官和朝官中斡旋自如,尽力周济士大夫,并且广泛结交文化名流,与过往刻板印象中的锦衣卫形象绝不相同,以致于清修《明史》都能给出“名臣子掌卫,士大夫……颇赖其力”[2]2339的盖棺定论。
五、结论
本文主要对明代湖北麻城进士家族的一员——万历时期锦衣卫长官刘守有的家族背景、仕宦履历、为政梗概、生平交游进行了初步探究。尽管刘守有出身于麻城望族,但是在其祖父刘天和去世后,刘家香火难继,加之刘燦官位不显,刘氏家族的势力一度中衰。但是经过刘守有十数年的努力,刘家在明代后期再度显赫,维持了麻城望族的家族身份。刘守有的成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坚实的姻亲网络,如前述的徐阶家族、曾烶家族、梅国祯家族等;二是广泛的士人交游,如前述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王国光、凌云翼等人,无一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僚;三是注重个人形象的塑造,通过和王世贞、屠隆、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人的交流,刘守有无疑在掌握舆论权的文化人中获得了口碑。刘守有在担任到锦衣卫最高长官后,积极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促成了时人对锦衣卫观念的转变。因为历史、文化等各种原因,加之现时影视作品的塑造,每每谈起锦衣卫,总会给人颇为消极负面的印象。但通过对刘守有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锦衣卫的形象并非完全没有一丝亮色,锦衣卫的身份不仅是良好的晋身之阶级,而且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兼济天下,乃至在一定范围内引领政治风气的变化。
注释:
①张金奎.八十年来锦衣卫研究述评[J].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1)30-36.
②刘天和墓前碑上有碑文:“钦赐,荆湖鼎族,大执金吾,海内名家,清华望第”。
③据《麻城县志》载:“刘璲字士约,训之孙,弘治庚戌进士。知丰城县,恺悌果断,兴学育才。县好淫祀,首毁之,以正民俗。自守狷介,不私一钱。征敛有方,奸猾屏迹。述职为江右第一。”见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M].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718.
④考诸明朝对于荫职规定:“大臣恩荫武职,必须世嫡或嫡长子孙别有职事,方许次房借荫。次房亦有职事,方及再次,待后身终及应替日,仍还嫡长子孙世袭。若一家二荫或原有世职,则以职大小为序,职大者与长房,次者与次房。”当刘天和得荫职赏赐时,刘滐已经在任,已有职位了,因此他不承袭其荫职是有可能的。参申时行,等.大明会典[M].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0.
⑤据《黄州府志》载:“刘守有,以祖天和袭锦衣千户”,见邓琛.黄州府志[M].清光绪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667.
⑥早在张居正初中进士之时,“徐阶辈皆器重之”;而在徐阶取代严嵩(1480—1567)成为首辅后,更是“倾心委居正”,以致于在嘉靖皇帝驾崩前后,徐阶、高拱、张居正身居内阁,“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分别见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4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639.
⑦万历七年(1579)江南地区发水灾,徐阶写信询问张居正为何迟迟不下发蠲免钱粮的命令,张居正耐心回信:“兹不敢徒用镯免存留,虚文塞责,以重得罪于元元也。”徐阶的信函,见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M].续修四库全书第16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2-543.张居正的复疏,见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79.
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万历帝对刘守有将抄家所得据为己有的说法并不相信。第一,刘守有本身就属世家贵胄,很难有贪图蝇头小利的动机;第二,无论万历帝或刘守有事先都很难知道抄家的实际所得会有多少,更毋论处于信息边缘的言官群体。如果万历帝以“莫须有”的名义指派刘守有强制征收物件,事后才发现诬枉,显然有损君王和大臣之体面。综合考虑之下,万历帝对这一弹劾视而不见。
⑨“东宫旧阉张鲸、张诚间乘陈其(冯保)过恶,请令闲住。”见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03.
⑩关于明代文官荫叙的问题,可参秦博.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J].史学月刊,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