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凛冬李西闽战胜了抑郁症
杨楠

图/受访者提供
遇到李西闽是在一个聚会上,他当时正在说自己对抗抑郁症的经历,说过去八年都在与魔鬼搏斗,如今终于能与魔鬼和平共处。他说得激动,仿佛这是他人生最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他曾经在部队服役,后来以写恐怖小说为业。他在汶川地震中被埋76小时,不吃不喝不能动弹,靠着求生欲和意志力等来了救援。后来他写了长篇散文《幸存者》,获颁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
“当初,以为获救后一切都会随风飘散,没有料到,活下来的总是被噩梦缠绕,比以前更加胆小。有点风吹草动,内心就瑟瑟发抖。特别是独处时,恐惧感就像潮水将我淹没。……我摆脱不了噩梦,我就是站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仿佛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那些生命中的色彩似乎和我无关,难以照亮我黑暗的心灵。活着,很无奈,也很愧疚……我背负着来自许多不同方向的压力。”他在《幸存者》的前言中写道。
对抗抑郁症是件大事,其中的艰难与勇敢甚至超过了被埋的那76个小时:因为痛苦太漫长了。他写了三本和抑郁症有关的书:《救赎》、《凛冬》和《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获救后三年,李西闽都认为自己的心理创伤是灾后正常情况。他不敢坐地铁,轰隆隆的声音让他想起地震时地底传来的轰鸣声,心脏憋得要爆炸;他时常感到旧伤疼痛,随身携带止痛片,钢筋曾经穿过他的肋骨;噩梦连连,地震发生是一瞬间的事情,来不及反应,但梦境越来越清晰:石头是怎么砸下来的,钢筋是怎么穿过身體的,还有声音,钢筋和肋骨摩擦,与磨牙相似;他在梦中焦渴,饥饿,有时发不出声音,有时又在呐喊;他感到孤独和内疚,为什么是自己活下来了,自己活下来和别人活下来又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社科院心理研究所一篇题为《汶川地震幸存者的创伤应激障碍及其影响因素》的论文通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30-40岁的已婚幸存者更可能产生创伤性应激障碍,表现为高程度的创伤性事件闯入(记忆闪回、噩梦等),更高程度的创伤表现是对创伤性时间线索的回避(比如不敢坐地铁,不敢看地震相关信息)。这一研究结果与国际主流研究结果相似,学者普遍解释,因为中年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就业、家庭需求和重建家园等各方面压力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创伤。
地震发生时,李西闽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和睦。他靠着回忆妻女、父母兄妹,还有朋友和仇人度过了那76个小时。他想,如果能活下去,名和利对他都不重要,能得什么奖,书能卖多少册,都不再重要,只要能活下去。
这一切确实不再重要。李西闽住在上海徐家汇附近,他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么真实,有呼吸,有声音,有行动。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年迈还是年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假如我死在废墟中了,这些景象就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眼帘中了,我会渐渐地被人淡忘,就像从来没来过。活着的人了解到的只是死亡数字,而大多数死难者的名字无人提及。”李西闽说。眼前是繁华,但他想到了川西的废墟。他不敢落泪,因为他是个幸存者,没有权利悲伤。
越来越糟糕了。噩梦惊醒后,李西闽独自坐在客厅等待天明,被埋废墟的每一分钟在眼前走马灯般重现,泪流不止。有时站在阳台,35层高,眺望广袤的远方,李西闽身体会突然战栗,生出一跃而下的冲动。身体里好像出现了魔鬼,魔鬼对他说:李西闽你这样活在噩梦中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死了就不会有噩梦困扰,一了百了。
李西闽把《幸存者》的版税捐了出去。他越来越顾家。玉树地震后他自带物资前往灾区救助——为了救赎自己。他想做一些事,证明自己活下来是对的。“那段时间都是靠价值感支撑,靠良心支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帮助别人就能解脱我获救的负罪感。汶川的时候,那么多人在找我,那么多战士一起把我挖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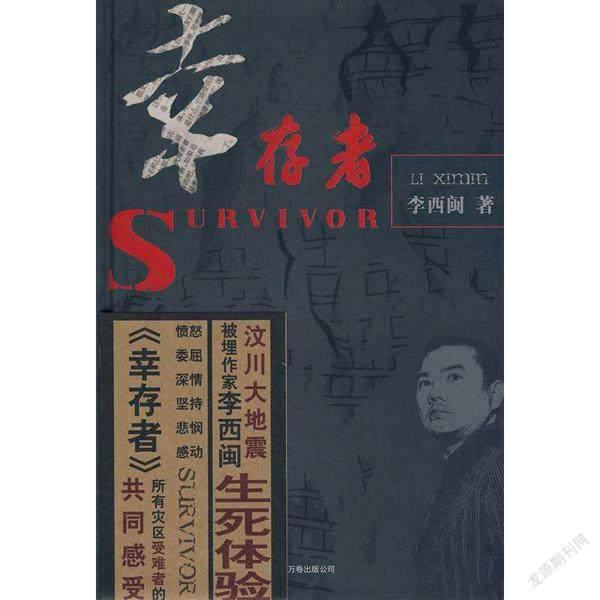
但玉树之行却成为对李西闽的一记重击。有些好事需要克服巨大的外界阻力去完成,你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做好事,却要遭遇那么多怀疑和误解,这让人感到沮丧。在玉树,魔鬼一点点啃食李西闽身体里的光亮。“震后的灾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充满了黑暗的情绪。玉树下暴雨,晚上很冷,整个玉树的狗都在叫,越叫我心里越凄凉,感觉好像死去的魂要出来了。”
离开玉树后,他回了老家。噩梦还在继续,只是梦境的主角变成了女儿。他梦到女儿被人绑架,他却动弹不得;他梦到亲人被刀抵着,他却无能施救。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李西闽在福建长汀县的长汀宾馆吞食了过量安眠药。魔鬼对他说:你活着还有意思吗?你是个无用之人,你活着就是在浪费粮食,浪费水资源,浪费一切资源。你不仅在浪费,你还给你周围的人带来痛苦。你写的书也是无用的,浪费纸张,浪费印刷工人的精力,也浪费读者的时间。你真的一无是处。
李西闽再一次获救。在微博上,陈村、沧月等作家都在呼吁紧急找人。然后是出版人沈浩波发出消息,说警察找到人了,应无生命危险。李西闽在长汀县汀州医院洗了胃,然后直接去了厦门。他不敢回长汀宾馆,他再次觉得愧对所有人,包括长汀宾馆的服务人员。他发微博道歉,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如今,再次搜索这则九年前的小新闻时,媒体摘取的网友评论大多是这样的:“你难道不爱你的李小坏(李西闽女儿)了吗。你要抛弃她?你就不能替她想想?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看不起你”、“你真不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希望这一定是最后一次。你是爷们儿!”。
返回上海后,李西闽确诊了重度抑郁——一种往往被外界认为是内心懦弱的疾病,少有人知道这会让人感到绝望,无法摆脱自杀的冲动。
该怎么去形容抑郁症?在《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的序言中,中科院院士陆林说那就是一只如影随形的黑狗:“任何人看到都以为它是一只再寻常不过的动物,然而只有你知道这只黑狗的不寻常之处——它以摄取你的所有情绪为食。它时刻跟在你的身边,你所有想要向他人宣泄的情绪都会进入它的身体,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而它在吞食你的情绪之后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你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你的,你只知道自从发现它在你身边之后,你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暗淡无光、模糊不清。” 威廉·斯泰伦在《看得见的黑暗》中描述了亲身经历:所有的精神生活层面都因抑郁症而坍塌,所有的生命功能都丧失殆尽, “令人精疲力竭的争斗,本能的崩溃,无时无刻不处于疲惫中,自我嫌恶,一种类似但又并非真痛的感觉,倒霉晦气的感觉,可怕的着了魔似的不安,强烈的内心痛苦,扰乱身体机能的突发混乱,极端痛苦的漩涡、无法平息的痛苦、恐惧的浓雾中接二连三的苦难、抑郁的黑色风暴、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黑暗、绝望之外还是绝望……”
离开医院时,李西闽仿佛又有了活着的信心。他包里装了一些药,这是他对抗恶魔的武器。有些药他至今服用,比如劳拉西泮片,一种高效的镇静药物;比如阿戈美拉汀,一种调解神经中枢活动的药物。
他已经知道抑郁症和情绪低落的差别了。前者有个清醒的脑袋,后者整个脑袋仿若浆糊,昏昏沉沉,整个人就像发霉了一样,动弹不得。他习惯拉起窗帘,不是因为喜欢黑暗,而是要逃避光明,逃避可以看到的任何东西。折磨他的不仅是现状,还有过去。李西闽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但过往的困苦常浮现在眼前。李西閩出生于闽西最贫困的一个村子,穷得吃不起饭,地瓜渣滓都没得吃。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全村都饿肚子,“偷做种的甘蔗(甘蔗最硬的部分)吃,都发霉了,吃了中毒,送到医院抢救回来。”他想起爷爷。爷爷脾气暴躁,经常被家人训斥;下身瘫痪后,因为生病带来污秽,家人就让爷爷睡在外厅,紧挨着天井。李西闽陪着爷爷一起睡,自认为可以保护爷爷。“有一年春天,爷爷突然大口喘粗气,眼睛瞪圆,我记得很清楚,爷爷喘了八口气。他最后伸手摸了我一下,然后手就松开瘫下去,再也没抬起来。爷爷的愿望是一个人吃一只鸡,但最终也没有实现。” 还有外婆,李西闽想起在部队时,有天梦到外婆去世,他没信。次日跟着部队外出演习一个月,回驻地后,打电话回家,得知外婆在一个月前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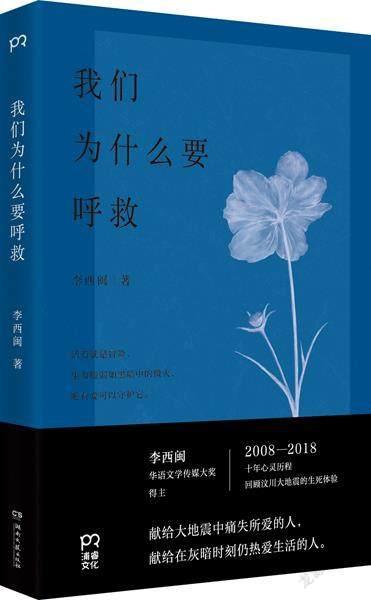
这些都让他充满负疚感,觉得自己有愧于爷爷和外婆,也对不起妻女。他早年嗜酒,经常喝得大醉回家。他已经为人父,却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必须有意躲着女儿。他想起这些痛苦,就会诘问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受苦受累。“自怨自艾,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惨的人,”他说。
负疚感是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一种情绪。他们对关心自己的人感到负疚,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能控制情绪。他们想要倾诉却又不敢,害怕被人说是矫情。他们会在心里审判自己,自己有愧于这个世界,对不起亲人、朋友、同事,乃至小区物业的保安。
因为在微博上讲述了自己的抑郁症,李西闽结识了一些病友。“互相搀扶,互相支撑”,他这样形容彼此的关系。对于旁人而言,他与病友的聊天记录就像是成群结队的摄魂怪,吸走人心的温柔与快乐:
“你每天也是脑子无时无刻想事情吗?停不下来,总是让你情绪糟糕。”“你有没有自言自语的现象,脑袋里总是想一件事还想不通。”“人生没什么意思,都是解决不了的麻烦接踵而至,那种被按下去水里的感觉,被淹没在水里,自己拼命想浮起来。”“我痛得快受不了了,胸口插着一把刀一样。”……
这些叙述会得到李西闽的鼓励:“活下去”、“一起努力”、“太难了,理解”、“以后心情不好和我说,我陪你聊天,我很理解。”……这些鼓励看起来有些单薄,但李西闽说,抑郁症患者其实并不需要安慰,有时候你越安慰,对方会越难过。“你只要陪陪他说话就好了,”他说。
对重度抑郁患者来说,自杀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意念。“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产生死的念头,那一刹那间要死就真死了,可是熬过那短暂的几分钟,又会回到现实之中,不想死了。”
李西闽已经找到了熬过那几分钟的方法:和朋友说话。在朋友的陪伴下,度过艰难时刻。而当他看到有病友发出这样的信号,他会打电话找对方聊天,甚至曾经赶往另一个城市,陪伴一个病友度过了一夜。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说的不仅是抑郁症患者要去呼救,也希望周围人能听到他们的呼救。那些极端的表达,是他们在求救的信号。”李西闽说。
李西闽不想死。几度濒临死亡之后,他突然明白死亡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生死之间就是一层窗户纸,伸手捅破就捅破了。
正因为死亡随时可能降临,活着的每一秒都是对死亡的战胜。活着本身就是在与时间对抗,尽管时间不可战胜。“小时候我想当个科学家,后来想成为作家。小时候想要走出穷困的土地,想要到广阔的世界里面去,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厉害的人。现在觉得成为什么都不重要了,活着是最重要的。”李西闽说。
2012-2014年是最坏的时候,李西闽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思考事情也费力。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见朋友,又害怕自己突然低落的情绪让人厌烦。他小心翼翼在妻女面前隐藏自己的低落,他害怕家人也会厌烦自己。每天送女儿上学后,他或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或是回家开着电视,都只是听个响儿而已,他记不得都放了些什么。
但有一天不同。那是2015年年末,他在电视盒子里翻到了电影《怦然心动》,他看见了森林与阳光,他感受到了温柔与爱情,他看到了闪亮的眼睛和鲜艳的个性。
“脑海中就好像有一阵春风吹过,春天来了。我一下就跳起来,去书房打开电脑,想写点东西。虽然一个字都没写出来,但我很想表达,注意力一下集中起来了。”第二天,李西闽开始写作,写了一个中篇散文,尽管写作速度是以往的三倍慢,但他写完了,他终于再次完成了一件事。“我真的很兴奋,那天写完之后突然发现我还是可以的,我得到了自己的一个肯定。”李西闽说。这之后他开始写《凛冬》,写一个抑郁症患者阿牛的故事,他寻求自身的解脱,也在帮助别人。
李西闽知道自己能好起来。他开始强迫自己每天出门一小时,寻找被抑郁症磨掉的感受力。“晒晒太阳,看到外面的人啊,植物啊,都是在向我传达信息。”外界的细小变化刺激着他,他发现自己还能感受到生活,他还能做些事情,他没有静止——只有死亡才是静止。
他依然会失眠,但不再拉窗帘了。他渴望太阳快点升起,阳光能烤化结冰的血液,他能重新感觉到血液的流动。他知道他不想再死,他看到了阳光,听到了音乐,他想呼吸。尽管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课题,但他想死守住生命这份礼物。
女儿在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的爷爷说,只要活着,总会有好事发生。
战胜抑郁症正是从恢复对外界细微的感知开始。伊丽莎白·斯瓦多在《我的抑郁症》中回忆说:“如果你假装态度积极,没准会弄假成真,谁知道呢?每一次你都挺过一点点。尝尝番茄酱;听一只鸟叽叽喳喳地穿过你的窗户;耐着性子穿针引线;嗅嗅新的面霜;谢谢邮递员送来的新书目,然后一页接一页地读。渐渐地,小小的行动变成中等程度的行动:扔掉冰箱里的废物,关掉电视机,对着婴儿车里的宝宝做个鬼脸。它们发展成更大的行动力:和朋友一起跳舞,挠挠狗肚皮,随着街上扬声器里的音乐起舞……”
在另一本自述走出抑郁症经历的《十死换一生》的结尾,作者希瑟·B·阿姆斯特朗说她希望所有人身边都有愿意聆听自己、相信自己的人,“我更为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没能挺过去并从那个洞里爬出来的人而哭。我为那些深陷谎言怪圈的人而哭,他们深信这世界没了我们会变得更好。”
绝非如此。要相信这个世界没了你们,不会变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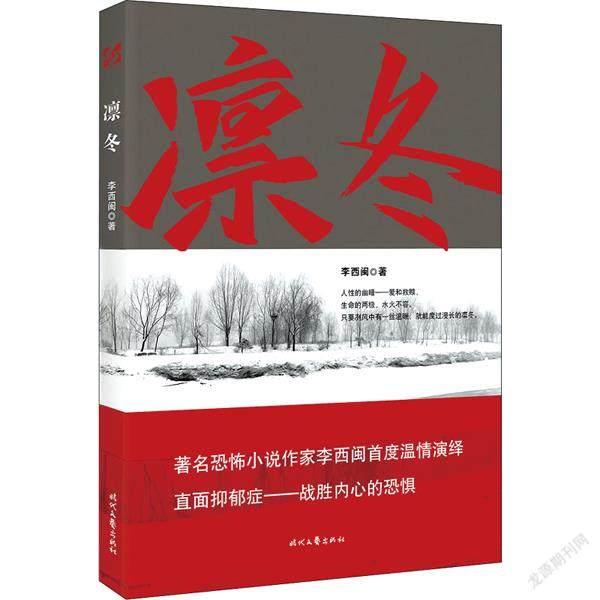

根據李西闽作品《救赎》改编的电影《灵魂的救赎》
李西闽在写《凛冬》时日渐好转,他把自己的感受一点点写出来,通过面对自己的感受,去消除恐惧。他还坚持吃药,坚持出门,鼓励自己与朋友相聚。而更重要的是,他在阅读了一些疗愈抑郁症的书籍后,选择了与抑郁症和平共处的方式。
“我觉得既然一下子治不好,我就选择和疾病和平共处,疼痛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发作也是正常的,我这样想心里就会好很多。”李西闽说。
就像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的那首诗《我允许》:“我允许我升起了这样的情绪/我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发生/任其发展,任其穿过/因为我知道/情绪只是身体上的觉受/本无好坏/越是抗拒,越是强烈/若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绪/伤害的,只是自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不断与脑海中的恶魔之声对抗,让李西闽身心俱疲。仿佛越对抗,恶魔就越活跃,大脑运转越来越快,好像要爆炸一般。“不要去战斗,不要去对抗,就让恶魔在身体里沉睡,或者做些别的事情,不去回应脑海中那些声音,与它和平相处。”他说。
当李西闽感觉强烈的情绪来袭,比如突然流泪,脑袋发晕,精神阴沉——好像身体里在下雨——他会立刻给朋友打电话,寻求外界支持。“当我度过极端情绪后,我就立刻行动起来。我会去吃药,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换一些音乐听,或者强迫自己走到街上去看看,接收路上每个人身上的亮光。当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你是黑暗的,但当你走出去,在街上看到有人对你笑一下,这就是一种能照亮你的光明。”他说。
重度抑郁症患者很难说自己是否已经痊愈,魔鬼可能还会出现。2019年,李西闽因为朋友的一则死讯,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抑郁中。为了不影响家人,也为了能疗愈自己,他去厦门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都是昏昏沉沉的,有四个月没睡觉,晚上一直睡不着,但也不清醒,很痛苦。”他甚至去私人诊所尝试了电击疗法:“每天下午去做一次,用电流刺激整个脑袋。到第三天的时候,我晚上就能睡三个小时了。到第十天,我觉得有点清醒了,我就不想做了。自从能睡着,人就开始慢慢恢复了。”
电击疗法是精神科常用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争议颇大,起效和副作用都十分明显。在《十死换一生》中,希瑟正是通过十次电休克疗法,打开了自己治愈抑郁症的开关。主动选择电击疗法的患者,往往是因为有着对治愈的强烈渴望,愿意尝试任何治疗方式,或是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永远爬不出泥潭,与这种恐惧相比,电击疗法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们想用一切,甚至用生命去抗击抑郁症。
赶走抑郁症是一件大事。这是一场与魔鬼的战争,要懂得作战技巧,首先要允许魔鬼存在,然后尽可能绕过魔鬼。如果迎面撞上,也要勇敢面对。目标是重组破碎的自我,找回丢失的魂儿,走出黑洞。
尽管赢得一场战役实属不易,但只要赢过一次,就能再次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