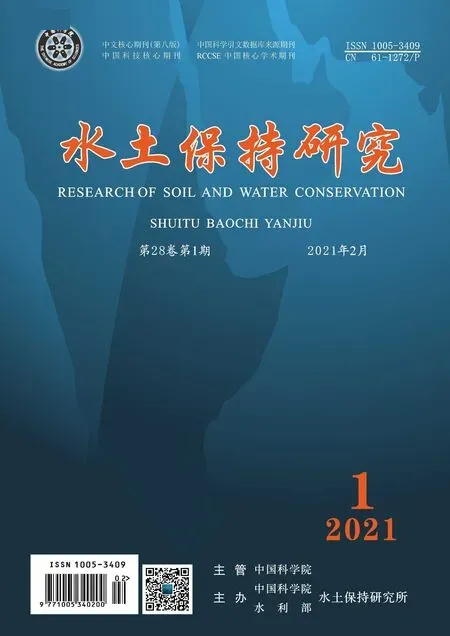基于景观格局的武汉市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
侯 蕊, 李红波, 高艳丽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生态风险评价是用来描述和评估人为活动、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大小的过程[1-5],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安全研究的基础。基于景观格局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则是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为诱因,直接从景观的空间格局角度来定量识别和评估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本底安全风险,成为当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领域的研究热点。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利用方式与程度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直接作用于土壤、大气、水文等自然地理要素,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6]。在人类活动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内,由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区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并能够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得以体现[7-8]。许多已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与生态风险密切相关,并对区域生态风险起着决定性作用[9-10]。景观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空间异质性且景观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元,因此景观尺度可作为研究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重要尺度应用于生态风险评价[11-12],目前已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研究。Paukert等[13]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结构角度构建了景观尺度上的生态风险指数。Ayre等[14]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对美国俄勒冈州森林景观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刘世梁等[15]建立基于景观格局和生态学过程的综合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对云南省红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进行分析。吕乐婷等[16]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对细河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评价。石玉琼等[17]将景观格局和植被生产力结合对榆林市景观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李青圃等[18]从“自然—人类社会—景观格局”3个维度对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上进行流域景观格局的优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在评价对象上既有流域[18-19]、行政区[20-21]、沿海区域等[22-23]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区域,也有农牧交错带[24]、水土流失地区[25]、自然保护区等[26]生态脆弱区域。在评价方法上大多基于风险源汇和景观格局两种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学者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27]。当前,关于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主要侧重于描述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特征方面,而将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变化相结合,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及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方面缺乏深入探究。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之下,面向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近郊区,区域内山水林田湖草各自然要素同样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由于近来年受快速城镇化发展影响,景观生态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区域面临生态风险升高的趋势。本文以武汉市江夏区为研究区域,以空间格网为评价单元构造基于景观格局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对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时空特征进行分析与评价,并进一步探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及其响应弹性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及提高生态风险预警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南大门,属于武汉“1+8”城市圈南部枢纽,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总面积2 018 km2,将近占武汉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地理位置114°01′—114°35′E,29°58′—30°32′N。地形以平原为主,属中亚热带过渡性湿润季风气候。全区水面面积约500 km2,境内共有大小湖泊23个,湖泊面积大约占武汉市所有湖泊总面积的50%。
“十三五”以来,江夏区以“生态立区、工业兴区、创新强区”为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武汉市南部生态新城,充分发挥江夏作为武汉市生态控制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作用。江夏区在近十几年来城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并由此产生山水林田湖草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和异质化,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面临失衡,生态风险增加。因此,以江夏区为研究对象,从景观生态格局视角下进行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评估对于江夏区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好地贯彻落实其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未来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利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下载的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在ENVI 5.2中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图像融合、图像裁剪等,并用最大似然法对4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07)将区域内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然后结合实地调研进行目视修改,并选取一定数量的验证样本采用混淆矩阵法进行精度评价,结果显示Kappa系数均达到80%以上,符合解译精度要求。最后得到分辨率30 m的土地利用分类结果见附图5。

2.2 土地利用变化度量指标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用来描述某一时间段内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面积变化情况的指标[28],以表现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程度及不同类型间、不同时段内或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情况。本文计算了2000—2015年不同时段内武汉江夏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及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以分析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1)
式中:K表示在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期末某一土地类型的面积;T为研究时段长度,通常以年为单位。
(2)
式中:LC为研究时段内区域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表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整体情况;LUi为研究起始年时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ΔLUi-j为研究期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其他类型面积的绝对值;T为研究时段长度。
2.3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评价精度,并将不同位置的生态风险指数值在空间上进行可视化表达,本文利用ArcGIS的渔网分析功能,采用等间距网格采样法,将每一网格作为风险指数评价的样本单元,对研究范围内进行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借鉴已有研究[21],渔网大小宜为平均斑块面积的2~5倍,本文划分2 km×2 km格网,得到581个生态风险样本小区,计算每一个小区内的生态风险指数值,并将其作为样本中心点的生态风险水平,然后利用空间插值得到整个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水平。参考前人研究[29-31],本文引入景观干扰度、脆弱度和损失度指数,通过指数间的叠加来构建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体系(表1)。

表1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方法及含义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3)
式中:ERIk为第k个生态风险小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Aki为第k个风险小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Ak为第k个风险小区的面积;Ri为景观损失度指数;N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2.4 空间统计学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研究某一空间变量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程度如何,因此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作为一种空间变量,可以对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以研究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全局Moran′sI和局部Moran′sI两种指标分别测度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和局部空间差异特征。
由于空间插值的前提是数据具有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本文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rcGIS的地统计分析模块采用指数模型进行半变异函数拟合,然后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得到4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值的空间分布,基于自然断点法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分成5个等级:Ⅰ低生态风险区(ERI≤0.1)、Ⅱ较低生态风险区(0.1
2.5 响应弹性分析法
弹性表示为因变量的相对变化与自变量相对变化的比值,揭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本文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引入弹性系数分析江夏区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特征[20]。计算公式如下:
(4)
式中:ERC表示T时段内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系数;ERIb和ERIa分别为研究期末和期初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LC为T时段内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3.1.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在土地利用分类图基础上汇总得到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表2)。整体上,江夏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水域为主,二者占总面积的80%以上。2000—2010年江夏区地类按面积大小依次为耕地、水域、林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草地,2010—2015年建设用地面积超过了林地面积。研究期内耕地不断减少,面积比例从63.03%减至57.04%,建设用地变化与之相反,面积比例从3.41%增至9.36%。草地和林地面积也在减少,但是变化幅度较小,水域和未利用地二者波动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表2 江夏区200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
3.1.2 土地利用速度变化 根据公式(1—2),计算得到江夏区每个时间段内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与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表3)。可以看出3个时间段内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均为最大,分别为9.39,2.65,13.00,且在2010—2015年扩张速度最快;耕地、林地、草地的动态度均为负数,表明三者面积始终减少,且耕地和林地在2010—2015年减少最快。3个时段内江夏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别为0.45,0.14,0.74,表明在2010—2015年这个时段内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类型间变化最为活跃。

表3 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3.1.3 土地利用方向变化 将相邻两期土地利用类型矢量图层在ArcGIS中进行叠加,并利用Excel的数据透视表功能计算得到2000—2015年江夏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4)。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化,耕地是土地利用主要转出类型,转出为建设用地10 699.67 hm2,占转出比重的87.83%;转出为水域1 347.79 hm2,占转出比重的11.06%。建设用地是土地利用的主要转入类型,其面积增加的来源类型多样,其中有88.49%来源于耕地,是建设用地最主要的转入来源。而草地、林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所有转移类型中,转出为建设用地分别占其转出比重的56.01%,79.17%,77.87%,61.14%。200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点表明随着江夏区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生态用地均存在转出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风险加大,人类生存环境将面临潜在威胁。

表4 200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hm2
将不同研究时段内地类转换面积较大的前6种进行提取并空间可视化。从分时段来看,耕地转出为建设用地一直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转移类型。2000—2005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江夏区的北部城区,由原来的中心区向东部及东北方向扩展;耕地转出为水域散落分布在江夏区的西部、东部及南部。2005—2010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仍向东部和东北部靠近洪山区的范围扩展,但与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建设用地扩展的范围与面积显著减小。2010—2015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大,而且扩展方向开始向江夏区的中南部、西部、东北部进一步延伸。从整个时间段来看,建设用地的转入来源类型多样且转移面积较大,北部建设用地增长规模较南部明显,庙山、藏龙岛、纸坊、金口为扩张较快区域。
3.2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3.2.1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分析 基于Fragstats和Excel软件,根据表1中所列公式分别计算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并进一步分析其变化规律(表5)。可以看出15 a来,各景观类型斑块数目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加,直接影响景观破碎度指数、分离度指数。建设用地由于面积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斑块数目增长速度,导致其破碎度指数、分离度指数不断减小,表明建设用地各斑块趋向于集中连片式发展,集聚程度增强、内部稳定性增大。耕地作为区域的优势景观类型其优势度指数最大,其他地类优势度指数变化不显著。从各地类所受干扰程度来看,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的干扰度指数较大且随时间递增,建设用地的干扰度指数随时间逐渐减小。从损失度指数来看,未利用地的损失程度最大,且表现为不断增大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未利用地的破碎度和分离度指数不断增大导致干扰度相应变大,另外,未利用地的脆弱度指数最高也是其损失度大的原因,建设用地由于近年来的规模化集聚扩张、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景观损失度减小。

表5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
3.2.2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特征 根据公式3计算得到各风险小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导入GeoDa软件得到Moran′sI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图1,图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I值看,四期Moran′sI值分别为0.486 4,0.493 7,0.485 3,0.509 8,值均为正数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集聚效应。从局部空间自相关的LISA集聚图看,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建成区中心附近林地、草地所在区域和东部梁子湖附近未利用地,建成区附近的林地、草地受外界干扰度大,尤其是建设用地的转入影响,破坏了原有景观的稳定性,使景观损失度增加;低值集聚区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西部、中东部,此区域以水域和耕地为主,受外界干扰程度小,低值集聚区在2010—2015年向东部牛山湖附近转移,集聚程度增强。总体来看,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强度整体分异显著,局部空间差异也在扩大。

图2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LISA集聚图

图1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Moran′s I散点图
3.2.3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布格局 将各风险小区中心点风险指数值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分布图(图3)。四期生态风险均值分别为0.117 4,0.157 0,0.163 6,0.190 8,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将近占研究区总面积的一半,2005年之后,较低生态风险区所占比重最大,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占比从2000年的49.81%下降到2015年的0.01%,而其余4类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均较2000年不断上升。

图3 2000-2015年江夏区土地利用各生态风险等级分布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低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风险区分布广泛,高生态风险区呈团状集聚分布在江夏中心城区青龙山林场附近与东部、东北、西南部分区域,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的“高—高”集聚区在位置上大致重合。此区域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分布较广,并且为追求经济发展,大量林地、草地开发成建设用地,破坏了原有景观的自身稳定性,景观受外界干扰易损程度大,生态风险升高。从整个研究时段来看,低生态风险区转为较低生态风险区是最主要的转换形式,还存在着高生态风险区随时间逐渐向外层推移扩大的趋势,表明此处风险升高较快,需要重点加强监管力度,防止其生态进一步退化,以维持区域环境的稳定。
3.2.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 分别将每一期的土地利用类型图与生态风险等级图进行叠加,统计汇总出每种土地利用类型下各生态风险等级所占的面积比例(图4)。2000年有92.8%的耕地分布在低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风险区,2015年下降到73.33%。林地、草地景观类型主要分布的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占比不断加大。水域景观主要分布在较低生态风险区,主要是因为其干扰度和损失度较小,所受生态风险较低。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较低生态风险区和中生态风险区,且随时间变化较高生态风险区和高生态风险区占比有减小趋势。原因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建设用地从无序零散状态向有序规模演变,系统内部稳定性提高,受人类干扰后损失度降低,导致生态风险的降低。未利用地2000年有46.8%的面积分布在高生态风险区,到2015年其比重达到65.5%,主要原因是未利用地干扰度、脆弱度和损失度指数均较高,且随时间呈递增态势,表明未利用地的生态风险系数不断提高,需要加强保护监管力度。

图4 江夏区2000-2015年不同地类下的生态风险变化
3.2.5 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分析 由表6可知,生态风险随着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在不同时段内其响应效果也呈现差异变化。3个时期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均表现为正响应,即土地利用变化造成了生态风险的增加,且3个时段响应弹性系数持续减小,表明研究区内土地生态系统风险水平趋于稳定,土地利用变化不再是作为区域生态风险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虽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耕地的大规模转出,造成江夏区内生态风险强度不断增加,但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却表现为不断减小,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因子由于更加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而趋于多元化。

表6 2000-2015年江夏区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
4 讨论与结论
(1) 研究期内,江夏区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应着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的变化。在2010—2015年期间,各地类间转移变化最活跃。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趋势相反,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15 a来共有8.41%的耕地转出为建设用地,且集中分布在研究的北部。耕地作为优势景观类型,对维持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景观生态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
(2) 4个时期江夏区全局自相关Moran′sI值分别为0.486 4,0.493 7,0.485 3,0.509 8,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正相关性增强,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局部自相关格局的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随时间推移其空间分布特征发生变化,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整体分异显著,局部空间差异也在扩大。
(3) 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处于较低等级。2000—2015年,较低、中、较高、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分别增加了32.6%,12.22%,3.37%,1.6%,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减少了49.8%,且高生态风险区在空间上呈团状集聚分布,并表现为逐渐向外层推移扩大的趋势,表明这些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较快,风险不断提高,需要对这些区域重点加强监管力度,防止其进一步退化,以维持区域环境的稳定。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整体呈增高趋势。
(4)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来看,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分布地区整体上受生态风险胁迫程度较轻,而草地、林地更容易遭受生态风险影响,未利用地所在区域的生态风险最高。从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系数不断减小可以得出地类变化对生态风险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减小,生态风险的影响因子更趋于多元化。
本文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背景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构建指标体系对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进一步探究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风险间的内在联系,为江夏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发现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近郊区与城乡融合发展区,近年来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使得大量耕地、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转出建设用地,原有完整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化,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受人为干扰后易损程度大,生态风险持续增大。按照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对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行为必须谨慎对待,严格控制城镇空间的无序扩张,确定城镇开发边界,以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为重点,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规模效应。加快落实“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将由耕地资源单要素保护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保护转变。本研究仅从景观格局角度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缺乏对区域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得到的结果不具有绝对性与代表性,但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研究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仍具有可行性。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应探讨影响生态风险变化的不同驱动力与多尺度下的生态风险评价,并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有效的生态管理建议,为指导区域“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供依据。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初级中学德育工作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