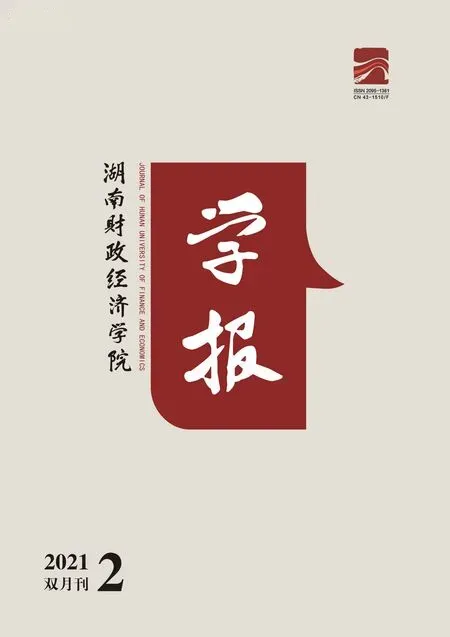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现实关切、接续理路与研究进路
——兼评贺雪峰教授《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胡伟强 余 华,2
(1.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一、引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两大重要国家战略,当前,我国正处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期和交汇期。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指出要“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1]。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吹响了“十四五”的奋斗号角,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面振兴”[2]。这表明,以脱贫摘帽为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主体战役转变为与乡村振兴相配合,已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务。
那么,在此背景下,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的现实基础、实践问题、接续理路及可能的研究进路是什么呢?“华中乡土派”杰出代表、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长江学者贺雪峰教授在其近著《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以下简称《乡村振兴诸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中,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从农村的社会结构、建设重点、土地制度、基层治理、村社集体等多个维度全面透视了当前乡村发展的实际境况,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转向、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着力构建解决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相互配合的贫困治理新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全书的论证观点鲜明、视角独特、切中肯綮,极具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是一部以全局视角解读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的经典之作。
二、把脉乡村从脱贫迈向振兴的现实基础
全面脱贫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农村?作者站在农民本位的立场,基于对当前农村现实境况的调查和阐释,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为我们勾画出了农村的真实图景,反映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长期坚持在农村调查第一线去思考与研究的学术积淀。
1.该书廓清了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书中作者开篇就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村地区的分化、农户的分化、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进行了精彩独到的剖析,认为我国目前已分化形成了至少三种不同性质的农村: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以及占全国农村70%以上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与此同时,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也分化形成了举家进城的农户、全家留村的农户、及占一般农业型村庄70%左右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3]农户,而农民个体不同生命周期则表现出年轻时进城谋求城市就业和收入,年长年老时或进城失败时就思虑返乡的不同逻辑。毫无疑问,这种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农户、农民个人生命周期所存在的剧烈分化和巨大差异,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
沿此问题深入探幽,作者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并由此指出了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3]及“中坚农民”[4]“老人农业”[5]的农村社会结构。显然,这是准确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都形成了“老人农业+中坚农民”[6]的结构,它是一个建立在集体经济和集体土地制度基础上,与村庄熟人社会机制相关联,保持村庄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结构。这是因为,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是必然的趋势,青壮年农民进城后的农村家户大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进城就有可能改变当前农村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格局,就有可能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出仅靠农业收入就可以维持体面生活的“中坚农民”。这些“中坚农民”主要是由在城市化中那些不愿意或无法离村的中青年农民构成,虽然目前在村庄中占比不高,但是作用很大,他们成为村干部的主要来源,而且“中坚农民”是从农村土生土长出来的,对农村有感情,同时也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乡村振兴的可靠力量。
2.该书明晰了乡村振兴的体制基础
作者辩证思考了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认为当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已经由之前的剥削型体制转变为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即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还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用农民宅基地,保留了农民返乡的退路。也就是说,为什么农民进城失败后可以从容返乡,继续过上不愁吃住的生活呢?正是保护型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条件,它不仅塑造了当前农村的社会结构,而且使农村具有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刻理解和思考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及允许农民可以自由返乡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农民就可以忍受进城的失败,就永远不会在进城失败中感到绝望,就能够获得身体、心理和生活上的安全感,就可以对未来抱有希望。也正是因为农民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才能够避免我国出现像其他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的大规模贫民窟和城市内二元结构等问题,才使中国具有强大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各种风险的能力,才使得农村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三、直面乡村从脱贫迈向振兴的实践问题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7]。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8]。贺雪峰教授在20多年的村治研究过程中,始终秉持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聆听时代跫音、回应时代呼唤、解决时代问题的学术理念,故此,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直面实践中的现实困难,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理性反思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种值得警醒的问题。
1.乡村振兴在地方实践中存在误判和急躁的问题
从时间维度看,乡村振兴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和总战略,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分为不同阶段,对此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信心和战略耐心。从空间维度来看,乡村振兴也有一个先后快慢的问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和区位条件较好,有望率先实现乡村振兴;而中西部刚刚脱贫的农村,乡村振兴必然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乡村振兴在不同地区的推进方式与策略也有不同,需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因地施策,边前进边摸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因此,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要立足于村庄实际,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产生出了两个有所差异的偏离方向:一是有些地方各级各相关部门普遍存在急躁情绪,激进地通过行政力量打造形式上的美丽乡村,既脱离了地方实际也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错将长远战略目标作为当下就能实现的战术目标,错将还需要经过三十年奋斗、到2050年才能达到的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当成当下就要达到的目标。另一个则更为普遍和严重,即在急躁情绪和政绩冲动的作用下,中西部的一些地方陷入“线性思维”窠臼,简单地照搬照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振兴的经验,采取“锦上添花”的策略,重点支持具有特殊区位或旅游资源的乡村,打造所谓的乡村振兴样板、美丽乡村样板,这在实际上加剧了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更为糟糕的是,在这种错误思维的导引下,无论脱贫还是振兴,一些地方均没有科学、准确研判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而是片面强调发展新业态,同质化地推进乡村文旅产业,却忽视了中西部农业型村庄产业基础薄弱、贫困户市场能力不足的现实,脱离了“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9]的“大国小农”[10]的基本国情农情,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还可能存在资本下乡发展产业剥夺小农机会和资源趋向优势区位农村而产生新的不均衡问题。
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实践中异化的问题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简言之,就是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其本质是城乡之间的一种建设用地指标置换的工具。其核心在于拆旧建新,即地方政府通过村庄整治腾挪出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并复垦为耕地,并由此形成建设用地结余指标,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在城市近郊征用等量耕地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从而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地矛盾,实现建设用地内部结构调整,节约集约用地并保护耕地,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但是,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却与上述初衷背道而驰,使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异化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增减挂钩作为压箱底的政策手段,不断拆迁农房、推进农民退出宅基地、促进“农民被上楼”[11],一厢情愿地认为其政策效果能够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能够筹措扶贫和建设资金。而实际上,其逻辑谬误在于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所产生的资金并不是生产出来的新财富,而只是财富的转移支付。更严重的是,这样做不仅歪曲了增减挂钩制度的初衷,而且还会造成农村资源的极大浪费,断掉进城失败农民的返乡退路,进而诱发城市贫民窟的形成,还可能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产生误导,冲击“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11],滋生出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者,丢掉公有土地制度的制度红利。
3.村庄类型和村庄管理体制错配的问题
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的乡村治理篇,作者开门见山指出,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11],而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村庄和城市化了的村庄两种类型,乡村管理体制则主要分为现代管理体制和传统管理体制,这样就形成了四种理想类型的匹配[11],不同类型的村庄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乡村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但是,这其中就包括传统村庄与现代管理体制、城市化了的村庄与传统管理体制两种错配,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的村庄与体制的错配模型却在村庄的治理实践中真实存在,即东部一些已经高度城市化了、工业化了的村庄其管理体制并没有与时俱进,吊诡的是,与此恰恰相反,中西部一些传统村庄却盲目照搬已城市化了的村庄的现代管理体制,而且这种用城市办法来管理传统农村的错配情况和错误逻辑最为普遍和常见,这就造成了治理体制高成本的空转,并衍生出大量的形式主义与资源浪费。
4.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和内卷化问题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以来,为防止扶贫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滥用,国家自上而下建立了极为严格和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比如扶贫数据库、扶贫台账、“回头看”制度、普查制度等,发挥制度和程序的威力,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基层干部进行权力约束,在此过程中,填报表格、办事留痕、保存凭证等各种自证清白的形式措施成为了基层干部应对复杂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法宝,并且在日常工作中占据了主要时间和精力。这样一来,原本应与村民群众打成一片,预留出更多时间去解决贫困群众实际问题的基层干部现在却疲于填表格、留痕迹、应付检查,逐步丧失了服务村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从乡村治理上看,这就出现了治理过程对结果的替代、治理手段对目标的替代、治理形式对实质的替代,这就会导致基层工作脱离农村农民的实际需要,这就使得乡村治理陷于空转和内卷化,并造成形式主义的不断抬头和久禁不止。同时,复杂制度在防止村庄权力寻租的同时,也导致村级治理中制度运作成本高昂,村务决策和执行因相互掣肘而效率低下,重大村务迟迟不能达成和执行,甚至可能造成村庄各利益主体利用复杂制度的无序斗争,及村级组织的瘫痪,并进而导致村级治理陷入困境和僵局,面临失败的风险。亦即作者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所谓的“复杂制度的悖论”[11]。
四、探寻乡村从脱贫迈向振兴的接续理路
如何促进乡村从全面脱贫迈向全面振兴?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在持续住村调查的基础上,从乡村振兴的逻辑场域出发,给出了可能的接续思路,提出了振兴乡村的可行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即,要坚定乡村振兴“三步走”的战略定位不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明确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和小农户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扶助对象和群体,搞清乡村振兴的建设主体与依靠力量主要是组织起来的“中坚农民”和低龄老年人,辩证看待乡村振兴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并发挥好农村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功能。
1.要坚定乡村振兴“三步走”的战略定位,绝不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
乡村振兴战略是世纪战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总体部署,乡村振兴分“三步走”: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目前,第一步任务接近完成,第二步已开始迈开,第三步要到2050年才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三步走”的战略定位很重要,正如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所指出的“振兴乡村必须立足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基础”[11]。当前最重要的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服从国家现代化战略总体部署,明确现阶段的乡村振兴还处在初级打基础阶段,不能激进冒进、盲目求快求全,如果急于求成,就可能犯浮夸冒进的错误。中央战略很清晰,就是要到2050年才能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就是说还需要经过六个“五年规划”的艰苦努力,才可能达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错将战略目标当成当下就可以实现的战术目标,就可能会遭遇失败。
2.要明确乡村振兴战略主要扶助的对象和群体
乡村全面振兴是个系统工程,应注意相关方面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应注意“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为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和小农户雪中送炭[11]。事实上,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地区的农村因为优越的区位条件,很早就实现了乡村的工业化,产业繁荣,农民财产收益较多,因而不是乡村振兴的建设重点。而与此相反相应的是,在利益稀少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集体经济缺失、村治资源匮乏、激励机制缺乏、村庄空心化边缘化严重、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薄弱,突出地表现为:农民的主要家庭收入在村庄之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村经济不活跃,农村人气也不旺,并且过度依赖政府投入,工商资本参与不足,市场化机制不充分,既无地利之便,又无特色资源,但却聚集了最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故而,一方面,从乡村振兴的扶助对象来看,当前乡村振兴面向的应主要是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上讲,只有中西部乡村得到发展,中国乡村才能全面振兴,全面小康才更加殷实。另一方面,从乡村振兴的扶助群体来看,重点不应该是乡村资本和大户,而应该是小农户,即要为能力比较弱、缺少进城机会、收入比较低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生产生活的保底条件,尤其是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农民和传统小农农业。质言之,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应当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3.要搞清乡村振兴目标的建设主体和依靠力量
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反复强调,乡村振兴要以亿万农民群众为主体,但这个农民的主体必须是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不能是单个的农民或个体农户[11]。换言之,就是说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组织农民,将自上而下的惠农资源、惠农政策的投入和供给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那么,究竟如何组织农民?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组织农民的最重要的主体力量就是“中坚农民”,他们是作为村干部的最佳选择,是乡村振兴的可靠力量,应当重点支持和依靠“中坚农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作者还分析指出,将农民组织起来,不仅要依靠“中坚农民”,而且还应当充分调动农村的低龄老年人的力量。在当前,中国农村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低龄老年人大都愿意返乡种田,在农业普遍实现机械化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不再是重体力活,农忙往往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他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若能将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就可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就可能形成低成本、高质量的应对老年化的中国方案,这也是积极应对“十四五”时期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探索。此外,组织起来的低龄老年人还可以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再造村社集体、构建村庄主导的治理机制,为农民提供生活的意义世界。
4.要辩证看待乡村振兴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发挥好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一方面,乡村振兴是以国家快速城市化、产业迅速升级为前提的。从城市化角度来看,只有当大部分农村人口进城且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少数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实现规模经营的时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才能实现。但是,当前的乡村振兴还处在初级阶段,农民虽然大量进城,但因为城市生活成本比较高,经济有周期,进城农民一般都会保留农村的退路。应当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返乡退路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好,而是因为在城市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不得不被迫返乡,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当中国完成城市化、实现现代化以后,所有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有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他们不再需要农村作为进城失败的预留退路的时候,城乡关系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农村就成为了城市生活的升级版,比城市更为惬意的“强富美”的乡村生活就是可能的,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三步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农村充当了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正是依靠农村这个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劳动力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竞争优势,也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故此,中国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才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综上分析,在《乡村振兴诸问题》中,作者强调指出,必须辩证看待乡村振兴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为进城失败的农民预留返乡的退路[11]。延此理路,作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保障农民返乡退路最有利的制度条件就是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中国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它们的功能与作用,以发挥农村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五、启发乡村脱贫与振兴衔接的研究进路
《乡村振兴诸问题》的价值不仅在于阐明了乡村从脱贫迈向振兴的现实基础、实践问题和接续理路,而且还在于书中所体现出的作者一贯所倡导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即坚持走向田野,用脚做学问,以村庄调查为基础,以实地案例为牵引,来理解和审视乡村社会本身。这对于政策部门“抓紧研究制定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意见”[12],和学界继续深化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1.要在呼啸着走向田野的过程中去探寻乡村脱贫与振兴衔接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感召下,全面脱贫高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亲自督战,全社会广泛动员、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与此相映衬,新时代农村反贫困与谋振兴的生动实践也展现出千差万别、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壮美图景,这无疑为我们进行理论创造、促进学术繁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那么,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才能认识和研究好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相关论题呢?《乡村振兴诸问题》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借鉴,书中作者关于社会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及组织再造等方面的诠释论证和核心观点均立足于长期调研的田野事实,以实地调查来反观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理论逻辑,并剥离和剖析出现实中存在的困境及成因,进而找寻可能的建设路径,演绎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概念与逻辑理路,这在事实上表明了坚持在农村第一线做调查的重要性。实际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教导我们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3]。为此,要探寻全面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可行路径,我们就需要先深入到热火朝天的农村实践中去,真正去贴近土地贴近农民进行充分的调查。也只有扎根中国乡土做调研,才能让学问走出书斋,切实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要在对农村社会基础的整体感知和把握上深化对二者衔接的理性认知
当前中国村庄已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农民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里人,农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传统治理逻辑也业已被突破[14]。“乡土本色”已然褪去,“后乡土中国”已经来临[15]。亦如《乡村振兴诸问题》为我们所呈现的那些日新月异的变革场景,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镇化和市场化大潮中,乡村社会结构剧烈分化带来村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准的参差不齐、差异迥然,中西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村庄“原子化”“空心化”和“三留守”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社会变迁与发展中出现的治理内卷化和扶贫领域出现的“精英俘获”等问题往往相互勾连。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大量惠农政策和资源的下乡,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也越来越强,对村庄治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切使得我们无法割裂开乡土社会基础巨大变化的客观事实而去探讨某一具体研究问题。故此,我们必须将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研究视阈放置在整个农村社会基础之上,从剧烈变迁的乡土社会自身寻求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和契机,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上予以审视、防止偏颇,也只有这样,制定和出台的两大战略有机衔接的政策意见或办法才能贯通理论与实践、落地并生根。
3.要在致力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加快对二者衔接的学术研究
《乡村振兴诸问题》延续了贺雪峰教授以往村治研究的特色,即强调在聚焦农村某一具体研究问题之前先呼啸着走向田野,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完整的,未经已有理论或常识切割的,面向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各个经纬的厚重经验质感,然后在对厚重经验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础上,尝试对具体研究问题进行一般性解释和抽象概括提炼,进而形成紧紧贴近中国农村实际的中层理论乃至一般化理论。这亦是作者20多年来村治研究中所努力倡导的——在饱和经验法、饱和经验训练及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经验的“大循环”和“小循环”,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抑或谓“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16]。在这里,笔者愿意说,如果我们希冀进一步深化和加快两大战略有机衔接的学术研究,那么华中村治学者所倡导的建立在饱和式调研基础上的饱和经验研究方法就值得重视和研习,只有从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的理论,理论才有生命力和解释力,也只有在沉浸式的经验质感中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才会散放出强烈的实践之光和学术之美。
六、结语
社会科学的理论思考不是书斋中的穷经,也不是学者间的玄谈,而必须要回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可以说,关切现实、关照经验是理论研究的职责所在和生命所系。《乡村振兴诸问题》正是这样一部紧密关切现实,结合实际寻找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上乘之作,全书广度与深度兼具、理论与实践并重,既体现为作者准确把脉乡村从脱贫到振兴的现实基础,立足于当前乡村实际的务实精神,又表现为作者直面乡村从脱贫到振兴的实践问题,走出书斋、走向田野、面向大众,回应时代疑问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态度。读完这本书,相信广大读者会和作者产生深深的共鸣,那就是,只有乡村振兴了,农民才能在农村过上有根的、有身体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的有情有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