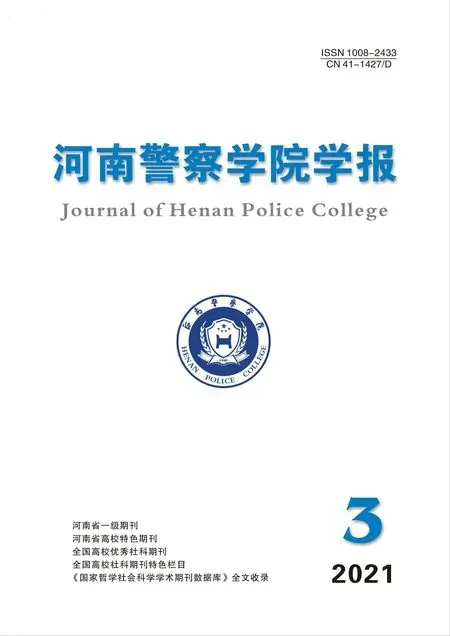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司法扩张与限缩解释
刘天宏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司法扩张类型
从“淘宝反向刷单第一案”开始,使用计算机网络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学者们认为,基于“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传统犯罪面临着网络化的新型挑战[1];随着新型案例在信息化时代的出现,传统时代中总结的概念与范围必定要发生变化[2]。具体来说,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罪在司法实务中有以下扩张类型:
第一,行为人利用淘宝平台交易规则,通过反向刷单方式启动淘宝处罚机制,导致他人店铺搜索排名被降权,该行为最终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这就是“淘宝反向刷单案”,也称“反向炒信案”。“反向刷单”就是自己或要求他人购买同行业竞争者的商品,并故意给予差评或故意给予好评,制造出同行业竞争者违反平台规定刷单的假象,从而触发网商平台处罚虚假交易的规定,使同行业竞争者遭受降级处罚的行为。本案最具争议的就是“反向刷单”究竟是否属于类似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破坏生产经营行为。法院在裁判中认为:“行为人基于恶意竞争之目的,以同一账号大量多次购买淘宝平台上某网商之商品,从而使得网商平台错误地认为该店铺行为属于虚假交易,极大地干扰到该店正常的营业活动且使得该店营业额大幅下降,其行为属于‘以其他方法’破坏企业生产经营。”(1)参见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2015)雨刑二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此判决一出,学界褒贬不一。有观点指出,南京中院的判决,第一次将恶意的网络刷单行为认定为犯罪,这不仅彰显和体现了法治的权威与力量,也反映了司法以民生为导向[3]。有学者认为,对破坏生产经营的“其他方法”的解释应当体现法益侵害的同类性,应该以法益侵害性质对“其他方法”进行解释,使其能够适应当下新时代的互联网犯罪特征并对其进行有力打击[4]。而持反对论者则担忧本案判决使得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被扩张,突破了刑法固有文义,违背了罪刑法定之铁则。如,有学者认为,“刑法不应当被视为惩治互联网犯罪行为的先行军。基于新兴的网络时代背景,破坏生产经营罪的严重扩张不仅有违反罪刑法定之虞,还会造成许多矛盾,其司法结论值得我们反思”[5]。
第二,网络中批量恶意注册的行为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理由是该种行为严重扰乱了互联网秩序。批量恶意注册主要指大量黄牛在12306网站上恶意注册账号用于抢票,从而使得12306平台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升级和改造;在微博平台上恶意注册批量用户账号进行“刷粉”,对用户造成严重的信息骚扰,扰乱了微博平台的正常运营秩序等。对这些行为,有论者认为,该恶意注册行为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其他方法”应当扩张解释。决定“其他方法”外延的并非是“毁坏机器设备”和“残害耕畜”,而是其后的“破坏”,即只要对生产和经营造成破坏就是“其他方法”,而不一定是对物的暴力[6]。
第三,恶意攻击商家网络经营平台,导致其商品下架或平台无法正常工作的行为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这种类型主要有:行为人利用 YY、QQ 等语音社交软件相继开启群聊语音房间并召集大量人员,通过远程语音方式煽动和指挥多人恶意购买商家(如,同一时间向天猫某一店铺集体恶意拍货,导致商品瞬间库存不足)、恶意提现支付宝资金和以骚扰方式攻击网商客服人员,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
此外,除以上三种较为典型和争议较大的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行为外,实践中还将利用网络进行流量劫持的行为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7]。还有论者认为,对网络水军(2)网络水军是指特定个人、群体或者组织为了操纵网络舆论而专门雇用的从事删帖、刷帖活动,在网络上造势的人员。在网络空间的恶意舆论造势行为,也应当用本罪规制[8]。
二、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司法扩张成因
(一)以社会危害性取代犯罪构成的结果导向定罪思维
刑法不应当成为单纯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的工具,但遗憾的是,司法机关在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旗帜之下,对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其他方法”进行了扩张乃至于类推。只要认定行为人造成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达到了数额标准或司法解释所要求的人数、次数标准(3)根据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入罪门槛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或者三次以上破坏生产经营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则直接认定行为人有罪。这便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在司法上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以社会危害性取代犯罪构成的判断,以结果导向取代行为导向。
这种以社会危害性为指导的结果导向定罪思维在实践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以“淘宝反向刷单案”的二审判决书为例,在二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犯罪的立案标准为50万元,而二被告人的行为很明显并未造成如此大的经济损失。”也即,二人的行为虽属于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行为,但因不具备该罪之损害后果,法院只能作无罪宣告。法官显然也意识到了反向刷单的行为并不一定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而是更加贴合损害商业信誉罪的构成要件。而翻遍刑法各条,法官发现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完全可以包含反向刷单行为,故而最终顺利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这种以社会危害性判断取代刑事违法性判断,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少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罪名的适用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以刑制罪、片面追求观感、迎合舆论民意使得本罪沦为第一大口袋罪。学者们均认为,对于“其他方法”应当严格按照同类解释规则进行解释,其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应当解释为与条文明示列举的放火、爆炸等方式相当,对公共安全存在高度危险性之行为,而不能随意理解[9]。然而,当面对破坏生产经营罪时,对于“其他方法”的解释仍然很宽泛。
(二)三段论倒置的演绎推理
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方法是大陆法系法官适用法律、书写判决书、得出结论的思维方法。法律条文为大前提,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刑罚或自由是结论。然而在实际处理案件时,三段论的演绎推理往往被倒置,这是法官以社会危害性判案,追求结果导向的必然结果。
以行为人为了泄愤报复进入他人网店平台,改低商品价格并销售他人商品案件为例。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先以本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出发点,以结果追溯行为,结果有严重危害性的,那么其行为手段也同样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发动刑法进行处罚。此时,司法机关以行为人改低价格造成他人经济利益损失的案件事实为大前提,寻找与之匹配的法条,终于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找到了答案。于是,司法机关将以低价方法出售商品的行为认定为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在撰写判决书时,再将三段论正置,运用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对法律中的大前提“其他方法”进行扩张,使其包含了改低价格,最终形成判决。张明楷教授认为,“三段论的倒置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裁判者在面对案件时,即便先入为主地得出了有罪之结论,再寻找适用的刑法条文,并使得该案之事实与法律条文之规定相适应,这也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10]。笔者对此并不反对,因为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法官在拿到案件事实时,其思维过程必然是先得出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罪轻罪重的结论,之后再去寻找法律依据。霍姆斯将其凝练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法官基于其判案经验都会存在一定的预设。然而,虽然法官的思维过程是倒置的三段论,但其在形成最终结论,说理论证时应当严格遵守正向三段论的演绎推理逻辑,将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不能任意颠倒。张明楷教授在肯定三段论倒置思维后又补充道:当然,如果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先前得出的有罪之结论在后来的法条查找中并无与之对应的条文,却仍旧对被告人定罪处罚,那么这种做法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案件是先得出有罪结论而后却找不到合适的法条,最后只能是通过“解释”来牵强附会。
(三)同类解释规则的错位适用
司法机关在扩张适用破坏生产经营罪时的结果导向思维和三段论倒置推理都是从较为宏观和整体的层面进行的分析,而这里提出的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错位则是在较为微观的层面展开的。同类解释规则是在体系解释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解读法律之方法,其要求对分则各条文的“等”“其他”,应根据法条列举的内容与性质进行理解[11]。对“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中的“其他方法”也必须适用同类解释规则,来考察它与“毁坏”和“残害”的相当性。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同类解释规则把握得过于宽松,没有正确认识到法条列举的“毁坏机器设备”与“残害耕畜”在适用同类解释规则时具有参照意义。
第一,实务中,法官将“同类”转化为“法益侵害的同类”(社会危害性的等价),将较为严格的同类标准替换为较为宽松的类似标准进行运用。有学者指出,同类解释中“类”应当区分为四类,即,行为危险的同类、行为强制程度的同类、行为方式的同类,以及行为所具有的法益侵害的同类[12]。对于本罪,除法益侵害类型的同类外,行为方式的同类也不应被忽视,因为本罪的罪状明确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在“反向刷单案”中,“‘恶意好评’致使他人店铺以及产品信誉受损,并使得其搜索排名降低就属于以类似于破坏‘机器设备’的手段破坏他人在网店平台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13]。这种以“类似”代替“同类”的论证方式达不到同类解释规则的要求,解释结论也使人难以信服。
第二,实务中,法官在适用同类解释规则时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其不是将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与法条所列举的“毁坏”“残害”从行为对象、方式和强度等方面进行同类比较,而是用法条中“其他方法”后的“破坏”来与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比较。这种“向后看”的同类比较使得同类解释规则被虚置。因为,“破坏”一词在刑法中意涵丰富,其在不同的条文和罪名中有着不同含义。如,在破坏选举罪中,“破坏”一词同时就包含破坏选举秩序、妨害选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行使两层含义。再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是指秩序被破坏,而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破坏”,是以物理力、有形力进行破坏。如果在适用同类解释规则的时候“向后看”,以“破坏”作为行为参照的标尺,那么,行为人扰乱、干扰生产经营秩序的行为也会被归入本罪中。那么刑法分则第三章所有的行为均可以按照本罪定罪,这显然是对同类解释规则的滥用。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向前看”,即应当以毁坏机器设备和残害耕畜这两个列举项对“其他方法”进行解释。
三、对网络型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正确理解
对本罪“其他方法”解释时,不能因为其带有网络犯罪的属性就过于宽泛地理解。笔者认为,要防止“其他方法”被不合理地适用,应当坚持先解释列举项再解释概括项,并且应当坚持先形式解释后实质解释。也就是说,先运用文义解释来解释本罪的“其他方法”,再在实质解释的立场下,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来解释。
(一)坚持先解释列举项,后解释概括项
先解释列举项后解释概括项是同类解释规则正确适用的表现。而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使用同类解释规则时往往是“向后看”而非“向前看”,即用“破坏”来解释“毁坏”和“残害”。这种“向后看”的做法表面上看是违背了同类解释规则的解释步骤,实质上则是司法机关只注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注重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因此,笔者认为,为纠正这种“向后看”的解释思路,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来解释兜底条款时,有必要确定先解释列举项后解释概括项的解释顺序。
对于列举项的解释,应先运用文义解释方法来解释“其他方法”的文义,再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考察本罪中的法益侵害,从而在“其他方法”的文义射程之内考察实质的法益侵害,从而合理解释本罪的“其他方法”。第一,破坏生产经营罪为有形的物理力的损坏。这种见解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毁坏是一致的,应采用毁坏学说中的物理毁弃说。因此,对于本罪中概括项的破坏行为也应当做有形的物理力的解读。有实质解释论者在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持效用侵害说,认为只要是破坏财物效用的行为均属于毁坏;而在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则持物理毁弃说,并将反向刷单等行为认定为妨害业务的行为[14]。这说明,在对于破坏生产经营罪中的“其他方法”的理解上,部分实质解释论者也承认,对于兜底内容的理解不能只注重法益侵害的相同性。第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对象应当是类型化的、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物质性生产经营条件。只按照形式解释将机器设备和耕畜解释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难以涵盖经营领域,有理解过窄之弊端。但将其实质解释为一切生产经营中的条件则又过于宽泛。因此,对于本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在进行了文义解释后再进行客观目的解释,取二者的优势而摒弃其弊端。
(二)坚持先进行形式解释,后进行实质解释
有学者指出,“形式解释论的解释结论不是带有入罪倾向的解释,是因为其在形式考察后还要结合所解释罪名的法益做实质考虑,这种双层保险、双重限制使得解释结论不会过于扩张犯罪的成立范围。而相反的是,实质解释虽然一再宣称其是没有入罪倾向的解释,但是在实质解释后不再也无法再做形式方面的考虑。因此,形式方面被人为省略,实质成了唯一的解释标准,形式所具有的限制机能自然也无法发挥其限制入罪的功效”[15]。笔者并不认为,将实质解释置于形式解释之前是不妥当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案件的判决结果都表明:实质先于形式进行解释的方法容易将只具有处罚必要性而无刑法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
从本罪来看,实质优先于形式的判断方法是将本罪的法益定位为生产经营中的利益,之后再将概括项中的“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解释为以其他任何方法对他人生产经营中的利益造成损害,进而只注重法益侵害而忽视了列举项所蕴含的行为对象类型和行为手段类型。因此,反向刷单、恶意批量注册等行为均符合“以其他任何方法破坏他人生产经营中的经济利益”这一解释结论,从而达到了入罪目的。正确的做法是,在解释时遵循先形式后实质的判断思路。这样就可以将“其他方法”限定在刑法文义范围之内,也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形式判断在先,实质的价值判断在后,这样可以避免定罪只是对量刑的一种正当化、短视的、结果导向的刑事政策分析,防止回归到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定罪和量刑的传统思维与做法上”[16]。邓子滨博士则从反向批判的角度对实质优先、目的优先表示了明确的否定和担忧。他认为,“实质优先、目的优先实际上是以目的的正当性来论证手段的正当性,这是目的论支持者经常陷入的泥潭,并且经常被他们所推崇的目的所反噬”[17]。笔者认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三)解释结论
我们应当摒弃实质解释、客观目的解释在刑法解释中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坚持先形式解释后实质解释、先解释列举项后解释概括项的判断流程,正确运用同类解释的规则将“其他方法”与列举项中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从法益侵害、行为对象、行为手段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具有等质性的行为。在淘宝上反向刷单炒信的行为由于不具备有形的物理力的手段要求,且其针对的对象是主观的信誉、声誉,因此不能被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于恶意攻击商家网络经营平台导致其商品下架或平台无法正常工作的行为,由于其侵犯的是网络秩序法益,所以也不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除此之外,与列举项不具有等质性的其他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本罪。对于构成寻衅滋事罪、损害商品声誉罪等其他犯罪的,在详细考察案件情况和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可以依据这些罪名定罪处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的,应当依照《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规制。对于仅仅违反了商业规则、网店经营平台的准则,尚不构成违法的行为,应当依照商业规则、平台准则严加管理。构成民事侵权的,相应的民事主体可以对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