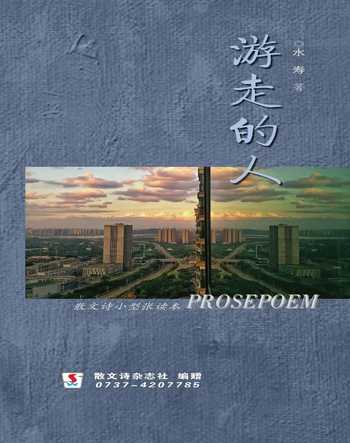在场
祁照雨
隔 壁
梨花很活跃。它们开满了地面和床铺。书桌上是被它们的光所照耀的地方。我在光之内,辨认着自己的身影。
布谷鸟控制着我行进的节奏。我愿意再慢一点,我愿意在这根树枝上收敛自己的喉咙。我愿意画地为牢。
清晨专心做一件事,用清水洗脸是一种修行。流水的声音大于雨催生万物的声音。我们同样渴望自己生长。
光照耀的局部是这里的西部,光照耀的地方有滚烫的沙子和我们正在康复阶段的胃病。我们的弹性很快就会恢复。
我们都在寓居,在仰慕天空中飘摇的纸片,也在同情落在地面的星辰。我们的复杂性就是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到底是谁?
面对天空,歌已经到达尾声。面对墙壁,信纸才刚刚铺开。隔壁柔软的雾气正在灌醉我的眼睛。
我看到的是留在树杈上的信物,是漂浮千里而盲目乐观的酒桶,是耳聪目明但词汇有限的壁灯。
手中的缰绳已经勒紧,太阳认为我的脸是刚出土的瓷器。我们都认同这样的误解。但我们都承认,太阳出来的那一刻,我很安静。
穿越黑暗
沉默。终止的对话是虚拟的灯泡,在我的臆想内,物种很丰富,它们侵占了我脚下的星球。我的渺小理所当然。
我的翅膀之外便是峡谷。峡谷的山壁上都是对我的劝诫。我虔诚地回忆着自己的失误。黑暗中的道路是用失误铺成的。
被放大的缺憾是雄鹰,是尖锐的喙,俯视我年幼的步伐,我的逃避,是手掌上的蚊虫在探索聚餐的地址。
我应该放过它们,我应该心怀神明,我应该在晨光里清洗自身的污垢。噪音结束了。黑暗远去,灯笼上的天空,引来流水潺潺,我恢复的听觉听见了人间最常见的話。
黑暗结束了,我在一本花瓣叠加的回忆录上,看见自己的分身正在纠正。
那些花儿
宽阔的夏天。宽阔的人行道和车站。流浪歌手看见的焰火像是专属的。天空是谁离别的特定地点,车流往来,行人上车走了。
连成线的戏剧接着上演。换了几种角色,只有自己才清楚。但我们乐此不疲地把背影留给别人。
我歌颂的翅膀因你而起。我追忆的星辰因你而晦暗。这些神秘的力量,是上天垂怜的神迹,也是流水东去的自然。
鲜明的线段上,是往来者运送礼物和弃物的车辆。纷纷避让的行人,根本看不懂里面的海鲜和水滴。旧物总归是旧物,旧的速度让我们惊讶。
我们各自为对方整理头发,又各自从人缝里抵达新的海岸,我们的陆地逐渐分开。我们听着潮水从对方的方向涌来。
告别,必须用雪地来衬托。我们都曾认为彼此很洁白,我们都曾经用宏大的语句来信仰彼此和未来。
陈旧的海苔来自哪里:是梦中的呓语,还是面对月亮时的感慨?永久的静寂。弧线层层荡开。
他们的节日
赞美的语言像泛滥的水藻。在道路的关键节点上,我们终于达成共识。我们发自内心地说出相同的话。我们像一群正义之师。
阳光下的激烈并不适合反思。五彩斑斓的纸张很适合我们的抒情。空洞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在美好的日子闲庭信步。
空中飞扬的气泡很坚强。
我们都喜欢励志的故事。
因为,我们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饥肠辘辘。
美好的道路,美好的空气的摩擦和碰撞。一天之内的丰富,是我们对于天气充满魔幻色彩的揣测。海很快就会形成,来渲染此刻的漂浮。
一串槐花就是足够大的惊喜。上面洁白的花瓣,像谈论哲学的飞虫,在今天下午,它们会赞美和批判自己的雷同。
我是旁观者。我是我的旁观者。在那篇小说平庸的架构和高潮里,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结局。
花 开
直到满山荼蘼走进黑白照片,事情依然没有定论。此生的目的,是进入下一个轮回,还是将自己锤炼成一颗种子?
他一生占有过的,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他自己。比如一生奔赴的东方,比如曾经钟意的篝火和雷阵雨。
像一条柔弱无力的陈述句坐在北方的天空,仅仅是为了让他人发出对于春天的感叹。
意义在满山遍野地驰骋,不肯落幕和回归。
唯有一张脸漂浮在幽暗的水面。那才是它看见的自己——真正的自己,一种不会发光的象形符号,一种固态的机关。
以土壤的姿态将春天归还。
我看见他更多的部分只是水面下的浮游生物。群聚,热烈,永远满怀热泪,不知老之将至。
快 马
使自己抽象,使自己在融化的夏夜像个自由人,在停泊已久的船舷上画上蓬松凌乱的鸦群。这样的表达使我酣畅淋漓。
环环相扣的因果相映成趣,但有些纽扣注定会脱离,在黑暗中的长椅上研究一支上进的蜡烛。这样的场合有天然的美感。
作为个体,作为霞光中落落寡欢的部分,我倾向于荒野中璀璨的噪音。我们出现在某个纪元里,带着孩童的调皮。
在萋萋的芳草里,做一个斗牛士。在厚重的云层里,做一个悠然自得的皮匠,我可以适应不同身份,我可以在乐队里很称职。
银河疏漏的五月。鸟语花香的笼子。像个冒然生长的胆囊。里面的绿林好汉是独一无二的。里面的钓翁也是独一无二的。
万花筒
找自己就要去寻找此刻的反义词。你并没有被直接描述,而是借助他人的命运呈现出来。
一只猫的身体里,有组成你的碎片。
一条鱼的姿态里,有你歌唱过的离歌。它们的相聚和叠加是因为风在吹。
东风吹来的是你的吉祥,北风吹来的是你的意志。
当红色和绿色叠加在一起,就是你的背影出现的时候,光,似乎都在此刻拥挤而来。
但你的面目始终面对着另一个方向。
一圈一圈迷离的路程,你仍在钓鱼的路上,怀着某种渴望,坚信转弯时会有某条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出现。
你仍在一层一层的真相之下。
稚嫩的胳膊握着刀和棉花糖,在刹那之间变换成了另一个身份。隐匿,洗白,只有春天浩荡无垠。
被编号的部分由磁场牵引,你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时间。你找到的永远是一张碎片,它们只能用来替换另一张碎片。
温度在上升。你察觉了自己身下的座椅——你从来没离开过,你从来没有看清过,你从来没有对过。
公 园
灯柱突然亮起,我们的星球是自己搭建的,光是伟大的创造之一,令我们成为更强壮的逃匿者。
丛林密集处,有幽静的洞口。我在那里发现了自己的肉身,它在野蛮之地露出了本来的模样,像一头睡着的狮子。
虚拟的水系在我身边围绕,我们用微缩的方法将黄河和大江移植到这里,并教会它们市井俚语。我们的交流毫无障碍。
我坐在那里,接受树木与喷洒的水对于昏黄的认知。我松弛的表弦,带着违约的快意,接受了令万物失重的迟缓。
飞扬的光粒子,飞扬的下棋人,飞扬的楚河汉界与生活的游乐场。飞扬的虚拟战场与最后的马踏连营。我们的现场接近慢镜头的剖析。
这才是公园该有的样子。风,吹动着一个塑料袋,从我的脚底走过。我知道我们类似的近况。我说:今天我将在这里休憩,希望我们永不再见。
晴转阴
多愁善感的海面正在捕捞自由的船只。我们想将它们归类、存档。我们希望找到自由发生的规律,以及高潮期。
我们回归的房间内布置着数、圆周率、周长和多元多次方程,我们打碎的奥妙,让光如期出现。
晴天,鲸鱼在我们的头顶使用五线谱,将天空的柔软编织成一条街道。阴天,鲸鱼收敛了翅膀和羽毛走了,留下某个没有奇迹的大洋。
我们数着飞翔的衣物,在寂静的木屋里提取潮湿的酵母。我们的生活堆积在一起,陈旧而熟悉,没有任何折痕。
风,将人间的色彩混淆在一起。
我们在一个完整的岛屿上,我们在与海鸥交谈,我们在阴影下的身影融入泥土。
俯 视
看见灯,如看见自己。我们的短暂和疲惫如出一辙,共同构成世界荒芜的部分。我们迎接雨水,如迎接迷路的善良。
遇见花开,便走进去。看里面的刀片和冰川,看里面的故事和人。里面的帐篷是香气出现的地方。
我昏迷,我苏醒,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接近粮食,并把自己登记在册,又变成漫无目的的绵羊,绕过树桩和餐桌。
我苏醒,我替换自己,我将自己置换成等价值的工具,替别人出现在讨价还价的谈判桌上。聚光灯,很冰冷。
继续低头,继续俯视,旋转的镜头下,酒类蔓延出山谷。从来没有东方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呼啸而过的车辆带走了珍稀动物。
漫长的公路并不是充满逻辑的秩序。我们认为的道路,也许只是下一段眩晕的开始。我们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将自己替换出去。
雨 前
一切都还没有成形。我以为的雨,一直是一条项链,挂在建筑上,我看到的是一场关于雨的电影。
海的切面就在那里,当建筑也变成站立的湖,我还没准备好做一条称职的鱼。我们接触水的时候,看见了里面人为的神性。
我闻到了水汽,闻到了水汽里的原始人,甚至闻到了他们对于一个黄昏的赞美。他们的打渔具有原始的美感。
我穿过这些水汽,带着不可避免的折射,我的冲浪板沿着固定路线飞越,我沿着固定路线走入误差。
雨始终没有成形,我始终没有走进水里。我读的诗句也很干燥,像被人利用的可燃物,只形成微不足道的气泡。
風 声
恍如我坐的地方就是鱼鳃。我需要的氧气唾手可得。可是,这份便捷让我迟疑。就像我沉重的肉身不应该如此轻易得到爱情。
鸟的眼睑还在眨动,今天还有更多的凶险。我休憩的片刻,定格在别人的视线范围内。
我知道我是赤裸的猎物。
我们不会和解,在宁静的夜晚,在着火的地图上,烟雾里的南与北都已断绝。我们能比昨天更相爱吗?
开花的季节,隐忧也在盘旋。我知道,这片土地布满了绳索,我知道我必须永不入眠地警戒,我知道,我将永远这样活着。
如梦令
你看,我蓝色的舌头。这是我在人间的所有成就。它的敏感,是我对自己最大的真诚。我从来没有对过几回,并将继续错下去。
可爱的舌头,万物因此而辉煌的舌头。窗外的夜色也无法关闭的舌头。
我们在一同渴望遇到一个意外的刺客。
无趣的音律也能绕梁,将我的绿植悬挂于洁白的墙壁上。那是一种鲜明的暗示,墙壁变化的速度大于我老去的速度。
很多事我们都心知肚明,比如今天的功败垂成,是明天重蹈覆辙的开始。我们未能超脱父亲的辱骂和规劝。
对于一切味道都甘之如饴。
我们成为陀螺之前,总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去欺骗那些锋利的羽毛。我不愿过度清醒,我只是凌晨没有路灯的马路。
渴 望
被撕碎的夜晚怎么也不肯恢复。
钟情的玻璃片以蓝色居多。晚上的北方,处处皆是海面。
不认识的人总会给我很多建议。但眼中的世界依旧,海面居多,陆地逐渐沦陷,向着光移动的执念不断。
我渴望将绿植铺满整张床。渴望所有的绿植都有敏锐的触觉,渴望所有的直觉都有具体的形状。
我流动的属性应该更强烈一些,以规避现有的经线和纬线,我是重新醒来的河床,向东方承诺着未来的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