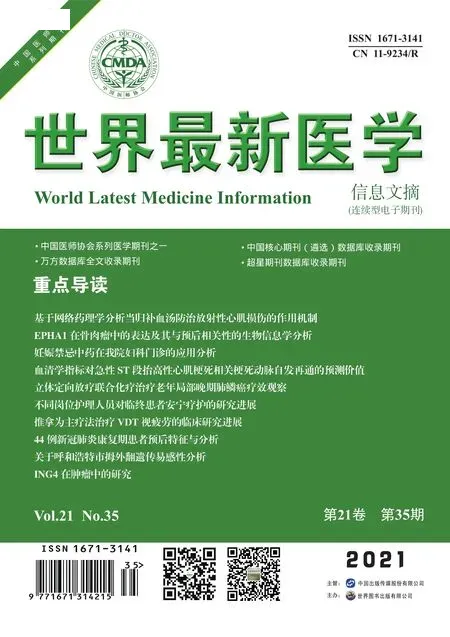股骨粗隆间骨折治疗现状与进展
巴得热力·特尔巴图,袁治国,张昕,徐兆晨,秦进
(1.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2.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3.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0 引言
股骨近端骨折有A、B、C三种(根据Muller AO分类),分别为关节外股骨粗隆间骨折、关节内股骨颈骨折和股骨头骨折。
股骨近端骨折患者总量中,IFF(股骨粗隆间骨折)占比约为55%,主要发生于骨质疏松的高龄患者,由于我国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剧,导致高龄脆性骨折的发生率正在迅速增加,且该病老年患者围手术期的死亡率高。发病原因方面,在老年患者多由低能量如跌倒等原因引起,年轻患者中,股骨粗隆间骨折主要由高能损伤造成,并伴有其他损伤。因为粗隆间骨折是囊外骨折,所以股骨头的血液供应受影响几率较少。该型骨折通常有手术指征,大部分病例手术治疗效果满意,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以手术治疗为主。现已有多种技术可用于IFF临床治疗,以下简要综述临床中应用比较普遍的几种IFF治疗技术。
1 非手术治疗
IFF极少行非手术治疗,这主要是因为其会引发多种并发症。但对于那些非手术治疗可以获得疼痛控制的丧失行动能力的患者不失为一种手段。对于大多数粗隆间骨折,内固定是适用的治疗方法,包括髓外和髓内固定系统。最佳固定方式取决于骨折的特征。
1.1 保守治疗
股骨粗隆间血供丰富,如牵引等保守治疗即可使不适宜手术患者达到骨折愈合的目的。郭金超等[1]对618例股骨粗隆间骨折中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的患者生存预后进行对比,手术治疗组共有551例,占89.16%,非手术治疗共67例,占10.84%,其中手术治疗组患者半年内死亡60例,生存率为89.11%;保守治疗组半年内死亡30例,生存率为55.22%。保守治疗患者半年内生存率显著低于手术治疗患者。
内固定、术后早期康复训练是IFF临床治疗的两个基本原则。患者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病史、伤前不能活动且对肢体功能要求不高时需考虑保守治疗,因为此类患者的手术或麻醉耐受力严重不足。骨骼条件允许前提下,股骨髁上牵引、胫骨结节牵引这两种持续骨牵引宜成为保守治疗的首选,这样能将患者下肢力线与解剖结构恢复最大化,对短缩畸形、外旋和髋内翻风险下降有利。若患者因自身状态太差而不能进行骨牵引,视情况可予以持续下肢皮牵引方式。牵引治疗患者需长期卧床,牵引持续时间通常、为6至12周,重量一般情况下约等于患者体重的八分之一即可,治疗期间还应定期复查X线片以掌握恢复效果。缺点时保守治疗康复周期较长,压疮、坠积性肺炎等并发症易出现。近年来中医治疗也获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张胜军等[2]认为中医辩证分期理论针对股骨转子间骨折进行辩证论治,使骨折后期肿胀明显减轻,骨折愈合时间缩短。
2 手术治疗
2.1 外固定架治疗
微创固定模式中的外固定架应用比较多,采用这种方法时,术中骨折断端无需暴露,骨折附近软组织受损程度或机率明显低于开放性手术,能为骨折附近血运提供有效保护,确保骨折端对合与维持,缩短愈合用时。此法对老年患者(疾病严重、手术耐受时间短)比较适合。Wang等[3]证实,和保守治疗相比,外固定架能显著降低髋内翻风险,减少骨折引起的并发症。Zhang y等[4]证实,外固定架手术术后疼痛轻、出血少、时间短,术后功能结果和死亡率可接受,这是DHS不具备的优势。他同时认为,外固定架会参考 患者日常行动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且固定强度不足(因其为间接固定)。基于随机对照分析,Petsatodis等[5]证实不稳定粗隆间骨折采用外固定器时更易出现髋内翻,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愈合,而且肢体功能很难恢复到理想状态。局部麻醉后即可开展外固定架术。也有相当的研究[6]显示微创外固定架治疗疗效优于牵引治疗,且并发症少于牵引治疗。
外固定架治疗粗隆间骨折最大的不足就是容易出现钉道感染,术后护理有难度,增加了钉道感染的机会。但是外固定架对患者损伤小,术式手术费低,手术及麻醉操作技术难度不高,这些优点使得外固定架值得推广用于基层医院。
2.2 髓外固定系统
2.2.1 动力髁螺钉(DCS)
起初,动力髁螺钉主要运用于临床治疗股骨髁间骨折,后来才用于IFF的治疗中。从结构上来看,动力髁螺钉和悬臂梁系统相似,钢板和拉力螺钉有95度的夹角,这种设计思路与髋部性能标准(对生物工程力学)相吻合,可坚强固定骨折断端,以降低骨折端发生旋转和移位的概率[7]。方松清等[8]总结了119例股骨粗隆间骨折分别采用DHS和DCS内固定治疗的相关资料和术后疗效,认为为了达到最佳固定效果,DCS固定更推荐被应用在A2型、A3型骨折中。在临床上,DCS常用于DHS固定后失败或骨不连患者的内固定翻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粉碎性髋部骨折都是DCS的适应症,对于大粗隆粉碎超过上二分之一的IFF患者不应选择该方法进行治疗,因为不完整的骨折会不利于动力螺钉的置入[9]。
动力髋螺钉 (DHS)仍然被认为是Evan'sⅠ、 Ⅱ、Ⅲ型(少数)骨折,尤其是骨质状态理想的低龄患者内固定物的首选;而对于包括部分 Evan'sⅢ型、Ⅳ型以及反粗隆间Ⅴ型等不稳定型粗隆间骨折,动力髁螺钉 (DCS)是不错的选择。固定可靠,内侧支撑较好,可以有效的降低内固定衰竭和髋内翻的发生率并缩短卧床时间[10]。但目前由于其本身的诸多缺点以及髓内固定装置的更新迭代使得其也逐渐被其他内固定器材取代。
2.2.2 动力髋螺钉(DHS)
1955年,动力髋螺钉第一次进入临床应用,IFF临床治疗就此迎来新选择。DHS借助股骨头内的滑动螺钉与股骨干侧方的钢板相结合,侧方钢板借助对钉与股骨近端的锁定,将骨折部分进行固定以达到治疗效果。DHS主要具备的优点为:设计完全遵循了骨折治疗的AO原则;基于滑动加压(股骨髓内拉力鹅头钉)、侧方套筒钢板支撑,有效固定好股骨干与股骨头颈部后即可共同承载起局部应力;在骨折位置形成一稳定支架并可有效预防髋内翻,其有效吻合了人体生物力学原理。DHS操作便捷、装置强度完全可以满足患者早期活动、患肢在活动中有显著的加压滑动,患者骨折愈合恢复效果也较理想。但该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在:由于手术需较长切口而造成患者软组织受损程度大,股骨外侧部位的骨膜也会被破坏;股骨颈内由于需置入较粗的拉力螺钉,因而影响了股骨颈的骨质及血液循环,且操作空间仅允许置入一颗螺钉;该装置中的颈干角不能改变。总结后发现DHS为开放性手术,术中需要充分暴露大粗隆,导致软组织剥离较多,使骨折处局部血液供应受到破坏,多种术后并发症易发生,如股骨头坏死、骨折愈合延迟等[11]。所以DHS在治疗不稳定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无法保证外侧壁的完整性,普遍被认为容易导致骨折复位失效,使骨折愈合时间延长,延伸了康复周期,也更加容易诱发骨折晚期并发症,现已少见其被用于临床治疗。
2.2.3 经皮微创加压钢板(PCCP)
经皮微创加压钢板(PCCP)是一种内固定系统(基于微创理念),属于以DHS为基础研发出的内固定装置,主要由股骨粗隆间螺钉(3枚)、股骨颈螺钉(2枚)、钢板(1块)等组成。手术时可闭合复位,滑动压缩螺钉的动(静)态加压主要用于颈干角的维持。颈部两螺钉间距固定的设计,对股骨头旋转、切割有预防作用。Cheng Q等[12]指出,无论从术后并发症、术中出血量还是手术时间等方面来看,经皮微创加压钢板的优势均超过DHS,是治疗AO/OTA31、A1-A2、Evans Ⅰ型的有效内固定方法。基于34例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采用经皮微创加压钢板治疗研究分析,谭家昌等[13]证实此法的优良率高达97.1%。张世民等[11]认为PCCP外侧壁缺失型股骨粗隆间骨折仍有一定困难。比较三种常用的术式,DHS如发生外侧壁破裂,则会使得器械内固定失效的风险增加;PFNA力学结构优良,但对软组织和骨皮质刺激大,术后髋股部疼痛的发生率高。Gotfried[14]提出PCCP避免了以上两者的缺陷,PCCP创伤小,操作简单,对骨质疏松病人更适用,在临床中是不错的选择。
2.2.4 股骨近端解剖钢板
解剖钢板的优势主要在于有效结合了传统骨折钉板固定与股骨头颈多点固定。这种技术典型优点包括出血少,手术简单,隐性失血量低,更适用于有严重基础疾病的病人[15]。高泓一[16]等对股骨近端解剖钢板、DHS治疗后的76例不同类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疗效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从远期预后质量、术后并发症、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四个方面来看,股骨近端解剖钢板效果明显超过DHS组,钢板按照股骨近端形态制作,股骨头颈通过3至4枚拉力螺钉多点固定,有效控制旋转应力,提高稳定性,内固定牢固程度所受骨质疏松的影响因此而减少。但该固定系统极易因后内侧骨折处理失当而失效,从而引起钢板或螺钉松脱、髋内翻、疲劳断裂,现已很少使用。
2.3 髓内固定系统及人工关节置换
2.3.1 Gamma钉
以粗隆间骨折优势归纳分析结果为支撑,Halder[17]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 Gamma钉研发。Gamma钉的技术原理主要是基于闭合复位思想展开IFF微创治疗。由远端两枚锁钉、弯性短髓内针和近端头顶加压螺丝钉组成的Gamma钉,其主钉经髓内插入,主钉与近端固定交锁螺钉间力臂短,因此能有效弱化其所承载的剪切应力,同时髓内固定也使骨折远端的固定效果增加,生物力学上的优势明显。弯矩小,力臂短,近端锁钉能滑移至外侧从而加大骨折部位的压力,对骨折愈合有利;抗剪力大,主钉远端截面独特的三叶草瓣状设计、钉体的弯曲面结构以及拉力螺钉共同形成扭矩,可以有效而且均匀地传递负荷;远端锁钉能抗旋转、抗短缩,可防止旋转移位及髋内翻的发生等为Gamma钉的优势所在[18]。其不足之处在于:近端外翻角与主钉截面太大,增加各种并发症风险,比如股骨干术后骨折发生比例达12%[19];此外Gamma钉末端结构设计有缺陷,被认为是其术后假体周围骨折发生的原因[20]。现该型髓内固定装置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逐渐被临床所淘汰。
2.3.2 股骨近端髓内钉(PFN)
PFN主要是在发现Gamma钉的缺点后开发的一款内固定装置,适用于粉碎的不稳定型骨折。PFN系统以Gamma钉为基础增设近端防旋螺钉(1颗),改进后的设计使防旋功能和抗压力被增强,提高近端稳定性;且在尾钉与远端锁定螺钉栓间距增加后,继发骨折(股骨远端应力集中导致)风险就此降低,提高了治疗效果。术中,PFN能闭合复位骨折,骨折端只要能有效保持对位对线即可,无解剖复位需要,手术用时时间不长,但其同样有不足之处,比如骨质疏松严重的高龄病人采用PFN时,将降低螺钉把持力;再发骨折、螺钉切割股骨头和退钉等情况均有可能出现[21]。PFN伴随着PFNA等新型固定装置的涌现,现亦少见。
2.3.3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PFNA)
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PFN优势的技术创新,这种创新设备实质上是把传统螺丝用螺旋叶片锁(2片)技术代替,螺旋叶片旋转形成压力作用到骨骼中,表面积(刀片直径较大)、核心作用力(逐渐增加)确保内固定置入后压力稳定。且该固定装置的拉力螺钉置入过程中使松质骨逐渐受压,使固定更牢靠,更适合松质骨锚,防止旋转,从而提高了稳定性。曾超[22]等对共958例患者应用PFNA固定与DHS固定治疗方式比较,发现PFNA能缩短平均手术时间、减少平均术中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内固定失效发生率。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骨质疏松伴生)临床治疗的首选推荐为PFNA[23]。目前该型内固定装置仍是临床工作中骨质疏松性股骨粗隆间骨折治疗的首选治疗方式之一。
2.3.4 联合加压交锁髓内钉系统(InterTAN)
InterTAN 髓内钉系统最初被Ruecker 等[24]公开报道。InterTAN髓内钉本质上是一种髓内固定设备,被设计专用于股骨近端骨折,主钉的近端设计为4度外翻角,含梯形横截面,旋转稳定性(髓腔内)高,手术路径包括经大粗隆顶点微创入路。该系统的特点为联合交锁组合钉,旋转、成角稳定性因此有明显提升,从而增强了拉力钉的抗切出力,使Z效应发生率极低;下方加压钉拧入过程中会形成加压作用。空心稳定螺钉(主钉近端中心置入)可以把术后联合钉滑动避免或消除。发夹分叉开槽(远端)设计意在将远端应力分散,以此减少远端骨折等棘手并发症的发生,远端交锁包含有静力与动力交锁两种方式[25]。
它由美国Smith-Nephew 公司设计和研发,能有效降低术后下肢疼痛,减少应力性骨折风险[26]。现因InterTAN 需反复扩髓,会造成大量骨质流失,对基本复位要求也较高,且价格高昂,导致目前在基层医院未被大量应用。另有部分学者[23]认为Inter TAN适用于不稳定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
2.3.5 人工关节置换术
人工关节置换为IFF患者提供了另一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粉碎性骨折患者的关节进行置换。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在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同意这种治疗的学者认为,可以固定骨折大小粗隆,重建股骨距,骨折康复用时会因人工关节置换而减少。近年相关Meta分析[27]提示与内固定组相比,从术后并发症、下床负重时间、理想性来看,人工股骨头置换组的优势更明显。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手术有很多并发症,在减少长期卧床引发的全身性并发症、早期负重锻练、髋关节功能恢复用时等方面,人工髋关节置换的优势超过内固定,但其术中输血量比内固定高,这是因为术中出血量大。手术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人工关节置换存在并发症,如置入假体松动、断裂、术后关节疼痛不适等[28]。对于IFF患者年龄超过80岁,有明显骨质疏松症、粉碎性和不稳定性骨折、难以正常复位、难以牢固固定的新鲜骨折以及内固定失败之后的翻修手术、一般情况较差不能耐受二次翻修手术的患者,可考虑人工关节置换。该法术后功能恢复较快,可缩短卧床时间,并具备使二次手术、下肢静脉栓塞、泌尿系感染、褥疮和肺炎的发生率显著降低等优点[29],患肢功能会因此而迅速恢复,患者生活质量将显著改善。目前在我国髋关节置换术为老年患者股骨近端骨折的首选治疗方式之一。
2.3.6 股骨近端仿生力臂重建支撑防旋髓内钉系统
张殿英等[30]通过临床实践及相关研究发现:骨折一旦发生,股骨近端原有的内、外侧壁结构丧失,压力侧与张力侧骨小梁受到损害,导致原有股骨近端生理性杠杆失衡,即刻产生杠杆外移效应。故认为现有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各分型系统均是描述骨折内、外侧骨折块的大小、移位和粉碎程度,而未能阐明股骨近端骨小梁系统受到破坏这一机制,对骨折前后的生物力学改变缺乏认识,因而也较为片面。“杠杆-支点平衡”观点被张殿英等就此提出[31],并基于该设想初步设计出股骨近端仿生力臂重建支撑防旋髓内钉内固定系统,该系统包括主钉、压力钉、其特征还包括至少一个张力钉;主钉、张力钉和压力钉形成至少一个三角形支撑结构,主钉的近端段和远端段一体成型,近端段设置第一钉孔和第二钉孔,其中第一钉孔固定张力钉,第二钉孔固定压力钉。该系统重建了张力骨小梁及压力骨小梁所形成的“word三角”稳定支撑结构,被认为可有效防止髋内翻、股骨颈短缩、股骨部分内测移位、内固定断裂、松动、动力螺钉或螺旋螺钉切出、股骨应力性骨折等并发症发生,有利于骨折愈合[32]。笔者认为,该系统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和理论依据,研发成功并开始应用于临床治疗后,将为IFF临床治疗带来更多的选择,更多有关该系统的优越性有待进一步生物力学方面及临床应用方面的验证。
3 总结与展望
多种方法均能治疗IFF,但IFF临床治疗(无手术禁忌时)的第一选择依然是手术。根据不同类型的骨折、合并其他疾病情况、以及对手术的耐受程度,应当在治疗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及手术方法的适应证谨慎选择,合理选择治疗方案。近年来涌现的如PFNA、InterTAN髓内钉、粗隆间加强型髓内钉(trochanteric fixationnail advanced,TFNA)等为临床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启发。内固定装置联合骨水泥等术式也被认为有一定生物力学优势,伴随医学相关领域有关骨生物材料的创新与突破,相信未来骨水泥联合内固定等术式将在骨质疏松患者的内固定治疗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如DHS、PFN、PFNA等传统内固定装置联合应用骨水泥时稳定性明显增强,并发症减少,较之传统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骨水泥,新型骨水泥如磷酸钙骨水泥、硅酸钙骨水泥、硫酸钙骨水泥、复合材料骨水泥等应用于增强内固定稳定性方面的优势明显,必将为未来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治疗带来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