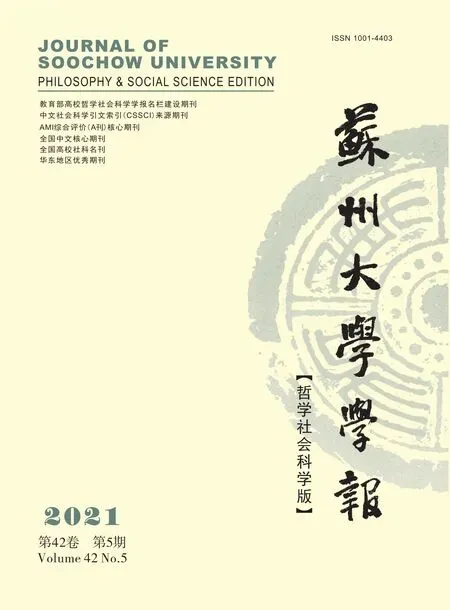程抱一与雅阁泰风景诗学之比较分析
巫春峰
(天津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204)
法国当代诗评家米歇尔·科罗(Michel Collot)经研究发现,“风景”一词在西方的本义是“一幅风景画”,并由此得出结论:“风景不是一块地方,而是一种对其观察或者绘画的方式,在美学和(或)认知学角度将其视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它从来都不是‘在场’的,而是‘在视域中’和(或)‘在艺术中’。”[1]12这与西方文艺一贯标榜的“表征”观(représentation)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表现,剥离了风景的感性之美。这种完全依照主观看法的风景显然与中国的山水精神是不同的。“风景”的首次出现可追溯到陶渊明,他曾留下“露凝无游氛,天高风景澈”(《和郭主簿·其二》)的诗句,而“风景”一词在这里取其本意,指涉的都是自然界的现象,缥缈的风和闪耀的光才是风景的真正内涵之所在。从词源学分析来看,西方的风景从一开始就浸染着认知主体的色彩,使得思想实体与广延实体完全割裂,而中国文化始终探求的是在山川真景中参天地化育之奥妙。
二战后的法国当代诗歌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风景诗作,其代表诗人有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菲利普·雅阁泰(Philippe Jaccottet)等。他们受现象学影响,关注当下即将逝去的事物,将目光转向被文本主义所忘却的感官世界,风景因其感性、跳宕、多义等驳杂不一的属性而进入诗人的视域。六七十年代在法国盛行的结构主义将一切都囿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并随之创造了诸多概念和术语,而这代诗人却扬弃体系化的概念,反对僵化的定义,主张在“感知”的浑融中把捉风景的整体意义,正如梅洛·庞蒂在《感知现象学》中所说:“在风景中有一个弥散的潜在意义……但无须对其做出定义”[2]325。因此,“风景诗学”一词是在并未于批评界形成统一内涵认知的情况下得到使用和沿袭下来的。从广义上讲,这个词意指将风景作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其内蕴颇丰,涵盖了“感性与意义”“主体与客体”“灵与肉”(1)参阅Collot,Michel.La Pensée-Paysage.Paris,Actes Sud,2011.等内容,是重新塑造内与外、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想媒介。我们在进行诗歌分析时将凸显风景所蕴含的模糊性与综合性,让其涌现在一股挣脱概念束缚的活力之中。
作为法国当代诗坛泰斗之一的雅阁泰在其作品中对风景予以了特别关注,在《具象缺失的风景》更是开宗明义地说道:“多年以来,我不断回归风景,它也是我的栖居之地。”[3]1纵观其作品,不管是诗歌散文抑或是艺论,风景无处不在,而他对风景的思考蕴含诸多东方元素,他在《明澈的东方》中呼吁西方抒情诗在东方的思与诗中汲取新的灵感,并屡次提及中国诗歌及老庄思想。(2)详参姜丹丹《雅各泰的风景诗学》,载《文化与诗学》2008年第2期。深受道家思想熏陶的法兰西学院华裔院士程抱一(Cheng Chi-Hsien)(3)程抱一,原名程纪贤。1971年程抱一加入法国国籍,为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其法文名,先采用Cheng Chi-Hsien(程纪贤),后改用Francois Cheng。其中文笔名,开始用程抱一。不遗余力地向法国推介中华文化,国内目前大部分研究在双重视野下从历时性角度探索程抱一和影响过他的作家及作品之间的关系,揭示其在汲取异质文化的同时进行再创作的本质。但在共时性视角下探讨他与法国当代诗人的思想碰撞还略显不足,这些诗人与其同辈,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对他并没有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的正是横向比较。程抱一对风景的思考贯穿于所有作品中,与雅阁泰存在很多契合之处,值得我们深究。
两位诗人年龄相差仅四岁,本是瑞士人的雅阁泰于1946年定居法国,而程抱一晚其三年抵法,他们不仅共同见证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且尤其是二战后,在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背景之下,他们都以批判性的清醒态度重新审视诗歌价值并在早期的作品中表达了从灵魂深处与本真世界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精神内涵来看,两位诗人对风景的观照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注重肉体与外部世界接触时的相感相应,以虚怀若谷的谦卑姿态实现主体与世界在敞开之境的融合,以景外之景来厘清“存在”与“存在者”的问题。但究极而言,尽管雅阁泰最具东方情怀,他仍是一位“纯粹”的西方诗人,诗歌中使用的神话、意象、修辞等都深深地烙上了西方的印记,他借鉴东方哲思的目的是在上帝缺席的贫困时代从万物的闪耀中寻觅神性之光辉。而程抱一寻求的更多是融贯东西的创造性写作,其底色是道家文化,从作品中比比皆是的道家词汇就可见一斑。
一、情感与灵感
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探讨了诗人创作灵感来源这一重要命题,他将其归结为神灵的启示。受启示的诗人形象在西方根深蒂固,影响力深远。然而,随着尼采的“上帝已死”,在现当代诗歌语境中,对于诗评家让克劳德·庞松而言,“源头已经枯竭,因为已没有源头”[4]88。面对上帝的隐退,诗人们只能寻觅新的源头,马拉美最终将“主动权交于词语”,在抽象的词语筑成的城堡中寻找上帝留下的踪迹,但是博纳富瓦斥责那是“无人的寝室、无火的炉膛、从外部观看的事物、‘濒死’的躯壳,就好像本应该震荡其所有感官的感性生命蜷缩在它空间的表象”[5]217。博纳富瓦在这里给迷茫的当代诗人点亮了一盏明灯,那就是充分挖掘人的感性深度,让生命打破空间无限性的桎梏,在转瞬即逝的时间维度全方面地建立与世界的感性联系。我们看到,博纳富瓦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具有同一旨趣,庞松援引德国哲学家在《存在与时间》的理论来剖析当代诗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所有存在,在有可能成为理性的客体化之前,它首先是感性地从属于这个世界,作为世界的栖居者,而不是主体。”[4]73为了摆脱形而上的主体,他认为:“诗语言固有的目的就是打通情感的所有存在可能性,也就是存在之大开。”[4]73人的感性存在也因此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因为人通过感知参与到世界的进程中,已不再是笛卡尔式的一元化纯意识,在这方面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梅洛·庞蒂在《感知现象学》中指出:“感知就是与世界的这种生命联系,而世界则把感知当作我们生活的熟悉场所呈现给我们。被感知的物体和有感知能力的主体把他们的深度归功于这种联系。”[2]64
但是这种单向的被感和感知却无法满足梅洛·庞蒂对主客二分的拆解,他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学说,最终将“我的身体”理解为“一个主客体(objet-sujet)”[2]194。如此一来,作为身体的主体通过知觉这个中介返回感性之根,与世界发生一种活泼泼的、肉体的、本真的联结,超越了物我的隔阂,弥合了主客的裂痕。
这种将人的存在变成知觉的存在的思想为当代诗人提供了另一扇窗户,与其被动地等待神灵的降临,毋宁纵入大千世界的洪流,正如尼古拉·卡斯丁所说的那样,让自我转变成“一种无尽的被动与主动的交织,一张我与世界在感性的织布上不断编织的网”[6]42。在这张感性的网上跳动的是人的情感,人与本初世界零距离接触的那种怦然心动,在科罗看来,“它是主体在与外部世界人或物相遇时的感性答复,主体努力将其内化并创造出其他东西,与情感的源头相似,却是新颖之物:诗歌或者艺术品”[7]2。在西方一直游离于边缘地带的情感终于在当代重见光辉,取得了合法性地位,成为诗人灵感的新源泉。
雅阁泰在其作品中就屡次提及情感、自我与创作的相互关系:“如果起初在任何物体前都没有产生情感,就不会有诗歌,亦无趋向诗歌的运动,单纯用词来作诗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8]21他甚至直接将“情感”比作“灵感”:“决定这些时刻的是情感一定程度的压力,如果不将其抒发出来会很难受,就是这么简单地经历了一次‘神灵的启示’。”[9]294-295由此可见,雅阁泰笔下的情感涤除了浪漫主义时常被后人所诟病的感伤主义,它既非个人情感的汪洋恣肆又异于人对物的单向投注,是物我相会的完美见证者,其内蕴更近似于程抱一所推崇的“情景交融”:“人类的情感能够在景中展开,而景色也拥有情感,两者处于不断的融合中。”[10]148
在感知中,风景的感性在场自我显现出来,正如美国哲学家斯托尔斯在《论感官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样:“在感知经验中现实以无思的形式显露。物体就在我面前,但我不是静止的、至高无上的认知主体。我的存在因物的存在而存在。”[11]243我们借助程抱一的一首诗来阐明情感的作用:
Midi le muet.正午静谧。
Les fourmis transportent leurs vivres,蚂蚁运送食粮,
Le long d’un muret herbeux.沿着深草矮墙。
La campagne à perte de vue,乡野一望无际,
Taitsa joie d’être.万籁俱寂,自得其乐。[12]137(4)本文所有程抱一诗歌的翻译都摘自朱静的译本《万有之东:程抱一诗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部分内容作了改动。文中其他未指明译者的译文,皆为作者自译。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串长长的罗列清单,它展示的是“世界多元化的共时性在场”,其目的是“记录情感最初的万千景象”。[6]22诗人笔下的场景皆是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琐事,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前知觉世界,梅洛·庞蒂将其称为某种逻辑世界的本源,是一种先于述谓活动的在世存有:“我们只有在原初存在的经验中看见它们突然涌现才会承认有一个先于存在的世界、一个逻辑,就像我们知识的脐带以及我们意义的源泉。”[13]260用卡斯丁的话来说,“在现象学视角下,在源头处是肉体、沉默(muet)的感性世界”[6]25。我们注意到诗歌第一行的最后一个词正是法语单词muet,它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无人、万物自为自在的前语言境域。感性在场这种内在的沉默性不仅体现在诗歌所呈现的事实中,而且也在音素的效果上得到了加强:“mrit”“muret”重复首句“muet”的前两个音,而“vue”则通过[u]的谐音与其遥相呼应,最后一句综括全诗,以动词“Tait”(缄默不言)收尾,起到在所指层面与“muet”相和的作用。
诗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罗列式句法与名词性句法的使用。罗列式句法注重袒露事物的本真面目,而名词性句法由于缺少动词的存在更为强调的是观照主体心念意识的泯灭,他已跳出思量的陷阱:
名词性句法扬弃了主谓之分,特别适合表达与世界的一种前述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之别消弭,就像在情感或者感知中那样,先于所有分析与评判。它常见于“评注式”的文字,与“被观照之物”的关系是瞬间的、非理性的。我们可将其类比于孩童“以一词表达一整句意义的话语”,主位与述位不分彼此,“不仅包含了主体的原动作用,还体现了他与物情感-性欲的关系”。[7]284
如此看来,诗歌的第一句和第六句就不再是“一边是主语,另一边是从外部赋予的谓语”:“正午”也好,“乡野”也罢,用来作修饰语的“静谧”与“一望无际”实质上和主语指涉的是同一件事情,换言之,主谓间因没有带主体“我思”之色彩的明显动词而凝结为一体,好似共同诞生于未分化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动词的缺失远非一种缺陷,而带来一种整体的效果:陈述获得了绝对价值,因为它的运用场域不再取决于一个主体”[7]285。那么,陈述活动的主语是谁呢?在名词性句子中,给人的印象是“陈述在自言自语,没有任何陈述活动主语的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语完全地消失,“他只是无法再加以定位,加以区分,我们可以说他整个都溶于了陈述中”[7]285。因此,作为陈述活动主语的诗人在观察风景的时候已经身心俱遗,与眼前一望无垠的田野浑然一体,内与外、物与我、动与静的对立已然失去了意义,让位于统一的整体。这正是最后一句诗所表达的,因为动词的变位是单数形式,那主语是正午?是葡萄?抑或是诗人?三者皆不是,诗人观景所感受到的“快乐”之情实则为物代言,就像雅阁泰所体悟的那样:“很可能一些强烈的情感令我们预感到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给我们暗示一个隐藏的统一体。可能这类启示呈现给我们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已跳出自我的躯壳,从而更加开放地学习外部世界。”[14]115这与庄子观鱼的典故有着相同的精神内蕴,质言之,人与物的共振源于他们是同质同构的。
二、身体与肉身
情感作为将人嵌入感性世界的支点使得当代诗人与哲人最终探究情感的寓所也就是人的身体。精研感性肉体的梅洛·庞蒂独具慧眼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相反,这个世界不是我,我对它的爱恋近乎爱我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我身体的延伸;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就是世界。”[2]83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著名的“肉身”说:
这意味着,我的身体是用与世界(它是被知觉的)同样的肉身做成的,另外,我的身体的肉身也被世界所分享,世界反射我的身体的肉身,世界和我的身体的肉身相互僭越(感觉同时充满了主观性与物质性),它们进入一种互相对抗又互相融合的关系。这还意味着,我的身体不仅是被感知者中的一个被感知者,而且是一切的丈量者,世界所有纬度的零度。[13]297(5)本文所有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中文译文均参考罗国祥译《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部分内容作了改动。
秉承天人合一思想的程抱一与梅洛·庞蒂惺惺相惜,认为在西方觅得了知音,在他的作品中一些有关身体的论述与法国哲学家不谋而合。他在《此情可待》这部小说中直接将身体比作风景:“所有自然的美景都在身体中找到:柔美的丘陵、幽隐的河谷、泉水与草地、鲜花与果实。难道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身体当作风景来欣赏吗?”[15]86在《天一言》中,他则反其道而行之,风景也可被暗喻为身体:“这块土地的每一寸地方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它感性的在场。血红色、柔软的黏土筑成的深深河谷还有那纵横交错的小道好似古老大地敞开的脏腑。”[16]122②(6)本文所有程抱一《天一言》的中文译文均摘自杨年熙译《天一言》,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雅阁泰也提及过类似的思考:“所有融于一体,毫无逻辑可言。事物,世界。世界的肉体。”[3]135
身体与肉身同一性原则与梅洛·庞蒂的“交叉”理论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为表里,它是对“肉身”说的进一步探究。“触”与“被触”两者同时发生,交融互渗,物我不分:“我的手指的肉身=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既是现象的手指又是客观的手指,相互既外在又内在,呈交错状,为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组合。”[13]310除了“触”与“被触”这组词外,梅洛·庞蒂还对“看”与“被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析。与触碰所不同的是,在东西方视域下,眼睛都被看作是心灵的窗户,目光交汇之处,打开了另一个维度:“我们的目光不是意识的行为……而是我们肉身的打开,很快就被世界的肉身所充盈。”[17]1563目光所禀有的穿透力无法满足于停留在表面,它要像“一只猛禽”或者“锋利胜于语言的刺”[18]30一样撕裂触摸的表皮,使其向纵深掘进,臻于更深层次的融合,就像雅阁泰的目光那样:“诗人的目光是推翻这些墙的撞锤,给我们找回了现实。”[19]301这样犀利的目光就闪现在雅阁泰的一首诗中:
在空间中
一无所有,只有闪闪发光的山峰
一无所有,只有炽热的目光
交错
乌鸫和野鸽[18]50
“空间”的法语“étendue”在音与形两方面都容易让我们想起resextensa,即广延性的东西,它是rescogitans(思考的我)所对应的客体。但是这种二元对峙的格局在第二行诗中被消除了,因为人与物设立的种种藩篱已消失殆尽,我们可以从法语“miroitant”(闪闪发光)这个词来加以阐述:它源自镜子(miroir),在西方传统中,时常与顾影自怜的那喀索斯在一起出现,显然,这与雅阁泰的旨归相去甚远,他更关心的是反射与被反射者的关系,与梅洛·庞蒂的“镜像”观颇为相似,“因为这是直接来自身体—世界的关系的结构—反射与被反射者是相似的”[13]319。第三句诗中,内与外、诗人与山峰、远与近的差别已被完全逾越,只剩两对互相交错的目光,它让诗人直面自身的灵肉处境:“不用从外部来看待它。这不是一场节目,而是真正地亲身经历体验过的。这个奥秘就居于我们身上,我们只能与之浑为一体。当我们处于世界的身体,也就是其核心时,一道目光,甚至当我们在观看时,目光已经融于其内部。”[20]83
程抱一虽未在其诗中直言目光交叉,但通过巧妙地使用人称代词“你”也实现了看与被看者的神会:
永恒就在眼前,
永恒即此时刻。
你将突然闪现,
你可睁眼看清:
在你消失之前
你将一无所知。
但你看,你赞美。[12]145
要想参透这首诗的精妙之所在,需结合程抱一对陶渊明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解读:“‘见’这个动词在古文中也有‘出现’的意思,那么第二句诗我们也可理解为‘南山悠然地出现了’。我们知道南山(庐山)只有在云雾突然散开之时才会露出其全部的光彩……诗人看见南山的动作与南山的自我显现是偶合的。”[10]100-101第一行诗描绘的是两个目光交汇前的情境,程抱一故意将“你”字省略,事实上,永恒应该在“你”面前,此时的“你”既可指人也可代物,为的是淡化两者泾渭分明的差异。第二句强调这种相会并非唾手可得,它只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撷取,非理智所能及。第三、四句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突然闪现。在上帝缺席的暗淡背景下,这种思想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对“现象”一词的诠释:“理解为:自我的显现。”[21]43但若这种自身的敞开没有被一个人的目光抓住,则“一无所知”。那人究竟在何处?最后一句与前面几句用空行隔开,它标志着一个新的事实被引入,陈述的主语还是“你”,但是唯有人才会用诗语言“赞美”这一瞬间的圆满,两个“你”交相辉映,个体生命融入宇宙整体,“目光的交汇也带来了身心的交汇。在这场彻底的相遇中,看的主体同时被看,因为被看的世界也是一位‘观看者’”[10]136。从语言学角度看,最后一句的“你”本应是抒情主体惯用的“我”,在程抱一眼里,抒情主体不是感情的宣泄者,他的感性存在需要一个“对话者”[10]101、一个他者来打破这种自给自足:“只有当主体走出自我,与自我重合,不是以身份等同的方式,而是以自我性(ipséité),它不排除反而包容他性,就像保罗·利科所呈现的那样。不是为了在自恋的世界中孤芳自赏,而是实现‘作为他者的自身’(Soi-même comme un autre)。”[22]115-116
为了进一步丰富“交叉”论的内涵,身为东西方摆渡人的程抱一试图为此着一点东方的色彩,他向法国读者介绍了“老天有眼”:“中文里表示‘看’的都带有神圣的意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说法叫‘老天有眼’。”[10]109无独有偶,雅阁泰在《具象缺失的风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正是:“最崇高的希望就是整个天空成为一个真正的目光。”[3]181
“交叉”论除了“看者”与“被看者”之外,还有“可见”与“不可见”,就诗人而言,风景在五彩斑斓的外衣下还藏有肉眼所不能及之处:“从我看开始,甚至在这之前——我刚看到这些景色,我已经感到吸引我的是类似遁逸的东西。”[3]21
三、可见与不可见
西方传统中被称为风景的画作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则被冠以“山水画”之名。程抱一倾其身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并探索中西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热衷于用一组词来表达事物的传统完全源于其三元思想:“在二元式结构中形成一对,诸如‘阴阳’‘天地’‘山水’之类的,二元表达实则是三元的,因为它既阐明了两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也说明了两者之间所发生的。”[10]146-147山水画因为涵摄了山(阳)和水(阴)这两个元素而变得缥缈无形,特别是云雾气氲蒸腾之时,整个景色时隐时现。相较于西方注重形似、致力于追求明晰性、憧憬理想世界的画法,程抱一认为这与典型的“模拟说”密不可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模拟’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复制艺术,另一方面则是虚幻的表象艺术。”[10]137亚里士多德将此学说与认知行为结合起来,而这在程抱一眼里则加剧了主客的分离:“为了得到形式而钻研物质的艺术家定会掌握物质与形式,并且对之有所了解,这使得他能肯定的是,‘模拟’的工作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以至于“在他心中激起了掌控世界的欲望”[10]137。博纳富瓦对此也持同样的批判态度:“就像西方的画家一样,他们是概念性‘模拟说’的信徒,而这个学说只分析表象,耽误了与物的相会。”[23]28
程抱一将世界看成是阴阳二气不断交汇而创化的生命体,宇宙生命一词(univers vivant)散见于其作品中,这都归因于天地间鼓荡的勃勃生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气”融物质与精神、一与多、可见与不可见于一体,是一切生命世界的本源,它使万物与人相融相契:“由于‘道’的动力性特别是‘气’的行动,从太初开始就持续保证了从无到有的进程……生命的运动和我们对此运动的参与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互相的、持久的勃然喷发。”[10]96-97在西方的创世论里,上帝创造了世界,而在中国我们更强调“造化”二字,虽只一字之差,但折射出的世界观却相差甚远:创造更注重的是人的创造力,其创造物也自成一体,已然完结;中国除了“造”之外还有“化”,而且后者更重要,它把世界与人置于大开的视域中加以观照。因为不绝如缕的元气的运化作用,才能达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之境,而风景因其高与低、静与动、实与虚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中国人探索现实的最佳选择。下面我们通过程抱一的一首诗来揭示风景的可见与不可见:
安宁大地稳实存在。
间或有血有肉,间或
缥缈空灵,因时而变。
在此,得天独厚之人
心领神会,不发多余
之言,他们深恐诸神
也会嫉妒人间。[12]112
第一句诗强调了此时风景的轮廓是清晰可见的,这一点可从“稳实”二字看出。第二句把我们引入一个异于前一句的事实:眼前有血有肉的景色开始模糊化、气化,笼罩在一片朦胧的薄雾中,与雅阁泰的体验如出一辙,“某个时刻,山脚消失了,只能看见山峰,就像有些中国画中的那样”[14]64。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隐与显、有与无、收与放的辩证关系,与中国画所推崇的“不即不离”有一定的渊源。于连在《大象无形》这本书中做出如下解释:“时而我‘抓住’其形,将之画出(用形象表示),时而我‘松开’,提起毛笔让线条悬置-虚化(留白):时而我让形返回和谐-未分化的本源;时而我画实,时而我入虚。我画,我‘非画’。”[24]150在这段话的启示下,虚实相生、可见与不可见并存、有形与无形交汇的风景只能通过实写与“非写”(désécriture)完成。“非写”甚至就是放弃写作与言说,虽然人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意识的运作使得“人把世界当做对象,在世界的对面把自身摆出来”[25]325。唯有当人摆脱作为智性工具的语言之束缚,才能无执无求,悠然会心,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10]157之际将语言转化为雅阁泰笔下“向气打开的过道。”[20]43如此,静穆的观照才能与生命的律动相得益彰,在一静一动、一显一隐间,与不可见的诸神“神会”,而这里小写的“诸神”既不是希腊的又不是基督教的,更接近于雅阁泰所赋予的意义:“不是宗教上的,尤其不是神话学上的,而是类似轻盈、高处、不可见这些感觉,也就是气之诸神。”[14]64同样的经历也出现在雅阁泰的散文诗中:
比起从前,我更加强烈地、持续地被外部世界所吸引。我不能将我的目光从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移开,在我对它的敬意中我发现我的喜悦与惊愕感不断增加;我真的能用壮美一词来形容,尽管涉及的一直是一些朴素的风景,没有绚烂多姿,更多是一些贫瘠之地和有限的空间。然而,这些壮美之景在我看来越来越澄澈,越来越气化,同时越来越难理解。再一次,这个滋养的奥秘,这个令我兴奋的奥秘就像一只有力的手把我推向诗歌。[14]14
我们看到雅阁泰的情感游离于“喜悦”与“惊愕”之间,与程抱一一致,因为他也认为风景中藏有“一个难以琢磨的奥秘,一个隐藏的美却迷人”[16]20。雅阁泰自年轻时代就选择隐居在法国的格尼昂小镇,他最痴迷的风景之一就是观赏周边的群山:“这些山令我感到惊叹不已之时正是它们不可见之时,是水气的轻盈令我迷茫。现在,庞大的山脉变成近乎雾霭之物。”[14]55-56两种情感再次交织,它源于风景的可见与不可见。对于科罗来说,“奥秘”是诗语言创新的催化剂:“如果风景在肉眼或者精神之眼下展露无遗,那么只能产生一个详尽的目录或者具有秘教色彩的感情抒发。当它是一个超越已有规范准则的‘奥秘’时才会有语言的创新。”[1]335那么诗语言如何表达这种不可见呢?让我们再来看一首雅阁泰的诗歌:
大地在那里完结可见
升腾而起,合于气不可见
(在光线中可见
上帝无形的梦在游荡) 不可见
在石头与梦幻间 见与不见的交织
这片雪:逃逸的白鼬[26]103见(不见)与不见的交织
这首诗出自雅阁泰最具东方神韵的诗集《气》(Airs),虽寥寥数语,然蕴涵隽永。我们可以借助科罗的“视野”法来分析这首诗。第一句的大地完全呈现在诗人眼前,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大地的“内在视野”,此时诗人挖掘的“不仅是这个物体的固有意义还有它在我们心中引起的震颤[1]350,它指向的是诗人与风景相会的那一刻。但如果一直以事物的内在性为旨归就会趋向于客观的描写,这在雅阁泰看来抹杀了“事物的运动与生命”,因为“忘记了给这些事物中的不可见留有空间”[3]10,因此需要引入“外在视野”:“永远不要停留在事物,要否定之,要么回归事物之本身,要么借助其他意象。”[1]351第二句中大地变得轻盈,它的厚实性被无孔不入的气体所刺破,有形逐渐遁入无形,作为虚的气正是突然闯入的“外在”,它否定了大地的实体性,与其相互渗透。三、四句的括号在法语中有题外话之意,实际上是诗人对所使用意象的一种怀疑,因为超现实主义的意象滥用引向的是彼岸世界,这是雅阁泰一直所扬弃的。似梦似幻的暗喻仍然属于“外在视野”,诗人想用不同的意象来“最大程度地界定风景之真理、内心共鸣的多样性”[1]351。最后一个是“多重视野”,将风景中的各种元素编织在一起,形成相互生发、相融无间的统一体。前四句一句写实一句写虚,韵律跳动于句与句之间。第五句的首个词“两者之间”(entre)将坚硬的石头与超逸的遐思联系在一起,乍一看,两者似乎毫无关联,但雅阁泰的用词实则极其考究,他在作品中屡次写到“岩石变为雾气”[14]57,颇有中国古代“云根”之遗风。“云根”之说完全不是东方式的奇思异想,它关涉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宇宙的方式,即人融入天地之化育而不是其观察者,正如雅阁泰说的那样:“这些(个)表达试图揭示既不有关世界也不有关我而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真理。”[14]57最后一句中的指示词“cette”给我们指明了人的在场,按照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理论,指示词的使用一般是在话语中,禀有这里和现时的功能,它涉及陈述活动的发送者与接受者。
此外,指示词在法语中一般都为虚词,为何诗人用一个空空如也的词来指涉主体的存在呢?这种以虚代实、计白当黑的写法与中国的“虚心纳万象”遥相辉映,雅阁泰一颗净水禅心,自我的虚化是为了映射万物的光辉:“自我的隐退是我发光的方式。”[26]76那么这只“逃逸的白鼬”作何解释?也许它就是这世界的本真面目,永远游走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易经》中的“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可为全诗作注脚,它始于大地的宏观视角而终于一片雪的微观世界,似中国竖立的山水画,目光由远及近,由高到低,逐渐返于眼下的这片雪,流连盘桓于白鼬斑驳的踪迹,可谓“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但是诗人也隐约感到在这变中有一个不变之物,是它使得万物周流不息:“不可见的力量,世界的中心在片刻又重新呼吸:化育为树木山川,但是在注视的目光看来,出现了它们的脆弱性,它们的运动,它们时隐时现的本质。”[20]43雅阁泰笔下的“中心”在程抱一看来就是“道”,要想抵达这个中心,需要超越气聚气散的风景之本身,从而洞悉大道之光辉。
四、景与景外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重要命题,程抱一在《美的五次沉思》中是如此介绍的:“风景要超越其单纯的象,而以显现的形式出现。”[10]160换言之,在景之外确实存在着超越它的另一维,但这种超验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雅阁泰在《日记》中指出:“在此刻的无限丰盈中和在最具体、最普通、最日常、最卑微、最当下的事物的静观中难道不能发现绝对和超验吗?”[27]100在此在(ici)中让彼岸(au-delà)闪耀,在感官世界中瞥见神性,这是法国当代诗歌最显著的表征之一。这里涉及的是风景所承载的本体论问题,也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中“在”与“在者”的范畴,梅洛·庞蒂在论述可见与不可见关系时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不是一个实在的不可见,就如隐藏在背后的物体,亦不是一个绝对的不可见,与可见毫无关联,而是这个世界的不可见,它栖居于此,支撑着这个世界,使其可见,它内在及自我的可能性,这个在者的在。”[13]193这个终极的“在”在程抱一笔下演变为“太虚”“道”“无”等具有鲜明道教色彩的概念。在雅阁泰作品中则化为“至高”“绝对”“无限”甚至“上帝”等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词,然而,他声明“剥离了任何宗教上的参照”[3]31,因为除了上述词外,他使用更多的是诸如“神”“气”“光”这些意义弱化的表达。为了呈显风景之外“在”的晶莹真境,首先要超越风景的现象性:
说出源自你的,
说出支撑你的;
超脱种种偶然。
世界期待被说,
为此你才到来。
你所说属于你:
真生以及密匙。[12]145
“源自你的”很可能就是诗人眼下的这片风景,而根本在于把捉使风景成为风景的东西,对程抱一来说,“风景的表征越是精彩越是得益于赋予其活力的太虚”[28]90。雅阁泰也有着同样的看法:“物还是物,草还是草,但是有物在后面闪光,忽而在下,忽而在里。”[29]66真正“期待被说的”世界是凌驾于现象世界之上的,雅阁泰将之归于“气”之活力:“所有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刻不稳定的平衡,两种不同力量的相遇,勃勃生气中的短暂停止。”[30]20
不能陷入“象”之现象性的泥沼中,因过于有棱有角,但又不能脱离之,要使其剥离有形的外壳,跳出物质的厚实性,让气渗透之、鼓荡之、升腾之,达到生气远出之境。雅阁泰深谙此道,风景在他笔下氤氲磅礴,飘飘欲飞,动静相宜。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开花的扁桃树“是一团似白非白的雾气,悬于大地上”“一片悬于空中的云彩”“天地之间的霰”[20]177;而“看不见的鸟儿的叫声”好像“悬于空中的气泡,视而不见的小球,在空气中翻腾着”[3]75;山“飘了起来,悬于气中,只是一大朵云”[31]9。对此雅阁泰有他自己的解释,好似出自一位澄怀味象的高人之口:“对于长流不息的神来说,所有事物都是气的暂停,是暂时的,是片刻的休憩。整个宇宙就像悬空的气。一阵风飘落花园,当风再起时,物化了;但一切如是,神在永恒地呼吸。”[20]43神的呼吸不言自喻,万物也在呼吸,词语的炼金术就体现在“之间”“悬于”这些表达上,我们知道,“之间”(entre)也是程抱一融贯中西的一生最鲜活的写照。通晓中国文化的于连阐明了这个词最隐秘最根本的含义:这个“之间”并非“事物之间”,“而是内在于事物之本身……是让事物丧失‘自我’或者跳出‘自我’,将其引向缺失,弱化其充实性、打开其自在性:如此它才会呼吸,释放自我,气脉畅通,融于万物”。[24]146明乎此,困扰两位诗人许久的奥秘才有了“密匙”,万物得到了根本性的敞开,“真生”从遮蔽走向敞亮。
在超越了风景之本身后才能进入至高的神之境界,也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神韵”:“神代表了超于气的状态……它和气一样指向宇宙的根基。根据中国的思想,元气是万物动力,而神掌控宇宙的精神与意识。”[10]157宇宙的神与人的精神若想产生共鸣,不可目视,只能神遇,程抱一借小说人物天一之口点破玄机:“因为真正的现实不限于外部的绚丽,它是意境。它丝毫不是画家的梦境或者幻想,而是气与神所承载的宇宙大化。既然由神与气推动,那只能以心灵的眼睛才能看到,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慧眼。”[16]173我们先来看雅阁泰的一首诗:
我不知,不知如何说
否则,如一天夜晚,高空中打开
在视觉之外
甚至不是打开:
存在在那,大开的存在[31]99
从“打开”一词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从有蔽走向无蔽,清朗朗地显现出其真面目。最后“大开”的表达令我们想起里尔克,在大开中任何时空、物我、生死的界限都不复存在,所有都连成一片郁郁勃勃的生气。人要想进入存在的澄明之境必须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因为语言的表达功能已丧失,眼睛的视觉也被剥夺了,唯有庄子的“坐忘”才是众妙之门,这正如雅阁泰的自我抉择:“对自我的关注遮蔽了生命。一刻真正的忘我,所有屏障变得透明,以至于我们能看到光芒的底部,目力之所能及之处,同时,一切都轻盈了。因此灵魂真的化为小鸟。”[20]1如果说这首诗是于空寂处见流行,那么程抱一的诗就是在流行处见空寂:
山丘乐音回响心中
我们心中波涛汹涌
万物无不乡音娓娓
万物无不吐露心声
水气荡漾,月桂婆娑
神明在那显露,倾听一切
欢迎之神、联姻之神、和谐之神[12]114
诗人摒弃了所有感官而独尊听觉,但是此听觉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听,更准确地说是“听之以气”,或者诗人已化成无形的气,与物神游,因为气通万物,所以山丘的乐声才能回荡在我们心中。作为主体的我们成为万物的倾听者,老子口中的“山谷”,或者雅阁泰笔下“世界的仆人”:“万物渴望缓慢地化育……呼吁我们精神的帮助使其摆脱重力,渴望穿越我们,从我们的口中重新出来,就好似它们努力变得越来越玲珑透亮,不断攀向一座顶峰。”[9]131水气相互转换,不为其形所拘囿,由虚入实,由实返虚,往复无穷,鼓荡翻卷,其间荡漾着一股冲虚之气,气象万千,大化流衍。我们注意到两位诗人在将最终本体在敞开状态中呈现出来时都使用了一个副词“那里”(là),它正是景外的明证:“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越过现象的屏障,我们感到一个往返于自我的在场,完全的,统一的,不可言传却也不可否认,就像慷慨的恩赐,它使得一切都在那,神奇般地,发着太初的光芒,吟着一首心与心、灵魂与灵魂交流的歌。”[10]160物与人在神的欢迎中相拥,天地得以联姻,万物交相辉映,最终达到天、地、人融于互摄互映、互生互化的琴瑟和鸣之境。
五、结语
在程抱一与雅阁泰的视野下,风景成为一个可感、可触、可看、可居的四维空间。勃发兴腾的情感是风景与人相遇的脐带,为人重返有血有肉的大千世界奠定了基石。人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在体,风景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存在,两者融于梅洛·庞蒂“肉身的主体间性”[17]1281中。风景与主体通过肉身、目光彼此交流达到互相交叉、双向渗透的状态。然风景的本质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它迫使诗人不断尝试、探索、重新书写,因为在动静虚实背后藏着更深的本体存在,只有透过风景空灵俊逸的表象才能达到对真理的直接砥砺。我们可以用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兴会”“应目”“会心”“畅神”来加以概括。二战后深陷价值追问和意义求索危机的这代法国诗人都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禅宗思想(7)参阅Jaccottet,Philippe.L’Orient limpide in Une transaction secrète,Paris,Gallimard,1987.Thélot,Jérme.Verdier,Lionel.Le haïku en France:Poésie et musique,Paris,Éditions Kimé,2011.Gaspar,Lorand.Approche de la parole suivi de Apprentissage avec deux inédits,Paris,Gallimard,2004.,在古淡澄静、心与物冥的禅诗中觅得了救世良药。他们在神性根基坍塌之后高举生命体验的大旗,强调通过感性来感知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利用肉身化主体、在世存在等理论撼动西方传统哲学所构筑的二元论大厦。在他们看来,风景(Paysage)正是通往“家园”(Pays)的必经之路,而这个家园已不再笼罩在意识的阴霾之下,它更趋近于梅洛·庞蒂笔下“认知一直所谈论的前认知世界”[2]3。这种与世界建立的“前科学体验”,使得对朴素世界深切依恋的诗人们将风景视为“我们思想的故乡”[2]32,呼吁我们走出系统化、技术化的抽象语言,淡化并消解超然的我思,在境遇中去真切地体味缥缈多姿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