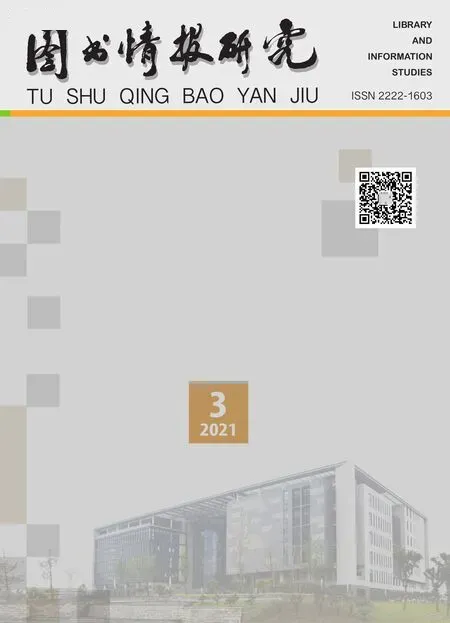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目标、路径与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1 引言
在五千年连绵不绝的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涉及领域包括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含种植、林业、畜牧、渔业、蚕桑等)、水利、交通、纺织、医药、机械、建筑、勘探、冶金、造船、航海、造纸、印刷、陶瓷等诸多方面。诚如李约瑟所言,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1]。然而,受传统儒家思想及封建科举制等因素的影响,古代官方及民间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历来不是很重视,常视之为“奇技淫巧”,像明末《天工开物》这样的科技名著,清代四库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连书名都不曾提及,后几近失传,近代在日本被发现后才返流到中国。其他科技文献的散佚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自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在古代科技文献整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古代科技门类繁杂,文献数量众多,存在形式多样,且在内容和文字上与普通文献一样存在散佚、失真和讹、脱、衍、倒等不同情况,加上学术性、专业性强等特点,整理起来有相当难度。关于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现状,笔者曾撰文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出版的历程作了整体性回顾,从多学科综合性整理、单学科专题性整理(包括古代科技文献书目的编纂,古代科技文献的点校、注释和今译,古代科技文献的汇编、选编与影印,古代科技文献专题数据库的构建等)两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取得的成绩,但也指出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家底不请、学科失衡、界限模糊、体例相杂、学术失范等问题[2]。今接续前文,继续探讨现阶段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目标、路径与实施方案问题。
2 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目标
古代科技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都是由物理载体与记录内容组成的。但与珍稀的古籍善本不同,古代科技文献的整理更侧重于文献内容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重在发掘其学术价值,而不重点关注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古代科技文献的整理应达成以下三个目标:
2.1 保护古代科技文献资源
与普通古籍一样,古代科技文献也存在因历年久远而发生纸张霉变、虫蠹、脆裂等情况,因此要通过对存放环境(如温度、湿度、光线、灰尘等)的控制,使其文献实体的物理寿命尽可能地延长。但对于古代科技文献而言,文献内容的保护更为重要。由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科技文献记录内容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有的以著作的形式存在,比如《考工记》、《周髀算经》、《天工开物》等;有的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存在,比如被收入杂家名著《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被收入子书《管子》的《地员》篇,被收入文集《蔡端明集》中的《荔枝谱》,被收入丛书《说郛》中的《蜀笺谱》;还有的是以零散的片段式文字出现在历代经书、正史、方志、笔记、文集及阴阳、儒、墨、名、法、道、农、兵等诸子百家的著作甚至档案文献中,比如载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综合记载了很多物候、气象、天文、渔猎、农耕、蚕桑等方面的知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多有与农业、蚕桑相关的诗句。内容极为分散的特点,造成了我国古代科技知识缺乏系统性,如果不及时做集中整理的话,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因此,著名农史学家夏纬瑛还曾专门对《夏小正》和《诗经》进行过整理与研究,撰有《夏小正经文校释》和《〈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
另外,古代科技的各个门类之间发展是不同步的,这造成了科技文献的数量比列失衡。因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原因,医学与农学在我国古代科技里面最为发达,因而文献数量也最多。据已有的书目统计,我国古代仅医药类文献就有13 000 余种,农业类文献约有3 000 多种,而其他学科领域的科技文献数量则要少得多。但就是这有限的数量,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至于更为具体的学科分布、馆藏地点等,更是不甚明白。这种家底不清的状况加剧了古代科技文献资源保护的难度。
2.2 服务当代科学技术研究
古代科技文献整理服务于当代科学技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史学即史料学,科技史作为史学的分支,其研究过程中当然要大量地运用科技史料。这就对古代科技文献的整理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保证有充分的史料供应。这就需要对历代科技知识的文献记录做系统的梳理,将零星、分散的记录集中并加以系统化;二是要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古代科技文献经过历代的传抄和翻刻,可能存在版本不善、文字错讹、文献作伪、内容散佚等问题,这就要求运用文献学的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对它们进行整理,使之尽可能恢复或接近文献最初的面貌。
第二,为中国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贡献古人的智慧。古代科技文献是古人科技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科学思想和发明创造,至今造福人类,有的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仍有启示作用。例如,我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采用低温萃取法,成功提取了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历代典籍中关于地震、旱涝、蝗灾、瘟疫等自然灾害的海量记录,对于研究自然灾害的发生周期性规律,进行科学预测和预防具有重要价值;我国海洋油气平台的钻井技术,也是受到四川自贡古老的卓筒井的开凿技术的启发。因此,运用文献学及现代信息技术的方法,将蕴藏在古代科技文献中的知识和智慧揭示、报导、挖掘出来,也是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重要任务。
2.3 弘扬优秀的古代科技文化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先贤们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与西方近代科学重视逻辑实证和理论研究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固然存在过于强调经验、侧重社会伦理、轻视理论研究等不足,但其中孕育的中华民族的对自然的大无畏探索精神,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认识世界的整体观,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关注国计民生的实用主义思想,等等,在当下的科学技术发展中仍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对古代科技文献的系统整理,完成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文化的全景式梳理和总结。这有助于弘扬优秀的古代科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的话语权。
3 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基本路径
笔者在《简明古籍整理教程》一书中曾将古籍整理的路径划分为五个层次[3]:古籍实体的保存性整理、古籍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古籍语义的阐释性整理、古籍内容的组织性整理和古籍知识的数据化整理,且每一层次都有与其对应的文献整理方法。古代科技文献大多属古籍的范畴,因此这一划分对古代科技文献的整理也是完全适用的。
3.1 古代科技文献实体的保存性整理
古代科技文献的文本内容、语义思想和知识信息等,都是依附于文献实体而存在的,因此古代科技文献实体的保存性整理是后续整理的前提和基础,其整理方法包括对分散保存的古代科技文献的采访、典藏和修复等。与普通文献一样,古代科技文献的采访也有调查、征集、购置、捐赠、交换等方式;典藏包括入库验收、上架、保管、流通等环节;修复则以“整旧如旧”为基本原则,在修复过程中做到安全第一、最少干预和过程可逆,最大限度地延长其物理寿命。古代科技文献实体的保存性整理可依附普通古籍的采访、典藏和修复工作,通常由图书馆、资料室等文献收藏机构来完成,此不赘述。
但古代流传下来的科技文献的物理载体终究是要老化、消亡的,因此必须进行内容的迁移。在这个内容迁移的过程中,古代科技文献的实体也发生了转换。因此,古代科技文献的实体保存性整理衍生出了影印、制作缩微胶片和数字化等新的形式。像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大型丛书,常采用原版影印的方式,有时也会加入导读、点评、注释、提要等其他整理方式,如中医古籍出版社自1993年陆续推出的《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中筛选宋、元、明、清各代刻本、写本、名医手稿、珍籍秘方等孤本300 余种,分15 卷影印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影印近百万字的各个时期的陶瓷史料以及《陶说》、《景德镇陶录》等陶瓷古籍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科技译著集成》,影印江南制造局翻译和引进的162 种科技译著,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测绘、气象、航海、医药卫生、农学、矿学冶金、机械工程、工艺制造和军事科技等学科领域。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数字化起步较晚,早期多采用书目数据库的形式,用于揭示馆藏和检索古代科技文献,之后出现了单书检索系统,至今发展成书目、全文、影像多种数据类型并存的局面,但数字化成果总体数量偏少,代表性的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建成的农业古籍数据库、中国中医科学院承建的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等。
3.2 古代科技文献文本的复原性整理
古代科技文献在流程过程中存在文本内容失真的情况,文本复原性整理方法包括:通过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考订,选择古代科技文献的善本,作为阅读使用或进一步整理的底本;通过不同版本及他书资料之间的比对校勘,解决古代科技文献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文字及篇章次序问题;通过各种辨伪方法,确认所整理的古代科技文献不存在内容作伪的问题;通过各种文献辑佚的途径,恢复古代科技文献部分缺失或整体亡佚的文本内容。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解决了古代科技文献文本的可靠性、准确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
在古代科技文献的版本研究方面,已有系列研究论文发表,如赵燏黄的《〈本草纲目〉的版本》[4],杨维益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之版本及其内容沿革探讨》[5],肖克之、李兆昆的《王祯〈农书〉版本小考》[6],潘吉星的《〈天工开物〉版本考》[7],肖克之的《〈齐民要术〉的版本》[8],崔锡章的《〈脉经〉版本流传考略》[9],肖克之的《〈农桑辑要〉版本说》[10],李飞、李莉的《古农书〈树艺篇〉的版本流传及其价值研究》[11],张雯的《〈黄帝内经〉著录版本源流考》[12],李明杰、陈梦石的《沈括〈梦溪笔谈〉版本源流考》[13]等。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古代科技文献的版本研究多集中在农学和医学名著上面。
古代科技文献的文本复原性整理,以校勘的成就最高,且成果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如农学方面有夏纬瑛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中华书局1956年)、《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1956年)、《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沈冬梅的《茶经校注》(农业出版社2006年);医学方面有黄龙祥的《黄帝明堂经辑校》(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87年),刘渡舟的《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陈自明的《妇人良方校注补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李积敏点校《经验广集》(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田文敬等《太平圣惠方校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数学方面有刘五然的《算学宝鉴校注》(科学出版社2008年);天文学方面有邓文宽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赵友钦的《中外天文学文献校点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陶瓷学方面有陈雨前的《中国古陶瓷文献校注》(岳麓书社2015年),周思中的《中国陶瓷名著校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以上所举,只是部分所见。从书名来看,多数是在校勘的同时,也完成了标点和注释,有的还涉及补遗。这些校勘之作,多由各专门领域的专家完成,学术质量很高。偶有瑕疵的,可结合后期的一些勘误性质的论文来纠谬,如卢家明的《古代科技文献点校疑误举隅》[14]。
古代科技文献的辨伪和辑佚成果相对少了许多。因为科技文献在古代不受重视,作伪情况不似经书和其他子书那样严重,所以辨伪成果相对较少。但我国对科技文献的辨伪起源很早,如《汉书·艺文志》对《神农》十二篇的辨伪:“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15]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科技文献散佚严重。以两宋科技文献为例,《宋史·艺文志》著录农学、医学、天文、历数类文献合计920 种,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只有300 种[16]。隋唐五代以前的留下来的就少多了,如李淳风《九章算术注释》在唐代流传还比较广,被收入《算经十书》,成为国子监算学教材,但《宋史·艺文志》却无记载。先秦两汉文献留下来的更是十不存一,据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17]统计,汉代所藏农学文献9 种,至近代时皆亡,只有6 种辑本存世;天文类文献21 种,只存1 种;历谱类文献18 种,只存2种数学文献;医经7 种,只存1 种,还是残本;方经11 种,只存1 种。东汉张衡的《灵宪》是天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阐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日月星辰的本质及其运行等重大问题。他的另一部天文学著作《浑天仪》测定出地球饶太阳一周所需时间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这两部著作在《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但到了《宋史·艺文志》中均不见著录。
清代学者对古代科技文献的辑佚作出了杰出贡献。笔者据孙启治、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18]统计:农家类文献有辑本30 种;医家类文献有辑本10 种;历算类文献有辑本有35 种,其中就包括王谟所辑的张衡《灵宪》、洪颐煊所辑的张衡《浑天仪》;术数类文献辑本86 种。不过,以上161 种古代科技文献的辑本全都是清代学者所作。比较而言,近现代以来我国在古代科技文献辑佚方面少有成绩。
3.3 古代科技文献语义的阐释性整理
所谓语义的阐释性整理,就是运用传统的标点、注释和翻译等方法,帮助读者准确理解原文的语义。其中尤以注释最多,如石声汉的《汜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夏纬瑛的《〈周礼〉书中有关条文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商君书农政四篇注释》(陕西科技出版社1985年)、缪启愉的《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伊钦恒的《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邹介正的《相牛心境要览今释》(农业出版社1987年)、傅振伦的《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周魁一等人的《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中国书店1990年)等。在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实践中,标点、注释往往与校勘一并完成,如上文列举的各种“校注”即是。
古代科技文献的注释存在一个学科专业性的问题。以《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为例,这三家都是史家作注,都不是术家之注,因此像《史记·天官书》这样的古天文学文献,注释中就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文革”以后吴树平等人又组织了数十位专家作了《史记全注全译》。
3.4 古代科技文献内容的组织性整理
由于古代科技知识的文献记载极为分散,利用起来极为不便,需要对其进行分门别类,以简要的形式揭示和报道其内容。有必要的话,还要对古代科技文献的内容加以重新组织编排,形成新的内容集合,以满足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题需要,这就是古代科技文献的内容组织性整理,其具体方法包括对古代科技文献的编目和编纂。前者是对其内容的揭示、报道和分类,后者是对其内容的重新组织和编排。
我国古代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始于清康熙间梅文鼎编纂的《勿庵历算书目》,后有丁福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编的《算学书目提要》、宣统二年(1910年)编的《历代医学书目提要》。民国时期,又有1924年毛雝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1929年上海中医书局编的《上海中医书局书目提要》等。建国以后,古代科技文献书目的编制在多个学科领域展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53 至2019年,我国共编纂古代科技文献书目54 种,涉及医药、农学、地理、气象、算学、陶瓷等学科。举其要者,如薛清录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王重民的《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中山图书公司1974年)、张卫国和王秀珍的《中国农业气象文献目录》(气象出版社1994年)、李迪的《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荣的《中国陶瓷文献指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88年)等。这些书目基本上是专科性质的,尚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古代科技文献总目问世。
为了满足不同学科、不同专题的对古代科技文献内容的不同需求,还需要运用不同的编纂方法对古代科技文献的内容进行集中、筛选、归类、组织和编排。例如,汇编以文献的丰富性、完整性著称,集中汇集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领域的资料,如《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中华书局1975年)、《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9年)、《藏族古代历算学资料汇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国陶瓷文献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等;选编以文献的学术代表性、版本珍稀性见长,如《中医古籍选读》(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选取《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及温病学主要著作,所选内容以切合临床需要为标准;《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精选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各代医药稀见抄本50 余种,排印点校出版;类编以体例的分类性、系统性为特色,如《中医古籍医案辑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收录历代医学家所编的3000 余种医案,按类分为“疾病医案”、“学术流派医案”、“著名医家医案”、“经方名方医案”四个系列,每个系列下再按类细分。如“学术流派医案”以派为纲,以医家为目,分为“伤寒学派医案”、“河间学派医案”、“易水学派医案”、“温病学派医案”和“汇通学派医案”。文献编纂方法还有很多,如全编、节编、摘编、合编等,此不一一赘述。
3.5 古代科技文献知识的数据化整理
如前文所述,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当代科学技术研究贡献古人的智慧。这就要求文献整理深入知识加工的层面。传统的纸质文献整理方法,多停留在文献单元和信息单元层面,未能深入揭示其中的知识单元。所谓古代科技文献知识的数据化整理,是将完成数字化转换后的古代科技文献的数字文本,当作下一阶段知识整理的数据,然后通过语义标引、数据关联分析、本体构建、知识图谱、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古代科技文献的内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以实现知识发现和知识重组的功能,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知识服务。
古代科技文献知识的数据化处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成果不多。略举其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柳长华教授主持开发的“中医药古代文献知识库系统”,支持中医知识的分类检索(病症、医案、方剂、本草),当输入一个或一组中医概念时,系统会判断此概念的类型,并优先输出此类知识的检索结果,其他知识则按关联度的大小排列。该库是在基于知识元的中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19]的指导下,对古籍深度加工标引后所形成的成果。再如,丁侃梳理了“基于知识元的中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系统表述了中医古籍元数据规范体系,通过对中医古籍元数据的研究,构建了以知识元结构为标准的中医古籍元数据分类体系,并列举了六种类型的中医古籍知识元实例,示范了中医古籍语义元数据在知识元标引中的应用[20]。
要说明的是,以上五个层次的古代科技文献整理路径虽然在逻辑上是逐层递进的关系,但在具体整理方法上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彼此融合的关系,比如有的古代科技文献在考订版本、校勘文字的同时,也完成了标点和注释;有的古代科技文献在影印的同时,也完成了汇编或选编,甚至加入了导读、提要等。
4 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从读者的角度讲,他们对古代科技文献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有的可能需要阅读整部文献的内容;有的可能只需要解决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有的需要通览整个学科领域内的所有文献;有的则只需要精研某个作者、某个学科领域内的代表作;有的注重比较研究同一种书不同版本的不同记载;有的可能关注古代科学家的成长、科技思想的形成过程。而古代科技文献的数量既多且分散,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一两次系统的整理就能满足所有读者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笔者在2019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课题设计中,提出了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四个设想。愚以为,这些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4.1 编纂《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
困扰我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源保护的一个长期问题,就是家底不清的问题。虽然在医药、农学、地理、气象、算学、陶瓷等学科领域已有不少专科性的书目问世,但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水利、交通、机械、手工业、纺织、冶金、建筑、造船、航海、造纸、印刷等众多科技领域还没有相关的存世文献的揭示和报道。当前,就我国古代科技文献的总体数量、学科分布、文献类型、馆藏地址、学术价值等,做一次全面系统的文献普查和揭示报道,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本课题组将对国内各主要大型图书馆展开一次馆藏古代科技文献资源的普查,摸清自先秦以来我国古代科技文献存佚的基本状况,在已有的各种专科书目的基础上,查阙补漏,编制一部全面揭示我国古代科技文献存佚情况、摸清我国古代科技文献家底、整体展示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
《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的编纂将遵守以下原则:第一,在款目的著录上,详尽地揭示古代科技文献的各项信息。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的要求,对古代科技文献的题名与责任项、版本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发行项、载体形态项、丛编项、附注项、标准书号及获得方式项等进行详细著录,并为读者推荐善本。第二,在分类体系上,要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门类,方便读者检索利用。但在具体类名的拟定上,应尊重我国古代书目的传统,适当借鉴其类名。第三,在书目编写体例上,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尽可能为每部古代科技文献撰写解题。解题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通过书目解题,可揭示该文献的成书背景、流传过程、作者生平、学术价值等。而对于没有留存下来的佚书,也可以通过书目解题保存其相关信息,成为科技史的重要内容。
4.2 编纂《中国古代科技代表作选刊》
现存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数量,据初步估算约在2 万种以上(实际数量当以本课题组完成文献普查后公布的数字为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全部影印出版。其中既有学术价值很高的传世精品,也有鱼目混珠的劣品、俗品,这就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认识上的模糊。因此,从各个学科、技术、工程领域内遴选出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经典文献,集中展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本课题组拟咨询科技史领域的专家的意见,在各学科领域内遴选出一批版本优良、校勘精审、内容完善、学术价值高的代表作,以《中国古代科技代表作选刊》的形式影印出版。该丛刊的编纂应遵从以下原则:第一,严格按照《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设定的古代科学技术门类分类编排。但有的学科如医学、农学,已有代表作影印出版的,可不必重复。第二,文献的影印要遵从学术规范,尤其要精选版本。古代科技文献与普通古籍一样,存在大量同书异本现象。以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例,就有不下60余种版本。因此,必须考察古代科技文献的版本源流,从中选择最好的底本。在这方面,一是可以利用前人版本源流考订的成果,二是直接借鉴善本书目,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顾宁一主编的《中医古籍善本书目提要》、傅景华等主编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余瀛鳌与傅景华主编的《中医古籍珍本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等。第三,每部科技文献应撰写导读,介绍该书的产生背景、成书经过、作者生平、主要内容、学术价值等,可直接借鉴《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的书目解题。
4.3 建设“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文数据库”
数字化是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的必然趋势。古代科技文献的纸质载体的寿命终究是有限的,如不将其内容转移到新型载体上,承载着古人科技智慧的文献内容必将随着纸质载体的腐烂而消亡。再者,现有的古代科技文献大多以纸质的形式分散保存,科技工作者利用起来非常不便。通过建设“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文数据库”,既可以实现我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源的集中管理和长期保存,也可以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快速高效的文献检索服务,而且还可为后期的数据加工和知识挖掘打下坚实的基础,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建设要求是学科门类齐、文献数量多、数据质量高、检索功能强。数字化是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源长期保护的必由之路,而且从单位成本来看,文献数字化要比纸质文献影印低得多。因此,建设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文数据库的首先要求就是收录文献要全面。其次,该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必须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这就要求文献数字化必须遵守传统文献整理的学术规范,包括数字化之前的底本选择、数字化过程中的文本校勘等。在涉及异体字、讳字等待有时代特征的文献信息时,应尽可能原样保留;对于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特别是一些器物、草药名词等,可用超链接的方式嵌入辞典工具;适量添加书影,提供图文对照。再者,应提供丰富便捷的检索手段等,包括分类检索、题名检索、作者名检索、全文关键词检索等。该数据库建成之后,未来还可进行数据分析和知识挖掘,提供更多的知识产品。
4.4 编纂《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必然要关注和研究古代科技人物。实际上,历史上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与科技人物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经历等方面是密不可分的,而人物传记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科技人物也是科技思想的天然载体,通过对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发展的脉络。因此,科技人物的传记资料也属科技文献范畴,而以往的文献整理忽视了这一点。已有的成果中,人物收集也不够全面,如《历代科学家传记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只收录古代科学家37 人;《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2年)收录古代科学家传记249 篇,但所收人物偏重科学家,技术、工程领域有影响的人物鲜有收录。
本课题拟对中国古代所有科学、技术、工程领域内有学术贡献的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进行涸泽而渔式的搜集和整理,编纂一部《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文献搜找范围包括历代正史、类书、丛书、文集、野史、方志、家谱、碑志、文集、学案、书目提要等。对于有的古代科技人物而言,可能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没有单独列传,其个人身世只有只言片语。这就要求在转录传记资料时,应分别采用全录、节录甚至摘录的方式。对于单篇传记还要为之编写按语,对古代科技人物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和学术贡献进行介绍和点评,同时用备考的形式注明传记资料的文献出处。
在编纂体例上,《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拟按照传主所属的科技门类归类,类下再按年代顺序编排。这样做的优点是,能直观呈现各领域内科技人物数量的多少,纵向揭示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发展和传承脉络。要说明的是,古代科技人物不仅包括在学科理论上有建树的科学家,也包括在技术、工程领域有发明创造的能工巧匠。只要是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有所发明、发现和创造的历史人物,都可归入科技人物的行列。该书的编成,可为后期古代科技史研究提供古代科技人物的学科门类、数量、籍贯、职业等相关的统计资料。
5 结语
古代科技文献整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远不是一两个项目和几部工具书的编纂就能轻松完成的。本文提出编纂《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总目》、《中国古代科技代表作选刊》、《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资料汇编》以及建设“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全文数据库”的方案,只是粗略地构筑了中国古代科技文献资源保障和服务体系。实际上,在这个大的体系框架下,古代科技文献整理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比如单种科技文献版本源流的考订,单种科技文献内容的点校和注释,海外中国古代科技文献的调查和回归,等等,目前已经完成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需要有关部门制定长远的古代科技文献整理规划,有条不紊地扎实推进,并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才能最终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