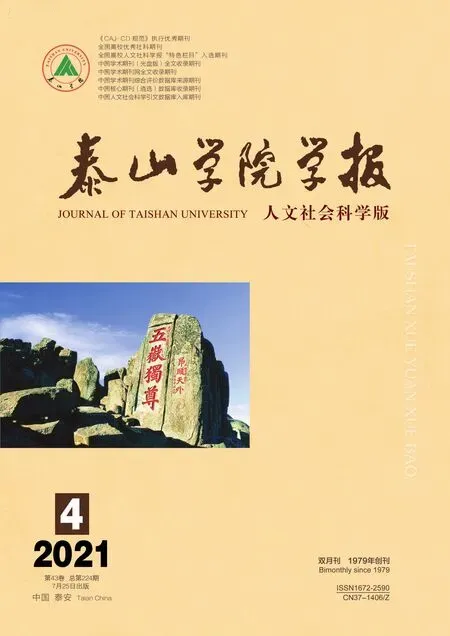从《论语》开篇看儒学视野中的学习观
魏建培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271021)
人是什么?这是古希腊哲学恒久追问的问题,无论是柏拉图在《斐多篇》,还是亚里士多德在《灵慧论》里,都在追问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毕德格拉斯回答:人的本质即存在,是一颗永恒、自给的灵魂。苏格拉底至理名言“认识你自己”,指的就是“认知”这个本质的灵魂。而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是生生不息的演变的过程,人也不是给定的本质性构成,而是一个与宇宙耦合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的存在。人与天合一,是一个自发的创造性存在。所以,古代中国关于“人”的哲学问题不同于古希腊的“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追问“何以成人?”儒家的回答是“学以成人”。儒家的人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造性转化、提升为“仁”或“圣”的过程性存在。这一转化提升过程,就是通过“学”,学在儒家传统中具有核心价值。所谓“学”首要是快乐的享用,享用生活,享用自然,享用人类文化传统,享用作为创生、开辟内在人格世界的手段。享用是创造性自我的转化与提升,通过创造性自我的转化,使自我具有了诞生性——仁性主体不断生成;把内在人格世界的价值,作为创造新生活、新文化传统的动力与原理。自我的诞生性使生活世界和宇宙具有了诞生性,自我参与了生活世界和宇宙的创造性转化。所以,儒家创造性学习,是以个人人格世界成长为核心,仁智合一、知行合一、身心合一的过程。
作为哲人的孔子,在《论语》开端,以最为凝练、高度概括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出了贯穿《论语》甚至是贯穿整个儒家古典文本的一个根本性的哲学人类学问题,以及最为切近人、切近生活的儒家学习之道。这正体现了孔子的高明之处,这么深邃的、建基于宇宙观和人性观基础之上的学习观,孔子竟用如此平淡无奇、妇孺皆知的语言,给出了最为切中的表述。作为哲人、师者楷模的孔子,把“学习”本质定义为人之为人的创造性存在,是人终其一生的存在方式。
一、“学而时习之”——学习即自我创造性存在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表达的,正是学习作为人的存在之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人要通过学而成为“君”,君即仁者或圣人。这表明儒学的人是一种关系性、形成性的创造性存在。但“君”不是一日炼成的,而是要把学作为自己存在于世的根本方式。“学”指学成人(仁、圣)之道,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而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道”、“见道”、“学道”,即效法仁者(圣人)。何为习?甲骨文中的“习”是“羽”字下从“日”,意指鸟儿在晴天里试飞,“日”属阳,所谓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即为“习”。引申为人要根据社会现实不断效仿圣人之道进行践行。后来篆书误把“日”写成“白”,流传下来。故“学”而“习”,就是学成人之道、对照成人之道,在社会中不断地创造、提升自我,与时俱进地行成人之道。
(一)学习作为自我创造性存在
学习是自我创造性存在,也是个人与世界建立互联关系的本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部《论语》所表达的,皆为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的自觉。叶公曾以挑衅、嘲讽的口吻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这句话充分道出了孔子是如何看待自己和看待学习的,即把自己作为一个终生的学习者,把学习作为生命追求和存在于世的方式。“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视学为生命本质,从容而淡定地看待人世浮华,以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了人生自由旷达境界。如王阳明所言“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所学之物转变成自我生命意向,以及在这种意向中个体生命充实,由此达成一种非关外在事物的生命之‘悦’”。①刘铁芳.学习之道与个体成人:从《论语》开篇看教与学的中国话语[J].高度教育研究,2018(8):15,14.学习对个人生命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或工具。学习是在个人存在层面展开的,而不是技术方法层面的行动,是个人努力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本质性行动。正如荀子《劝学》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所学,以为禽犊。”学习是充实自己,成就自己,是个人生命和生活本身,是主体精神的建构本身,而不是显示自己。
学习的本质是成长,是创造自我存在的方式。学重在理解自己的内在人格,习重在行动与创造。“由孔子所开辟的内在人格世界,是从血肉、欲望中沉浸下去,发现生命的根源,本是无限深、无限广的一片道德理性,这在孔子,即是仁;由此而将客观世界乃至在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成就,涵融于此一仁的内在世界之中,而赋予意味、价值;此时人不要求对客观世界的主宰性、自由性,而自有其主宰性与自由性。这种主客观的融合,同时即是客观世界的融合。这才是人类所追求的大目的。”②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1-62.此一内在人格的创造,需要不是单纯的思辨功夫或信仰的指引,而是人在生命中自觉地反省与创造性的行动。
(二)学习是立身于生活世界,享用生活并创造生活
学习源于生活并创造生活。在儒家看来,“人是相互联系的社会物体”③[加]安乐哲.安乐哲卷(孔子文化奖学术精英丛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137.,人本质上是关系性、生成性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它通过无可简约的人与人相互关系,人才于自己的行为中变得学会反思自己,从而诞生了自我意识,因此具有了追求亲和关系的自由与创造性。所以,学习则意味着融入生活关系之中,探索并享用生活的滋养、转化并创造自己的主体精神,凭借学习生活而生活,个人的生命靠学习而成长,即个人有赖于学习而建构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儒家的学以成人过程,是在生活世界与他人的关系和交往之中进行的,个人成长是与家庭、社会不可分离的。人不是亚里士多德式“心灵”意义的独立个人,而是相互联系的群体的人,人通过多种多样的关系与身份建构自身,创造机会走自己的路,去追求行为和做人的中庸之道。本质上,人就是自己众多身份的结合体。儒家的人是在生活关系之中学以成人,实质上是追求在关系之中的具体的自由成长。这种自由不同于古希腊传统的本质的个体观,儒家思想的自由是具体的:在家庭身份与社会关系中能够充分地实现自己。
首先,学习是在家庭、社区、社会、学校进行的活动,是生活情境性的活动。知识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个人的认知是在生活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学正是将外部的、存在于主体间的东西转化为内在的,为个人所持有的过程,而习则进一步表明不能只依靠自身的经验进行“学”,必须把个人认知与生活世界互动,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命表现在意义的追求之中,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活意义,人的生活即人的生命求得意义的活动。”④金生蚆.学校教育生活之于儿童的意义——对儿童享用教育生活的现象学解释[J].教育研究,2018(6):8-15.生活世界“作为由人的生成活动所展开的世界,是通过人自己的活动而生成的时空,即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本质上,人的生活世界是构造的,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①刘铁芳.学习之道与个体成人:从《论语》开篇看教与学的中国话语[J].高度教育研究,2018(8):15,14-22.学与习是整个人的具身参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生活的活动过程,该过程包含“学”和“习”两个环节。真正的“学”总是蕴含着某种创造自我德性主体的生命实践的意向,“习”则是与时俱进地基于生活世界创造自我德性主体的生命实践。所以,“学”与“习”作为成人之道带来自我主体性的不断深化、充实与圆融,并由此带来生命自得之“乐”。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乐正是颜回之乐,一种专注于学、不假借于外物所创造的生命之乐。生命因学而精彩,因习的践行而升华。
其次,学习是建构世界意义的本质方式。站在人类生命、精神、文化历史传统的视角来看,每个人都是被抛入到人类文化传统之中的新来者,新来者通过给人类带来新生,带来人类新的希望,使人类面向未来时间的维度上有可能获得生命、精神、文化、历史传统的展开、传递与创生,使人类重新具有了诞生性并获得传统的历史性升华。人类生命、精神文化传统生生不息,学习的过程是人类繁衍更新这一基本过程的核心,代际生命、精神文化传统传递与更新仰赖于学习。
“学习”乃是享用、发展人类文明传统,是我们更加全面觉醒到自己对于人类文明传统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一个人通过学习不断地让自己切入生活、切入人类世界,就像人的一次次诞生,即具有创新性。人以自身的学习主动开创了某个新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学习在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学习通过个人的诞生性给了这个世界诞生性,这是提供和维护世界的根本,是将世界和人类事物领域从通常的“自然”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奇迹。正是由于学习使后来者历史性进入人类文明传统之中,圆成新一代的生命成长,进入到生机勃勃的生活之中,开启人类文明传统的新的可能性,赋予传统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活力。学以成人乃是参与传统,继承传统,学会参与到验证、扩充并把它们改良这一无止境的任务中。参与、继承、进入、创新人类文化传统,一点点进入到人类生命理想的代际传递与创生之中,使人类生命、精神文化传统代代生生不息,此乃参天地造化,是学习作为建构世界的意义本质方式。
人类的世界因为学习的诞生性而具有了诞生性,世界因此获得了新生和新的意义,进入创生和更新、处于不断诞生之中,人类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处于不断绽放之中,学习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与精神双重超越。这意味着学习使世界具有了历史与传统,历史与传统又使得人类生活成为代代共同生活世界。
二、“有朋自远方来”——学习即合作创造
“学而时习之”,感而“有朋自远方来”。“有”通假“友”,“友”在甲骨文为“双手并列”,引申为为共同志向而联手、互助合作。“朋”者,“凤”之古字也,本意为凤凰。“朋自远方”者,“有凤来仪”也。《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实出于此。“有凤来仪”之地,即人杰地灵之地,文明教化之地。而行“成人(仁、圣)之道”的君子,就是“人中之凤”,行“仁”之君子“自远方来”,即“有凤来仪”。“仪”者法度也。“朋自远方来”干什么?法度也。以“文明之道”法度之,教化之,使文明彰显天下,这才是真行“成人之道”。“远”,遥远、久远,不单指空间上的,“仁之道”不是凭空而起,源远流长。“方”,非“方向”而是“旁”的通假,广大之意。与朋友为共同志向而合作,为共成“成人之道”而同行,可以相互启发、相互赠与,帮助对方各自打开意识阻滞,实现经验与意义的重构,创造新的自我与世界,将儒家的成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成就“人(仁或圣)之道”。
(一)有朋自远方来——合作创造新的自我经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达了儒家学以成人的关系观,正如罗思文所言,“在很大意义上,我自己的身份不是我个人实现的;我自己变成什么样子,我自己负的不是全责。当然,要成为一个好人也需要大量自身的努力。不过不一样的是,很大程度上,我自己是谁以及我该怎样被认同,主要取决于他人,与我互动的他人,正如他们是谁、该怎样被认同,也部分地同时取决于我对他们的作为。”①Rosemont(1991b).转引自: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M].孟巍隆,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3.所以,人是完全处于境遇、情势、关系中的人;学以成人、做人,无非就是大家一起做角色之事与关系之事,否则就难以成人、做人。仁义丰厚的朋友关系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资源,它使家庭、社会与世界处于不断诞生性之中。如唐君毅所言,“且物必与他物感通,而后愈有更大之创造性的生起……个体之德量,由其与他物感通,新由所创造的生起而显;亦由时时能自觉地求所感通,求善于感通,并脱离其过去之习惯之机械之机械支配,及外界之物之力之机械支配,而日趋宏大,但此非一般物之所能,唯人乃能之耳。”②唐君毅.唐君毅全集·第四卷[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100,98-100.远道而来的朋友,把我卷入到了新的相互感通的关系之中,把我带入到了新的观点、境遇之中,看到了自己的习惯的惰性,开启了自己的新的诞生性,自我处于不断诞生性之中,自我精神生命处于不断绽放之中,朋友给自我带来了精神生命的超越。朋友作为本地生活世界的新来者,他在当地世界中、在当地构成的历时和共在的共同生活中成为美好的人,而这些美好经验、记忆也将进入当地的历史之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种快乐,是朋友到来激发出来的儒家的宗教感,也即获得价值感和人格归属感的那种强烈意义,在充满意义的朋友关系交融成长之中,油然而生;当朋友到来,并诚心诚意渴望在与其关系之上奉献、赠与之时,是朋友间为一种激发的灵感而活着。这种宗教感本身,是个人学习、成长不断诞生新的活力、新的精神、新的希望;这种诞生性也使社会具有了诞生性,社会不断更新、创造新的意义并日益繁荣。
(二)有朋自远方来——合作创造新的生活经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明人是在境域中的文化存在。因而罗思文说:“人都是在具体文化社群之中出生长大,各文化社群皆有自己的语言、价值观、宗教倾向、风俗习惯、传统以及相应的对‘为人’的基本认识。简而言之,没有文化之外独立的人。每个人都由具体希望、恐惧、欣喜、悲伤、价值、观念,但是这些情感与观念总是与人的如何认识自己分不开,而人对自己的认识又受到所属文化社群的极大影响。”③Rosemont(1991b).转引自: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M].孟巍隆,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3.这段论述至少表达了两层涵义:一、人是文化动物,其情感、观念深受其所在地方的文化的影响;二、人类的文化具有多元性。远道而来的朋友不是“赤裸”着到来的,而是带着其从小浸润其中的文化作为赠礼一起到来的,这是另一种文化的赠与、精神的赠与,朋友带来不同的文化,会使我们产生惊奇、顿悟,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及其当地的生活、风俗、习惯和传统,我们开始重新理解自我的存在,开始陌生化地审视我们自己和当下的生活。个人深受当地文化的塑造,这种塑造使得个人成长为关系之中的人,融入家庭、社区、社会。但是由于当地文化对人的影响也会表现出限制的一面,当地文化中也有一些令人生畏的地方习俗,一个人由于长期浸润其中,因习惯的力量,也会逐渐变得与之相安相乐。如果这种文化生活“持续地导向某种老套或机械的运作模式”,④杜 威.儿童与课程.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那么,人的心灵也会对之逐渐产生兴趣。这会导致一个长期在当地生活的人心灵的麻木不仁。而通过远方朋友的到来,长期生活在当地文化习俗中的人开始惊醒,实现对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对当下麻木的生活采取“陌生人”的视角。而陌生人“变成一个不得不对几乎所有——在他所接近的群体成员看来毋庸置疑的——事情都质疑的人”。⑤[奥]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理论研究[M].霍桂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7.他并不想当然地接受当下的生活现实和文化模式,为了重新获得意义,他必须根据他改变了的经验来阐释、重塑他所看到的,他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探究。作为陌生人就是要“超越一个人所处的情境,拒绝以既定的现实的名义赋予那种现实。”⑥Maxine Greene.Teacher as Stranger: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M].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3:7.这种“不断超越给予的、既定的,获得现实性,其行动建立在悬置自然态度,全面觉醒的意识基础之上。”①郭 芳.教师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9.所以,以陌生人的视角看待日常生活现实,要以好奇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世界,不停地追问和质疑,就像远道而来的朋友一样,看到之前从未看到过的生活细节和方式,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地方习俗与惯例,以“陌生人”的视角展开对生活的惊奇和探究,正如《中庸》所言:“恐惧乎其所不闻,戒慎乎其所不见”(《论语》),学习之道就是质疑、探究,从自然态度的人转化到全面觉醒的君子层面,全面觉醒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处境中所有的一切采取慎独的态度,并达成意识的张力最高水平。让个人从想当然的自我和麻木的生活中超越出来,活出自我鲜活而积极的德性来。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有朋自远方来”的过程乃是凭借朋友的崭新视角,悬置自我想当然的自然状态,转换到全面觉醒的层面,把学习扩展到自己以前难以企及的地方,由此而使得学习的意义得以扩展,看到学习的新的风景。朋友正是作为自我学以成人过程中的他者,生动地参与着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深化。“有朋自远方来”,进入“我”的世界之中,打开我封闭的意识与生活,参与创造着新“我”,让自我中的非我,在与朋友之间的“如切如磋”多重视角的碰撞、会话过程中,促成个体内在自我“如琢如磨”的意识觉醒,由此而促成个体自我的日新其德,亦如《大学》所言,“‘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所以,“有朋自远方来”带来的正是脱离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世界,展开对日常生活世界多元视角的质疑与探究,突破意识障碍,实现全面觉醒,与朋友彼此之间达成创造新自我的契机,自我生命因鲜活、丰盈、圆融和不断更新而由衷的快乐。
三、“人不知而不愠”——创造“南风之熏”,人人皆可成圣
(一)君子人格世界的精神魅力即创造力
“人不知而不愠”,这里人是指普通人们或民众而非君子;“知”是“智”的古字;“人不知”,不是人不知道、不理解我;而是指普通人或民众,缺乏儒家传统的“成人之道”之智慧的修习。“愠”,不是“生气、发怒”,而是“郁结”。《孔子家语》有“南风之熏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其中的“愠”即为“郁结”。“不愠”是君子使之不郁结、使之同样礼仪文明化。一个家庭、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等,如果由“不知”者构成,则要造成“郁结”,所谓民怨沸腾、矛盾冲突、万事不和等,皆为“不知”而“愠”的结局。
君子通过学习在社会生活中行动,践习成人之道,首先是达到最高境界,成为圣人。然而,仅仅如此是不足的。君子追求成人之道,还要使“人不知不愠”,让缺乏儒家哲学思想智慧修习的民众,享用君子的浩然正气创造的淳朴民风,创造性地转化自己的内在人格。君子将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条件统统调动起来,使它们展露出一种积极和谐的状态。君子能够在自己的身上体现、诠释与绽放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风采。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内部的相互恭让(仁义礼智信的风俗)形态构成;在这一构成中,处于这一境遇中的“其他人们”的方向和意愿,都同君子所绽放的影响与魅力合为一体。这足以构成一种强大能量,转变人与人共同生活的经验,让平凡展现魅力。这才是真正君子之道!
(二)基于生活世界日常经验的修炼,人人皆可成圣
儒家的学习之道是建基于对天(宇宙)和人性的深刻体悟、反省后的一种人生存在的自觉行为。儒家从宇宙观到人性观,回答了儒家哲学的学习观,学习是生生不已的宇宙创造性体现,学习是人性之根本的自由与创造性的活动。学而时习之便是对这一学习观的注脚,有朋自远方来,便是通过他感来启动自我创造性学习向更广更深处拓展,进一步创造自我、创造生活、创造世界。学而时习之,是创造个人生命意义、生活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本质方式,是敞开自我与整个宇宙创造性延续演变的和合行为。
上述来自宇宙观、人性观基础上的儒家学习之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觉参与修习和体认到的。但是,孔子认为,即便对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学问之智匮乏,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的文明化、法度化及通过日常经验的修炼,而达成成人之道。因为儒家有一个基本的信念是:学会如何以最非凡的方式去做最普通的事情,人皆可为尧舜。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皆可日常生活经验的修行中成为君子。正如陆象山所言,“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陆九渊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下);《论语·学而》有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如果一个人能在家庭、社会、自然中通过普通事物不断地践行,通过日常经验自然生成,也可以达成仁、义、礼、智、信的人生自觉,不亦君子乎?所以,即便一个人没有学过儒学传统,对儒家建基于“知天知性”之上的学习观不甚了了,也可以成就君子人格。
四、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从学习观的角度看,当前学校教与学产生的问题根源,是西方工具理性宇宙观所秉持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思维模式,即认定宇宙及其中任何事物都是其本质性存在并决定其发展、路径和结果。建基于其上的学习观,根本上仅是孤独的心灵认知、利用外部事物本质、规律。人是认知性的、工具性的人,认知者是知识的局外人,人的自我创造性的自我生成置于次要位置。由此,导致了学习异化为控制,过度竞争,人性扭曲,以及强制的技术化、程序化的学习——逃离学习。其次,人是一个本质性存在。洛克等人赋于个人理性、自治的神圣权力,为人从神学统治中获得自由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个人作为理性、自治的个体也为其后来被宰制留下了一个缺口,从而导致学习异化和人性扭曲。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的学习观是建基于中国古典儒学宇宙观和人性观基础上的,而古代中国宇宙观和人性观恰恰是一种生生不已的过程性、生成性、关系性和创造性观点。为此,中国古典儒学提供了解决西方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中国智慧。儒学的关系性、过程性思维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了本质论,这为当代学习观从根本上超越本质主义二元论提供了可能性。人本质上是关系性的、生成性的,是伦理角色,是在充分的角色关系中创造性生成自我的个人性,这对克服当代自我中心主义的过度竞争的学习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这样,人由认识性的人、工具人,提升为关系中的创造性存在、生成性存在。学习的本质由认知的工具意义转化为具有生存论意义,是人与世界联系的方式,是自我创造性存在与转化,而非功利主义的。《论语》开篇所表达的学以成人(仁、圣),仁智兼修,教人基于生活世界、以日常经验为中心的、知行合一的学习,对当代学校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