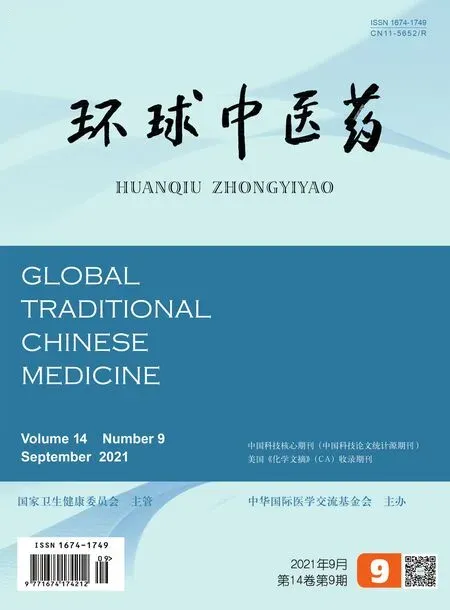“以通为用”法在糖尿病肾病中的应用
赵卓 马赟 李婷 张亚楠 延小丽 陈志强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也是终末期肾病最主要的病因之一[1]。糖尿病肾病对人体的主要危害来自于微血管病变引起的肾小球硬化[2],早期多无明显症状,继以水肿,持续白蛋白尿、肾功能受损、高血压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糖尿病肾病在中医古籍中无特定的病名,各医家多将其归属于中医“消肾”“水肿”“尿浊”“关格”范畴。糖尿病肾病病因复杂,进展迅速,目前发病机制复杂且尚不完全明确,仍缺乏病因性治疗的手段,因此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轻并发症的危害,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和社会意义[3]。
“以通为用”原是中医对六腑生理功能的基本概括。随着中医理论的不断发展,各代医家逐渐赋予通法更深更广泛的含义。李宗源在《医纲提要》中指出:“通之义有三:一曰宣通, 二曰攻通,三曰旁通。”通法含义不仅局限于通六腑,更包含宣通气机、活血化瘀、发汗、涌吐、通络等[4]。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们生活环境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型糖尿病发病率远超1型。当代糖尿病肾病患者临床症状多以实证为主。大部分患者多有情绪焦虑、形体肥胖、胸闷脘痞、身体困重、口中粘腻而不欲饮、面色紫黯、爪甲紫黯,舌质淡黯或有瘀斑、舌体胖大、舌苔黄厚,脉滑数等临床表现,其中医病机与气机郁结、湿滞三焦、瘀血阻络密切相关,在治疗过程中将“以通为用”贯穿始终。
1 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病机与气郁、痰湿、血瘀密不可分
1.1 气机郁结可导致糖尿病肾病
当今社会竞争愈发激烈,人们心理压力亦越来越大,抑郁、愤怒、恐惧等不良情绪对人体的伤害越来越大。李玉爽等[5]认为情志失调是消渴病产生的原因之一,情绪过激,超过肝脏调节限度,则机体内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造成一系列的心身反应疾病。随着“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提出,现代临床医学发现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即糖尿病是一种身心疾病[6]。情绪激动会使交感神经兴奋,引起胰高血糖素分泌增加,继而血糖升高。情志忧郁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生活质量因此下降,治疗的依从性及治疗效果也因此受到影响[7]。对于情志与糖尿病的关系,许多古籍都曾有明确记载。《灵枢·五变》言:“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瘅。”刘河间《河间六书·三消论》曰:“消渴者……耗乱精神,过违其度,而燥热郁盛之所成也。此乃五志过极,皆从火化热,热盛伤阴,致令消渴。”《临证指南医案·三消》说:“心境愁郁,内火自燃,乃消症大病。”这些阐述都说明肝气郁结是导致消渴病的病因病机[8]。肝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郁怒伤肝,气机不畅,易从火化,耗伤津液,内生燥热,发为消渴[9],消渴日久损伤肾络发为消渴病肾病。胡经航[10]也曾写到肝气郁结是导致糖尿病的主要病机, 应以疏肝解郁为首。故气机郁结是糖尿病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
1.2 痰湿壅滞三焦为糖尿病肾病的核心病机
在当代生活背景下,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成为糖尿病的重要诱发因素。孔微教授[11]认为过食肥甘,湿浊内生,郁而化热,肾居下焦,湿热之邪易袭肾脏。《素问·奇病论篇》云:“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多食肥甘厚腻,酿生湿热,湿热中阻,损伤脾胃,导致脾胃升降失常,水谷精微不得运化,停而为饮,滞而为湿。湿性黏腻,易壅滞三焦。张振忠教授[12]认为糖尿病肾病病机与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肺失宣降、脾失运化、肾失气化, 导致三焦闭塞,决渎功能受损, 津气布散障碍,其基本病机是三焦决渎失职。《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三焦者, 決渎之官, 水道出焉。”决,疏通之意;渎,水也,亦指沟渠,意指三焦是水液升降出入的通道,三焦将水液传输于肾,依赖肾脏蒸腾气化分清降浊,同时肾脏蒸腾气化分清降浊需取道于三焦。三焦不通,湿浊趋下,肾体受损。肾不主水,水液气化无道,泛溢肌肤,发为水肿;肾不主藏,精微外泄,则发为糖尿病肾病蛋白尿[13]。疾病日久,肾脏衰败,秘别清浊功能减弱,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湿浊毒邪更易阻滞三焦,恶性循环,如环无端,造成血肌酐和尿素氮水平持续升高。
1.3 瘀血阻络贯穿糖尿病肾病始终
唐容川《血证论》谓:“瘀血在里则口渴,所以然者;血与气本不相离,因有瘀血,故气不得通,不能载水上升,是以发渴,名曰血渴,瘀血去则不渴矣。”首次明确提出瘀血与消渴密切相关。国医大师邹燕勤教授认为,糖尿病肾病基本病机以脾肾亏虚为本, 湿瘀阻络为标,而瘀血贯穿糖尿病肾病病程始终[14]。疾病早中期以湿热浊毒致瘀为主,《丹溪心法》云:“血受湿热,久必凝浊。”湿热内蕴,蒸腾津液,血液雍聚,久而成瘀;痰湿阻滞气机,导致气滞而瘀。而到达疾病终末期,脾肾衰败,阳气不足,阳虚致寒,无力温煦血行,血行不畅而致瘀。赵玉庸教授提出“肾络瘀阻”为糖尿病肾病基本病机,肾之络脉包含运行经气的经络之络及运行血液的脉络之络,气血阴阳亏虚导致经络运行不畅[15];肾脏小血管迂曲,血行不畅,导致脉络瘀阻,瘀血湿浊相互胶结,持续存在疾病各个阶段。现代研究发现,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与血流动力学改变、微血管病变、血液流变学异常密切相关[16]。血液粘稠度高,流速缓慢导致肾脏灌注不足,糖基化终产物的堆积及炎性介质等多因子的释放,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肾小管萎缩,最终导致肾小球硬化,符合中医学血瘀范畴。故瘀血阻络贯穿疾病始终,是疾病能否转归的重要因素。
2 治疗糖尿病肾病的气郁、痰湿、血瘀应当“以通为用”
2.1 通调气机以治郁结
针对七情内伤,气机郁结导致的失眠、烦躁不安、口干口苦、胸腹满闷不舒、善太息等症状。临床常用小柴胡汤加减,其中柴胡为君,《药性论》载柴胡“破拥气”“令人宣畅”[17],其性善条达肝气,疏肝解郁,升举肝气。黄芩为臣,清泄里热,肃降肺气。肝气以升为合,肺气以降为顺,再佐以半夏、生姜,和胃降逆。升降并用,使气机上通下达,表里通畅。“见肝治病,知肝传脾,先当实脾”临床上常配伍陈皮、砂仁、豆蔻等,既能疏通脾胃之气,又能顾护脾胃之气,使邪去而不伤正。
2.2 通利三焦以治痰湿
《湿热条辨》中薛生白认为中期湿邪在膜原和三焦, 可以产生各种转化, 如湿重、热重或湿热并重[18],故治湿尤为重要。此类患者常伴有口中粘腻、脘腹痞胀、纳呆恶心、舌苔黄厚腻等症状。根据《灵枢·营卫生会篇》 “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三焦生理特点,制定三焦分利治之的基本原则。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 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故治上焦,宜宣通,常用藿香、佩兰、香薷、桔梗等芳香化湿、开宣肺气之品。肺为水之上源,上焦得通,如提壶揭盖,三焦气机得以通畅;治中焦,宜疏通,常用陈皮、半夏、砂仁、白豆蔻、焦神曲、白术等苦温燥湿之品,其中陈皮、半夏常以对药使用,半夏性辛温,主燥湿化痰,《本草从新》曰:“半夏乃治湿痰之主药。”陈皮性辛、苦、温,入脾胃经,偏于行气、下气之效,两者合用,彰显“治痰先治气,气顺则痰消”之意。此外,还多用砂仁、豆蔻、焦神曲、白术等健脾补气化湿药,重在健脾醒脾,以治生痰之本。诸药合用,中焦气机得以疏通,痰湿之邪得以运化;治下焦,宜攻通,常用攻毒泄浊,淡渗利湿之品,如土茯苓、积雪草、蒲公英、蛇舌草、酒大黄等苦寒泄浊之品使湿浊从大肠而去,从而减轻肾脏负担;茯苓、冬瓜皮、车前子、薏苡仁等淡渗利湿之品,使湿浊从膀胱去而达到利水消肿的效果。
2.3 通络消癥以治血瘀
糖尿病肾病日久患者可见面色黧黑、肌肤甲错、肢体麻木刺痛、舌色暗红有瘀斑、舌下络脉迂曲等症状。诸多医家一致认为久病必瘀,瘀血不去,肾气不生。故将通络消癥贯穿治疗始终。临床常用丹参、当归、川芎、红花等活血化瘀之品,其中丹参既活血祛瘀,使得瘀血去,新血生,又凉血滋阴;当归补血兼活血;川芎为血中之气药,活血兼行气,同时气行则水行,增强祛湿利水药物的效果;红花活血通经止痛。此搭配共奏瘀血去、新血生、气机畅、化瘀生新之效。现代临床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物可改善患者血液高凝状态,增加肾脏入球动脉和出球动脉的血液供应,改善肾脏微循环,对减少尿蛋白,改善肾功能疗效显著[19]。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曾提到“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根据久病入络这一特点,常加用藤类药物,如青风藤、海风藤、络石藤、鸡血藤等,明代倪朱谟《本草汇言》曾说到:“凡藤蔓之属,皆可通经入络。”藤类植物攀援性强,柔韧有力,无处不达,取类比象,藤类药物能够通经活络,搜剔肾络之邪。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言:“久则邪正浑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药疏通诸邪。”疾病日久,瘀血阻滞肾络,病位之深仅用草木之药效果欠佳,非血肉有情之品不能及也。故重视动物类药物的使用,如鳖甲、地龙、水蛭。鳖甲善于软坚散结,活血消癥;地龙、水蛭性善走窜,长于通行经络,直达病所,对糖尿病肾病日久,瘀血阻于肾络效果显著。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虫类药对降低尿蛋白定量,改善低蛋白血症具有明确的效果[20-21]。
3 圆机活法,临证化裁
3.1 浊毒内盛,专通脾胃
在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后期阶段,患者往往出现纳差甚至不能进食、恶心呕吐、大小便闭等湿浊毒邪内盛的表现,在此阶段若不加特殊干预,患者将出现血肌酐迅速升高,到达尿毒症期。患者的食欲对疾病的治疗至关重要,诸病能食者,虽病重但仍可挽救。《内经》始, 就有“人以脾胃为本, 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张仲景也曾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食欲可看作是胃气的外在表现。针对上述症状,需专注于病人的食欲问题,常用半夏泻心汤合二陈汤加减,辛开苦降,调畅气机, 甘温调补,扶助正气,使清阳得升, 浊阴得降, 中焦气机升降恢复正常,脾胃运化功能得以改善,从而能够进食,使得气血生化有源,疾病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如《素问·经脉别论篇》所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只有脾胃功能正常,气血津精才能化生,四肢百骸才能得以濡养,机体才能进行正常生理活动。临床治疗中通常一到两周的时间,患者恶心呕吐症状将得到明显缓解,食欲得以改善。
3.2 益气温阳,以补达通
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过程中离不开补气、补阳法的应用。气属阳,主动,主煦之;血属阴,主静,主濡之。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血液在脉道中正常运行,主要依靠气的鼓舞和推动。气虚运化水液无力,可致痰湿内停;气虚无力统血,可致瘀血阻滞。生黄芪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张景岳言:“黄芪味甘气平,气味俱轻,升多降少,阳中微阴。”黄芪生用,有走而不守的特性,在补气之余更善于鼓气,使气行而不滞。对于水肿较轻,微量白蛋白尿的患者,黄芪用量通常为30~45 g,补养正气,鼓邪外出。黄芪性善走表,具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本草正义》中赞其:“能直达人之肤表肌肉, 固护卫阳,充实表里,是其专长,所以表虚诸病,最为神剂。”此外,《医学衷中参西录》曾写到:“善利小便。”小剂量黄芪不足以达到利水消肿的作用;对于水肿较甚,大量蛋白尿,24小时尿蛋白定量3 g以上的患者,临床常用量加至90~120 g,以补肺健脾,利水消肿,临床效果显著。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表明黄芪中包含的活性成分黄芪多糖、黄芪甲苷Ⅳ等具有调节血糖,降低血脂,降低尿蛋白,利尿等药理作用[22-23]。
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过程中还应重视温阳药物的使用,例如仙茅、仙灵脾、巴戟天等,对温肾阳、补肾精具有明显效果。温阳药的使用不仅起到温补肾阳的作用,更可以达到温通的目的。《灵枢·五癃津液别》云:“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于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疾病日久脾肾衰惫,脾阳虚无力运化水液,导致湿浊内生,肾阳虚不能司膀胱开阖,使湿无去路,由此导致痰湿内盛。阳虚无力温煦脉道,寒凝血脉,可致瘀血阻滞。故温补肾阳以壮命门之火,使得阳盛推动气行,气行则推动水行瘀散。
4 结语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严重及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隐匿性强的特点要求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重视,严格控制血糖,并且定期检查微量白蛋白尿情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延缓疾病的发展。在中医药治疗过程中,根据当代患者的体质特点,将“以通为用”贯穿始终,准确辨析相关证候规律与特征,根据正邪虚实轻重,灵活用药,临床效果良好,将有望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临床论治思路的探索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