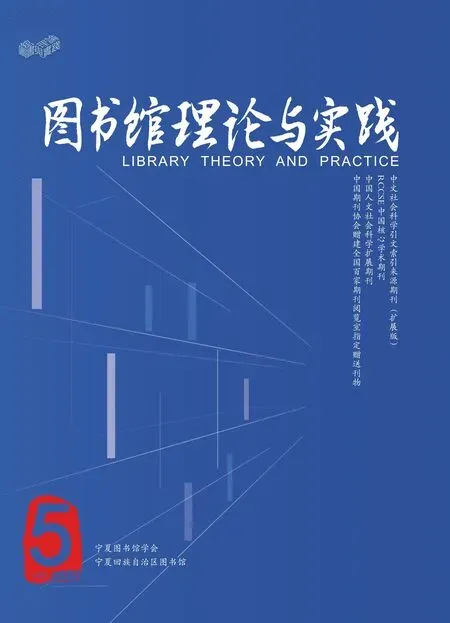试论汉唐之际官方藏书建设的非持续性窘境
郭伟玲(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中国藏书事业的起源是官府藏书。汉武帝入藏书之所,看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1],喟然而叹。武帝之叹开启了统治阶层对国家藏书的重视,官方藏书事业从需求时代进入自觉时代。
自汉至唐千余年间,孕育着书史的多个关键点,知识生产者由贵族精英阶层向平民士子阶层延展,阅读行为向普罗大众渗透,图书的大众传播媒介意义趋于明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藏书事业的变或不变成为历史选择。图书生产和传播的模式随着载体、装帧、印刷术等因素发生转变,“文献形式的每一次根本变化,都会导致文献管理技术与方法的重大改变”[2],如文献分类依据从学术分类到学科分类再到“以义归类”[3],分类法从六分到七分再到四分。当分类思想逐渐向“为治之具”之教化功能目标演进时,官方藏书的目的也渐渐功利化,成为政治的附庸。与藏书操作层面的改变相对应的,则是官方藏书事业命运的相似性,汉唐千余年来官藏事业繁荣之后的崩塌似的衰败,其发展历史呈现相似的往复的闭环轨迹,“大抵新朝之兴,……其时为粉饰升平计,乃广开献书之路,盛置中秘之藏。然一至王朝颠覆,乱者四起,兵戈水火之余,中秘所藏,民间所庋,必又大受损害。必至继此而起之新朝,始为收罗,以为缀点升平之计”[4],民间之书被汇集到天子宫中,然后“藏之秘府……无人得见”[5]994,政治、军事等因素造成藏书的顷刻毁灭,然后帝王再次锐意建设,如此往复,形成了汉唐千余年官方藏书的发展悖论,名为藏书,实为“秘”书,限制图书的传播范围,增加图书散轶风险。官方藏书的增长模式、藏书布局、藏书利用、机构竞争、藏书思想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汉唐之际官方藏书的非持续性窘境。
1 藏书增长模式的单一与固化
古代官方藏书的来源可总结为继承(包括战利品)、复制、购募、官修和献书,汉唐之间知识生产持续加速,图书形制巨大变革,但官方藏书增长路径固化,存在思维定势和经验假设。
1.1 征集购募行为的思维定势
新朝初立,往往下诏搜集图书,存在“莫非王土”的思维定势。朝廷将搜集对象称为“遗书”“逸书”,图书拥有者是政府,不过短暂遗落飘散在民间,这些承载“经邦立政”的典籍“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6]868,朝廷下诏以“天威”与利益相诱导,将散轶之书重新回归国有。下诏民间征集图书或效果显著,如隋开皇初购求图书,一两年间,“民间异本,往往间出”[6]616;或效果不佳,如唐武德初重金购募民间遗书,数年之后仅“图典略备”。可见,民间征募并非官方藏书建设起死回生之“仙丹”,却一再被新朝依赖,一方面是思维定势,另一方面则是意在教化。
1.2 官方搜访行为的经验假设
在下诏的同时,官方亦遣人搜访图书,朝廷根据历史经验假设民间肯定存有逸书,但现实并非如此。
第一,假设的前提条件并不时时存在,民间藏书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一方面,民间藏书更易散轶,私藏更难保持。私人藏书家以仕宦阶层为主体,容易受到政治风云和军事动乱的影响,如唐中宗时薛谡之败,其家藏均为簿录所得,唐顺宗时柳宗元被贬,家中藏书三千卷去向不明。另一方面,民间藏书不足以支撑一次又一次的搜集行为,如唐朝王方庆乃王羲之后代,家藏法书却所存无几。“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卷。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惟有一卷见在,今亦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上之。”[7]647-648
第二,假设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一方面,“藏书家之藏书形成,古今中外莫不累积渐进而成”[8],私人藏书主体因为知识生产的下移、社会阶层的流动、政治军事等因素同样在变化,因此民间藏书的生长期并非在新朝初立时。另一方面,汉唐时期图书的生产方式和出版内容制约着民间藏书的发展。纵使唐时已出现印本,“手抄笔录仍然是生产和复制图书的主要方式”[9],且印本内容倾向于实用性和普及性,而藏书家更青睐经史类图书,技术处于起步阶段的印本在他们看来是“雕版印纸,侵染不可知晓”[10],故藏书事业并未因技术进步而获得推动力。
1.3 图书增长途径多元化的可能性
汉唐之间官藏建设方式单一且固化,未能与政治、文化的转型相协调,从源头上导致藏书规模除峰值期(如南朝梁太清年间、隋大业年间、唐开元天宝年间)外,均在峰值下方起伏式发展。历史在发展,而藏书在转圈。南朝梁元帝萧绎曾著《金楼子·聚书》叙述“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11]的过程,收集途径如继承、抄公私藏书、获得他人藏书、民间定点搜罗、市场购买、他人所献等。可见聚书手段并不稀少,但为什么聚书手段发展至隋唐逐渐单一和固化?其原因或需从历史大环境中去寻找。南朝梁元帝以衣冠礼乐为核心、以藏书建设为表象经营国家软实力,却落败于北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焚书之际发出“读书万卷,终有今日”的感叹。之后,以关陇勋贵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如北周隋唐)将官方藏书作为礼乐典制的映射表象,朝廷搜求图书,并不在意手段的多元与搜集效果,而是落脚于建设国家藏书这一行为所能带来的政治益处,即“为治之具”[6]616。唐玄宗开元年间官方藏书大建设,最终迎来了裴耀卿之叹:“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12]。
2 藏书种类布局的不均衡
国家藏书建设思想发展至隋唐时期逐渐明确,“藏用为治”的图书思想将官藏与政治相结合。图籍乃“为治之具”,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宗教、思想等手段控制文献典藏的著录与流动,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从而为构建统治秩序服务[13],以政治意识为先导的官藏建设必然失衡,形成“厚此薄彼”的藏书布局。
第一,典藏控制。首先,禁书不入藏。汉唐之间各朝均有禁书法令条文,但禁止内容稍有区分,如曹操禁谶纬与兵书、北魏宣武帝禁天文、前秦苻坚禁老庄、唐太宗明确表示谶纬不入官藏。其次,限制宗教书籍入藏。佛道等宗教典籍虽不属禁书,但统治者仍希望能够将其翻译、流通与典藏。唐玄宗下《禁坊市铸佛写经诏》,“禁坊市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14],诏书禁止佛像、佛经自由流通售卖,虽以敬佛为缘由,但客观上控制了佛教典籍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六朝以来,国家时有禁宗教图书之举,但并非全盘否定,而是通过分类、著录、辨经等手段有意甄别宗教图籍中的“疑经”“伪经”,“‘疑伪经’录的编纂与查禁在隋唐逐渐形成制度”[15]。最后,经典入藏审议。臣民献书存在审议环节,但评价标准并不客观。唐长安年间王元感献书,诏令两馆学士议,“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本章句家,见元感诋先儒同异,不怿,数沮诘其言”[16]4347-4348。
第二,目录控制。古代的目录编制从来不是简单的学术活动,而是通过编制目录“辩章学术”,确定文献乃至文献所承载的思想秩序,因此,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文献分类、文献目录和类书编纂活动在方法论上都始终贯穿着一种选择机制——选择符合统治集团伦理教化标准的类目名称、类目次序、收录原则、评价原则等[13]。唐魏徵《隋志》明确提出书目著录标准:“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6]616。目录编撰者以“教理”为著录标准,对文献进行区分对待,或删或附或著,开元年间毋煚明确提出书目编纂的指导原则应以“邦政所急,儒训是先,宜垂教以作程,当阐规而开典”[17]1677-1678,强调图书著录是作为后世思想的章程典范,应该按照“邦政儒训”的需求为先导标准。政治影响下的选择性著录对某些图书的收藏与传播十分不利,很多有价值的藏书都在目录之外湮灭了,正如《新唐书》所言:“《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益明。其余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16]935
第三,收集排斥。历次官方藏书搜访活动并非应收尽收,而是有所取舍。牛弘认为“经邦立政,在于典谟”[6]868,唐玄宗强调“国之载籍,政之本源,故藏于蓬山”[17]157,可见,能够体现邦政国本的经史典籍是藏书募集的重点,其他图书则是根据需要、偏好而进行收集。唐末官方图书搜集困难,罗衮因此建议扩大买书的范围,“不限经史之集,列圣实录,古今传记,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17]3867,进一步说明以往的图书购募活动对图书内容限定在经史之类,集部和子部的图书相对较少。
综上,我国古代的官方图书建设普遍按照统治利益来进行不同类别书籍的区别与取舍,图书入藏与兴化致治直接关联。藏书的勃兴受益于统治阶层的提倡,也受限于社会思想与政治意识的接受与排斥,藏书、政治、思想三者交错交织,官方藏书布局的不平衡则是其复杂关系的表象之一。
3 藏书利用之不完备与封闭性
3.1 官方藏书有条件的利用
唐代官藏利用的不完备虽是总体上的定论,但相对于之前,已然向前走了一大步。第一,唐朝所建立的中央各藏书机构之间可对比抄写、补充藏书、互通有无,图书开始流动。第二,鼓励藏书的在馆利用,而非施恩个案。以弘文馆(宏文馆)为例,馆内二十万卷藏书对馆内学士和学生开放,鼓励学生留宿馆中,“开元二年正月,宏文馆学士直学士学生,情愿夜读书,及写供奉书人、搨书人,愿在内宿者,亦听之”[7]1115,史馆、集贤院、秘书省藏书均对机构内任职者开放。第三,对官员的有条件开放。唐朝规定各朝实录修撰完毕后,收入秘书省内,允许朝内三品以上官员进行抄录;唐玄宗天宝年间和唐德宗大历年间,均出现了官员和宫人借阅秘阁藏书及许多可查考的利用其他机构藏书的个案与特例,可证明唐代官员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借阅官方藏书。
3.2 官方藏书彻底的封闭
官方藏书虽有开放的事实,但封闭仍是核心思想。唐玄宗、唐德宗将藏书出借为“弊”,说明在他们意识中藏书的利用是制度疏漏,官方藏书应以藏为主,始终保持封闭状态。虽历史上可找到的图书流通的例子很多,涉及阅览、外借、赐书、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但所有利用均无制度保障,而源自君王的意志。如开元六年(718)内府图书整理完毕,玄宗“制令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东廊观书”[18],群臣观书的本质是夸耀而非开放,因此停留的时间很短,“移时乃出”[19]。藏书的封闭思想不仅是君王独有,而是君臣共认,甚至君王想要传播藏书都会受到官员的反对,《唐会要》载:“开元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秘书正字于休烈上表抗议,言:“臣忝叨列位,职刊秘籍,实痛经典,弃在戎夷。昧死上闻,惟陛下深察”[7]667。一个“秘”,一个“弃”,充分说明了藏书思想中所存在的彻底的“藏”与“权”的归属意识。
3.3 官方藏书思想的形成
中西官方所主导的藏书建设均非单纯的文化目的,而是充满了政治要素。如公元前300年托勒密一世筹建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誉为后世图书馆的典范,而实际情况应当是托勒密一世有意识地收集图书以形成一个图书馆和研究中心,作为对埃及进行希腊化的一个步骤[20]63,有学者指出“该图书馆内所在国的文献,完全未予收藏”[21]。百余年后,西汉武帝因“礼崩乐坏”喟然一叹,开启西汉官方藏书阁的建设。中西方的图书馆建设均具备政治因素,在建设规模、存在时间、参与范围等方面不分伯仲,但一个走向封闭,未能形成社会文化与藏书建设之间的良好互动,一个走向开放,以文化传播和利用为主要目的,成为缪斯神庙、文学与学问的研究院。两者原点启航,却背道而驰,其原因值得探讨。
(1)官方藏书的建设。中国古代官方藏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图书收藏的行为表示王朝对知识载体的尊崇,进而将其作为朝廷崇文政策实施的象征,因此建设途径是自上而下的,君臣通过政令与专使购募藏书,将藏书与国家兴衰关联。收之则兴,散之则败,这一思想一脉相传。明代邱溶在《大学衍义补·图籍之储》认为“人君之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时之事,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是以圣帝明王,……莫不以是为先务焉”[22]。牛弘、魏徵等人的国本论、经籍论等藏书理念更证明了官方藏书建设是施政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彰显教化、建立秩序、控制思想。官方藏书建设的落脚点是政治权力,导致藏书概念化,官方藏书建设指向政治目的,用数量、规模代替影响与作用。而古典时期西方图书馆被认定为“一批经过编排、易于取用,由熟悉编目之人员管理,且供多人应用的文字资料”[23]13,藏书建设强调专业性。如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设,托勒密一世“将筹建图书馆的工作,委托给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这个人是迪奥夫拉斯图的学生,也是个百科全是式的作家”[20]63,许多“杰出的文人和学者,……曾先后担任馆员”[20]68,通过鼓励图书生产、施加学术影响反哺所在地域,使其成为文学生活中心。
(2)官方藏书的所有权。官方藏书建成后,图书属性发生改变,不再是知识载体,而是定义了归属权。各朝各代统治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将散藏于民间的图书聚集至官府,藏书不仅发生了地理空间转移,更是发生了物权的转移和属性的变化。统治者将官府藏书认定为一种财富,将其封闭在深深贡院之内,“在上者以书籍自私,不复公之于天下”[2],成为帝王府库之中的珍宝,他人无法利用。如两汉时期“霍山以写书而获愆;东平以求书而见斥”;隋炀帝藏书三十万卷,“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24]。这样的私有心理让统治者制定各种制度保证图书的归属,同时也维持了官方藏书的封闭性。
(3)藏书物化的社会基础。藏书的封闭性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古人也有将借书、还书称为“痴(嗤)”,对借书行为不认可由此可知,贞观四年(630)王绩欲向陈叔达借《隋纪》,“前舍弟及家人往,并有书借,咸不见付”[17]580,陈叔达避无可避,才缮写后送至;学者方嘉珍等[25]将藏书封闭性的心理根源与儒家文化之孝道、竞争、为名、歧视等方面进行联系,认为古代士人心安理得地封闭自己的藏书,无论仕宦还是隐者,均将藏书物化为资产,而资产则属私有,不可共享借阅。古代藏书活动中亦有提倡藏书开放者,但相对于提倡藏书私有者,少之又少,梁启超认为:“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26]。与其说我国古代缺乏公共藏书机构,不如说是缺乏藏书公共思想。
4 藏书机构的叠加出现与重复建设
秦汉时期所确定的中央多机构藏书格局为之后历朝所继承,形成内外台阁制度,但“在更替继承中续有发展,形成各自特色”[27]。西汉“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6]614,曹魏有“秘书中外三阁”,南朝文馆与秘书监、内府均有藏书,隋唐两地多机构内外按照藏书职责进行区分,宋朝则是三馆秘阁,多机构相辅相成的合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藏书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但更多地使得官方藏书建设呈现往复状的发展道路。以唐代为例,秘书省作为藏书专职机构,在继承前朝藏书的基础上多次进行民间的图书购募,完成了初步的藏书积累,之后出现的如内府、弘文馆、集贤院等,藏书的原始积累来自对秘省图书的复制,贞观年间唐太宗“令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征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处,其功未毕”[16]936,弘文馆的二十万卷藏书或来源于这种规模浩大持续数年的抄写行为。由此可知,唐藏书机构之间职能的交替变化并没有导致藏书制度呈现质的飞跃,反而因为图籍职能的迁移造成了某一时间段藏书建设的顾此失彼。唐朝中央机构藏书建设方式并不是个案,隋朝东都观文殿图书来源于西京嘉则殿内藏书的剔除选择,而嘉则殿内的三十七万卷藏书也是因为“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6]616。在前印刷时代,图书复制主要依赖手工抄写,一个新的藏书机构的出现势必会分流已有机构的物力人力,因此,中古时期藏书机构的叠加出现与重复建设同样可算作官藏发展的历史短板。
4.1 制度演变
多机构藏书布局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追根溯源可从制度上来解释。
其一,制度决定者和运作者是人,历史制度演变有客观沿袭,也有君臣的主观推动,制度的变化具有偶然与必然,官方藏书制度变化,尤其是多机构并行的官方藏书制度的出现亦是如此。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帝制中国是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的案例,支配者——君主的日常权力运行依赖于官吏群体和文书制度,而君臣之间矛盾共存,“家产制君主总是会恐惧官僚阶层成为一种固化的、自律的、身份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对自己构成威胁,从而倾向于以官僚制以外的手段来对官僚制进行限制”[28],即去规则化,打破原有的已定的规则与形式,制定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图籍文书成为改革的现实着力点与突破口,如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汉武帝时期职掌秘籍书奏的尚书职位及曹魏时期的秘书令与中书令,图籍作为天子最可决定的事务范围,被用于扩张自己的权力和领域,藏书新设机构的政治性由此可知。其二,中国古代官制常有叠床架屋之弊,新的机构或官职产生,原有机构和职官并不废除,呈现共存状态。唐开元天宝年间,秘书省的图籍职责被集贤院所接替,集贤院“其职具秘书省”,但是秘书省仍然存在,并履行着原有职责;中唐以后,集贤院图籍职责还归给秘书省,但机构仍存。其三,制度包括成文之法和不成文之法,君主意志影响两者转化。如天子近臣更易获取更大的权力,即皇帝认可某人的时候,他所担任的职官会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彼居甲官则甲官之职重要,居乙官则乙官之职重要”[29],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职责类似的机构。唐贞观年间,弘文馆深受唐太宗信任,高宗武后时期弘文馆的权责被削弱;集贤院在开元天宝年间一枝独秀,中唐以后,诸多文馆一并没落,成为官阶标志。但这种局面会因某人某事而出现波澜,唐宣宗大中年间,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铉任弘文馆大学士,弘文馆因承担了《续会要》的编撰任务而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4.2 历史影响
新旧藏书机构的叠置与重复,中央文化机构的图籍管理职责数次迁转和分流,造成了各藏书机构的藏书布局无任何分工可言。虽有馆阁藏书新机制诞生,但主要表现为藏书权力在内外空间上的复制与挪移,并无新的藏书建设方法、内容与理念的诞生,也未开拓官藏建设新领域。多机构并存机制对官方藏书事业的建设推动力不足,反而会因为某一时期的权力旁落造成某一机构内藏书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如唐初内库、弘文馆、集贤院、秘书省均曾出现过书库年久失修、物资供给不足等情况。藏书机构建设与权力分配相交错,新机构的兴起多源于君主的“组阁”欲望,官方藏书无布局无配合,数次的图书抄写增加了官方藏书事业的内部损耗,不同方向的延伸削弱了官藏向前发展的动力。
5 君臣流于表象的图书观
汉唐官方藏书建设事业几经兴废,但千余年间图书价值观并无革新性进步,仍然是重量不重质、形式大于内容、收藏大于利用的图书政治观。
5.1 图书建设数量重于质量
汉唐间藏书聚散的几个峰值,如南朝梁武帝太清年间、隋朝隋炀帝大业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玄宗开元年间,藏书规模以万卷计量,但数量并不等于质量。唐贞观年间,秘书省抄写规模宏大,官藏数量大增;但藏书种类没有增加,胡应麟认为:“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经籍。……然迄贞观中,未闻增益,诸臣亦绝无目录之修,何也?盖太宗所骋志文词,所钟嗜翰墨,于经籍盖浮慕焉”[30];开元天宝年间,藏书整理活动持续进行,开元末毋煚《古今书录》与《内外经录》著录集贤殿藏书62,352卷、5,560部,与《隋书》著录14,466部、89,666卷见存图书相差甚远;文宗时期秘书省藏书扩充为十二库,抄写与搜访并重,最终藏书单本56,476卷,较之贞观初藏书单本量增长并不显著。综合汉唐官藏史料,历代君臣论及藏书建设时,首先关注数量增长,且是通过抄写复制方式所获得的增长,对于入藏图书种类,反而在购募、献书、著述等环节进行限制,对某些图书的不采、不收、不藏,如限制时人文集与文学作品、雪藏争议的经史注疏、禁止新的宗教典籍等。藏书种类在限制范围内缓慢增长,藏书建设不以图书种类齐全、收罗丰富为目的,导致文学、科技、音乐等领域的发展并不能惠及官方藏书建设,藏书种类固化现象严重。
5.2 图书整理形式大于内容
在前印刷时代,图书生产以手抄为主,内容传递与形式制作合二为一,但官方藏书与私人藏书在两个方面的重视程度却存在细微差别。历代官藏对于图书形制的坚持是一贯的,且建立了利用图书装裱形制分类的典藏制度,但内容校勘往往是阶段性、暂时性的。私人藏书则强调图书校勘精良,内容远远大于形式,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苏弁“聚书至三万卷,皆手自刊校”,韦处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李泌“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之后还要强调主人已通读。究其原因,可从管理体制和藏书观念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官府藏书的管理方式不同于私人藏书,藏书管理的各个环节由不同的职官负责,图书制作与典校是管理流程中不同阶段,分属于吏员匠人和校正官员,如熟纸匠、装潢匠、笔匠、拓书手等图书抄写与制作人员,专业水平超乎私人藏书家之上,但机构内校正人员多为官场新人,只能应付图书入藏抄写校对,如需对内容进行校勘,需要延请专门学者进行,而私人藏书家多学问专深,自己就能进行图书内容的校勘。另一方面,官方藏书建设政治目的明确,历代君王多明言重视典籍,但其中真正爱书读书之人屈指可数,因此当图书进入藏书机构之后,当书库被各种装饰精美的副本填满之后,图书的种类与内容并不重要,形式才是一切。
5.3 图书收藏高于利用
顾炎武认为,文教政策“密于禁史而流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5]995,虽专指唐代君王,但也一语中的地说明古代君王的图书观点止步于建设阶段,对于藏书的利用却普遍没有给予重视,甚至刻意避免。即使是藏书机构任职人员,也只能偷偷地抄写官方藏书,如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31],类似史料遍布历代,古代官方藏书的封闭性是一贯的,其根源在于统治者的国家图书“藏大于用”的建设理念。西方巴比伦与亚述时期、埃及时期、希腊时期、罗马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亦多由皇帝和政府支持,创立伊始即对学者或公众开放,相比之下汉唐之际的官藏却逐步走向封闭。两汉时期,官员有权阅览利用;六朝时期,需申请机构内职官才可读藏书;唐朝即使任职也不能任意阅览;发展至清朝,文津阁等七阁名为开放,实则图书控制更加严格,清朝图书政策“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家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5]995。一方愈发封闭,藏书成为帝王私产和宣传工具;一方虽经历波折,但藏书“为全民服务”[23]131的理念逐渐树立,再次兴起时藏书的公共意识水到渠成。其中差别,虽有管理体制、文化背景等原因,但藏书建设者的藏书初衷和图书理念亦非常关键。
6 结语
笔者从藏书增长模式、馆藏布局、藏书利用、藏书机构、藏书观念五个方面分析了汉唐之际官方藏书建设的非持续性困境,虽观点联系史料,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藏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在现代藏书史研究中,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概念和语言体系或显或隐出现行文中,如模式、布局、利用、价值等,古人虽然涉及,但因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不同,导致古今理解的偏差。因此,拙文以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原则为出发点,对官方藏书建设所做的对比和总结,会受到世界观、价值观和专业背景的拘囿,阐述文本所表达意图与中国古代官方藏书的历史之间存在差异。无论我们如何分析和评判中国古代官方藏书事业,它作为光辉璀璨的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曾让历代君臣为之努力和自豪,困境的出现不代表官府藏书的消散与虚无,而是与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合作竞争此消彼长,共同构成古代藏书文化,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基本的文化基因,影响着图书馆的事业发展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