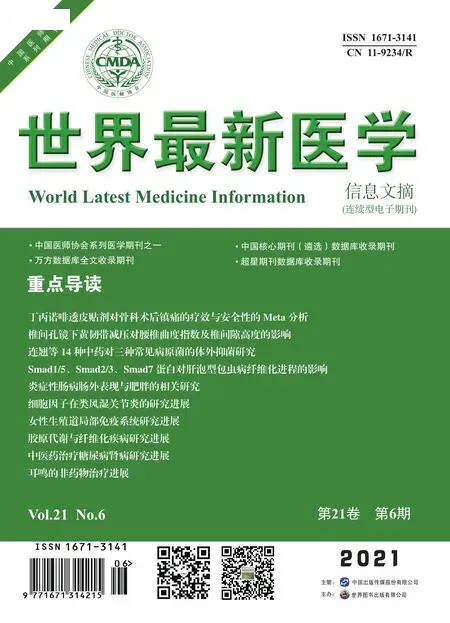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父母病耻感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
温李滔,潘胜茂,唐省三,来慧丽,胡亚妮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0 引言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组从行为学定义的全面性精神发育性疾病,其核心症状为社交交流障碍、行为刻板重复和沟通交流障碍三联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布欧洲、亚洲、北美洲地区ASD儿童平均患病率在1%-2%之间,美国8岁儿童ASD患病率为1.69%[1]。我国学者对儿童ASD的患病率进行meta分析发现:0-6岁儿童ASD患病率在3.51‰[2]。照顾ASD患儿,父母不但承受精神折磨,还经历求医治疗挑战,大量研究表明ASD患儿父母都承受着不同程度病耻感困扰[3]。随着新医学模式的发展,ASD患儿父母病耻感严重影响一个健康家庭功能正常运转和健康社区维护,引起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关注,成为我国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ASD患者父母病耻感影响因素、测评工具以及干预措施3方面进行综述,旨为探讨符合我国文化背景下ASD儿童父母病耻感的干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ASD儿童父母病耻感的相关概念
病耻感(stigma)又称“污名”,指个体因患某种疾病被贴上标签,遭受歧视,从而产生的一种耻辱体验。Link指出,病耻感由被贴标签、社会刻板印象、地位丧失、歧视5个因素构成[4]。ASD儿童父母病耻感是指ASD父母因其子女发育障碍性所致的羞辱感和社会公众对他们所采取的歧视和排斥态度。病耻感可分为感知的病耻感(perceived stigma)和实际的病耻感(enacted stigma)。前者是指妨碍ASD儿童父母谈论亲身经历、寻求帮助的羞耻感和对歧视的预期感受;后者是ASD儿童父母遭受他人歧视及不公平对待的经历[5]。ASD儿童家长易内化社会互动中对ASD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从而体验到病耻感。
2 ASD儿童父母病耻感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研究证实,影响ASD儿童父母病耻感的因素有家庭因素、临床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
2.1 家庭因素:应对策略不足
父母体验病耻感与其患儿疾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6]。Sarkar[7]等人发现母亲比父亲更易受到病耻感影响她们与亲朋好友间互动,原因在于母亲会承受更多外源性的歧视、社会舆论以及社区内异样眼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8]家境贫穷、学历低下的父母与教育水平高、生活水准高的父母获得更高的病耻感,可能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属更理性看待大众异样眼光或舆论纷纷,从容不迫应对疾病连带病耻感。研究证明[9]母亲更易因ASD儿童的言行举止异常而受到歧视,可能是母亲感知病耻感比父亲要强,还有ASD儿童日常生活更多由母亲照料及陪伴,父亲更多精力在于赚钱来支撑家庭经济运转。
国内学者也研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也是病耻感产生主要因素,不同国度其文化背景涵义也不尽相同。而Dunn等研究提示,自我效能与感受到的价值贬低和歧视间存在负相关[10]。Kamei A[6]等学者通过对比美国与日本ASD儿童父母感受到病耻感发现,因文化背景迥然不同,日本父母比美国父母体验更多疾病连带病耻感,更强烈感受到被社会孤立。
2.3 卫生服务因素:保健人员不理解
8.4%的城市社区初级卫生保健人员和74.7%的乡镇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都把ASD主要发病原因归因于“教育不当”或“亲情缺失”[11]。国外研究表示有[12]45.1%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把ASD形成是因为父母照料不足或冷漠所导致的。美国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比专科医生更显著的将ASD的病因归咎于父母的教育因素,很少认为ASD是一种全面性精神发育性疾病[13]。研究结果显示[14],有14例参与研究的ASD儿童父母在陪患儿进行康复治疗是就感受到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歧视,被初级卫生保健人员认为“小孩目前这种状况,是父母让小孩缺乏家庭关爱和教育不足造成”的经历。超过一半以上的社会培训机构工作者认为ASD疾病发生主要原因是由于家长们的“教育不当”。疾病错误归因是一个不良社会因素,也会导致社会人群将儿童行为异常问题归咎于家长“亲情缺失”。因此,保健人员及培训机构工作者应加强ASD相关知识的学习,多站立在患儿父母视角上,忧其所忧,分担患儿父母情感上焦虑,从而减少保健人员及机构工作者的歧视而产生连带病耻感。
以上针对患儿父母连带病耻感的相关研究,尽管在对象选择、研究方法以及对病耻感理解的文化敏感性有差异,研究结局不尽相同,但都表明了ASD患儿家长们具有较深病耻感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病耻感对ASD患儿父母就业、心理功能、社交功能以及生活品质等方面有严重影响,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病耻感。
3 ASD病耻感的相关测评工具
①病耻感水平[15]:采用Link等人2002年修订的病耻感系列量表的中文版,2007年由徐晖汉化,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贬低-歧视感知量表,病耻感应对量表和病耻感情感体验量表,共有8个维度,46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包含贬低-歧视感知、保密、退缩、教育、挑战、分离、误解、不同/羞耻8个维度,其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6、0.79、0.61、0.75、0.68、0.64、0.71、0.73,各维度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病耻感水平越高。
②连带病耻感量表(Affiliate Stigma Scale):该量表是由Make等人开发最初用于评估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照顾者病耻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范围为0.85~0.94。台湾的Chang等学者[16]将连带病耻感量表用于痴呆照顾者中进行检验,量表有3个维度22个项目:情绪维度包括7个条目,行为维度包括8个条目,认知维度包括7个条目。量表采用4级评分法,1~4分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总分值越高表示病耻感水平越高。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9,三个维度的Cronbach’s α范围为0.822~0.855,证明该量表良好的稳定性。
4 降低ASD患者父母病耻感的相关措施
各国积极采取措施降低ASD患者父母病耻感:包括社会支持、心理支持、认知支持等从而保护ASD父母利益。
4.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人遇到外部复杂事件时,从社会内外部资源中获得物质及精神的缓助,即包括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而客观支持是人获得外部资源比如物质、人际关系网等参与,主观支持即个体所感受到被人肯定、尊重的情感体验。国内学者[17]的实验证明,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共同展开残疾群体病耻感效应干预,可以显著减轻病患家属的病耻感。Mak等[18]研究证实,一方面通过网络、杂志文章、社交媒介等传播途径普及公众ASD疾病的常识,另一方面协助ASD患儿父母提高自我控制意识和寻找社会支持资源,可以降低父母疾病连带病耻感内化。研究发现获得社会支持越多家庭更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困难,使家庭功能得以正常运转,从而减少父母病耻感内化[0]。因此,我国应以科普自由行模式开展ASD知识宣传提高公众对孤独症常识认知,自发性为ASD儿童父母建立支持小组;其次国家层面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及宣传反病耻感运动;最后完善ASD患儿就诊疗程及有效监管康复机构,为ASD家庭提供整个生命周期的养育教育指导、保险服务和职业发展规划咨询[19]。
4.2 心理支持
因亲人不支持、社会不理解、康复技能缺乏以及治疗干预巨额花费,所以ASD儿童父母不但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近年来有研究发现[20]:ASD儿童父母存在焦虑、抑郁、绝望等负性情绪的心理问题,约有超过三分之一ASD儿童父母抑郁量表评分高于常模水平。自我同情心理调节功能突显了病患家属自身强大心理素质,有助于降低个体疾病连带病耻感,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教育训练技能[21]。个体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有助于提升ASD儿童父母疾病认知,改善负性情绪,减轻自我病耻感。提升疾病认知,增加疾病理解,掌握疾病管理技能,增强内心自信,能够有效减轻病患家属的各方压力,从而促进ASD病患家属病耻感的干预疗效[22]。教育技能训练能够提升ASD患儿家长们社会适应能力和改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积极应对疾病带来的病耻感[23]。有学者研究发现病耻感与抑郁焦虑呈正相关,而正念疗法能够有效降低ASD儿童父母病耻感与抑郁焦虑的关联性,同时能够使父母正视病耻感带来的负面影响[24]。
4.3 认知支持
认知疗法是根据人的认知过程,影响情感和行为的理论假设,强调人的情绪来自人对所遭遇事情的信念、想法、观念,而非来自事情本身,认知疗法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应付、问题解决等技术进行心理辅导,发展适应性行为,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25]。有学者研究表明举办ASD科普知识培训有助于提高公众对ASD的认知及理解[26]。通过学习ASD病因等相关医学通识,父母可在养育及康复路上为小孩和自身争取一种身份认同感,照顾者有足够底气维护小孩独特性,从而减少病耻感[27]。因此,利用多方资源加强宣传,促进公众认知,获取大众理解,减轻公众对ASD的误解与歧视;建议大众传媒对ASD患儿及家庭给予正面报道,充分唤醒社会群体的大爱,并内化为实际行动关爱和支援ASD患儿及父母,提供他们生活信心,降低疾病带来病耻感。
5 ASD患者父母病耻感研究展望及存在相关研究问题
ASD病患家属病耻感研在国外已开展大量系统探索研究,尤其是欧美国家,但国内相关研究甚少,而针对不同区域间比较研究目前尚未进行。目前国外对该领域研究量表种类繁多,但针对适应我国文化背景下信效度高的病耻感量表相对较少,给科研人员带来研究技术上的困境或难以开展深层次的研究。ASD患者父母病耻感水平,公众对ASD患者父母歧视的严重程度,产生病耻感的主要原因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如何破除社会公众对ASD的刻板印象、打破医疗服务行业的局限、形成家庭生命周期支持,帮助ASD儿童父母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念,提高ASD患者父母自尊和自我认同感,降低病耻感,促进其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全面康复、提升其生存质量,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