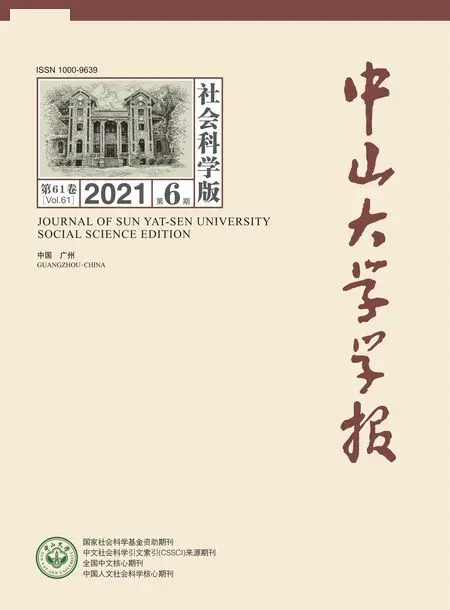《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华效应*
蔡鸿生
一、题解
19世纪末,法国作家小仲马(1824—1895)的小说《茶花女》传入中国,译本畅销,风靡一时,在晚清人士中引发持续的轰动效应。所有这些,既是重要的文化现象,又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后人回顾。
关于书名的来历,略加说明如次。
《茶花女》原为法文La Dame Aux Camélias,花名源于人名卡梅尔(George Joseph Kamel,乔治·约瑟夫·卡梅尔),耶稣会士,1688年奉派到菲律宾传教,46岁病死,遗著《吕宋岛植物志》,著录当地山茶花的性状和品种,是他调查发现的。经瑞典植物分类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确认,按例以人名作为茶花的学名(Camellia)。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是巴黎著名的“交际花”,喜欢在剧场度过夜生活,随身带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一月之内,她25天带白茶花,5天带红茶花,因而被人加上“茶花女”的外号。意为“爱茶花的女郎”,并无别解。
二、林纾与《茶花女》的译述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1899年发表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书前有“小引”云:
关于林纾译西书之原始,黄濬有更详细的记述:
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以告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②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9页。
游石鼓山、译《茶花女》,看似一次闲适郊游的产物,实则是林纾为“遣悲怀”而实现的精神解脱。他的爱妻刘琼姿1897年病死,林纾中年(45岁)丧妻,陷入伤逝的悲痛而难以自拔,友人魏季渚才有这样的安排。
这部王述林译的古文体悲情小说,是晚清文坛的奇葩。用心,用情,用笔,都是独具一格的。钱鍾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早已指出:
在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藉助于文
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改,他
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生手的林纾仿佛进行拉锯战或
跷板游戏;这种忽进又退、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③钱鍾书:《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2页。
① 刘译:It takes a teacher to transmit the Way...[4]36
林纾的尝试总算成果,旗开得胜,不胫而走。尽管译文中红颜“薄命”的传统笔法出现5次,仍令读者耳目一新,产生了罕见的轰动效应。
三、社会效应的具体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本刊行于福建,印100册,非卖品,只在“朋友圈”中流通。不久即成为热门书,大量翻印,风行海内。1904年,林纾的同乡严复曾赋诗惊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首名为《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的诗,虽套用唐代刘禹锡《赠李司空妓》的句式:“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却表达了异于前代的社会心理,流露出“荡子肠”中的新意识,也许可以勉强称之为反封建意识吧。当然,用封建意识来抒写读后感的也不乏其人,如吴东园的《茶花女本事诗》,就仍弹“倾国佳人”的老调:“天生丽质曰马克,似此佳人难再得。少小名噪巴黎斯,一顾倾城再倾国。”读者群中,既有名流,也有俗客,还有一位年正少壮的齐白石。他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写了八个字的评语:“人间恨事,天下妙文。”④马明宸:《借山煮画——齐白石的人生和艺术》,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96页。真想不到,白石老人也是赏花人!更想不到的是,仿作也出现了。1907年,钟心青著的《新茶花》小说,可作东施效颦之例①钟心青:《新茶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重印本。。
最轰动和最集中的社会效应,并不是读书,而是演剧。《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于1851年亲自将小说改编成话剧,作曲家威尔第又于1853年将其改成歌剧。从此之后,茶花女就上舞台说话和唱歌了。西风徐来,使晚清留日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吹拂,竟在东京搬演茶花女遗事,揭开了近代中国话剧运动的序幕,下面作一简介。
赴日留学,是晚清知识界的新潮流。1907年2月6日,日本官方宣布:中国留日学生共17,860余人②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69页。,主要集结于东京。以“开通民智,鼓舞精神”为宗旨的“春柳社”,是留学生中的进步团体。创建者李叔同(1880—1942),出身天津书香门第,1905年到日本东京,入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是个多才、多艺、多情的热血青年,为赈灾(淮河灾民)发起义演,剧目就是《茶花女》。李氏男扮女装,粉墨登场。为表现女主角的苗条身段,他不惜减食束腰,练声练舞。1907年2月11日,话剧《茶花女》在东京公演,观众二千余人,大获好评。值得一提的是,观众席上有女侠秋瑾,仅仅五个月后,她就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任上,因谋起事不成而被杀害了。
演出成功,李叔同百感交集,写了《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情悲意切,非同凡响:
东邻有儿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
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③《李叔同诗词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诗中有“谶”,七言等于预言,“誓度众生成佛果”,果然在他后半生中充分展开了。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定慧寺剃度为僧,法名演音,法号弘一。随后长期驻锡闽南,弘法传人,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一代高僧。1942年10月13日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留下绝笔“悲欣交集”四字。多年之后,赵朴初先生在追念弘一法师的诗里,有“深悲早现茶花女”之句,堪称知人论世了。
茶花女的原型,是巴黎名妓玛丽·杜普来西(1824—1847),其死后葬于蒙马特公墓。20世纪旅法的华人,不少人因受林译小说影响,都成了茶花女墓的吊客。1912年,正在巴黎大学深造的陈寅恪先生,时年23岁,也曾亲访其墓,久久难忘。经过半个世纪,他76岁忆及此事,还赋诗追念,一往情深。全诗已佚,只存一个长长的诗题:
癸卯(1963)春,病中闻有人观巴黎茶花女连环图画,因忆予年二十三旅居巴黎曾访茶花女墓戏赋一诗,今遗忘大半,遂补成之。光绪中,林纾原名群玉,仿唐人小说体译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其文悽丽,为世所重。后有玉情瑶怨馆本,镌刻甚精,盖出茶陵谭氏兄弟也。④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4页。
寅恪先生病中补成的早年诗作,虽未能传世,但据诗题可以推知,其中必有深沉的历史咏叹。不言而喻,他在“颂红妆”(柳如是)之前,已经颂过“洋红妆”(茶花女)了。这段“金明馆”的掌故,证明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华效应,确实既深且远。陈氏八字:“其文悽丽,为世所重”,可作定评。
四、晚清西来文化激素之命运
晚清的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包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和精神危机。表现为具体的历史事件,就有甲午海战、戊戍变法、八国联军、同盟会革命活动等。随着社会的动荡,思想文化也动荡起来了。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如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584年刊于广州)、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刊于杭州),等等,都是西学与神学的混合物,由洋人“送来”的。至于国人“拿来”的,则是晚清的新动向。作为西来的文化激素,这些世俗性读物,既有“情”的,又有“理”的。前一类可以林译《茶花女》为代表,后一类则首推严复(1854—1921)的《天演论》。他选取英国启蒙思想家赫胥黎的名著《伦理与进化》,用古文笔法译述,坚持“信、达、雅”原则,1898年正式出版,比林译《茶花女》还早一年。十多年后,此书版本超过30种,畅销全国。据胡适回忆: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①胡适:《四十自述》,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46页。
至于林译《茶花女》为什么也是“一种绝大的刺激”,金克木先生是将它放到上海滩上去理解,指出在时人眼中,这部小说既是爱情的悲剧,又是道德的喜剧:
为什么《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八九八年)能风靡一时?将此书和差不多同时的《孽海花》(一九0四年)等一对比就可以明白。那正是上海滩上昏天黑地之时。妓院和赌场成为官僚政客文人豪士的聚会之处,又是交际场所即情报总汇。同时还有不少人发出世道人心不古的慨叹。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看,这部法国小说中有嫖,有赌,有情,有义,又有道德规范终于战胜一切罪恶。亚猛正如同《会真记》中的张生“善补过”,马克(马格尼特)也如《西厢记》中的莺莺“善用情”,一般无二。同是爱情的悲剧,道德的喜剧。于是古代心情,现代胃口,西装革履在妓院中赌场上讲道义,巴黎小说遂化而为上海文学了。自然得很,何足为奇?②金克木:《中国文化老了吗?》,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7—158页。
经过以上的对比,可知两书的效应同中有异:《天演论》说的是“理”(进化),《茶花女》谈的是“情”(人性)。不过,异中也有同:无论严译还是林译,都是名译,但也都是不忠于原著的意译。由于其“意”切合晚清社会潮流之意,也即在“礼崩乐坏”中寻觅生机,因此才能成为精神兴奋剂,激起千重浪,引发出跨世纪的社会效应。历史昭示后人:书之传不传,书之显与晦,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取决于时代。著述如此,译述也是如此。用句似玄非玄的话来说,正所谓:时也,运也,非人力所能强也。一部文学接受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史。
—— 百年林译小说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