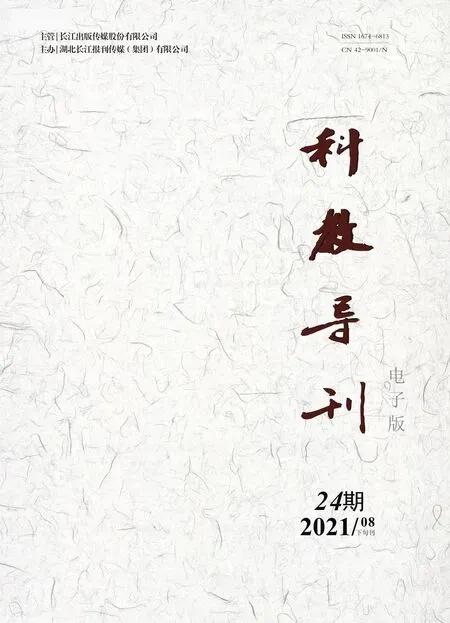“很+NP”的三个平面分析
丁泉琨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上海 200433)
“很+NP”属于“副词修饰名词”结构中的一类。虽然违背了一般性的语法规律,即多数语法理论都把“能否受副词修饰”作为区别谓词和名词的标准,但是在日常交际中,“很+NP”有着广泛的接受度。文学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结构,如“他很绅士,他实在是很绅士,我躺在床上只想到了这么一个词。”(铁凝《大浴女》)。
这一结构是如何合法的呢?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王德亮(2009)、顾鸣镝(2011)、陈亚萍,于善志(2014)从构式理论出发认为“很+NP”经过语义压制达到了整体意义大部分意义之和的效果;李少敬(2014)从认知的角度认为转喻和隐喻为“很+NP”增强了主观性从而使其大众化;吴骏良(2019)基于语言模因论认为“很+NP”的流行是大量复制与创造性使用的结果。以上研究有助于分析对于“很+NP”结构的生成。而从更全面的视角,即综合句法、语义、语用起来看,目前还缺乏较成熟的研究。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层面分别对“很+NP”结构进行描写和推理。
1 句法平面
“很+NP”这一结构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可能源于汉语中与之相似的两类固有结构,“很+AP”和“名词谓语句”。很+AP,如“小王是个很积极乐观的人”,“很”增强了“积极乐观”的性状程度,“很积极乐观”作定语,共同修饰中心语。名词谓语句,如“他(孔乙己)身材高大,清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鲁迅《孔乙己》)”;“鲁迅,浙江绍兴人”。在这两个例句中,“清白脸色;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浙江绍兴人”都是体词性结构作谓语。这两类结构都具有一定的描写性。
“很+NP”也具有描写性,它不仅可以作谓语和定语,而且可以作状语和补语,都由“很”加以限制。这是副名结构的一个特点,即副词修饰名词时,修饰的是句子成分,而不是把词作为词,短语作为短语来修饰的(赵元任,1979)①。下面来看“很+NP”的句法表现。
1.1 “很+NP”在句法平面的形式与意义
“很+NP”结构在语序上可以分布在谓语、定语、状语、补语的位置。如:
例1你就是现在这种打扮,很中国,很东方。(琼瑶《水云间》)②
例2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7月29日)
例3愫细很淑女地啜饮着高脚杯中的红酒。(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例4“蜜丝赵也很漂亮。”“不过穿得很小家子气。”(亦舒《独身女人》)
例1“很中国”作谓语,与主语成分“打扮”共同表示“陈述——被陈述”的句法意义;例2“很阳光(的)”作定语,与中心语“孩子”共同表示“修饰——被修饰”的句法意义;例3“很淑女(地)”作状语,与中心语“啜饮”共同表示“修饰——被修饰”的句法意义;例4“很小家子气”作补语,与“穿(得)”共同表示“修饰——被修饰”的句法意义。
“打扮”与“很中国”之间虽然是主谓关系,但是“很中国”其实也是一种修饰,可以变换成“打扮得很中国”,“很中国”修饰“打扮”。
1.2 “很+NP”在句法平面的选择与要求
一方面,作为程度副词,“很”在句法上可以被“特别、非常”等替换,如“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生”等,可见程度副词在这一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类推性。
另一方面,在表示“修饰——被修饰”的偏正结构时,“很+NP”和“中心语”中间需要有“的、地、得”,否则语句不通顺。如“*这是一种很傻气动物”“*她很气派走了过去”“*王刚哭很女人”。这里可推想出“很+NP”在句法上一般是不独立的。
2 语义平面
2.1 “NP”的语义选择限制
“很+NP”中的“NP”具有语义限制,即具备一定的附加特征义,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具象名词:淑女、平民、小孩、铁、奶油、阳光、男人、英雄。
第二类抽象名词:文艺、娱乐、理想、现实、骨感、霸气、精神、理性。
第三类专有名词:上海、重庆、西安、北欧、鲁迅、梵·高、布尔什维克。
在“很+NP”中,名词需要具有一定的“描写性”,即“附加特征义”。第一类名词在结构中不再是其指称含义,更多与该词的外延相联系;第二类名词是表现实物主体状态、品质、情感等的抽象名词,外延义更深;第三类名词是特指在某一言语社团具有较高辨识度的地名/人名/译名等。
2.2 “很+NP”所体现的认知因素
语义方面还可以结合认知模型理论进行探索。该理论认为认知模型(CognitiveModel,简写为CM)是在人们与外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CM虽由各个构成部分组合而成,但却表现为一个整体的完形结构,具有完形性;CM是人们心智中认识事物的方式,具有内在性。多个关于同一事物的CM就构成了关于这一事物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CognitiveModel,即ICM)。转喻就是在一个ICM中,用其中的一个CM2来理解另一个目标CM1,而这两个CM之间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contiguity)。
在“很+NP”结构中,名词的意义从其具体所指的完形对象转化为描述该对象的性状这一层面。在一个名词的ICM中,也就是一个名词众多的CM中,其语义重点在于其中关于性状的一个CM上,即它的语义目标是性状这一层面,这层面在认知上凸显的结果是代替了整个名词的ICM,即以部分代整体。这时,“很”作为程度副词,表示程度。“NP”在进入“很+NP”结构之后,NP的附加特征义被“很”激活,得以语义上的凸显。以例1-4说明:
例1中的“中国”属于第三类名词。“中国”进入这个结构中后,就不是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例2中的“阳光”属于第一类名词。“阳光”不是指自然界中太阳发出的光线,而是指“性格活泼开朗”。例3中的“淑女”也属于第一类名词。“淑”,温和善良的;“女”,女子。但这里不是指“温和善良的女子”,而是指“(啜饮时)优雅”。例4中“小家子气”属于第二类名词,在这里,不是指“狭隘的心胸”,而是指“穿着拘谨”。
2.3 “NP”的语义指向
“很+NP”在句中时,无论位于哪个句法位置,其语义指向都是指向体词性成分的,即一种描写性的修饰。“很中国”指向的是主事“打扮”,而不是打扮的人,也不是打扮这一“动作”,打扮作为动作而言是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来描写的。“很阳光”指向的主事“冬梅”。“很淑女”指向的是施事“她”,而不是“啜饮”这一动作;“很小家子气”指向的是主事“密丝赵”,而不是“穿”这一动作。
3 语用平面
3.1 “很+NP”的语用意义
“很+NP”具有独特的语用意义,主要体现在“简洁”“立新”“标记”三个方面的语用价值。
“简洁”是指说话者可以用较少的字符表达同样充分的信息。“很中国”也可以表达为“很有中国特色”,但后者更费力,前者符合“省力原则”,且更容易进行类推操作,如“很美国、很西方、很北方、很大陆”等。“很+NP”的母框架为“很+AP”和“名词谓语句”。“很+NP”的结构虽然违反了常规,但丰富了表示修饰的句式结构,使语言表达富有新意。认知角度看,反传统的结构是一种“标记”,更易引起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很+NP”进入交际时,“很”一般读重音。另外,“很”凸显了“NP”的附加特征义,句子的信息焦点也集中在“NP”所具有的描写性特征义上。
在信息时代的影响下,网络语言尤其是标题党格外追求快捷新颖、重点突出的表达方式,“很+NP”正好满足了这一表达需求。
3.2 “很+NP”所涉及的语境因素
能否激活出NP的附加特征义离不开语境,尤其是以“背景知识”为代表的非语言语境。祝莉(2003)通过语感问卷考察了哪些动物名词可以出现在“很+NP”结构。调查显示,并不是所有的动物名词都能出现在“很”后,使用频率为[很牛、最豺狼]>[很驴]>[很猪、很狐狸、很狗熊、很鹦鹉、很兔子]>[很猿猴、很绵羊、很骆驼、很狗]>[很鱼、很青蛙]。
在第二节语义层面,我们已经探讨了“附加特征义”方面限制,然而涉及到具体的言语环境时,“很+NP”还受制于说话人的感觉、知觉、风俗习惯、种族、宗教信仰、文化水平等主观因素。就词汇本身,豺狼具有凶残狠毒的特征义,牛具有倔强能干的特征义,驴则有愚蠢无能的特征义。这些为“很+NP”言语形式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在汉民族语言文化中,这些特征义与文化义相符合,因此句子能准确无误得生成并且被读者理解,如:
例5十字街上还有一个饭铺。一般是挂一个或两个红幌,(挂蓝幌的是回民馆子)……挂四个的是省城的大饭店,挂八个幌的是当代宰客最豺狼的地方。(阿成《凡世风景》)
例6“再说陈小凯那小子就是太牛了。”“唉,人家是陈局长的儿子呗!”(楚天石《绿色》)
但如果词汇特征义与民族文化相冲突时,句子就难以被理解。
例7“两人看起来都挺斯文的,怎么吵起架来还很狗呢?(引自祝文)”
这里的“狗”是“很凶”的意思,本族语为汉语的人基本可以明白。但在很多外国人看来,“狗”是可爱忠诚的动物,很难把“狗”和“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缺乏文化背景知识时,即使每个字都认识,也无法正确理解该句话的内涵。
4 结语
综上,“很+NP”结构在句法、语义和语用层面都显示出一定的选择和限制,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才能使用。本文虽然存在缺乏定量统计的局限性,但是对“很+NP”结构展开了较为具体全面的描写与分析,为国际中文教学提供了本体理论的参考。
注释
① “很”和“NP”是在语义深层发生关系,“很”修饰的其实是名词短语中的附加特征义和语境意义,因此能被接受,这一点将在后面具体解释.
② 本文个别例句转引自吴剑(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