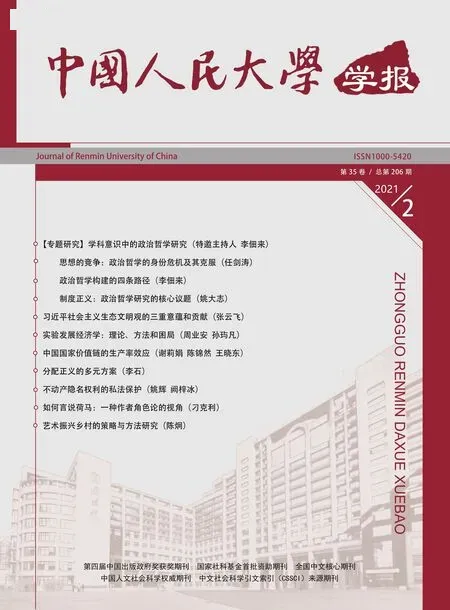环世界与超国家:民族主义退场后的世界秩序重构
近代以来,一个改变世界的制度发明是将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国家 (Nation-State)。但是“民族”与“国家”有着大相径庭的历史渊源和行动旨趣①张凤阳:《西方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与逻辑》,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5 (6)。,民族没有国家一般的组织架构,民族身份的确认也不像取得国籍一样需要履行手续或契约。深入考察“民族”的含义不难发现,民族形态古已有之,但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却是与西欧“主权国家”相伴生的,都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产物。民族从来不是自在的或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但我们却很难确指民族的构成要件或者可被称为“民族性”的独特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民族给出了复杂交织的论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族所代表的意义确实含混不清。②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9世纪至今,西方对民族的理解分裂为两种:一种是西欧国家最初使用的在政治上将人击碎为“原子”的主权人民,另一种则是种族—文化意义上的族裔,后者在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流行。③马德普:《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载 《政治学研究》,2019 (2)。以亚洲为例,亚洲各国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是在古波斯文明的东渐、印度教的传播、唐帝国的崛起和蒙古铁骑的征服中被反复强化的首要身份认同,是用以凝聚人群的文明内核。①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163-172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正因民族概念本身的模糊,众多学者数十年来努力想找到一种划分民族的先验标准,试图将民族与某些确定的概念(如通用语言、宗教信仰、历史记忆、出生地或血缘)绑定在一起,但这未能严格澄清民族的定义,总是遭遇各种“例外”——典型的如犹太民族,他们因千年来流散世界各地而操不同语言、拥有迥异的肤色外貌,但他们仍以“同一民族”的名义建立了民族国家以色列。
为了绕开那些令学者们陷入争论的客观指标,美国政治学家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提出了“想象共同体”这一指向主观认知层面的民族国家理论,并在书中不吝笔墨地花费大量篇幅去厘清民族与族裔的非同构关系,他认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不是由宗教、语言等社会要素决定的,而是一种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6-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然而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理论的修补并不完美,既然想象能够凝聚人群,也就足以分裂共同体,安德森提出的这种旨在尽可能聚合多元族裔的理论反而成为分裂分子手中的利刃。民族共同体本质上的“有限性”决定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一种涵盖全人类的普世理论,且想象共同体理论对20世纪的国家问题缺乏解释力亦是事实。③Go,J.,&Watson,J.“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from Imagined Communities to Colonial Conflic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9,60 (1):3168.必须看到,民族—国家不会永续存在,“民族”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④徐迅:《民族主义》,2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也是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的有着历史局限性的政治观念,它已无法反映当今世界共同体形态的复杂现实,甚至会扭曲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剖析民族主义逐渐式微的原因,进而建构一个比“共同想象”更适合团结大规模共同体并帮助世界秩序走向“共在共生”的新理论——“环世界”理论,最后论证环世界在中国率先扩展的合理性。
一、“建治分野”:民族主义的两副面孔
今天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可以视为三种不同结构与原则的融合:政治与族裔的、语言与领土的、历史与文化的。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纯粹由民族学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所建立并维持的国家,目前学术界使用的“民族国家”概念其实是在主权意义上指称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领土与民族所居疆域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⑤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驱动这个组织运行的正是民族主义 (nationalism)。英国哲学家盖尔纳(Gellner)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早于民族建立的、基于利益的共同情感,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而非民族缔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⑥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holson,1964,p.169.16世纪以降,欧洲的民族国家化伴随着中央集权,打造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模板,进而成为主导当今世界基本政治单元的共同体形态,令其后新建的国家竞相仿效。在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开始着手重建一种远离战争的国际秩序——将民族自决与主权国家结合起来——从而引导世界开启了一个如英国经济学家白芝皓(Walter Bagehot)所说的“民族创建的世纪”⑦Walter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 on“Nation-making”.Chicago:Ivan R.Dee Publisher,1999,p.Ⅵ.,这种创建既需要由居上位者建立一套国家机器,同时也离不开平民百姓的认同和参与。从结果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凡尔赛条约》使民族自决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普世性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独立解放运动则直接催生了大量新的民族国家。
然而,人们渐渐发现,民族主义其实拥有迥异的两副面孔,它长于建国 (或者说它擅长挥舞“政治独立”的利刃来切割世界),却在治国方面表现糟糕。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选择使用“良性”与“恶性”民族主义①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398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来对这两副面孔加以区分的尝试并不成功,尤其是在“良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与自由主义兼容的”这一核心问题上,伯林始终未能说清。②刘擎:《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从观念分析向社会学视野的转换》,载 《社会学研究》,2006 (2)。事实上,我们很难在民族国家的常规治理中发现一种“良性的民族主义”,所有版本的民族主义都无法回应“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相矛盾”时何者优先的经典难题,如果主权国家可以凭借所谓民族自决原则独立,那么国家中的某一地区是否也可以同样的原则从共同体内部分裂出去? 当少数民族以独立为要挟向国家勒索过多的利益,国家是否应当为统一而妥协? 由于民族国家这个民族主义的物化形态自诞生伊始就带着一种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所定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结构性矛盾,因而,在一个被民族国家填充的世界中,似乎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生存矛盾的巨大威胁,这种矛盾不是由生活资料匮乏所引发的,而是由民族国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所必然导致的诸多风险和危机。③张康之:《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处境》,载 《学术界》,2019 (3)。
通常,诸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都或多或少具有向理论或哲学收敛的倾向,但民族主义是个例外,在孕育出“国族”(nation)概念之后,它并没有继续建构一种国家理论,可以说民族主义在政治动员上的强势与政治哲学上的空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我们可以回到民族主义诞生之初来找到解答——它本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潮——“民族主义乃是立志于推进国家统一、独立、发展的意识形态或运动……民族主义最初的目标都表现在统一国家内部的政治,以及针对其他国家,力求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在国际社会获得主权)。”④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2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所以,在最初建立一个国家时,民族主义往往能够为政治运动提供近乎不竭的能量,但到了“革命的第二天”,当他们着手治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时,民族主义却逐渐露出疲态。20世纪的历史证实了这一观点,民族主义在建立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中功勋卓著,同时它也在治理国家时犯下了累累罪行,在东欧、南亚与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种族)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像野火一样在这些地区蔓延,因为它能够给军阀和武装分子提供一套机会主义的、自证合法性的词汇”⑤叶礼庭:《血缘与归属》,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混乱成了野心家们的阶梯。“民族”的绝对观念和“国家”的暴力机制一旦结合起来,就成为无尽的暴力源泉,它把一个民族动员起来,为一种观念而不是利益去制造暴力,却不需要理由和程序。⑥徐迅:《民族主义》,8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族群、肤色、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些都是当时民族主义者在组织动员建国运动时喜欢谈的论点⑦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London:Everyman Paperbasks,1910,pp.359-366.,但是在治理国家时,前述要素的细微差别却纷纷成为引发纷乱和暴力的导火索,人们总是将现实的困境归因于那些“异族人”。在一个历史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初,民族叙事必须服从实际的政治需要,此时的民族即国民的总称,国家通过提供公民权和政治参与保障来尽可能抹平民族之间权利上的差异。然而,随着国家各个系统在建立之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民族国家对同质性的这种追求,会迫使它不断通过“排异”(如种族隔离、驱逐、屠杀等)或“吸收”(如同化、教育或政策引导等)的方式确认自身。
整体来看,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内核稳定的理论,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旨在确定以“民族”为基础的文化认同的社会运动,始终指向在社会层面快速区分出“他者”,以“民族”为理解自身存在的轴心,整合和确认国家与社会、自身同他国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成了一切矛盾的解释,也成了消除仇恨的答案,而这些差异中最直观、最凸显的无疑正是民族差异。在所有民族主义的文本中,总是存在着“外族人”这个无法被纳入共同体中的永恒他者,该话语没有为缓解矛盾预留空间,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一再引发处在中心的主体民族与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种族民族主义比公民民族主义更擅于制造“他者”(事实上,即便公民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更包容,不再将血缘作为分辨“自己人”的唯一标准,但它依然无法覆盖所有人),并通过与外族的对抗而激发团结,虽是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但终究建立在仇恨基础之上,它将共同体引向分裂。无论哪个版本的民族主义,在治国的时候都会频繁遭遇困境,不得不时常借助恐惧与仇恨来煽动民众情绪,通过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实现团结。
虽然明知民族主义极易在这样的混乱中滑向民粹主义,但民族国家的执政者为了在民主政治中生存下去,不得不继续饮鸩止渴,一些老练的政客则会巧妙地给民族主义戴上各种面具。比如,西欧和北美的民族主义其实质是自由主义,南美的民族主义则多属于共和主义,而俄罗斯民族主义则表现为对东正教教义和国家至上主义的坚守。然而无论什么样的面具都无法遮蔽民族主义将在民主制度中滑向民粹主义的现实,趋向保守和单一化的民粹主义对“国家边界”的保护意识是敏感而富有攻击性的,它会频繁使用全民公投来决定民族国家的命运。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崛起、“美国优先”战略实施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反全球化事件的出现,使知识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主权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以及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的概念适用边界。①David Lea.“A Re-Affi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The New World Order”.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2017,8 (1):24-38.如果民族主义只能令所有国家的处境都日益变差,那么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将是一个必然被淘汰的国家形态。事实上,尽管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异常清晰,但我们却根本无法锁定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边界,即便是在没有激进革命力量推波助澜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要求尽可能影响所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保守主义学者们,如约拉姆·哈罗尼(Yoram Hazony),试图通过批判一切会冲击民族国家边界的新思想来为这个衰弱的概念重新注入活力,他们将自由主义及全球贸易体系、基督教、伊斯兰教、纳粹甚至马克思主义等都视为另类的帝国主义,或为建构帝国提供过动力。②Yoram Hazony.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New York:Basic Books,2018,p.229.然而,哈罗尼等人对民族国家所做的非黑即白的判断(即不同意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却诉诸一种虚假的“稻草人”批判,无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往往并非针锋相对而是彼此欣赏的历史事实③Paul D.Miller.“The Vice of Nationalism”.Orbis (Philadelphia),2019,63(2):291-297.,这不但极大地削弱了保守主义为民族国家所做的辩护力度,而且更突显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秩序中的尴尬处境,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民族国家概念应该回到属于它的历史位置中。
二、环世界:一种分形结构的超国家
西方一直有一种超越国家的思想传统,从斯多葛学派到康德、尼采,再到哈贝马斯以及今天的欧洲左翼,许多先贤都曾构想过“世界公民”或论证过“无国界伦理义务”的合理性,这些思想都为超越民族国家和传统国际框架的世界主义注入了动力。除了世界主义者以外,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普遍主义者们也都曾做出过关于“民族国家将走向终结”的判断,尽管他们的理由、目的和论证方法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洞悉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的根本悖离将持续引发国际矛盾这一事实。今天的联合国无力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本身是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框架内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而非打破传统秩序,所以我们无法期待联合国带领世界走向共在秩序(order of coexistence)。民族主义退场后,民族国家也将不再是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它会被一种新的共同体所替代,我们认为,这种共同体是“超国家共同体”(supranational community)。有的学者将“超国家”定义为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结合成有机的国群共同体,其成员国家共享着某种信念、价值、目标,国民有着相似的生存方式和相处之道。①陈曙光:《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载 《政治学研究》,2016 (6)。然而,这种对超国家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束缚了,它依旧基于主权边界、利益分配和地缘竞争格局的传统视角来定义超国家,而不是站在人类共生共在的高度上理解超国家这个新事物。在共在秩序下,传统的国境边界、民族分殊和主权神圣性都将在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逐渐模糊,世界也将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向一种低对抗性的“天下体系”(All-under-heaven System),而形塑超国家的或将是“环世界”理论。
“环世界”概念最初来自德国生物学家尤科斯考尔(Jakob von Vexkull),用以解释他者形成的超乎我们想象的迥异环世界。②蓝江:《环世界、虚体与神圣人——数字时代的怪物学纲要》,载 《探索与争鸣》,2018 (3)。我们将环世界定义为一种由话语体系所构筑的包裹着存在者的坚韧的“壳”,所有存在者都处在环世界中,而不是直接与冰冷的一般世界接触。作为一种存在者与一般世界之间的多棱镜,环世界承担起了帮助此在(Dasein)认识世界的功能,也正是由于透过环世界经验到的事物与事物的本真具有差异,所以处在不同环世界中的存在者才会形成属于他的世界图景(Weltbild)——一种由知识论、方法论和伦理观辐辏而成的对世界的理解。③柳亦博:《话语体系与“环世界”》,载 《探索与争鸣》,2019 (5)。环世界所要追求的始终是人的共生,共生状态是存在者们共同在世的一种最富合作意义的想象④柳亦博:《环世界的扩张与重叠:一种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变革指向》,载 《学海》,2019 (4)。,我们可以称这种由环世界融合所形成的世界共在秩序为“天下体系”,它与传统的国际竞争秩序有着本质区别。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存在者感知世界的经验触角被极大地延长,几乎所有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将呈现出扩张趋势,环世界在扩张中难免会发生碰撞,只有同质的环世界才能在碰撞中融合。在环世界理论中,从最小的单位(个人的环世界)到最大的单位 (世界的环世界)是同构的,“个人—家庭—国家—世界”是一套比例缩放的“分形结构”。分形结构不同于中心—边缘结构或层级结构,分形结构可以用数学上的“科赫曲线”(Koch Curve)来表达,其内部充满了细节丰富的自相似性,但又并非是空间填充的,环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相似,放大部分的“细节”会发现它与部分同样也相似,即是说个体存在者的环世界与家庭的、国家的甚至超国家的环世界皆符合比例缩放关系。⑤杰弗里·韦斯特:《规模》,27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这种比例缩放关系是由环世界中诸核心要素和主网络结构决定的,如存在者、网络规模与损耗、认知模式与信息效率等,在世界范围内是相似甚至相同的。所以,包裹着个体的环世界与他所属国家的大环世界之间,既是同质的也是比例缩放的,在网络规模与损耗上是亚线性缩放关系,而在治理难度上则是超线性缩放关系。环世界理论并非使用了儒家视阈下的家国同构观,更不是将“一家”定义为“天下”,而是要建构一种从单个“细胞”到“组织”直至世界“有机整体”都是分形同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分形同构保证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大的世界图景上的一致,同时这种同构又能够包容环世界的异质性,它承认并尊重多种样态的环世界共在。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通过识别甚至制造“他者”来团结“我族”,那么环世界则是通过吸纳包容他者来实现团结。但这并不意味着环世界是一个完全消除了“他者”的世界,它只是不热衷于刻意制造“他者”。在这一点上,环世界与天下体系中的“无外”概念相近,都指向在“世界内部化”的过程中保留“和而不同”这一基本伦理。①赵汀阳:《天下体系的未来可能性——对当前一些质疑的回应》,载 《探索与争鸣》,2016 (5)。在环世界中,当然不会仅凭认同就足以消除全部的矛盾、紧张和冲突,即便是在规模更小、更亲密无间的家庭组织中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只不过环世界主张通过“协商、妥协”等代价最小的方式去化解冲突,而非通过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来抑制相对弱势的行动者导致玉石俱焚。应当说,在环世界形成的超国家不是对民族国家的加强,而是对它的消解。环世界的一项基本责任就是将世界打造成政治主体,“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②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2)。,通过制度设计和行动权力去限制那些破坏人类共在和合作基础的行为。
环世界联结起来的人群是跨越国界的,虽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主张世界各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国际性阶级,但阶级理论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平等”,而且这种平等主要是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实现的经济平等,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所需的一切。③G.A.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与阶级理论不同,环世界的终极价值指向“公平”而非仅在经济上平等,因为环世界并不视阶级利益与经济关系为人群跨国联合的基础。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比如法国与塞内加尔国内都有被压迫者,但两国的被压迫者却是异质的、疏离的,很难形成什么认同,更不可能联合起来组织跨国行动;美国与古巴两国也都有工人阶级,但相同的工人身份也无法帮助他们达成什么共识或组建跨国工会——真正能够将跨国人群团结起来的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比重或分配关系,而是具有共同的世界图景。
在国家治理的运行中,民族主义所发挥的一大功能是创造归属感,使民族性深植在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虽然环世界也能提供归属感,但民族主义的归属感指向世界的封闭,而环世界的归属感则指向世界的敞开。归属作为最有效、最经济的防范暴力的手段,“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 ‘说着你的语言’”④叶礼庭:《血缘与归属》,9-1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这里所谓“说着你的语言”,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语言,而是拥有共同的世界图景。当然,语言对于过去长达3个世纪的现代民族建构确实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许多民族国家的维护者在寻找令民族概念能够立足的基石时,都会诉诸共同的语言。例如,德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格林 (Jacob Grimm)就将民族定义为“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⑤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12-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试图通过通用语言来厘清民族边界。然而,民族及民族国家问题的复杂之处就在于,共同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又无法作为构成民族的充分或必要条件,比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可以容纳如新疆、西藏或者边疆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国族”,是无法被窄化为仅仅与使用“汉语”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的,机械地以“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模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只能强化不同形式“独”的倾向。⑥罗岗、潘维、苏力、温铁军等:《中国话语》,载 《开放时代》,2019 (1)。更关键的问题是,伴随着世界多元文化之间交流的增强,以及大数据、机器学习和高速移动网络支持下的实时翻译技术不断提高,沟通的鸿沟被技术所弥合,自然语言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在文化和词汇的融合中逐渐消除(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日常用语中外来词汇的增加),同时语言的认同塑造功能也将逐渐弱化。即是说,技术的进步使认同感塑造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这将直接导致传统的“语言塑造民族”争议被自动消解,使得问题的消失成为问题的解决。
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某人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关键,基本上是与语言无涉的,就像诸多法国学者强烈反对将法语列为取得法国国籍的先决条件,相反,他们认为公民权才是决定某人是否具有法国籍的标准。①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尤其是在现代的人工智能同声传译帮助下,语言更加难以成为一种入籍的障碍。因此,安德森所强调的那种由“印刷资本主义”整合各地方言并与新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伴生关系的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会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基于共享社交规范的多语言网络互动,比如基于“礼仪”的“全景直播”“远程教育”等集体游戏,这将成为一种比阅读的感官刺激更强,但想象力门槛却低得多的环世界敞开方式。安德森曾将印刷资本主义视为工业社会的远程民族主义基础,而在信息社会,这种基础必然朝着信息化转向,通过信息技术塑造存在者的世界图景。在这个过程中,“礼仪”将发挥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存在意义彰显在内部空间的沟通技巧,是在承认并尊重他者的前提下,被一套统一价值约束而形成的义理伦常、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一种参与成员皆遵守礼仪的游戏不同于单纯的玩乐,它能够快速建构起一种精神世界来促进所有人的合作意愿,以“虚拟现实”的集体互动形式传播文化内核、塑造并持续扩大着一种超越国家领土边界的文化认同。
三、由“国际”走向“世界”:亚洲的环世界融合与世界共在秩序萌芽
在一个争霸的世界中,每个国家身边皆是虎视眈眈的邻邦,环境逼迫着所有多民族国家不得不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国族”,以便最大程度地组织起自身的力量。此时,民族就是为了在政治上自我保存这个最基本目的,将国土上的全体居民组织起来的那种政治经济的结合,进而从政治生活蔓延到社会,渐渐成为人们关系的自然准绳。②泰戈尔:《民族主义》,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世纪以来,边界清晰且自我封闭的民族国家成为主流甚至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国家形态,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星球上只存在着“国际”而没有一个可作为整体来加以理解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被民族国家切分成两百余块碎片,且国与国的边际处未必严密咬合,在那些未被国家主权覆盖的缝隙地带,不仅是共同行动失灵的空间,更是道德失范的文明边缘。③张乾友:《我们如何共同行动? ——“同意理论”的当代境遇》,载 《文史哲》,2016 (4)。从人类演化、自由、合作、伦理等多重意义上,民族国家及其缔造的竞争性国际秩序都应当被超越,然而这种超越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划定的世界版图上构想出来的,因而我们才需要环世界理论和它建构的超国家。超国家对民族国家的置换,将带来国际关系、国家与世界关系以及整体世界秩序的一系列变化。帝国主义曾将世界视为征服、支配和剥削的对象,帝国作为亚欧大陆特有的现象,它从未将自己处身的世界视为政治主体④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7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民族主义则认为国家利益至上,世界只是需要被国家认识和把握的客体;而在超国家时代,没有什么民族或国家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外人或不可共存的死敌,环世界追求人的共生共在,基于环世界理论的超国家则会孕育出一种包容的世界秩序——天下体系。“任何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地区都被邀请加入天下的共在秩序……必定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任何他者化入共在秩序中。”⑤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3-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换言之,环世界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和敌对性,也不包含民族国家的竞争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是具有兼容性、共享性和友善性的天下体系,它的预期状态是限制任何成员自私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追求共享利益的最大化⑥赵汀阳:《“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载 《文史哲》,2018 (1)。,而不是快速“区分敌友”⑦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人类对超国家的构想由来已久,20世纪以来付诸实践的超国家包括苏维埃联盟、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苏联与欧盟。苏联作为曾与美国争霸的一极,却在1991年《阿拉木图宣言》后彻底解体,这直接宣告了中央集权式超国家实践的失败。欧盟在苏联解体的同年成立起来,虽然近来英、法、德、意等国的建制派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民粹主义和反一体化运动的挑战,但总体上欧盟依然保持着活力并仍在逐步扩大成员国规模。从本质上看,欧盟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经济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其成员国保持着自身主权、独立的政治系统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治理在国家与超国家层面的互补依存和联通”,民族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得以保留,并与公民创建的欧盟共存。①Jürgen Habermas.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A Response.Malden:Polity Press,2012,p.27.然而,在现行的国际游戏中,玩家必须是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欧盟要想进场参与博弈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成员国争夺“主权”。这种欧盟与民族国家的共存,一方面会导致国家主权的分离以及人民自身认同的分裂,严重时甚至要面临成员国脱离;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各国政府又饱受福利政策拖累而无力应对跨区域风险,除非它们都能够“在对内政策上鲜明地被纳入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有约束力的合作过程”②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载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8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面对这种矛盾,哈贝马斯强调,欧盟以及诸如“北约”(NA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跨国组织的出现必然会使“民族”这个陈旧的结构露出一道缝隙,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民族国家“失去权力”,但也恰可证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发展观以及民族国家消亡、后民族结构出现的必然性。③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86-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欧洲的一体化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服务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逻辑的超国家,而非一个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共在秩序为理想的超国家。因而,环世界理论在建构超国家时需要走一条与苏联的“政治整合”和欧盟的“市场整合”不同的“第三条道路”,基于一种普遍性的理念(如“和合”)拓展出跨越国界的文化共识,最终形成远程认同并构筑起同质的环世界。
帝国的征服秩序属于历史,环世界的共在秩序属于未来,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民族国家的竞争秩序会被逐渐解构为合作。帝国只能拥有臣属国,很难拥有不接壤的“飞地”,即便是威尼斯创造的海洋帝国也很难突破地理空间上的隔离形成有效的远距离统治。民族国家也很难突破地域的限制,世代散居于不相连的地方,彼此没有共同生活地域的人们无法形成共同语言,也就难以成为一个民族,因而民族国家占领的海外土地只能成为殖民地。但是领土国家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社会的“容器”④John Agnew,and Stuart Corbridge.Mastering Space:Hegemony,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1995,p.216.,随着全球化的流动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对距离的突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即使相隔重洋也能形成共同的文化、经济生活和心理模式,最终通过虚拟的“在场”使一种基于“和合”观念的“环世界”共识得以传递,并创造一种云状弥散的、边界模糊的“超国家”认同。应当说在通向有序自由的国家形态谱系上,民族国家处在帝国与环世界之间,帝国是一种人为的强制性建构,民族国家被视为一种人们依照自愿原则对帝国进行分解之后所形成的共同体,而环世界则是当技术打破了空间带来的流动性障碍之后,人们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追求自由合作的结果。当然,即便民族主义会逐步消隐,但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却不会因此停止。我们认为,在民族主义离场后,认同感的创造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能够由“环世界”承担起来,而且,环世界理论将率先于中国扩展开来,其所创造的世界共在秩序也将率先于亚洲进行实践。
为什么环世界能率先在亚洲替代民族国家理论? 又为何是中国扮演关键角色?
当前的世界,非洲普遍缺乏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性建构,澳洲(即便加上新西兰与太平洋其他岛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和人口体量,它们都不具备塑造新世界秩序的能力或愿望;美洲表现为一种鹰鸽博弈的国际关系,北美(尤其是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对拉美诸国施加强力影响,要想建构新秩序则需要打破由美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欧洲则被“欧盟”这个超国家高度结构化了,要想孕育出新的秩序则需要首先斩断工商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牢固绳索。所以,非洲与澳洲没有建构新秩序的能力,而欧洲和美洲都需要先行打破一个坚固的旧秩序,其难度都将超过由亚洲这个人口、资源与经济规模都足够大的大洲借助“一带一路”“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等制度建构去形塑一种新的世界共在秩序的难度。更重要的是,环世界是一种“文化整合”超国家,而亚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余大洲的文化具有更强的同一性,围绕着中国以及印度形成了“政治—宗教”的双核结构,这就使得亚洲各国的环世界在融合时会产生最小的震荡。美国政治学家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崛起的世纪,随着亚洲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 (即实现日本学者船桥洋一所谓“亚洲的亚洲化”①Yoichi Funabashi.“The Asianization of Asia”.Foreign Affairs,1993,72 (5):75-85.),世界的亚洲化进程也将随之开启。②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10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这描述的正是亚洲各国环世界的扩展与融合过程。
即便如此,为什么环世界会率先在中国向外扩展,这与帝国领土扩张有何不同? 考察中国的历史会发现,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游离在西方政治学概念之外的“异类”,虽然它早在秦汉之后就转型为国家政治,但这既不是城邦 (polis)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古代中国与帝国确实非常相似,比如没有国界(boundary)而只有实力所及之边陲 (frontier),但古代中国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扩张性质,而是作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③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63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列文森 (Joseph R.Levenson)、白鲁恂 (Lucian Pye)、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西方汉学家都发现了中国有别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并试图将之定义为“文明国家”,即将中国视为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单位加以分析。若照此逻辑,何故其他文明不能定义别的国家? 我们完全可以将世界上划出8个 (基于亨廷顿的理论)甚至23个 (基于汤因比的理论)“文明国家”④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8-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事实上,这一概念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国家”定义限制了对“文明”的理解,中国更应当在政治学意义上被理解成一种追求共在秩序的“环世界”。中国的独特性可从其政治发育源头窥得缘故,中国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思路全然不同,中国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自周朝开始,统治者与理论家们就在寻找一种不靠强力而靠信誉的统治方式,思考如何创造一个具有普遍正当性的世界政治制度,使世界成为一个政治存在,而天下成为一种政治制度,以实现不称霸的“以一治众”。在这种政治哲学下,唯有令一池水都清澈才能使池中每一瓢皆是清水,世界政治也就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⑤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76-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故此,既然亚洲是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代价最小的大洲,而中国又是亚洲唯一一个将共在秩序(也就是“和”的关系状态)内含于政治之中的具有文明连续性的大国,这一传统自周至秦汉大一统再到1911年辛亥革命横贯两千余年,且中国政治始终有着心怀天下的气度,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环世界将会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为中心向外扩展。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更倾向于拱卫民族国家缔造的竞争性国际秩序,因为在这个秩序下它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推行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主动封闭了自身的环世界,使它越来越不具备孕育一种宏大的世界共在秩序的基础条件。事实上,亨廷顿对此早有预言,他对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出现的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抬头的趋势,以及在西班牙语强势的冲击下美国社会的拉美裔化、精英的非国籍化、移民社群宗教崛起、移民原国籍政府对美国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等现象深感担忧,并预言了美利坚民族性可能演变的五种方向,其中就包括“出现一个依据人种和民族属性排斥或压制非白人和非欧洲裔人的排他主义的美国”①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4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中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与美国不同,这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属性终将渐渐淡去,即便现代中国曾努力参照民族国家模板建立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但它依然部分地继承了古代中国的智慧,也在政治中保留了追求“大同”和“共在”的基因,并化为一种内部兼容并蓄、平和中正的环世界,强调以文力(logos)守天下的德治。②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这种文明韧性和政治系统的多元包容性,是使中国最终能够率先超越民族国家,并将自身环世界向外扩展形成超国家的优势所在。当然,环世界的扩展会遇到很多阻力,但是当一种全球性危机(如新冠病毒、气候变化、核危机等)突然降临时,作为“环世界”的中国能够同时提供非凡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治理效能,并保持民众对政府较高的认同,这种面对危机所显现出的“制度优势”或将帮助中国率先完成环世界扩展,而融合正是其中一种扩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