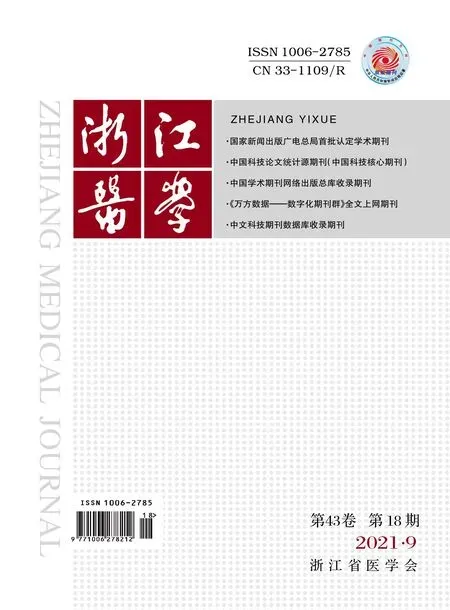川崎病小鼠模型研究进展
蔡小红 卢燕波 吴军华 邱海燕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种小儿常见病,其发病率逐年上升,已经取代风湿热成为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儿童后天获得性心脏病的主要原因[1]。然而,该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临床上尚无特异性试验和生物标志物可用于诊断KD,临床组织样本取材困难也进一步限制了人们对KD的深入研究。因此,构建出符合KD临床特征的小鼠模型显得极为重要,现就近年来关于构建KD小鼠模型的国内外研究新进展作一综述。
1 KD概述
KD又称为黏膜皮肤淋巴结综合征,是一种以全身性血管炎为病理变化的急性自限性、发热性疾病,好发于5岁以下婴幼儿[2]。其临床典型特征包括持续5 d以上的高热且抗生素治疗无效、非化脓性颈部淋巴结肿大、眼结合膜充血、唇充血皲裂、草莓舌、手足硬性水肿、皮疹(包括原卡介苗接种部位红斑)等[3]。KD可损害患儿的心脏和冠状动脉,表现为冠状动脉扩张、冠状动脉瘤,甚至可导致缺血性心脏病和猝死的发生[2]。研究表明,未经治疗的KD患儿发展为冠状动脉瘤的风险可高达25%,在及时接受高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治疗患儿中,这一比例可下降至4%左右,但仍有10%~20%的患儿对IVIG治疗无反应,导致冠状动脉瘤的加速发展[2]。有研究认为KD患儿的心血管后遗症可延续到成年[4]。
流行病学资料提示,链球菌、腺病毒、反转录病毒等多种病原体感染可能为KD的病因,但均未得到证实。有研究认为,川崎病是由免疫介导的,遗传易感因素与多种感染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5]。
2 KD小鼠模型
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小鼠、幼猪、幼兔和犬等动物成功构建了KD动物模型,由于小鼠品系较多,取材较为方便,诱导方式较丰富,成本也比其他实验动物更低,所以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选用小鼠来构建KD动物模型。
2.1 干酪乳杆菌细胞壁成分(lactobacillus casei cell wall extract,LCWE)诱导的KD模型 干酪乳杆菌是一种革兰阳性菌,在人和动物的胃肠道和泌尿生殖道中均有定植[6]。LCWE主要由肽聚糖组成,含有丰富的鼠李糖,可以对抗溶菌酶的降解[7]。1985年,Lehman等[7]将制备的LCWE单次腹腔注射于不同的近交系小鼠体内,发现LCWE可诱导小鼠产生局灶性冠状动脉炎,且冠状动脉损伤在组织学上与临床KD患儿相似。
LCWE诱导的小鼠模型在组织学上与人类KD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LCWE诱导的KD模型与人类KD在血管损伤病理过程中的相似之处。临床尸检研究显示,KD血管损伤包括连续相关的3个病理过程:急性自限性坏死性动脉炎、亚急性/慢性血管炎和腔内肌成纤维细胞增殖(luminal myofibroblast proliferation,LMP)[8]。Noval等[9]通过研究表明,LCWE诱导模型特征是主动脉根部炎性细胞浸润和细胞外基质的破坏、冠状动脉中坏死性动脉炎的发展、LMP引起冠状动脉部分或完全阻塞,可基本概括上述人类KD的3个病理过程。LCWE诱导模型也可模拟KD冠状动脉狭窄,其特征是冠状动脉狭窄、严重的冠状动脉炎和弹性蛋白降解,且LMP在冠状动脉狭窄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10],这与伴有冠状动脉瘤的KD患儿的组织学特征相似[8,11]。
KD是一种巨噬细胞相关的血管性疾病,促炎性M1型巨噬细胞可在急性KD的血管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12-13]。研究表明,LCWE诱导的巨噬细胞炎症反应也参与了KD小鼠模型的血管损伤[14-15],而巨噬细胞功能缺陷的C3H/HeJ小鼠在注射LCWE后不能诱导冠状动脉炎的发生[7]。
LCWE诱导的KD模型与人类KD在心肌损伤过程中的相似之处。KD患儿冠状动脉血栓闭塞可导致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11],在LCWE诱导小鼠的冠状动脉中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组织血栓闭塞[5]。KD患儿的心肌炎可致心肌功能障碍和纤维化,并可导致其长期心血管后遗症。LCWE诱导模型不仅可观察到小鼠急性心肌炎的发生,在诱导KD血管炎后于恢复期给予肾上腺素能刺激也可诱发小鼠的心肌纤维化和心肌功能障碍[16]。与临床KD相似,LCWE诱导小鼠也表现出电生理、心电图异常和心脏神经重塑,并可通过IL-1受体拮抗剂阿那白滞素(Anakinra)得到有效预防或改善[17-18]。
基于KD临床特征,许多学者发现T细胞、IL-1、TNF和1,4,5-三磷酸肌醇3激酶C(inositol 1,4,5-trisphosphate 3-kinase C,ITPKC)等在LCWE诱导模型致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如下:
LCWE诱导模型依赖于T细胞,CD4+T细胞和CD8+T细胞都存在于LCWE诱导的冠状动脉病变中,CD8+T细胞耗竭治疗可防止LCWE诱导小鼠的血管炎进展,RNA测序也发现了与CD8+T细胞细胞毒性功能相关的基因表达增加,而CD4+T细胞缺乏并不影响LCWE诱导KD血管炎的发生、发展[9]。Schulte等[19]分别向RAG1-/-小鼠、B cellnull小鼠和野生型小鼠单次腹腔注射LCWE,发现所有RAG1-/-小鼠均未发生冠状动脉炎,而70%的野生型小鼠和所有B cellnull小鼠发生了冠状动脉病变,这进一步表明T细胞在LCWE诱导的KD冠状动脉炎中起重要作用。
LCWE诱导模型也依赖于完整的Toll样受体2(toll-like receptor 2,TLR2)和髓样分化因子 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信号以及 IL-1β、IL-6和TNF等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14]。Lee等[15]发现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1和IL-1β在该模型冠状动脉损伤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冠状动脉损伤可被IL-1受体拮抗剂阻断。TNF-α在LCWE诱导的冠状动脉炎和动脉瘤形成过程中也至关重要[20],TNF受体的遗传消耗或TNF信号通路的药物阻断可保护小鼠避免血管炎的发生[15,21]。
LCWE诱导模型也证实了ITPKC在KD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ITPKC可通过控制细胞内Ca2+浓度来介导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Nod)样受体家族含pyrin结构域蛋白 3(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3,NLRP3)炎症体的激活、调节NLRP3的表达及随后IL-1β和IL-18的产生,从而影响高危ITPKC基因型患者的治疗效果[22]。
2.2 白色念珠菌提取物诱导的KD模型 白色念珠菌是一种条件致病性真菌,在一定条件下可在免疫受损宿主中转化为诱导炎症的病原体[5]。有研究认为KD发病与对流层风模式有关,在KD高发季节,对流层与地面气溶胶的微生物群有很大差异,其中念珠菌是高空样本中的优势真菌,占所有真菌菌株的54%,表明念珠菌可能是KD的一个致病因素,念珠菌动物模型具有一定可靠性[23]。
1979年,Murata[24]从KD患儿粪便中成功分离出白色念珠菌,并将培养上清液中的白色念珠菌碱性提取物(candida albicans derived substances,CADS)在第 1周和第6周连续5 d注射入小鼠腹腔,成功诱导了小鼠的冠状动脉炎,这种动脉炎在组织病理学上与KD患者非常相似。随后,Takahashi等[25]重复了该实验,发现有66%的CD-1小鼠发生了动脉炎,最常累及部位是冠状动脉近端区域和主动脉根部。组织学上,动脉炎特征是典型的增生性和肉芽肿性炎症,伴有大量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还可观察到血管内纤维层增厚、内弹性层和中层破坏,与人类KD的冠状动脉病变类似。
连续腹腔注射白色念珠菌细胞壁提取物也可诱发C57BL/6小鼠冠状动脉、颈动脉、腹腔动脉、髂动脉和腹主动脉等处的炎性病变,且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在该模型的血管炎发展中至关重要,JNK抑制剂可显著降低小鼠病变的发生率,并可在组织学上阻止血管炎症和组织破坏[26]。
2.3 白色念珠菌水溶物(candida albicans water-soluble fraction,CAWS)诱导的KD模型 CAWS是白色念珠菌培养上清液中释放的水溶性多糖成分,主要由α-甘露糖蛋白和β-葡聚糖复合物组成[27]。
2004年,Nagi-Miura等[27]研究表明,与CADS相比,CAWS诱导小鼠的KD冠状动脉炎发病率更高,且不同品系小鼠的冠状动脉炎发病率也有所差异,DBA/2、C57BL/6和C3H/HeN品系的所有小鼠均发生了冠状动脉炎,其中以DBA/2小鼠冠状动脉炎最严重,死亡率最高,而CBA/J小鼠的冠状动脉炎发病率仅有10%。
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了IL-1、TNF、树突状细胞相关C型凝集素-2(dendritic cell-associated C-type lectin-2,Dectin-2)和IL-10等在CAWS诱导模型中发挥的促炎或抗炎作用,具体如下。
IL-1β的释放需要两个信号:启动NLRP3炎症体诱导NLRP3和前IL-1β的表达,激活炎症体将前IL-1β切割成成熟形式。CAWS可通过Dectin-2/脾酪氨酸激酶(spleen tyrosine kinase,Syk)/JNK/NF-κB 途径诱导NLRP3炎症体的启动,并通过Dectin-2/Syk/JNK/线粒体活性氧(mitochondrial reactive oxygen species,mtROS)途径激活NLRP3炎症体,而IL-1β-/-、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 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spase recruiting domain,ASC)-/-(ASC参与NLRP3炎症体的组成)和NLRP3-/-小鼠不会诱发血管炎,表明NLRP3炎症体驱动的IL-1β产生是血管炎发生所必需的[28],而抗IL-1β抗体可明显减轻CAWS诱导的血管炎[29]。
KD心脏炎症的特征是弥漫性心肌炎发生在冠状动脉血管炎发展之前,Stock等[30]重复CAWS诱导模型发现,TNF和IL-1在KD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时机不同,其中TNF在急性心肌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NF受体缺陷小鼠不能成功诱发急性心肌炎。而IL-1对急性心肌炎之后的冠状动脉炎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IL-1-/-小鼠在CAWS诱导后会发生广泛的心肌炎,但不会进展为冠状动脉炎和主动脉炎。
趋化因子配体 2(chemokine ligand 2,CCL2)-趋化因子受体 2(chemokine receptor 2,CCR2)轴在此模型的血管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CCR2基因失活对CAWS诱发的小鼠主动脉炎和冠状动脉炎具有保护作用[31]。
天然免疫反应也参与了KD血管炎的发展,在CAWS诱导模型中,心脏成纤维细胞产生的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可激活组织巨噬细胞,促进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免疫细胞向心脏募集,从而导致心脏炎症,而阻断GM-CSF可有效阻止心脏炎症的进展[32]。
Dectin-2是一种C型凝集素受体,Miyabe等[33]研究表明,在CAWS诱导模型中,驻留在主动脉根部的巨噬细胞中的Dectin-2信号可诱导CCL2的产生及主动脉根部和冠状动脉中CCR2+炎性单核细胞(inflammatory monocytes,IMos)的募集。IMos在血管壁中分化为单核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并通过Dectin-2/Syk/NLRP3炎症体依赖途径诱导IL-1β的释放。随后IL-1β激活心肌内皮细胞表达CXC趋化因子配体1(C-X-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CXCL1)、CCL2 和黏附分子,诱导中性粒细胞和IMos在主动脉根部和冠状动脉中的进一步募集和积聚,从而引发血管炎症。在CADS和CAWS模型基础上,Oharaseki等[34]发现,在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多糖诱导的KD样血管炎模型中,野生小鼠和Dectin-1-/-小鼠血管炎发生率为100%,而Dectin-2-/-小鼠均未发生血管炎,这证实Dectin-2对α-甘露聚糖的识别是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多糖诱导的KD样小鼠血管炎发病的关键。
Nakamura等[35]研究了IL-10在CAWS诱导模型中的作用,发现GM-CSF可通过上调Dectin-2增加巨噬细胞对CAWS的敏感性。IL-10不能抑制Dectin-2的表达,但可抑制下游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1/2 的 激 活 和 IL-6、TNF-α等炎症因子的表达,减少Dectin-2+CD11b+炎症细胞的浸润,减轻小鼠主动脉根部和冠状动脉中的血管炎症和纤维化,改善心脏功能障碍和致死性,表明IL-10在KD患者治疗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2.4 克柔念珠菌细胞壁甘露糖蛋白(mannoprotein,MN)部分诱导的KD模型 基于CADS和CAWS模型的研究基础,2020年,Yanai等[36]将克柔念珠菌菌株放在天然或化学合成培养基中培养2 d,并提取其MN部分连续5 d注射入小鼠腹腔,发现克柔念珠菌MN部分可诱导小鼠产生血管炎,且菌株MN部分在天然培养基中含量更高、活性更强,诱导的冠状动脉炎更严重。
对克柔念珠菌结构进行检测发现,其主链为α-1,2-、α-1,3-、α-1,6-甘露糖链。Dectin-2 是 α-甘露糖特异性凝集素受体,克柔念珠菌MN部分对Dectin-2有强烈反应性,表明克柔念珠菌MN部分存在大量的α-甘露糖结构,与CAWS模型相似,其诱导的血管炎也是通过Dectin-2信号介导的[36-37]。
在27℃的中性pH下制备的CAWS因存在大量β-1,2-甘露糖残基而不会诱发小鼠血管炎[38]。与CAWS相似,在克柔念珠菌MN部分的核磁共振谱中也没有检测到β-连接甘露糖信号,进一步证实了克柔念珠菌细胞壁MN部分诱导KD血管炎模型的可靠性[36-37]。
Tanaka等[37]比较了不同念珠菌MN部分诱导的DBA/2小鼠血管炎发生情况,发现各种念珠菌MN部分诱导小鼠在第200天的死亡率分别为:克柔念珠菌(100%)、白色念珠菌(84%)、都柏林念珠菌(47%)、近平滑念珠菌(44%)、光滑念珠菌(32%)、吉利蒙念珠菌(20%)和热带念珠菌(20%),这表明MN部分诱导的KD血管炎强烈依赖于念珠菌的种类和菌株。
2.5 Nod1配体诱导的KD模型 Nod1是一种胞内模式识别受体,可参与许多疾病的炎症反应,在天然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39]。
2011年,Nishio等[39]通过研究表明,皮下注射或口服FK565(一种合成的Nod1配体)可诱导小鼠产生冠状动脉炎,且脂多糖可增强FK565的诱导作用。其冠状动脉炎组织病理学特征为全动脉炎、弥漫性炎性细胞浸润,主要为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并有冠状动脉弹性纤维断裂,不伴有纤维素样坏死,与KD急性期相似。而Nod1-/-小鼠不能诱导动脉炎的发生。
在此实验基础上,Ohashi等[40]对Nod1配体和CAWS两种诱导模型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与CAWS诱导模型中的主动脉根部、主动脉瓣和冠状动脉的弥漫性炎症病变不同,Nod1配体诱导模型主要累及双侧冠状动脉,具有位点特异性,与KD急性期的冠状动脉炎更为相似,因此Nod1配体诱导的动脉炎模型可能更适于分析KD患者心血管损伤的组织病理学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临床KD患者不同,Nod1配体诱导小鼠并不会导致冠状动脉瘤的发生。与CAWS组观察到的IL-6、IL-13、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IFN-γ 和 TNF-α 浓度升高不同,Nod1配体组主要表现为IL-1α、IL-1β、IL-5等炎症因子浓度升高,且IL-1β水平似乎与FK565诱导小鼠的炎症区域呈正相关。因此CAWS组和Nod1配体组动脉炎的组织病理学差异可能是由于其不同的细胞因子表达谱。
心脏CD11c+巨噬细胞的积聚在Nod1配体诱导的小鼠急性冠状动脉炎中起核心作用[41]。严重联合免疫缺陷小鼠可出现较弱但明显的动脉炎,表明获得性免疫部分也参与了纯Nod1配体引起的炎症反应[39]。在注射FK565后,脂多糖诱导的RAG-1-/-小鼠仍会发生大动脉炎和冠状动脉炎,因此T细胞、B细胞和自然杀伤T细胞在此模型中似乎是非必要的[41]。
2.6 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érin,BCG)诱导的 KD模型 BCG接种部位的皮肤损伤是KD患者早期特异性临床症状之一,约30%~50%的KD患者存在BCG接种部位的局部炎症再活化[42]。
2007年,Nakamura等[43]向C57BL/6J小鼠皮内接种BCG,4周后再次接种胞内分枝杆菌粗提取物(crude extract from Mycobacterium intracellulare,cMI)成功诱导了小鼠的冠状动脉炎,动脉壁周围有单核细胞浸润,而仅接种cMI或BCG的小鼠未发生冠状动脉炎。同样,静脉注射过氧化还原酶Ⅱ抗体也可诱导小鼠产生冠状动脉炎,但也仅限于事先接种过BCG后。
随后,Chun等[44]证实,腹部皮内注射两次(间隔4周)BCG可诱导程序性死亡(programmed death,PD)-1-/-小鼠产生KD样特征,包括持续发热5 d以上、脚底红斑肿胀、尾部皮肤脱屑和胆囊积水,冠状动脉炎症细胞聚集和内膜增生、动脉壁水肿,也可观察到肝动脉、肾动脉和胆管等器官的炎症反应。同样,腹部皮内注射两次(间隔 4周)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65也可诱导PD-1-/-小鼠产生与用BCG诱导相似的KD样特征,表明PD-1基因可能是KD的易感基因之一,含有HSP65结构的抗原可能是KD的触发因素。
2.7 牛血清白蛋白诱导的KD模型 2020年,齐双辉等[45]通过间断性腹腔注射10%牛血清白蛋白溶液成功诱导了BALB/C小鼠的KD冠状动脉损伤,其组织学特点为动脉内膜明显增厚、水肿及变性,内皮细胞排列紊乱,胞质内大量小空泡,周围炎性细胞浸润。
3 小结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诱导剂构建了KD小鼠模型,其中诱导剂以LCWE、CAWS、白色念珠菌提取物等为主,研究方向多在探讨各种小鼠模型是否能模拟KD病理过程。虽然各种诱导模型仅能模仿KD的部分临床特征,目前也尚未建立一种公认可靠的KD小鼠模型,但在KD病因尚不十分清楚、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的背景下,小鼠模型仍然是研究人类KD病因、病理和治疗等方面的宝贵工具,通过动物模型研究可极大加强人们对KD病理学的理解,推动导致心血管并发症的细胞和分子免疫机制的研究,为KD的治疗方法提供实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