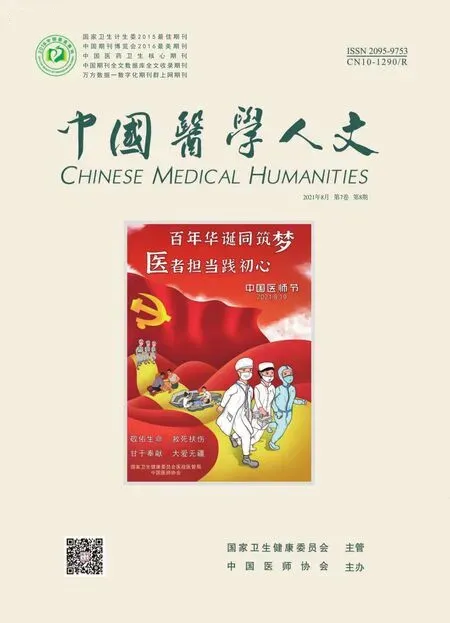谈谈医疗的公益性问题
文/王一方
近一段时间,医疗公益性问题的议论很多,仅从政治角度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的唯一宗旨,这就决定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必须强调公益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何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仔细分析,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公益性是国家卫生事业统筹规划中的公益性,指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的“生命至上”意识,政府决策中的健康优先思维;而狭义的公益性则是指医疗活动中的公益性,就是通常理解的医疗的保障性、福利性。“有病及时看”而且“看病能负担”,跟“看病不花钱”或“国家全负担”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格局还是有所区别,背后是“保”与“包”的纷争。
说到这,有人会列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诊疗费绝大部分由财政负担的事实来做广延推理,既然疫情期间能做到,日常诊疗也就能做到。这个推理存在诸多疑问,一是疫情救治只是少数人群、短暂时间里、单一病种的应急医疗,属于少数危难人群的定点救助;而慢病(长寿)时代的全民免费医疗则覆盖全体国民,全疾病谱诊疗,如果精算费用,未来的医疗费用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
毫无疑问,医疗公益性是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其核心是尊重医疗卫生事业的二元辩证规律,即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对立统一,平衡好民生意愿(政府把民众的健康系在心上,责任扛在肩上)与民粹诉求(期望不病不痛,长生不老,一旦生病,只要医疗获益,把风险留给医生,把代价留给国家)。全民政府与全包政府的张力,尽可能做到合理负担,减少浪费,提高效率,如老百姓负担太重,会造成民怨,继而动摇执政为民的法理基础,如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势必压垮国民经济的预算-支付体系,窒息经济活力,并造成新的过度医疗、医疗挤兑与卫生资源浪费。
如何深入认识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问题的实质,最大限度地拓展医疗公益性,需要置身于历史的长河里去思考,历史是智慧的铜镜,在历史的镜像中,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三个公益性,慈善公益性、保险公益性、财政公益性,三箭齐发,互补、互生才是公益性的全貌。
慈善公益性
回望医院的前世今生,医院曾经是教堂的附设机构。公元313年,基督教在罗马成为合法宗教,救死扶伤成为基督教会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325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规定,凡建立教会之处必须要配备慈善场所,凡建教堂之处都要有医护馆舍。最早的医院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利亚主教巴西里乌斯(Basilius von Caesaria,329-379)在凯撒利亚城门旁边建立了第一所基督教医护所(医院),后来蔓延至欧洲,法碧奥拉修女(Fabiola)在罗马城,兰德里主教(Landry)在巴黎也相继建立起医疗护理所,进入中世纪,在欧洲大陆,凡教堂必有医护所。
中国近代,一大批传教士医生来华办医,创办于1835年的广州“博济医院”,就是由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创办的。传教士医生一词有两重含义;一层是传教(传播福音),第二层是治病救人,对于皈依宗教的人士,常常给予免费的医疗服务。其实,在“免费”的背后有改变其信仰的诉求,传教士医生以免费(或低资费)医疗服务充当他们传教的工具,早期的“施(舍)医院”代表了“慈善公益性”,后来泛化到非宗教组织及个体。其内幕比较复杂,既有这些机构/组织的公益性行为,也有个体的公益性行为,如当今社会的个人针对社会医疗专项或个体医疗窘境的慈善捐款,医生、医院医疗行为中的“劫富济贫”(大夫为富人开具昂贵的野山参,烧炭服用,而对贫穷者则免费医疗)。现代社会逐渐发展成为“慈善基金会”形式,成为企业家们“散财有道”的新途径。今年百年院庆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由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基金援建的远东模范医院,更大的战略诉求是在华培植亲美情感。当然也有相对纯粹的慈善捐助,只为个人、机构彰显亲社会道德及人格姿态的医疗专项慈善资助,譬如以某位影视明星、企业家冠名的“光明行(老年白内障手术)”项目。不过,与国际成功经验(如梅奥医院)相比,我们在吸引社会慈善基金捐助方面还有巨大潜力。
保险公益性
近现代医疗技术的长足进步,技术建制愈加丰满,诊所演变成现代医院(综合、专科医院),医疗技术的提升,吸引社会财富投资这个领域,医疗/卫生经济学兴起,医院经营管理成为一大主题,筹资方式变化,保险筹资成为主流,产生了共享互助的“保险公益性”。
现代保险制度发端于一位医生的创意。1666年9月2日,伦敦城里一场大火整整烧了5天,过火面积占伦敦城总面积的83.26%;有13 200户住宅被烧毁,财产损失达1 200多万英镑,2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火灾造成的损失惨重,幸存者非常渴望能有一种可靠的保障,以便对火灾损失提供补偿。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满足,聪明的牙医巴蓬(Nicholas Barbon)1667年独资设立保险营业处,办理住宅火灾险,在巴蓬的主顾中,有相当部分是伦敦大火后重建家园的人们。
生命是最宝贵,也是高贵的财富,财产保险很快拓展到人寿领域,寿险业蓬勃兴起,而要保持长寿,不至于过早夭折,就必须致力维护投保者的健康,提供医疗、护理、养老保障服务,于是针对大病、重疾的医疗险、健康险、护理险(长期照护险)等险种便应运而生,编织成全方位、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体系。如今,保险业扩大保险服务筹资,运用金融杠杆投资兴办医院、养老院、体检中心,为投保者提供更细微的健康、医疗、养老服务。
毫无疑问,就保险个体的获益性而言,商业保险为投保者提供了超出保费投入的具有某种“公益性”特征的医疗、保健服务,很显然,这一份公益性“给付”是建立在一定基数的投保群体,保费收支精算盈利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实现双赢。以至于后来的政府由公共财政支出建构的医疗公益性体系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众筹-共担-共享-共济”模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基于这个思路,在筹资方增加政府、受雇机构的出资比重,来建构普惠的健康医疗保障体系。
财政公益性
在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鲜有财政经费承担国民日常医疗给付的案例,遇灾荒、瘟疫等非常时期,可能会以赈灾的名义发放微薄的救济款(含医疗补助金)。18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各国政府扛起部分人民健康(民生)的责任,将税收、财政收益的部分投入到公共卫生与国民医疗保健事业之中,医疗开始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加大政府投入,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于是,财政给付从无到有,比重增加,产生了“财政公益性”。
在西方,推助政府注资改善公共卫生治理的人是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他不仅是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现代病理学的先驱,还是社会改革家。1848年初,他被奉派到西西里亚调查斑疹伤寒的流行情况,他把公众健康恶化的原因归咎于恶劣的社会不公,斥责政府失职,并呼吁社会治理,如改水,改厕,改善居住条件,消除饥饿与贫困。1883年,卑斯麦在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实行国营医疗保险,从此,政客们纷纷以“改善健康照护”的承诺作为竞选政见。
新卫生运动发端于新英格兰。1842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收集分析卫生统计数据,1848年,英国通过第一部《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1867年9月,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书中最早提出了工业病理学的思想,它是马克思医疗卫生观的一个重要侧面,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立场,强烈的公平正义诉求。
由于公共卫生着眼于群体健康,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成本,于是,早期财政公益性的主要承付项目是环境卫生改善与传染病防控。1911年,自由党的财政大臣大卫•L•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以德国卑斯麦的健保法为蓝本,提出国家健康保险(National Insurance)法案,法案的主旨是国家为劳工阶级提供健康保险,费用由劳工本人、雇主、国家三家分摊。苏维埃联邦(前苏联)拓展这一思路,于1930年前后建立了国营医疗体系,当时苏联的医疗水准并不高,且幅员辽阔,城乡医疗发展也不平衡,因此,虽然费用由国库开支,但属于低水准的健康保障。“二战”之后的1948年,英国率先将公共卫生保障与国家健康保险拓展到全民医疗保障,建立了“国家健保系统”(NHS),将医疗、护理、长期照护依次纳入这一体系。北欧也陆续建立由国家财政承付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其实,这里的“免费”概念并不确切,一是筹资来源的异位,不来自保险费途径,而来自高额的税收(转移支付);二是医药分家,看病不需付费,拿药可能需要部分支付。由于最初设计者的误判,随着技术进步,病会越治越少,国家健保投入会逐渐减少,谁曾想技术越发达,病却越治越多,国家健保投入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财政持续加大投入成为一个瓶颈。另一个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国家健保体系的运行效率不高,预约、转诊、检查的等待时间太长,许多人由此而错过了有效的诊疗窗口,运行中还有医疗资源浪费的诸多问题。因此,同样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法国都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沿袭以保险筹资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医疗保健筹资模型,认为这样更有效率。
总之,医疗公益性是一个历史演进的概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长足进步,还将不断地刷新其概念内涵,丰富其结构、功能,更好地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