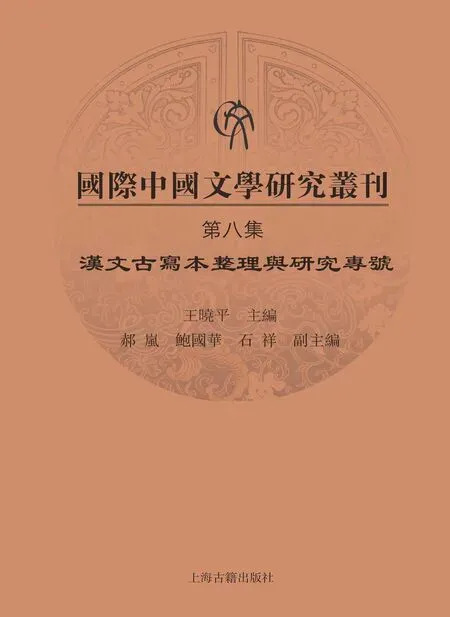書客舊事
王曉平

倫敦博物館前的書環
花園般的大學城裏,我在尋覓。尋覓什麽?尋覓一間書店。
不,不是那種堆滿考研指南、六級習題的書店。我尋覓的是一間可以站在那裏,捧起書本,就可以和孔子、佛陀、柏拉圖對話的書店,尋覓一個可以與一起思考、交談、辯論的朋友頷首擦肩、相逢一笑的空間,有一面張貼著壁報、海報、書訊、漫畫甚至塗鴉的牆壁,一排排映著穿梭的身影,既讓人沉静,也讓人焦慮,既讓人快樂,也讓人痛苦,既讓人嚴肅,也讓人輕鬆的書架。
在有著高聳入雲的圖書館大樓的校園,在互聯網時代,在遠離鬧市的大學裏,還需要書店或者書屋嗎?我想反過來問,圖書館、互聯網就已經具備你所需要的那些東西了嗎?
我是在天津“五大道”長大的。少年和青年前期最懷念的地方,就是老河北大學(今天津外國語大學所在地)的那間新華書店。那是一排平房的第一間,後面的平房就是理髮室、水房什麽的。書店不大,燈光也不明亮。我常常擠在大學生中間,一站就是半天。讀的除了《十萬個爲什麽》《知識就是力量》之類的科技類圖書之外,就是中外名著了。也就是在這裏,我知道了趙樹理、羅廣斌、曲波、楊沫,知道了保爾·柯察金、葉甫根尼·奥涅金、奥賽羅、邦斯舅舅……讀書,原來是那麽舒心的事情。大學書店,受惠的首先是大學生們,但又不僅僅是大學生們。
長大了再讀那些書,已是1973年。那時大學裏正在猛“反回潮”,中國書、外國書又大都不讓看了。好在我們的班主任申建中老師,看重的就是查原文、摳原著、讀全集。他一趟一趟跑圖書館,請求集體借閲,供批判用。全班就以這個名義,從圖書館借了一批外國名著。條件是集體借出,月内全還,不准聲張,不准外傳,不准超期。讀外國名著,就跟“地下工作”似的。想讀嗎?你從晚上8點到12點,我從12點到6點,人歇書不歇;宿舍熄燈,就打手電在被窩裏讀;排隊打飯,課間十分鐘,都成了搶讀時間。奔跑着去與約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對話。現在電視神劇的編劇,誰能編出這樣的“讀書傳奇”?
孔子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就是志向,心之所向;奪,就是强行改變。三軍之帥,可以隨時撤换,可人的志向就不是説讓變就變得了的。讀書,也是一種志吧。在大港油田試油隊的工棚裏,在後山白毛雪風狂吹的冬夜,在“深挖洞”的深深坑道裏,“我要讀書!”四個字一次一次從内心深處蹦出來,字字如春草,燒也燒不盡,凍死又復生,讓我黯然神傷,夜不能寐。
我上的那所小學,原來叫五區中心小學,後來叫新華區中心小學。現在知道,那就是胡佛的故居,在馬場道的東頭。後來上的二十中,也在旁邊,那是解放前的英國文法學校所在地,是愛潑斯坦(1915—2005)的母校。家搬到馬場道234號河北大學宿舍以後,每天上下學穿越五大道,在中外文化交融的氛圍中行走。
一直到今天,每當走這一條路,我都要在馬場道108號前停下來,多站上一會兒。因爲在這裏,我曾經多次拜訪過我最初的學術引路人,已故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家詹鍈(1916—1998)先生。
1958年以前,我大姐王恩東與詹鍈先生同在教育系心理學教研室。那時,在天津師範大學(後來的河北大學)和平樓二樓,常見到可敬可親的詹鍈先生。我當然不明白,爲什麽詹先生在當了教授之後,還要到美國留學,又爲什麽在美國拿到心理學博士學位之後,又要放棄在那裏任教的機會,回到祖國來。可後來聽到的消息就越來越糟,心理學成了“唯心主義”,心理學教研室散了,聽説詹先生去中文系教古代文學去了。
因爲有詹先生,108號成了我心中的一盞燈。更多的接觸是在我1973年上了大學之後。每一次回津,我都要去拜訪108號的詹鍈先生,跟他談我讀到的書。那時“左的錦標賽”尚未收場,記得我説起,讀到有些特會“跟風”的論文,覺得作者伸手就能抓來時髦的帽子,却看不出文章裏有什麽發現,我學不會這樣做,又不知該怎麽辦。對我列舉的那些“大作”,先生只輕聲説了三個字“瞎扯淡”。先生的“不徵不信”,讓我深爲嘆服。晚年詹先生腿脚不好,每次告别,他都把我送到院子門口。
後來讀的書多了,到國外轉了十來年,我好像漸漸悟出他出國與歸國兩次選擇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冥冥中,好像跟着先生的路在走。我想,如果孔子、朱熹、王念孫生在20世紀,他們有機會的話,也會出去看一看外邊世界,而不會只關起門來做學問的。
詹先生交給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任務,就是和杭州大學的陳植鍔一起翻譯松浦友久的《唐詩語彙意象論》。他介紹我與早稻田大學松浦友久教授(1935—2002)相識。這是我第一次從事學術翻譯,松浦友久也成爲我深度接觸的第一位日本漢學家。那本書也是我在中華書局出的第一本書。多年以後,在松浦友久東京都三鷹市家裏的二樓書齋,聽他談起詹鍈先生的學問,敬佩與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我們相對默坐,沉浸在對這位師長共同的想念中。在我求學時代,親眼看到詹鍈先生怎樣將海外漢學帶進《文心雕龍》和李白研究中,是多麽幸運。他用他的隱忍,用他的堅韌,用他默默的耕耘,用最後的生命,爲文學的學術交流架起了一座橋。
没等聽到新千年的鐘聲,詹鍈先生就駕鶴西去了。他或許不會想到,20年後的今天,憑着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從理論上説,我們就幾乎可以隨時與世界每一個角落的學者朋友交换資料,交談學術問題。也正因爲如此,我們更應該緊緊追隨國際交流的新脚步,也更應該記住那些給大橋橋墩打好第一樁的人們,與世界的漢學家和關注中國文化的人們携手前行,同步記録,跟進思考。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嗎?》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想,如果説在20世紀還有這一類人的後裔的話,當中就有一些像詹鍈先生那樣的人,也就是魯迅所説的“知識者”。他們的境遇像翻燒餅似的,冷也罷熱也罷,但那追求真話、真知、真理、真情、真相的“志”,不曾死亡過。也許他們不過是識字的“匹夫”,却因爲有了“志”的支撑,生命從來不缺乏光耀。
誠然,人各有志。在書裏、在書店裏,我們却總能與那些在精神家園“修橋”“鋪路”“造高鐵”的人們相遇。他們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架橋工”。
中外文學交流史研究,我們已經有了《中國文學在國外》《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中外文學交流史》三套大型學術叢書。那麽,爲什麽文化交流,還需要“志傳”呢?我們的《中外文學交流志傳》,就是想要爲這樣的知識者畫一畫像。中外文學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能有新高度、新樣態、新滋味,并由此而贏得新讀者,都是我們樂見的。那種將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和跨文化現象量化、簡單化、標籤化的文字,恐怕很少有人真心愛讀。
托馬斯·卡萊爾説:“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結晶。”史傳是正史中的人物傳。志傳,方志中的人物傳(或稱人物志)和獨立成書的各類傳記,稍晚於史傳出現。史傳和志傳無疑是傳記的正體。我們的交流史志傳,重要是人物志、學人傳。在學人的生涯中,有文化與文化的邂逅,語言與語言的肉搏,精神與精神的對撞,靈魂與靈魂的對話。
我國史書,被譽爲“史家之絶唱,無韵之離騷”的《史記》,紀傳部分那些生動的人物故事,不僅影響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士人,而且爲周邊國家的史書提供了典範。朝鮮半島的《三國史記》、安南的《大越史記》和日本的《日本書紀》等史書,無不記下了許多難忘的民族文化英雄的足迹。除了官修史書之外,日本還有《大鏡》等“物語風”史書,朝鮮半島和越南也有漢文民間史書、野史筆記,記述鄉賢民人的事迹。這些都是漢字文化圈可以共享的文化遺産,也是包括學術史在内的史學遺産。
20世紀的中外文學交流,爲我們留下了數不清的生動故事。我知道,在五大道,還發生過這樣的故事。在那個無學可上的時代,有兩位高中生,貿然敲開一家大門,提出了一個讓主人驚愕的請求: 請屋裏的老先生教他們外語。原來在他們正苦於無學無師的時候,路過這家門口,看到了貼在牆上的大字報,知道裏面住着一位留過洋的“學術權威”,就决定以感動上帝的韌勁“强行”拜師。經不起他們一次又一次的登門求告,老先生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請求,一個“地下學習班”就這樣誕生了。雖然這種高風險的學習没能堅持多久,只讓求學者學會了發音,然而這也足以成爲他們一輩子激勵自己的青春物語,或許亦可作爲中國人好學傳統的一個小小注脚。當然,它僅僅是不見於“五大道博物館”的衆多故事中的一個。那個時候,馬場道的每個窗口,或許都有一個風雨彩虹相互切换的故事埋入心底。
文化交流的動力所在是人心,其效力終歸也在人心。有人有心,才能講好故事。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有温度,就要擺脱自恃高深的“學報腔”。視野宜寬,材料宜富,叙事宜巧,道情宜精,議論宜深,如章學誠所説的“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
賴山東教育出版社知識者的遠見,我們的計劃得以啓動。我們希望見到的是這樣的書: 情理相彰,文情并茂,適當配以圖表。一册在手,有關某一文化現象的傳播、翻譯、交往、研究的全貌便能大體了然於心。不必面面精到,但閃光點能給人印象深刻。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智慧,用我們的文字,讓他們牽起手來,不再只是“在水一方”,“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央”。
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説:“由歷史所示,凡有改革,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婁羅。他只是大衆中的一人。我想,這才是可以做大衆的事業。”我們的大學,應該多出些這樣的知識者。讓這樣的知識者喜歡的書,一定是好書。我們能不能尋覓到這樣的書呢?讓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