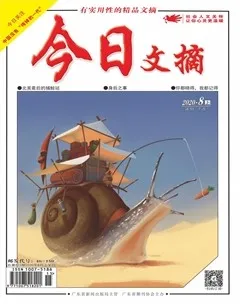北美最后的捕鲸站

2019年5月29日,在法罗群岛的首府托尔斯港,人们围在海岸边,被捕杀的巨头鲸的血液将海水染红。巨头鲸在迁徙中经过位于冰岛和挪威之间的丹麦属地法罗群岛,渔民将鲸鱼驱赶进领地峡湾后,将之捕获。法罗群岛的法律框架中规定了巨头鲸的捕杀方法和许可设备。
6个男人手持着安装在木杆上的锋利的金属钩刃,像一群工蚁一样围在50吨重的长须鲸身边。一个人爬上鲸鱼背,此时的他离地面足有3米高,他沿着鲸鱼宽阔的身体纵深切下一片。另外的工人剥掉鲸鱼皮和皮下脂肪,暴露出一条13米长的肉片。
高豪港的前世今生
精选的肉被去骨后会剁成块,速冻,最终作为品牌莫比·迪克的食品出售。
这一幕发生在1954年,高豪港猎杀和加工鲸鱼的捕鲸站。高豪港位于温哥华西北约350公里处,是一个隔绝的社区。这一年150头长须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西北海岸附近的水域被捕杀。除了长须鲸,在20世纪中期运营的20年中,捕鲸站捕杀和处理的还有抹香鲸、座头鲸、塞鲸、蓝鲸。
地理和历史双重原因使得高豪港成为了捕鲸的中心地带。鲸鱼通常会在迁徙途中沿着温哥华岛的西海岸游过,阔齐诺海峡在开阔的海洋和高豪港之间形成了一条50公里长的通道,海峡深处有个小海湾,捕鲸站就位于海湾尽头的岸边。捕鲸船上的人叉到鲸鱼后,会用拖船将它们拉过海峡,拖到村庄里。
从4月到9月下旬是捕猎的季节,这期间村庄的港口蔓延着鲸血和鲸油的腐臭气味。开往西雅图和温哥华的船只定期通过海峡,停靠在村庄里。离开的油轮装载着从鲸鱼肝脏中榨取的维生素A油,从鲸脂、肉和内脏中提取的不同等级的油,以及干燥和冷冻的食品。
现年84岁的哈里·霍尔记得,早在1951年就有大型油轮定期造访,那一年,作为暑期学生的他开始在捕鲸站工作。60年后,霍尔的朋友、本地商人乔尔·埃勒特森和志愿者建立了高豪港的博物馆,博物馆落成的地方曾是一个鲜肉加工厂,里面摆放着该站全盛时期的遗物和古董:生锈的鱼叉、鲸鱼肉标签和记录捕鲸生活时代精神的剪报。
霍尔说:“你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气味。”他把一座捕鲸站的气味比作一个养鸡场的气味,只不过是——30倍强。对他来说,给一条25米长的蓝鲸剥皮,就像剥根香蕉一样。“切割一头鲸鱼对我来说跟切割一只鹿没什么区别,除了身体要大得很多。”
50多年前,商业捕鲸行为在太平洋东北部的这个角落结束了,再后来,我们在有关鲸鱼的智力、语言和社会性方面获得了很多发现。公众舆论压倒性地发生转变,开始反对商业屠杀并在全球市场上将鲸鱼作为商品交易。
霍尔像一座“人类桥梁”,架在两个时代之间:一个时代将虎鲸视为害兽,并把其它鲸鱼物种视为商品,另一个时代几乎认为所有鲸鱼都很珍贵,并视其为文化的象征。
血腥换来的“价值”
高豪港作为一个岸上站,在当时是一个现代工业的奇迹。它为榨取鲸鱼身上的每一滴油和所有价值而设计。作为动物饲料的肉被移走后,剩下的脂肪、肉、骨头和内脏被放在能容纳55吨重量的巨型高压蒸煮器中,解析出大量的油。之后产生的沉淀物质会进入巨大的分离器,经过各种烹饪、干燥和蒸发的过程;富含蛋白质的液体变成干燥的鱼汤粉和鸡食,剩下的固体变成骨粉肥料。这些过程不断释放出的气味将整个村庄笼罩在恶臭之中。
驾驶一艘捕鲸船大约需要十几名船员,早期的捕鲸船包括改装的扫雷舰和比目鱼延绳钓鱼船。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艘追逐船从南极被带到了站内。观测者在望鱼台环视寻找喷水的鲸鱼,而追逐者在曾捕获或目击过鲸鱼的区域巡逻。
如果狩猎顺利,船能在海上停留达6天。在一个区域捕猎结束后,追逐船会将所有捕获的鲸鱼收集起来拖到海峡口。鲨鱼据说会对漂浮在海面上的死鲸的侧身撕扯出半月状的伤口,船员们用0.22口径的步枪来对付它们。
巨型的长须鲸大小仅次于蓝鲸,它们占据了高豪港1948年至1967年间加工的10362头鲸鱼的三分之一。同期3000多头抹香鲸被捕获。被杀戮的蓝鲸要少一点,但是由于它们的体型庞大,它们是最大的战利品。
抹香鲸也极其珍贵,但原因是:占据抹香鲸巨大的头部中很大部分,一种细长的桶状器官中被发现的鲸蜡油,是一种昂贵的商品。霍尔回忆,美国军方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会定期从高豪港的捕鲸站装运鲸蜡油,但他们只是众多青睐其耐热耐压性能的工业客户之一。抹香鲸的肠道有时会分泌出龙涎香——由无法消化的鱿鱼和乌贼的喙而形成的固体块状物质——里面含有龙涎香醇,这是一种无味的酒精,在历史上被用来赋予香水更持久的香味。霍尔说这非常稀有,他记得一头鲸鱼在站内产出了315公斤的龙涎香,在当时价值不菲。
不同等级的鲸油用来制作从人造黄油到鞋油等各种东西。然而,虽然鲸油用途很多,西部捕鲸公司受到了不稳定的商品价格和来自其他原材料的竞争的牵制。20世纪40年代末,全球植物油生产过剩迫使该公司将鲸油储存起来,直至价格上涨。1959年,鲸鱼肉几乎贬值了一半,而鲸油的价格跌至二战以来最低。
一年后,高豪港捕鲸站宣布关闭,因鲸鱼产品市场难以为继。鲸油正不断被来自植物和石油的质量高、价格低的油所取代。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对鲸鱼肉的嗜好,高豪港也许会一直停运下去。196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包装公司与日本最大的捕鲸和捕鱼企业之一太阳渔业株式会社,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随着日本资金和专业技术的涌入,高豪港重新开张,这次是为日本的食品市场供应新鲜冷冻的鲸鱼肉。
远洋工厂船队是全球捕鲸技术的又一次升级迭代,他们不再需要像高豪港这样的岸上基地。船队由一艘工厂母船和几艘捕鲸船、侦察船和补给船组成,这意味着它们完全可以在海上加工鲸鱼。这些工厂船由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带领,将鲸鱼追赶到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避开了监管和国际法的约束。
面对工厂船队高效的致命打击,小小的高豪港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当然,更没有希望的是鲸鱼。
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1964年,美国政府雇佣肯·巴尔库姆在旧金山海湾的两个站点检查鲸鱼尸体。后来他成了一位杰出的虎鲸研究者,并于1985年建立了鲸鱼研究中心。他和同代先锋的鲸鱼研究者意识到可以通过摄影,为鲸鱼拍照建档来辨认个体鲸鱼,这意味着他们能在海洋中长期研究活的鲸鱼,以及估算种群数量,绘制迁徙路径,以及更好地理解虎鲸的语言、社会性和文化。照片识别技术至今已被应用在好几种海洋哺乳动物种类身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环境及动物权利运动发展加快,对鲸鱼这种复杂生命及关系的真相揭露,清楚地表明杀死一头鲸鱼和杀死一条鱼是不同的。
到了1965年,高豪港曾主要猎捕的大型蓝鲸、长须鲸和抹香鲸开始难寻踪影,相对较小的塞鲸此时占据全年捕获量的70%。那一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该委员会于1986年禁止商业捕鲸)下达了在北太平洋捕杀座头鲸的1年禁令和捕杀蓝鲸的5年禁令。
不到2年,面对低迷的鲸肉市场和紧缩的种群数量,高豪港永久关闭了。
但是,当霍尔以博物馆的方式记忆高豪港时,日本捕鲸者正准备在太平洋进行商业捕鲸,这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他们最终停止了仅为科学目的捕鲸的守诺,并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到2019年10月初,日本捕鲸者结束了他们2019年的捕鲸季节,捕杀了256头小须鲸、布氏鲸和塞鲸,全部都在日本领海内。
霍尔说,这不是故事:包括冰岛、挪威和日本在内的国家从未停止捕鲸,不管大多数人如何看待捕杀鲸鱼的道德问题。日本坚持狩猎可以在不破坏种群健康的数量限制下进行,冰岛、挪威则受着习俗传统的影响和经济利润的驱动。
商业捕鲸的终结并不预示着高豪港的灭亡。现在,在飞行艇基地、港口企业、码头和船舶下水装置的辅助下,它演变成了一个睡房社区,为哈迪港附近的城镇服务。
高豪港的故事仍没落幕,至少有一些鲸鱼的故事还在继续。该区域座头鲸的数量正在反弹:30年前,在电报湾附近的约翰斯通海峡很少能看到一头座头鲸,但现在一次赏鲸之旅中可能会看到10头座头鲸。大长须鲸的数量似乎也在攀升,在高豪港的追逐船曾经狩猎的水域,大约400头大长须鲸会季节性的栖居在此。
抹香鲸、蓝鲸和塞鲸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它们仍是这个海岸的罕有物种。
它们曾被杀戮掠夺,现在却受到“缺席”的崇拜,它们的恢复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严歌荐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