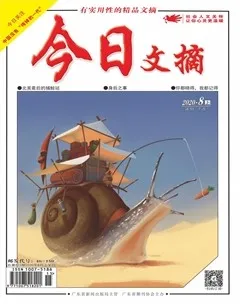日本蛰居族:隔离在世俗的门帘之外

梅卡·伊兰坐在屏风后,小心翼翼地等待对面的回答。逼仄的空间里,光线能透过帘幕洒在屏风两侧,但中间是不可逾越的距离。梅卡不懂日语,好在屏风那头的声音不难分辨:往往就是简单的“可以”或“不”。
“只有一次例外,说‘不’的人后来又接受了我。”梅卡思考良久,才对记者回忆道。这位屡获大奖的越南摄影师曾将镜头伸向许多不同的边缘群体,但当2016年她来到日本时,与潜在拍摄对象沟通的过程与以往完全不同。
梅卡的拍摄对象被称作“蛰居族”。起初,她脑海中的蛰居族概念与日本主流社会无异:好吃懒做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因为受不住学业和工作压力,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自我隔绝于世界。
梅卡逐渐发现蛰居族与世界的关系不那么简单。他们也读书看报,上网冲浪,乐于在熟络了后向梅卡打听异国故事,也会为她一展歌喉,表达对爵士乐的热爱。他们并不真的隔绝于世界,只是与这个快节奏的后现代社会有不同的节拍。
弱者或勇士
梅卡一般在下午造访蛰居族。他们白天睡觉,下午打起点精神,然后通宵打游戏或自我娱乐。但许多照片里,主角依然瘫在床上,或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曾经,蛰居族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今天的日本社会精致而高效,强调责任与争先,崇拜强者。开始蛰居前,他们也在格子间的秀场里做整齐划一的表演:早出晚归,挤地铁,打卡、开会、加班,恭恭敬敬而诚惶诚恐。
今年34岁的混血儿里奇已经蛰居多年,但梅卡依然从他身上看到了表演的痕迹:“他一直想努力表现得完美,他害怕犯错。”
巨大的压力造成人与人的疏离,这是日本留给梅卡的第一印象。“当我走进餐厅或者咖啡馆,看到里面人很多,但80%的人都是单独坐的。”梅卡回忆道。探索日本社会的孤独,成为了蛰居族项目的起点。
孤独文化是蛰居的背景,但并非主因。比如更年轻的蛰居族中条。大学毕业后,他梦想成为歌剧演员,但因为是家中长子,却被要求继承家族企业。上了一年班后,中条带着因疲劳而染上的胃病,开始蛰居。
毫不意外地,中条成了家人眼中的荒谬之人。但他也恰恰是典型的蛰居族:男性,通常还是中产以上家庭的长子,接受完备的教育,有一般人眼中良好的工作、事业或机会,但自己却有别样的想法。他们被虚拟地赋予了一切,事实上却一无所有,成为主流价值观下的难民与异类。
梅卡觉得蛰居族是勇敢的,而且他们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一部分。“在一个处处都追求完美的社会,在一个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群体责任的社会,有一些人能站出来做自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平衡。”
“无可无不可”
通常,日本的公寓即使再小,也有面向阳光的窗户。但每个下午为蛰居族拍照时,梅卡总发现自然光不够明亮,主角蜷缩在阴影里。她就地取材,打开室内所有可用的光源,却造成过分的惨白。这令人不适的光似乎投射着蛰居族的人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走入蛰居族的生活是不易的。对那些没有在第一次就拒绝拍摄请求的人,梅卡也不能很快与他们建立联系。先是跟随已经熟识蛰居族多年的志愿者拜访,但不进门,之后是进门但隔着帘幕或屏风。如是五六次,蛰居族才慢慢让梅卡进入自己的生活。
显然,他们在回避一切与人接触的事。没有搬出家庭的蛰居族甚至比独居的蛰居族更隔绝:后者偶尔还需要去便利店购物充饥,前者则由家人供应伙食,方式是放在门外,没有任何面对面接触和言语沟通。
对梅卡的接纳是个例外。“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娇小的女性,或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梅卡笑着说。但蛰居族并没有兴趣对着镜头表达什么,梅卡发现,他们只是在“无可无不可”地让摄影师完成自己的任务。
网络生活也一样。蛰居族会登录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但不参与讨论,也不回应梅卡的问候。他们关注世界变化,读书看报,但从来只是旁观。“现在,我已经无法与他们中的任何人联系。”梅卡无奈地说。在这个普遍联结的世界,蛰居族可以轻易“脱身”。
难以达成的和解
蛰居是全球性问题。韩国有超过30万青年人“赋闲”在家,美国有600多万无学无业的年轻人靠父母的资助生活,其中既有大环境所迫,也不乏主动选择者。在中国,媒体关注到“蹲族”:一群受过良好教育但不工作、少与人接触的大城市蜗居者。
日本已经形成了针对蛰居族的社会帮扶体系。整个拍摄过程,梅卡通过“新起点”的志愿者小栗联系蛰居族。“新起点”是专注蛰居族问题的公益机构,这里没有世俗社会的傲慢评价。
“事实上,志愿者们虽然在帮助蛰居族重返主流社会,但他们都是理解和认可蛰居族的。”梅卡介绍。他们多是年轻人,觉得蛰居族实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蛰居族沟通就变得轻松。通过门缝递信是每一个案例的开始,过程可能长达几个月甚至一年半。志愿者们不知道另一边的人何时会回信,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同意见面——即使是隔着门帘。
不过,一旦蛰居族愿意与志愿者进一步交流,后面的进度会快得多。最初的拜访会伴有他们喜爱的糖果和漫画书,随后是定期交流。志愿者不会诱导蛰居族走出门去找工作,只是想办法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快乐。
打开心扉后,蛰居族并不抗拒志愿者。蛰居是因为孤独、社会压力与人际关系,并不是反人类。“他们其实很缺乏朋友,所以建立信任后,他们会很依赖志愿者。”梅卡说。
也有一些迷茫的蛰居族有了回归主流社会的念头,只是胆怯。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们可以搬进“新起点”的社区公寓,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蛰居族和主流社会可以达成暂时性的和解。
在这里,志愿者会教蛰居族做饭、做咖啡、学习语言,他们共同工作,产品供应给社区里的其他蛰居族,也供应给普通市民。最重要的是,蛰居族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开始重拾与人交流的信心。
(周志达荐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