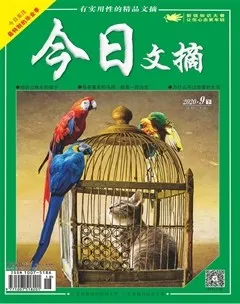在荷兰, 吃下一朵毒蘑菇的奇遇
想吃蘑菇先上课
去年秋季,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去荷兰中部密林里采摘蘑菇的活动信息,然而不仅活动价格不菲,还得提前考取荷兰政府颁发的“植物辨别证书”。有证书才能采蘑菇,这是为了避免人们采摘到毒蘑菇误食。而这张证书,不仅需要去专门的植物研究所上满160小时的课程、读完三本像字典那么厚的荷兰文的植物类书籍,还要缴纳一大笔培训费。一个采摘活动,搞得像是知识竞赛,我顿时没了兴趣。
可能也因为荷兰对于食用菌的严格把控,市场上和超市里售卖的食用蘑菇价格极其昂贵。普普通通的白色鲜蘑,在国内一斤只要几块钱人民币,在荷兰却是1公斤17.99欧元!比很多质量上乘的牛排还要贵!而像我们在国内常常食用的能炖汤的小蘑菇,在荷兰根本没得卖。想吃的话,得去中国超市里碰运气。菌种不全、价格昂贵,两大要素牢牢地扼住了我的口腹之命脉,以至于我在荷兰这几年,吃蘑菇的次数两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
去年年底,我搬了新家,来到了莱顿和海牙中间的一个小镇上居住,房前有一片花园。今年元旦过后,荷兰连绵的密雨终于暂时停歇,难得露出了一天的太阳,就在这见缝插针的工夫里,我偶然发现,自家花园里拱出了两颗大大的、水灵灵的“香菇”。说是“香菇”,也不完全是我熟悉的香菇的模样:这两朵棕色的大蘑菇,个头有拳头大小,伞盖又厚又结实,样子看上去平淡无奇,外表也没有毒蘑菇常见的奇怪颜色、绒毛、凸起等特征。我闻了闻,没有香菇的浓郁香气,但也没什么怪味。初次判断下,我已经把它认定为人畜无害系列了,至于能不能吃,我当时也没有很想吃它的欲望。
第二天,我受邀去同城的朋友家里做客,临出门前还瞅了一下家里这两朵“香菇”,发现它们比前一天长得更大了,撑得伞盖边缘都裂开了,看起来极其美味。一路上,我着重寻找路边的蘑菇,发现森林里、公园里到处都有这个品种的“香菇”,甚至到了朋友家,在她家的花园里也发现了同款“香菇”,应该都是这一批密雨过后冒出来的。朋友说,她家的花园里经常长出这种蘑菇,不知道是否有毒,是否可食用,反正她家的猫总是跟长出来的蘑菇玩,没见有什么危险,但她仍不建议我采来食用。
毒蘑菇下肚
当天回家后,我准备做个麻辣香锅当晚饭,在冰箱里搜一搜,有鸡腿肉、基围虾、豆腐干、鱼丸和几样青菜,好像少了点什么食材。我又跑去窗口瞅了一眼花园里的两朵蘑菇,心想:一般情况下,毒蘑菇都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而且外表艳丽有凸起,我这两朵蘑菇外表平淡无奇,既敦厚又朴素;而且,城市里同款蘑菇到处可见,朋友家的猫也经常揪着蘑菇玩来玩去,如果真的有毒,政府早就派人把它们全拔掉了,怎么可能到处都是?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一定只是两朵普通的大香菇!我毫不犹豫地把两朵“香菇”摘了回来,洗净过油,准备给麻辣香锅里加个菜。
麻辣香锅做完后有三斤左右,配上白米饭,我一边看剧一边津津有味地吃了一半。快吃完的时候,老公下班回家了,吃不惯中餐的他,自己煮了一碗意粉。
吃饱后,我在书桌前开始复习次日的考试,渐渐地发现自己不能够集中精神,脑中似乎有无数个人在对我说话,声音由弱渐强,“人数”由少渐多。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我的大脑就分裂出数万个分支,每个分支都有独立的思维,它们互相干扰互相讨论,让我恨不得撕掉面前的书。随后,我的身体也开始变沉变软,感觉自己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沉在一片流沙里,马上就要把我吞没。
这时,老公上楼给我送水果。据他所说,我当时正一脸痴相对着空气疯狂地摆动手臂做划船状,双眼迷离,嘴里还用中文大喊着:“好大的浪啊!妖风啊妖风!”他吓坏了,由于不知道我吃了“香菇”,但从症状可以看出,我应该是食物中毒产生了幻觉,于是抱起我就要去医院。
当时的我,第一反应竟然是:我不要去医院,这个时候只有急诊了,急诊很贵!于是乎,我开始强烈“反抗”,并试图用极其清晰的条理、强大的逻辑说服我老公:“首先,我拿的是国民医疗保险,每月125欧元,一年就是1500欧元的保险费,而只有当我每年花费超过800欧元,保险公司才会给我报销多余的部分。你现在给我叫个救护车的话,拉到医院检查一通下来估计六七百欧元,到了年底我就要交1500+600欧元,这不是给自己找钱花吗?如果我特别严重,花费超过800欧元,那也没什么治的意义了,我才不要躺在荷兰的医院里度过余生,要治病我也要回国治!其次,我的思维正常,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又不是很严重,根本没必要去医院,我明天还考试呢,我要复习!”
据说,我当时不间断地唠唠叨叨了二十多分钟,中间甚至没有一句重复的话,也正因如此,老公觉得我病得十分严重,必须去医院。从我的叙述中,他终于得知我吃了毒蘑菇。顾不上骂我傻,他赶紧背我下楼,开车送我去了医院的急救科。
解药可乐
我躺在病床上,医生检查了我的瞳孔、听力、血压,并给我验了血液和尿液,期间还问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荷兰的首都是什么,我的名字怎么拼,19×4等于多少等等。当时的我,虽然完全不能集中注意力去思考,但分析能力达到了顶峰。比如,我会分析,19×4,需要先算20×4,再减去一个4,至于20×4是多少,我偏偏想不出来。再比如,我开口问医生,你是从家里过来的,还是原本就在这儿的?如果医生回答他从家里过来,那么就说明我的病情比较严重,留守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已经治不了了。
医生给我做检查时,我还不忘非常客气地用荷兰语安慰她:“没事儿,不要紧,慢慢来,真是麻烦您了。”事后,老公告诉我,他当时看我在那里不停嘟囔加上各种逻辑分析,几乎要笑死了。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医生说我并没有什么大碍,不幸中的万幸,我吃的只是致幻类蘑菇,毒性不算太大,一般4个小时后,身体就可以代谢掉毒性恢复正常。所以我不需要洗胃,也不用吃特别的药,如果想稀释毒性可以多喝点可乐,三天后回医院抽血复查肝功能。
就这样,一通检查下来花了几百欧,我又被带回了家。那时距我吃下毒蘑菇大概过了2个半小时左右,是蘑菇毒性最高并开始逐渐回落阶段。到家后,眼前的场景又一次变了:地板、墙壁、桌子椅子等等全都像有了生命似的在进行重复活动,我试图回到书桌前继续复习,然而纸上的每个字都由二维变成了三维,挣扎着要从书上跳下来。我越看越觉得有趣,傻乎乎地笑个不停。
本来,老公准备听从医嘱,静静地等待我的症状消失,哪想到我“疯”得越来越厉害,他赶忙出门去买可乐帮我稀释毒性。临走前,他千叮咛万嘱咐,我不可以下床,不可以乱动,最多10分钟,他就带着“解药”回家。
不知过了多久,老公带着两大罐可乐回来了,我也应要求喝了好几杯,逐渐地,毒性慢慢退了,等我再次睁眼的时候,时间不过是当天的深夜,而我已经完全没有“看到小人儿跳舞”的那种幻觉了。
三天后,我来到医院验血验尿,次日拿到结果,一切正常,警报完全解除。医生说,荷兰这个地方由于气候潮湿,蘑菇的品种很多,有毒无毒的都有,外行人很难凭肉眼分辨,也因此政府一直严格把控蘑菇的采摘,荷兰本地的小孩从小就会被教育,不可以随意采摘食用路边或森林里的蘑菇。可即使这样,荷兰每年还是会有160~180宗因误食毒蘑菇而送医的报告。
其实蘑菇的分辨不能仅靠老一辈的“经验”,比如被虫咬过的无毒,外形艳丽的有毒,这是不科学的。在荷兰,有一种剧毒蘑菇“鹅膏”,外表朴素,还经常会被虫子啃上两口,然而它却含有剧毒,一旦误食,可能在几分钟内毙命。
在荷兰,对于蘑菇的“应用”很全面,它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有一些也会被用作药品。荷兰地处北欧,冬季黑夜长,国民得抑郁症的概率非常高。这些患者除了遵循医生的嘱咐积极奋战抗抑郁之外,还可能收到医生派发的用迷幻蘑菇做的抗抑郁药。据多年临床观察,这种迷幻蘑菇中的裸盖菇素物质,可以有效缓解轻度和中度抑郁症患者的症状。怪不得,我在当时中毒的时候一直傻笑,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也比平常更开心和自信。看来这次经历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至少今后有谁不开心,我就以自己的经历跟他开个玩笑:“兄台,干了这锅毒蘑菇,保你笑口常开!”
(静茹荐自《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