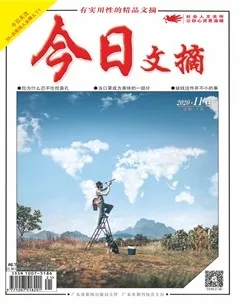冰场上的“劳伦斯先生”, 人生不能过早缴械投降

现在,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每次参加比赛都要戴假牙。这几年肖雨红看着他在冰场上,腿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内心有些胆战心惊。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去年的比赛,他忘记了动作,下场的时候很沮丧,妹妹和她的孩子都来了,给他扔了小猫小狗的布偶。他有些难过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国贸冰场最受欢迎的选手
姬凯峰的速度有些缓慢,滑行时双手会配合着一些花手和云手的舞蹈动作,称不上优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协调。偶尔小跳,他的身体会晃荡一下才能站稳。但他看上去沉醉其中,头上那副旧旧的白色耳机帮他遮蔽了周围所有的声音,在一个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乐和节奏中,那个枯瘦的身影反复练习几个单一的动作,如果成功完成,他会露出弧度很大的笑容。
从专业角度来看,他的花样滑冰没有太多欣赏性,但如果你了解这些难度动作是由一位75岁的老人做出来的,评价可能会全然不同。姬凯峰是国贸溜冰场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溜冰场已经开了21年,他在这里也滑了整整21年。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冰场上午十点开门,他拎着一个蓝色挎包准时出现,包里是他穿了十来年的黑色冰鞋和一条擦拭冰刃的毛巾。十二点多回家吃个饭、睡两个小时午觉,下午继续来“上班”,滑到四五点钟“下班”回家。
国贸溜冰场在国贸商城的地下二层,顶上是一个明亮而巨大的圆弧状玻璃罩。这里汇聚了北京最顶级的写字楼和40多万繁忙的上班族。一层通往地铁,常有下了班的人立在楼上,静静地看一会儿姬凯峰和其他的溜冰者来回穿梭,然后再坐地铁回家。
前段时间,有人拍了一段姬凯峰滑冰的视频发到了微博上,背景音乐是冰场当时正在放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坂本龙一为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作的主题曲,因此拍摄者给这段视频起名叫“国贸的劳伦斯先生”。画面上姬凯峰舒缓的动作和着那首略带悲伤的曲子,像是一个电影里的慢镜头。这条只有7秒的视频获得了近万次的点赞。有人在下面留言:“我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国贸滑冰了,现在21岁了,几乎每次回冰场都能碰到他。”
肖雨红是国贸溜冰场的主教练,曾经是专业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退役之后在这里工作了20年,在她印象中,姬凯峰是一位体面的老先生,衣着总是朴素而整洁,有时会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白色耳机滑冰。肖雨红见多了来这里滑冰的客人,有些熟客会做一些“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说但实际上不太合适”的事情:为了多蹭点时间,有人会先换好冰鞋,再去刷计时卡。还有人因为超时几分钟需要补费而跟工作人员吵架。“但姫大爷他从来不钻我们冰场的空子,他是一板一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那种,不会说有一点的那种投机取巧或者倚老卖老。”
他在冰场唯一的特权是,能踩着冰鞋穿过员工通道跑到肖雨红的办公室,站在办公桌前跟她聊半天花样滑冰的动作,只要手里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肖雨红都会陪他聊聊天。
姬凯峰最近在学的一个动作是后内刃转三,需要使用冰刀内刃倒滑出阿拉伯数字“3”的形状。他用刃不太准确,重心也找得不对,练了三个月,依然没什么进展,肖雨红能感觉到他的着急,经过冰场的时候看他立在那儿琢磨,尝试,却“还是不能完成”。他经常穿着冰鞋噔噔噔进来,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这个动作到底要怎么才能完成,肖雨红觉得,那种执着和痴迷有时甚至近乎神经质,仿佛那是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他反复跟她说:“我这个动作要是能成,可就太幸福了。”
姬凯峰年轻时是个摄影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他喜欢优美的动作,发现别人在做好看动作时,总是凑上去请教人家,有时候陌生人嫌他唠叨,不怎么理他,他更愿意去找肖雨红。有时某一个动作做成功了,他像一个老顽童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拉肖雨红上冰来看,“你看我滑一段。”他喜欢在人多时滑冰,只要逮到机会,就给其他冰友展示“滑一段”。
和我在冰场交流的时候,他提到自己现在一共掌握了七个舞蹈动作,我问哪七个,他索性站起来在平地上把它们都展示了一遍,他身形枯瘦,衬得宽大的裤管空空荡荡。旁边人来人往,有人用奇怪的目光扫他,但他全然不顾。
“他那个状态都让你感觉到很开心,他喜欢别人欣赏他,喜欢别人看他滑冰。”肖雨红说。
忘记生活的重量
姬凯峰痴迷在冰上的感觉,前进、后退或旋转,让他感到自由,风从耳边吹过,他张开双臂,有飞翔的感觉。戴上耳机就是自己的世界,音乐是他喜欢的苏联歌曲,最近常听的是《水兵圆舞曲》,跟着音乐滑起来之后,“什么事儿就都不想了。”
青年作家远子曾在国贸的一家书店工作,溜冰场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十七个远方》里描述过这种感觉,“也许是那些溜冰的人轻盈的姿态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沉重,我们就静静坐在溜冰场外围的凳子上,不说一句话,我们看着那些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在冰面上滑过来滑过去,就好像看着鱼缸里的鱼儿游来游去。”
对于姬凯峰来说,在漫长的时间里,溜冰也是这样的存在,可以让他忘记生活的重量。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摄影师,先后在故宫研究院、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外经贸部工作过,他拍过古老的文物,1990年拍过首枚长征二号E火箭的发射过程,再后来,拍的最多的是大型国企管理者的签字仪式。但那不是一份他喜欢的工作,总体来说,“没啥意思”,每天忙活一天,总是很疲惫,“但是为了吃饭,为了谋生,为了生活,我必须得搞这一项工作。”
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北京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室内溜冰场,位于首都体育馆。那时候姬凯峰三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儿子刚出生,他在体制内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无论白天工作有多累,晚上都会去首体滑两个小时的冰,那时候他还年轻,身体机能好,玩的是速滑,速度一起来,“就跟小鸟飞似的,特别舒服,心情特别愉快,happy and lucky(快乐和幸运)。”
白天上班,晚上滑冰,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和妻子收入都不错,儿子也一天天长大,和姬凯峰一样,那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但不幸遗传了母亲的心脏病。儿子15岁的时候,姬凯峰和妻子上班,儿子一人留在家里,晚上夫妻两人下班回家,看见孩子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夭折。
姬凯峰做了十年的梦,梦里是相同的内容,儿子住在别人家里,姬凯峰想看他,但不知道怎么的,就是看不见他。
姬凯峰没有哭过,他心中难受,但想着自己既然选择了继续活,就得好好活着。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将近50岁,无法再要第二个孩子,考虑过收养,后来阴差阳错,还是算了。儿子葬在了老家河北定州,他们在家里从此再也没有提起孩子的话题。
最难受的时候他去冰场去得更凶,滑得更猛也更快,“一想起这事我就难受,难受我就滑冰,我一滑冰就忘了这些事,不高兴的事。”
开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总是在冰上。去年老伴也去世了,他说:“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没人了。”他从北京南边搬到了距离冰场只有10分钟的小区。他以前一天来一次,现在变成了一天来两次。李岩是国贸溜冰场的教练,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也经常教姬凯峰动作,在他看来,姬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他其实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除了回家,在冰场待的时间是最多的。”
姬凯峰没有手机,我问要怎么联系他时,他说:“你给冰场打电话就行,我就在这儿。”如果不在这儿,冰场会给他家里的座机打电话。事实上,家里那台座机响起的次数很少,每周只有一次,是他妹妹打电话来问候他。
疫情期间,冰场关闭了三个月,他觉得心里空得慌,只能在小区里跳绳,或者拿又大又厚的速写本画画。后来他还花大价钱买了双排轮,发现完全不一样,只好放弃了。今年五月,妹妹在国贸吃完饭,去地下车库取车路上,看到冰场开了,打电话通知他。挂了电话,他捞上冰鞋就来了。
疫情期间都需要扫健康码,不使用手机的姬凯峰没法进来,肖雨红记得,为了让他进来,冰场专门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半天,如何既不违反规定又能让姬凯峰方便。
考虑到他没有离京的可能,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些额外的照顾,每次测完体温,在小纸条上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可以进入。“你会觉得他是我们冰场的一部分,好像跟冰场共存了似的。”肖雨红说。
他又回到了熟悉而舒服的环境,这里的冰用热水浇过,脚感更柔软,厕所里有热水,他畏寒,用不了冷水。更重要的是,所ln0Ot+ZjGEd+g4rjnb/eiQ==有熟悉的人也在这儿。
“我有可能死在冰上了”
到今年,国贸溜冰场已经21岁了,一波又一波学滑冰的小朋友长大又离开,冰场的工作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周围的店铺名字换了好几轮,但在肖雨红记忆里,冰场的模样一直不曾变过,冰面宽阔,围着冰面的栏杆还是20年前刚开业的样子。
姬凯峰也好像一直不曾变过,他总是按时出现在雪白的冰面上,他和冰场一起,成为了这个快速变化的财富地标中一个缓慢而恒定的存在。
姬凯峰近乎顽固地对抗着时间对肉体的侵蚀,多吃豆腐、鸡蛋、蔬菜和水果,绝不吃油炸和烧烤。他看不上那些过早缴械投降的人,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拉着小推车,装个两斤菜,他不想与其为伍,也许是常年运动的关系,他依然有一把好力气,去超市买东西,左手十斤米,右手十斤面,“跟玩似的我就拎回家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冰场一面墙上贴着他2006年参加比赛的照片,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西装背心,黑色的裤子,打着紫色的领结,两手张开,笑着感谢观众,有意气风发之态。
他觉得自己也许滑不了几年了,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身病的人没准比活蹦乱跳的人活得还长,现在看上去一切都好,“没准来个暴病,一下就完了。”
有时候姬凯峰家中有事,一段时间不来,李岩和其他教练会有些不习惯,但又不敢打电话去问,“人到这个岁数了,生老病死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们还是不想往那个方向去想。”过了几天,姬凯峰又出现了,李岩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心里会暗暗松一口气。
姬凯峰不存钱,每个月的养老金和退休工资一到账就从银行提出来。每个月各种花销有一万块,他把妻子留下的存款都交给了妹妹,妹妹比他年轻,刚刚60出头,为了相互照应,和他的住址只隔着一条街,“我以后有什么事,让她料理我一下就完了,我不费那脑子。”
他想把脑力和体力留给滑冰。直到现在,他还想做一些难度动作。李岩记得,姬凯峰一直想要完成一周跳,但被他劝住了。还有后内刃转3,他自己知道不理智,但还是想要尝试,“我都75了,我还追求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追求太厉害了,有点过头了。”他看着我,缓慢地说:“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但那大概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让他选择,他理想中的结局是能回到老家定州市西城村,那是他六岁以前待过的地方,死后可以和儿子葬在一起。
“我这辈子没什么正经的,也没啥能耐,给国家也没做什么贡献,我也有点狼狈,遇到些难事儿,你看我这辈子就是玩了一辈子,我还挺高兴的,什么也难不住我。”他把happy和lucky两个单词翻译成了俄文念给我听,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上了“非常”这个副词。
(陈珊珊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