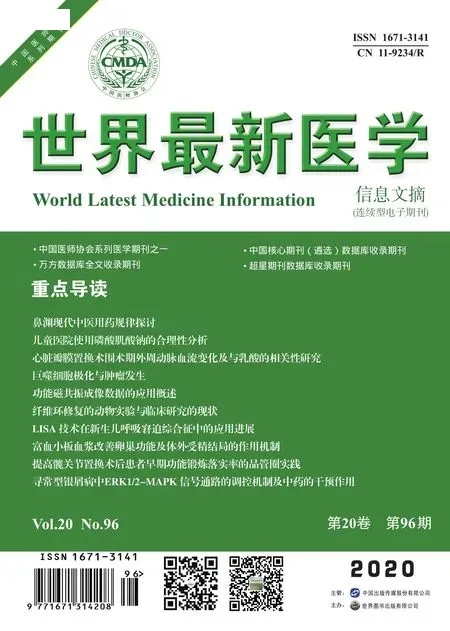环境因素对儿童哮喘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
宋翠柳,张大平
(长江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湖北 荆州)
0 引言
支气管哮喘(asthma 以下简称哮喘)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炎症性疾病,具有易复发,可逆性等特点,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儿童哮喘的患病率显著上升,目前全世界儿童哮喘的患病率高达14%,已成为儿童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1]。如此高的患病率并不能完全由遗传因素解释,虽然阳性家族史是一个高危风险因素,但其在儿童哮喘患病率中的预测值只有11-37%,显然儿童哮喘患病率的上升趋势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2]。本文就儿童哮喘发展中最有影响的环境因素: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微生物群失调、分娩方式、抗生素使用、肥胖、二手烟暴露、过敏原致敏、母乳喂养和维生素D水平等进行一一阐述。
1 急性病毒性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病毒感染在从毛细支气管炎到哮喘的所有喘息性疾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使用PCR的病毒检出率在儿童毛细支气管炎中达到100%,在儿童哮喘中达到85-95%[3]。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是引起婴幼儿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病毒,其住院检出率为50-80%[4]。人鼻病毒(HRV)是引起婴幼儿呼吸道感染第二常见的病毒,但大约在12个月后开始主导病毒检测[5],76%的哮喘儿童症状加重与HRV有关[6]。RSV主要引起婴儿下呼吸道感染(LRTI),HRV虽然更多的是导致上呼吸道感染(URTI)但也能导致LRTI[7],RSV和HRV引起的LRTI与哮喘的发展密切相关[8]。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关联是遗传倾向的结果,还是直接归因于病毒。急性病毒感染可引起多种细胞因子调节宿主反应、气道炎症和气道重塑,以及增加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9-10]。此外,病毒感染可增加上皮细胞产生IL-25和IL-33,从而促进Th2型炎症,或者,病毒感染可以简单地作为抗病毒反应受损的早期标志,减少I型和III型干扰素的产生和/或异常宿主反应,诱导IgEr的表达[11-12]。有研究发现,给予RSV免疫球蛋白干预的哮喘儿童,其哮喘发作率明显降低,这提示呼吸道病毒免疫球蛋白在哮喘发展中具有潜在的因果作用[13],然而,高昂的成本和管理负担限制了它对哮喘儿童的使用。虽然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RSV和HRV与哮喘发展是一个因果关系,但预防呼吸道病毒感染是否能显著降低患哮喘的风险是一个最好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解决的问题。
2 微生物群失调
人体是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的家园,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等,这些微生物栖息在我们的身体各处,在我们机体调节稳态、免疫和代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作用可能在子宫内就已经开始了[14]。在对哮喘发病机制的研究中,胃肠道和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失调已愈发引起广大学者们的关注。
胃肠道有数万亿的微生物定植,与宿主形成共生关系,这些微生物在结肠的分布最为密集,在为人体提供必需的营养物质、将膳食纤维代谢成短链脂肪酸(SCFAs)、确保免疫系统的发育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儿童哮喘的研究中,来自不同出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胃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改变与哮喘的发展之间存在重大关系[15]。在一项涉及近700名儿童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1岁时胃肠道微生物群的结构与5岁时哮喘的发展有关[16]。肠道微生物介导哮喘发病的机制是什么?由特定肠道细菌发酵产生的SCFAs受到了广大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大量研究显示SCFAs水平的改变与哮喘儿童肠道失调有关[17]。在小鼠模型中的研究也显示肠道微生物失调可以通过产生特定的SCFAs,形成幼稚免疫细胞反应参与哮喘发病机制[18]。其他与肠道微生物代谢有关的介质,如组胺和色氨酸代谢物,也参与了哮喘的机制,但具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19-20]。
在儿科研究中,呼吸道微生物群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鼻咽(NP)生态位上。鼻咽不仅更容易取样,而且也是吸入物质与呼吸道上皮之间最近的接触点。虽然NP微生物群的组成总体上与下呼吸道的组成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21-22]。因此,对NP微生物群的研究也能为与哮喘风险相关的生物途径提供信息[23-24]。大量研究显示NP微生物群的组成与哮喘患病风险、呼吸道感染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重要关系[21-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一致认为NP微生物群的组成在生命早期是动态变化的,随后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生物群中,在临床发病前的几周内,NP微生物的组成发生了显着性的转变[27]。
3 分娩方式
20世纪50年代我国剖宫产率仅为1%-2%,发展到1988年上升到了22%,到2016年则高达47.76%[28]。而根据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通过剖宫产出生的婴儿哮喘发作率增加了大约20%,其患糖尿病和肥胖等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也较高[29]。针对剖宫产对哮喘患病率的影响目前有两种理论学说,一种理论认为剖宫产对哮喘患病率的影响是由于微生物群的改变对免疫系统发育的影响所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阴道微生物转移可以部分恢复剖宫产婴儿的微生物群,从而降低哮喘患病率也支持了这一理论[30];另一种理论是:在新生儿分娩过程中约有1/3-1/2的肺液经产道挤压由口鼻排出,剖宫产婴儿相对于顺产婴儿,在分娩过程中胸廓没有受到充分的挤压,从而导致肺液的滞留,改变了早期空气-肺交换[31]。
4 抗生素使用
不仅剖宫产率,近年来抗生素的使用率也显著上升。据报告,40%的妇女在怀孕期间使用过抗生素,66%的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使用过抗生素[32]。在子宫内暴露于抗生素的婴儿中,哮喘的相对风险增加了20%,在生后第一年内暴露于抗生素的婴儿中,哮喘的相对风险增加了27%[33]。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机制有关:(1)由于在怀孕期间和儿童早期使用了抗生素,减少了婴幼儿暴露于微生物的机会,这可能会改变免疫系统的启动,增加哮喘、湿疹等过敏性疾病发展的风险[34]。(2)通过口服和皮肤途径直接接触抗生素可能会改变皮肤或肠道的微生物群,导致这些器官的免疫系统受体处于超敏反应状态,从而增加哮喘发病的风险[35]。
5 肥胖
儿童肥胖是现代公共卫生危机。在儿童中,肥胖是指体重指数(BMI)大于同年龄和同性别的95百分位数。在过去40年中,5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从4.8%增加到9.4%[36]。引起肥胖的因素很多,包括运动量的不足、饮食习惯的改变、环境因素等。儿童肥胖与哮喘、睡眠呼吸暂停、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37]。但肥胖引起哮喘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脂肪组织的促炎作用有关[38]。肥胖的其他驱动因素,包括身体不活动和超重状态,对哮喘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影响[39]。
6 二手烟暴露
长期以来,产前和产后接触烟草烟雾一直被认为是哮喘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长期暴露于烟草烟雾环境中,会损伤呼吸道粘膜上皮细胞,增强气道高反应性,降低肺功能,影响气道重塑,从而促进哮喘的发展。研究显示孕妇在妊娠期间吸烟,其胎儿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85%,生后直接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婴儿患哮喘的风险增加了32%[40]。因此控制吸烟人数,减少烟草烟雾暴露的风险对控制哮喘的发生尤为重要。
7 过敏原致敏
在过去的20年里,过敏反应的增加与儿童哮喘发病率的增加相平行[41]。哮喘儿童的过敏原包括吸入性过敏原和食入性过敏原,其中吸入性过敏原占68.8%,食入性过敏原占31.2%。在吸入性过敏原中尘螨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此外产黄青酶、多主枝孢、烟曲霉、白假丝酵母等真菌及动物毛发均在吸入性过敏原中占一定的比例[42],因此保持室内清洁及通风显得尤为重要;在食入性过敏原中鸡蛋白、牛奶、鱼肉、海鲜、花生、大豆等占主要因素。考虑到婴幼儿与年长儿相比其胃肠道功能尚未发育完善,更容易发生食物不耐受,因此也更容易因食物过敏而诱发哮喘急性发作。对于哮喘高风险儿童,必要时可行过敏原检测,以更好的规避过敏反应的发生。
8 母乳喂养和维生素D水平
母乳喂养和充足的维生素D水平是可能对儿童哮喘发展起保护作用的两个因素。这些措施成本低,易于实现。母乳喂养率随持续时间的不同而不同,81.9%的婴儿在出生时开始哺乳,60.6%长达6个月,34.1%长达1年[43]。在哮喘中母乳通过免疫球蛋白的生物活性提供早期被动免疫,然而具体保护机制尚不清楚[44]。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导方针,强烈建议胎儿生后纯母乳喂养至少6个月,含母乳的混合喂养到12个月。
调查显示在12岁至44岁的孕妇中,约28%的孕妇缺乏维生素D[45]。多项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子宫内25-羟基维生素D对哮喘的发展具有保护作用[46]。有临床实验证明,孕妇补充4400IU维生素D/天,哮喘的发生率降低20%[47]。此外,在Hibbs等进行的一项产后胎儿维生素D补充的临床试验中,发现持续补充12月的婴儿,哮喘患病率较补充6月的婴儿降低了34%[48]。这说明无论产前或是产后补充维生素D都可以降低儿童哮喘的风险,然而,开始补充时间、补充的具体剂量、补充疗程目前尚未确定。
9 小结
相当大比例的儿童哮喘可能归因于可改变的环境危险因素,包括急性病毒呼吸道感染、微生物群失调、分娩方式、抗生素使用、肥胖,二手烟暴露和过敏原致敏等。母乳喂养和充足的维生素D浓度可能对哮喘发作有保护作用。在缺乏有效的预防策略前,减少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对儿童哮喘的防治有重大意义。
利益冲突声明和作者贡献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或接受过制药公司的经费支持;第一作者(宋翠柳):综述撰写;第二作者(张大平):选题指导、论文修改、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