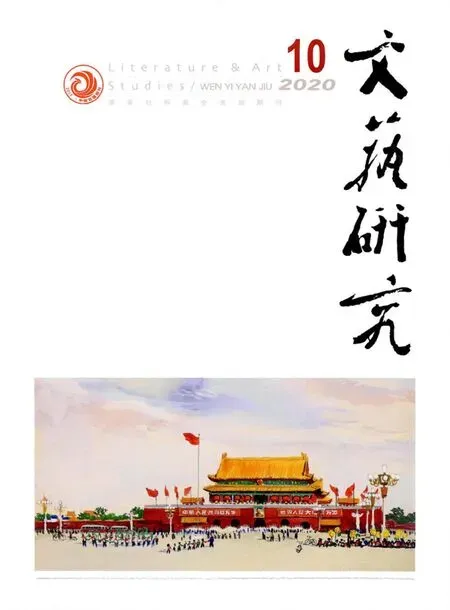戏曲导演制的引进与得失平议
傅 谨
1949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成立,从此“戏改”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戏改”中的改制重点是戏班所有制的改造,同时还内在地包括在全国戏曲领域推行导演制。导演制的全面实施,在本体层面上改变了戏曲的剧目体系和演剧体制,更改变了戏曲的创作模式和演出形态。这一措施对戏曲艺术的影响既深且巨,值得深入研究。
一、“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
一般认为,戏剧史上最早出现“职业化导演”,始于19世纪末德国的梅宁根剧团,此后德、法等国家才有剧院在戏剧创作中设置导演。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成就为导演在戏剧中的作用做了最好的证明,戏剧创作需要专门化的导演,这一观念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①。尽管20世纪初叶就有国人介绍西方的戏剧导演制度②,洪深、陈大悲等人在话剧领域亦有导演制实践,民国时期部分戏曲名演员也陆续尝试引进导演(编导),但是在戏曲剧团内普遍建立导演制的努力,“戏改”才是其真正的开端。
戏剧导演制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普及与“戏改”主持者所具有的“新剧”背景有直接关系。借鉴“新剧”的戏剧样式,改造被称为“旧剧”的中国传统戏曲,是“戏改”时期非常普遍的认知。“戏改”的最初阶段,各地纷纷举办艺人讲习班,内容不止于政治思想教育,传播各种具有“进步”色彩的戏剧观念亦属学习内容,其中就包括导演制。北京市文委组织的第一期旧剧演员学习班,请洪深主讲“导演的作用”,上海、天津等地的艺人学习班亦有相似内容。《人民戏剧》创刊号刊登了马少波的文章,他写道:“一个戏剧演出的成功,固然剧作、演员及所有的舞台工作者,都有着重要的或者说决定的作用;但只是有了好剧本,好演员,而没有好的导演工作,这成功是可能的么……导演在戏剧演出中是决不可少的业务上的组织领导者,有了科学的导演工作,才能更完整的把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统一起来,才能更充分的把平面的文学变成立体的艺术形象。”因此,必须在剧团普遍设立导演部门,“为了有组织的进行导演工作,最好组成导演委员会,或导演组,或导演团,或组成编导委员会,配备导演人才”,而所有演职人员“必须接受导演人的指导”③。
“戏改”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戏曲导演制的努力,最具代表性的是《新戏曲》杂志主办的“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这次会议于1950年8月25日下午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召开,时任戏曲改进局局长田汉担任主席,两位副局长马彦祥、杨绍萱都参加了会议,邀请的参会代表有王颉竹、尹清泉、白云生、李少春、李紫贵、阿甲、林柏年、周贻白、洪深、席宝昆、翁偶虹、唐槐秋、舒强、景孤血、韩世昌、郑亦秋等。他们中有韩世昌、白云生这样的北京著名昆曲演员,有景孤血、翁偶虹等与戏曲界关系很深的文人,而洪深、郑亦秋、周贻白、唐槐秋、舒强则都是中国话剧界有经验的导演,至于李紫贵和阿甲,也已经在京剧界享有导演之名,京剧名家李少春刚刚导演了京剧新剧目《云罗山》,评剧名家席宝昆在新中国评剧团里也有导演《九尾狐》的亲身实践。王瑶卿、焦菊隐、欧阳予倩受邀但因故未参加会议。从这个阵容看,《新戏曲》主编马彦祥在参会人员遴选上自有用意,考虑十分周全。参会者中,除唐槐秋委婉地拒绝发言,其他人都就建立导演制发表了各自看法,从中我们可以大概知悉“戏改”时期推行导演制的动机和阻力。
田汉和马彦祥对这次会议有高度期待,对在戏曲领域建立导演制意义的预判非同寻常。田汉充分肯定了《新戏曲》杂志在创刊之际就“首先提出戏曲导演问题”,开宗明义地指出戏曲导演制度的建立是“戏改工作中极重要的新的问题”,甚至认为“导演的有无已经为戏剧成功与否的分歧点”④。马彦祥亦阐述了主办这次座谈会的动机:“今天《新戏曲》月刊请各位同志来举行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因为几个月来,我们收到的各地戏改工作的汇报材料一致认为要提高目前新戏曲演出的水平,必须迅速建立健全的导演制度。”⑤马彦祥所说的“各地戏改工作的汇报材料”,可以从《新戏曲》创刊号里刊登的部分文章中看到。在这些对“戏改”初期工作的总结中,芜湖“戏改”部门特地将群力剧团的“树立了新的导演制度,对旧剧的删改,和新剧的编排以及如何体会剧情掌握性格等都是大家商量集中导演的”作为重要的经验⑥;太原市的“戏改”总结对剧团“建立了认真的排演制度——过去的剧团排戏都只是‘说说走走’,一切‘台上见’,尤其是名主角,现在不同了”,“有的队已经开始拟订导演制度”⑦给予了充分肯定;苏南地区的“戏改”报告明确提出,亟需改革的制度包括“导演制——一般的既没有健全的导演制度,又无科学的导演方法,形成导演就是抱本子,说说戏,尤其是在排演新戏时,更是这样”⑧。这些材料都说明各地“戏改”主管部门对导演制是普遍认同的。田汉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更把“新的演剧制度的建立”作为“戏改”一年来各地开展艺人教育改造的初步收获之一⑨。这里所说的“演剧制度”,显然就是指或至少包含导演制。
我们细读这份座谈会记录时会发现,马彦祥所说的“必须迅速建立健全的导演制度”,虽是“戏改”主管部门的预设立场,但推动者却缺少充分的理论思考和准备。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建立导演制对戏曲改进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却又有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什么是导演制,为什么戏剧演出需要导演,导演在戏剧中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及如何起作用,这些基础性问题都成为讨论的话题;其次,戏曲史上是否有导演也成为焦点问题,换言之,假如中国戏曲史上早有导演,所谓“建立”导演制就是一个假命题;再次,如果真要在全国戏曲剧团内建立导演制,职业导演从何而来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对戏曲领域导演制的作用与现状有充分认识,建立导演制才有坚实的理论依据。
田汉从戏剧整体性出发阐述实施导演制的意义,认为“旧中国戏曲看人不看戏,于今要大家看戏不看人,人的条件当然始终关系着戏的成败。但应当是戏中的人,即与戏紧密结合的人而不是离开戏的人,也不是单看某一突出的个人而当是演员整体,不是单看演员的演技而是整个舞台工作的浑然一致。凡此是改革戏曲的重要纲目,也是它成功的保障,要做到这样便须建立有效的导演制度”⑩。马彦祥指出,建立新的导演制是为了纠正此前角儿们过于强调突出自我、“根据自己的条件任意创造”⑪的现象。李紫贵也认为:“建立导演制度,先要有一个导演权威能限制演员向主题之外发展。以往戏剧界都是发挥自己的天才,这样下去,绝不会健全的。导演就应该和他商量,不使他的个人技术超出主题范围。”⑫翁偶虹则指出:“从先排戏也是分工的,但是主角任导演,后台管事再说零碎。还有的打鼓佬也当导演,请他给安锣鼓,由他决定剧本命运。这种分工式的导演,也是各找各的俏头,结果是主角至上,把别人的戏给削弱了,只表现他自己而已。”⑬尹清泉更直截了当地说:“有的演员不认识导演的重要,只固执他的成见,导演要他唱两句,他非要唱四句不可,所以必须建立导演制度。”⑭
这些言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理念,即希望通过建立导演制,改变晚清、民国以来商业剧场时代戏曲界形成的“角儿制”,矫正其弊端。对“角儿制”批评的理论依据是戏剧的整体性原则,其认为戏剧应该具有内在的完整性,各部分之间应该紧密配合形成有机的整体。此外,虽然有发言者提出戏曲应该通过导演制重建剧本与演出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座谈会对剧本的重视还不太明显。席宝昆提出:“我希望导演制度建立后,第一要通过剧本,第二要通过舞台及演员,要在这双方中间起桥梁作用,把编剧与演员及舞台都配合在一起,才可成功。”⑮杨绍萱认为,导演应该是“剧作家和演员之间的结合者”⑯。这是座谈会提及演出剧本仅有的两例。其实,在此后推行导演制的过程中,传统戏曲演出中的剧本问题越来越成为“戏改”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建立导演制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与界定戏曲中古已有之的“排戏”。杨绍萱率先提出,建立导演制首先要面对的是戏曲中原来有没有导演的问题。他认为戏曲史上已有三类与导演相关的现象:一是如魏良辅将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搬上舞台,二是师傅教徒弟式的说戏,三是剧作家兼导演⑰。因此,戏曲史上其实是有类似导演这样的创作者的,只是没有形成“制度”。杨绍萱有关魏良辅排《浣纱记》的说法于史无征,但他对戏曲史上存在的类似导演的现象之追索并非毫无意义。如果循他的思路,明末清初李渔、阮大铖等文人为其家班排戏的行为,实与一般意义上的导演差别不大。李少春也指出,戏曲并不是没有导演,只不过没有这个名词和这种制度⑱;翁偶虹更做了细致分析,他认为一般所说的导演分为两种,一种是掌握全剧排演的导演,还有一种则是负责安排场上表演者的技术手段的导演。就传统戏曲而言,后一种其实并不少见⑲。如何理解“排戏”这种戏曲行业中很常见的现象,与建立导演制的呼声是否具有合理性关系颇大。如果说只有剧团内常设职业化导演才是所谓“导演制”,那么只须解决导演与剧作家、演员的分工,导演制即可“建立”了。假如问题如此简单,建立导演制何需如此大动干戈?因此,马彦祥试图厘清“排戏先生”和导演之间的重要区别。他认为“排戏”还不是导演,“导演不仅要负责解决一个剧本从文字到舞台形象的许多技巧问题,更须要对如何以适当的技术传达内容,整个剧本的思想内容负责”⑳。
问题还有另一层。结合当时戏曲界的实际情况看,导演制的需求不只在于理论,很大程度上它还是由“戏改”时期各戏班剧团大量排演新剧目的现象催生出来的。换言之,新戏的新题材、新人物和新行为模式,都是传统戏班和艺人不熟悉的。新剧目喜欢安排全新的舞台美术设计,更让一直习惯在一桌二椅的简约情境中表演的演员无所适从,因此,演新戏就要熟悉此类新戏剧样式,包括熟悉新戏里越来越普遍运用的新型舞台美术设置。这就是北京市文化局干部王颉竹指出的问题。他说戏班“普遍有排新戏的要求,这种要求比上半年高的多,但是首先感到的困难就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们解决导演问题”㉑。传统戏班和艺人无法应对新的戏剧内容和舞台样式的突然涌入,这是戏曲界内部对建立导演制的需求的具体体现。可见,导演制推行的压力传导其实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然而,在座谈会的相关讨论中,这一点恰恰很少有人提及。
建立导演制看来已经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但是要真正使之成为现实仍非易事。短时期内要在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戏曲剧团中建立这种新的演剧制度,首先面对的困难是导演的来源。接下来更困难的是,即使这一制度借政府之力得到确立,对于从事这一职业的每个具体的导演者来说,如何才能真正获得在戏曲创作与演出过程中的权威性。如果仅仅把戏班里的资深艺人即“排戏先生”改名为“导演”,又会有违初衷。田汉指出,传统戏曲所依靠的“排戏先生”这一导演制的雏形,其最明显的缺点是“导演主要还是由演员兼任”㉒,可见导演职业化一开始就要避免把导演当作“排戏先生”。然而更重要的是,要让戏曲从业人员能够认可导演在剧团中比包括“角儿”在内的所有演员都更具支配性的艺术地位,在创作、演出中听从导演的安排与调度。如马彦祥所说:“首先需要演员们对导演有新的认识,认识导演工作不仅仅是过去排戏先生说场子的工作,这样才能建立导演的威信和职权,也才能发挥导演真正的作用。”㉓
按马彦祥所说,新的导演制度所要求于导演者的,应该远远超过传统戏曲“说场子”的排戏,但实际情况却是,多数新文艺工作者虽有许多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高超见解,其缺少的恰恰是艺人最迫切需要的“说场子”的能力,兼之对导演艺术原本就一知半解,“建立导演的威信”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座谈会上发言者举例称,焦菊隐、赵树理等在戏曲剧团担任导演时遭遇尴尬,而两位均非泛泛之辈,前者多年担任在京剧界赫赫有名的中华戏校的校长,后者也以创作和熟悉民间文学著称。这正说明要“建立导演的威信”,瓶颈不在思想觉悟,而在对戏曲技术手段的把握,且不能只是一般性地了解。李少春在座谈会上特别提到他编排《野猪林》时关于如何处理“白虎堂”一场里一个二黄倒板的过门的反复思考㉔。他显然是想说明,假如对京剧的舞台技术手段缺乏深入领悟,要想成为有“威信和职权”的导演,恐怕只是幻想。担任过戏曲导演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洪深指出,建立导演制虽是“当务之急”,但是“必须新旧结合”,也即戏曲应求助于新戏剧工作者的加入,毕竟假如导演仍由传统艺人担任,导演制的建立就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㉕。然而,包括洪深在内的新戏剧工作者,在担任戏曲剧团的导演时,都频繁遭遇艺人直接或间接的抵制,最典型的就是艺人要求“你先来来给我看看”。他们面对这种诘难无力应对,只能抽象论证戏剧中导演的作用及重要性,甚至觉得建立导演制的主要障碍在艺人觉悟太低,却不愿意承认关键在于自己的导演水平不高。
要树立导演的威信,除了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表现出让表演者心悦诚服的能力外,别无他途。所以,通过“新旧结合”来建立导演制是解决导演来源的基本办法,这几乎成为座谈会上的共识。然而,假如像马彦祥所说的那样,采取“新旧结合”方式,仅仅是因为“新的戏剧工作者可能把握剧本的政治内容,能够控制技术,但又限于对旧剧的技术规律不够熟悉;旧剧戏曲工作者则对于舞台技术固然熟练,但限于政治和文化水平,不易掌握剧本的思想内容”㉖,那就把原应承担戏曲新剧目排演主导者角色的新戏剧工作者,变成了剧目政治思想内容的阐释者。这一想法与田汉对导演制的设想相距甚远。
二、基于导演制视角的传统戏曲创作
如前所述,“戏改”之所以提出建立导演制的问题,是因为传统戏曲的剧目创作没有这种“进步”的戏剧制度,因此要加以改造。在这一意义上,梳理传统戏曲的创作模式、认识传统戏曲的演出体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至于座谈会参与者多次提及的名角领衔制的弊端,不过是参会者的“趁手工具”,未必是推动导演制建立最好的和最具戏剧意义的理由。需要补充的是,针对戏曲演员在台上自由随意发挥、“放水词”,以及大量演出“提纲戏”(“路头戏”)的现象,导演制被看成改变这些现象的有效措施。这一问题在座谈会上虽然只略有涉及,但并不表示它不严重。
通过《新戏曲》杂志邀请参加“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的人员结构,可以得知会议主办者的意图。尽管建立导演制是其预设的立场,但是他们仍希望厘清传统戏曲的剧目创作模式,有此基础,才能进一步讨论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建立导演制。因此,应邀参会的有已经出版了《中国戏剧史史略》的周贻白,有著名的“戏篓子”景孤血、翁偶虹,除了未能与会的欧阳予倩,杨绍萱对戏曲史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从座谈会的讨论情况看,戏曲史上的“导演”问题并没有深入展开。
戏曲在宋元时期达到了成熟形态,其后数百年里积累了大量经典剧目,我们对这些剧目的具体形成过程了解得非常有限。明清年间的笔记小说里,有阮大铖、李渔等为其家班排戏的零星记录,从中约略可知,在演出昆剧的家班中,文人们按其对自己撰写的剧本的理解,确定排场,指导演员表演,但是这些记录与浩如烟海的戏曲传统剧目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而且,如果从剧本角度看,除昆曲表演有完整的传奇剧本可依从外,包括秦腔、汉调、梆子、乱弹在内,绝大部分民间戏曲剧种,其剧目主要从说唱或民间故事改编,舞台呈现方式则由艺人设计安排,并在实际演出过程中逐渐充实与完善,在这些剧目形成之初,很难设想有完整的剧本可供照搬并经导演排练。目前所见各地方戏中的传统剧目,多数都在长期演出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增删才演变成型,它们应该说是历代艺人集体创造的成果,也正因如此,各地、各剧种,甚至不同艺人对同一题材的剧目都会有不同处理,由此形成了戏曲剧目本身丰富多彩的景观。其实,即使是昆剧,文人主导某剧目表演形态的设计大约也只是特例,一是仅限于自己的剧本,二是其设计安排的表演样式在此后无数次实际演出中也可能发生变化。周贻白在将属于演出本的《缀白裘》文本与文人原作比对后发现,“只有《桃花扇》的本子,是统一的;当唱即唱,当不唱即不唱”,其他的“出出都有删略。白口能多出许多倍,每个角色自己都会发展他自己那一部分,如此发展下去,慢慢的剧本就控制不住演员了”㉗。这种所谓“控制不住演员”,是指即使是最讲究按规范剧本演出的昆剧,也无法避免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有其自由处理与临场发挥的空间。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一点,传统戏形成的舞台化创造主体是演员,而不是外在于表演者的“导演”。田汉、马彦祥等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故他们强调不能由演员兼任导演。20世纪初有大量的民间小戏与歌舞发展为戏曲新剧种,它们可以作为宋元以来从南宋戏文直到梆子乱弹的经典剧目成型经过的有趣参照。北方评剧初期演出的剧本主要是由演员出身的成兆才编定的,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玉霜走红时,评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经典剧目,其间看不到戏班外文人参与的情形。南方滩簧系列剧种的主要演出剧目,一类是“弹词戏”,一类是时事戏,它们借用成熟剧种的基本表演手法,由表演者将这些故事搬上舞台。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沪剧、越剧、甬剧、锡剧等经典剧目体系大都形成。我们或无法追索具体某个经典剧目表演形态形成的全过程,但这些晚近形成的剧种的庞大的剧目体系,从文本到表演规范的确立,都是由表演者完成的,至少其主体是演员,甚至未经职业化编剧先将故事改造成戏剧文本这一中介。这一现象表明,大量传统戏的创作路径,主要是由表演者将现成的故事(而非剧本)直接舞台化,除少数剧目有现成的模板(如说唱文学中的唱词和其他成熟剧种的同一题材剧目)可供参照外,从唱词到念白概由演员设计处理。秦腔之后的大量地方剧种少有剧本存世,就是因为在故事转化为戏剧的过程中,剧本这一阶段被直接跨过去了。当然,从故事到舞台表演的转换并非一次性完成,大量的传统戏只有简单的故事框架与人物设置,没有或无须固定成型的剧本。剧无定本、词无定腔,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戏曲界常说的“提纲戏”就指这类情形。当然,新兴剧种和成熟剧种之间的情形略有差别。那些历史较长的成熟剧种的经典剧目,其舞台表演形态或已大致定型,但演员在枝节上的个人发挥,仍在可以想象的范围内。即使是最为人们熟知的经典,表演者一时高兴或有特殊的需要时,在某个场次增加或删减几句唱词,都是常见的现象,观众也并不以演员每次演出时唱腔、台词不一致为异。无须严格按剧本演出,本是戏曲传统戏的通例㉘。清末日本留学归来的周孝怀组织川剧改良公会,严令川剧艺人必须严格按剧本演戏,很多著名艺人因为做不到而挨了罚。戏曲的历史主要是“演活戏”的历史,这种演出制度与按剧本演绎的演剧制度天差地别。戏曲因“演活戏”而给予演员很大的自由空间,却挤压了“导演”可能存在的空间。无须按固定剧本演出,当然就无从排练,这是导演职业在传统戏领域不可能形成的首要原因。
传统戏曲也不是完全没有排练。戏曲一方面确实在大量“演活戏”,另一方面也并非没有表演规范。每个剧种都有一些代表性的经典剧目,都有其基本的规范化的表现形态。戏曲演员学习表演的过程,核心就是学“戏”,即掌握这些最重要的经典剧目规范化的表演方法,通过经典剧目的表演训练获得并提高表演能力。按人们对传统戏曲演员的想象,演员对本剧种所有重要的经典剧目均应烂熟于心,通俗地说,他早就学“会”了。这种“会”就是指掌握规范化的表演模式,即所谓“通大路”或“官中”的演法。昆曲、京剧之所以有崇高的地位,就是由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把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创造的表演模式相对固定下来,形成了经典剧目的经典表演形态。所谓“会”演戏,指的就是掌握这样的表演手段,演出前自然无须排练,这样的演员也才有资格“吃戏饭”。
戏曲表演并非单个演员的唱念做打的独角戏,戏剧永远是多人合作的结果。戏曲大量地方剧种的经典剧目没有固定剧本,且各自演出总是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每个演员的先天条件也不一样,优秀的表演者在舞台上可以且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新的理解与处理,可以且应该有精益求精的雕琢,一般的表演者至少也可以按其天赋扬长避短,不可能只按“官中”的样子一代又一代地“刻模子”。再加上戏曲演员很少固定在一个戏班,在这种人员流动性很大的演剧环境里,配角演员所需要“会”的,不仅是大致的戏剧情节和人物关系,还需要了解主角演员的戏路,当然,还包括遇到主演有独创性的新颖表演方式时要有临场应变能力。如此说来,演员之间事先无须“对戏”,“台上见”就能确保演出质量,靠的是深厚的艺术底蕴,既熟悉“官中”的表演,又能在对手有新处理时瞬间做出符合戏情戏理的应对,包括小花脸的现场抓哏,都是对“吃戏饭”的演员的基本要求。在主演和一般演员之间地位悬殊的名角制时代,这种演出形态对配角演员的压力尤其大,所以才会有上述座谈会上对名角领衔的“角儿制”一边倒的责难㉙,这为确立导演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其实,戏曲演员即使演传统戏,也不是完全不“对戏”,只是并非必须。在实际演出前,“对戏”即事先排练,从积极的角度看是对舞台表演的艺术完整性负责;从消极角度看,也可以解释为演员对演出剧目及其合作者的路数不够熟悉,缺乏自信。谭鑫培晚年多次拒绝其他配演或琴师事先“对戏”的请求,其中就包括梅兰芳为他配演《四郎探母》和年轻的徐兰沅为他操琴时提出的类似请求,理由是他的演出都是“通大路”的。按一般的理解,既然是“官中”的表演路子,为他配演的演员自然应该掌握,应该“会”演,“对戏”就显得很多余㉚。地方戏的演出习惯与京、昆不一样,演员间合作比较固定,但更多演的是“提纲戏”。演员都必须掌握一些唱词、念白、人物关系等方面相对固定的套路,如花园赋子、公堂赋子、乞讨赋子等类似的结构件,在不同情境下可以自如运用。每场演出的过程,往往就是演员运用这些套路以适应不同的情境、相互配合、演绎完整故事的过程,虽未经排练,但仍能保证演出的整体性。至于场上演员的舞台调度,有演对手戏时“杀过河”“推磨”等角色换位,多人出场时“一条鞭”“挖门”“钻烟囱”等套路,尤其武打时的各种“荡子”,这些都是演员要掌握的基本要领,只需舞台监督给出简单提示,就可保证表演时整齐有序。
戏曲史上从京、昆名角到大量地方剧种的民间戏班,平时演出剧目多为传统戏,这些剧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舞台样式,所以,每次重演并不需要表演者重新创作。然而,戏曲观众的欣赏需求是多元的,既有痴迷经典剧目且满足于反复欣赏、细致琢磨的,也有希望看新故事、听新曲调以追求新的审美经验的,因而终究有对新剧目的需求,这一要求当然会通过市场体现出来。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商业剧场纷纷推出新剧目,就是观众这一趋新欲望的表现。因此,从梅兰芳开始,京剧“四大名旦”除演出传统经典,也编排了不少新剧目。新剧目的出现对传统戏曲的表演形态所构成的挑战,要早于“戏改”建立导演制的努力。这些名角独立创作的剧目,时称“私房戏”,有别于“官中”剧目。在这类新剧目的创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演,即“私房戏”的拥有者。虽然每部戏剧作品均有众多人物,但是,因为所谓“私房戏”的创作,其动因本来就是为展现名角的风采、满足对名角有兴趣的戏迷,创作焦点也就聚集于“角儿”。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的无论是时装新戏还是古装新戏,均由他个人完成,并不与其他人合作㉛。程砚秋创作的代表作《锁麟囊》更是如此。他接到翁偶虹为他写的剧本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王瑶卿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他的唱腔和身段设计。该剧在上海首演时,几乎所有配角都是程砚秋到上海后与黄金大戏院老板一起商量临时确定的,当然就很难与这些临时找的配角演员排练㉜。因此,虽然民国年间京剧演出了大量新剧目,亦无须导演参与。反倒是始于晚清的上海商业剧场内的连台本戏,如王鸿寿创排的《铁公鸡》之类剧目,从安排脚色到场面调度,包括为多人武打时创造新的套路等,事先大都经过排练。王鸿寿本人在这些新剧目创作中的职能,就是上述座谈会上诸参会者所说的“排戏先生”。
可见,在传统戏曲行业,舞台呈现这项任务按本份是由表演者完成的,外行参与的空间很小。即使坊间多有民国年间文人协助梅兰芳创作新剧目的传说,若具体看那些新戏的创作过程还是可以知道,文人为他提供新的剧本,或也可以为他提供一些表演上的建议,但是唱腔与身段还是需要他自己或在王瑶卿等老艺人的协助下完成设计,这些“身上”玩意儿的安排,外人无法替代。荀慧生、尚小云、周信芳、马连良等在民国年间多有新戏创作的艺人,情况亦无不如此,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李少春创作《野猪林》《云罗山》时依然如故。
民国时期类似于西方近代导演制的新剧目创作模式,前有杨韵谱,后有樊粹庭。民国初年,杨韵谱组女子戏班奎德社,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出,他自己并不参加演出,是编导一体兼班主,奎德社的剧目演出制度与导演制非常接近。20世纪30年代,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部主任的樊粹庭辞去公职,他和豫剧名家陈素真在豫声剧院及后来的狮吼剧团密切合作,所担任的亦是编导一体的角色。杨韵谱的角色或可类比于李渔,不过他行内出身,是能教戏的;樊粹庭是读书人,在陈素真的表演形态设计上就无法起主导作用,他的作用与编导一体型导演更具有可比性。但是这些在传统戏曲创作中只是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田汉等人所熟知的越剧的例子,更接近于“剧本制”而非“导演制”。从姚水娟到尹桂芳、袁雪芬,她们改变了越剧唱“路头戏”的传统,聘请樊篱、南薇等喜爱越剧的文艺青年写剧本,但在表演上仍需演员自己做主,无法依赖那些所谓“编导”。也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戏曲名角相对于编导才处于予取予夺的强势地位,觉得编导是他们养活的,而不是相反。
三、建立导演制的具体实践
我们看到,在上述建立导演制的相关讨论中,对传统戏班演剧制度的描述并不充分,尤其是大量民间戏班的演剧形态,基本都在参与讨论者的视野之外。这些知识上的盲点,说明“戏改”的主导者们对民间戏曲演出的实际情况了解很有限,更说明建立导演制多半只是基于理论或案头的设想,这些都成了“戏改”主管部门欲推动导演制,却经常不得其门而入的原因。
在戏曲界推行导演制的实践步履维艰,这一看起来对戏剧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进步”的演剧制度,遭遇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争议与困难。20世纪50年代初各地演出的“解放新戏”,为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纷纷运用大量群众场面,传统戏演出明显缺少处理这类场面的手段,新文艺工作者一度因掌握了一点浅显的话剧导演知识而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但戏曲表演毕竟要依赖主要演员扮演的主要角色的行动表现戏剧内容,观众真正感兴趣并为之痴迷的也从来不是群戏。随着在戏剧进程中机械地引入群戏的现象逐渐冷却,群众场面的安排与调度作为推行导演制之理由的功效迅速消退。至于要在有灯光布景的格局中完成表演,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困难。民国年间,很多剧种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灯光布景,尤以海派京剧光怪陆离的机关布景为甚,包括王鸿寿在内的诸多传统艺人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在新场景中表演的难题,实际上,他们还是各种灯光布景之运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正因为对传统戏曲的演剧制度缺乏足够的认知,“戏改”的主管部门很难明确地锁定建立导演制的路径与重点,而传统戏曲演出仍然深受观众喜爱的现实,又迫使他们做出种种妥协。导演制被看成提高戏剧艺术水平、推动传统戏曲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推动过程中,那些盲目推崇西方戏剧观念而推动导演制建立的新文艺工作者在加入戏曲领域后,却无法通过被观众和市场认可的作品证明这一新的演剧制度的优越性,并借此取得对戏曲创作、演出及发展的主导权,“新旧结合”仍是不得已的选择。戏曲界对导演制的抵触情绪反而因此发酵。一篇署名李曦华的文章写道:“戏曲界接受话剧影响,逐渐地建立了导演制度,这是合理的发展。但是有许多戏曲团体的导演,常常只是一种名义,一种形式……如果有导演,就该建立真正的导演制度;被邀请做导演,你也必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导演。”㉝在《新戏曲》杂志召开上述座谈会之前,各地对导演制的抱怨就已不绝于耳,较常见的批评认为,是导演制让戏曲变成了话剧或话剧加唱。
在实践中,导演制的推行也困难重重。上海戏曲界在建立导演制方面早著先鞭,1951年开始举办专门培养戏曲编导的学习班。根据上海文化部门的计划,这个学习班要从社会上“招收50名左右政治纯洁,品行端正,有相当文艺修养并爱好的知识分子,进行短期集中的学习,在政治业务上提高到相当水准,希望通过这个学习班的培养并以此为桥梁,把政治、业务、写作上成绩比较优良的学员吸收到戏曲界里来,参加戏改工作,替戏曲界增加一批力量”㉞。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月的学习班期间,被安排讲课的南薇等人,其所擅长的主要是越剧的剧本写作,他们虽然也参与排戏,但最主要的贡献是撰写剧本,所以其讲授内容及讲习班的成效,与文化主管部门期待的导演制的人才培养,其实是有明显差距的。
这是个很说明问题的个案。“戏改”之初,戏曲界对导演制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要求演出有相对固定的剧本的层次上,这说明戏曲界本身对传统戏演出中过多的即兴表演是有所反思的。所以,即使是在传统剧目被更多允许在舞台上呈现、新剧目创作的压力逐渐减小时,导演制的推行依然是文化主管部门和戏剧批评的重要关注点。在经历了各种复杂的讨论之后,仍少有成功的范本。马彦祥在1953年就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国营剧团中已开始建立了导演制度,但绝大多数的剧团还缺少这一制度;要实行这样的制度也还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对于导演工作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他再次看到,建立导演制的根本解决路径,是“先需要演员们对于导演工作有新的认识,新的重视,这样如能建立导演的威信,也就能发挥导演的真正作用”㉟。在“戏改”与建立导演制方面一直处于模范地位的华东戏曲研究院,专门组建了作为非演出部门的研究室。该研究室在195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
我们在建立导演制度及排演方法上亦有了些改进。如越剧在《织锦记》及《春香传》均开始试行了较为正规的排演;京剧在《秦香莲》及《白蛇传》的排演上亦建立了较正规的导演制度,保证了艺术质量。并实行试用了排演小组,目的在于发挥艺术创作中的集体领导作用及加强艺术创作的整体性。事实证明,排演小组是有它的优越性的,只是我们还未加以很有效与很广泛的运用,但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㊱
这里提到的几个剧目,在该时期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创作演出中并不具代表性,因此他们用了“试行”“试用”这样的字眼。这是同时代很少没有责备表演者“觉悟低”的表述。确实,就当时的环境而言,要提高甚至改变演员对导演工作的认识,主要途径恐怕不是在理论上证明建立导演制的必要性,而是要在实践中拥有足够多能帮助演员理解作品、让戏剧演出更具魅力的导演。所以,推行导演制最大的障碍,还是在既熟悉舞台又无法被归于传统的“排戏先生”的导演人员的极度短缺。
在戏曲界建立导演制的设想,后来因为苏联戏剧专家的到来进入新阶段。“戏改”主管部门关于建立导演制的计划,原本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苏联戏剧为范本的。苏联专家组以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列斯里为组长,他们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专门的导演干部训练班,安排了导演学系列课程,并经常借观摩戏曲演出的机会向文化部门领导提出建议。这个训练班集中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生源,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像阿甲、李紫贵这样已经有一定戏曲导演经验的名家。苏联专家把或许最接近其本来面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体系带到了中国,然而遗憾的是,用该体系指导戏曲创作与表演,在相当程度上只会收到削足适履的效果㊲。
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领域在演剧制度方面最明显的变化并不是导演制的建立,而是在推动导演制过程中编导制与作曲制的悄然成型。戏曲演出必须依据定型的剧本,唱腔必须遵从定型的音乐,这些新观念为职业化的编剧和作曲提供了新的机遇。而在戏曲传统剧目整理与新剧目创作过程中,虽然导演作为一个新职业逐渐在戏曲界得到认可,但回顾这个时间段留下重要作品的导演,可发现他们多是从资深演员转行过来的,丰富的表演艺术经验在其导演活动中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导演并没有真正与“排戏先生”区别开来。直到“文革”结束,除部分国家级及省级等示范性剧团外,大多数戏曲剧团仍未有制度化的导演,排戏仍主要由老艺人主导。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派戏剧观念开始进入戏曲领域,具有话剧背景的导演对戏曲产生了新一轮冲击,主导创作了一批“探索性”戏曲作品。这些导演当然不复是原本意义上的“排戏先生”,但是人们渐渐发现,这一代导演遇到的仍然是三十年前的难题。即使戏曲导演走马上任,但在具体表演时仍要依赖有戏曲背景的“技术导演”,也就是说,由于对戏曲技术手段的陌生与疏离,导演在创作中很难让戏曲演员发挥和展现表演上的优势,因此鲜有佳作。相反,那些持续有优秀戏曲新作问世的导演,几乎都有戏曲表演的经历。《曹操与杨修》的导演马科是京剧武生出身,《徐九经升官记》《药王庙传奇》的导演余笑予幼年起就从事楚剧表演,谢平安、杨小青等优秀导演分别是川剧、越剧演员。就像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排戏先生”一样,他们未必在表演艺术领域有特殊成就,但是科班出身的演员经历,让他们既能为演员设计舞台手段,面对演员“你先来来给我看看”的挑战,也有一定的能力做表演示范。近些年在戏曲界成就突出的知名导演,如张曼君、石玉昆、韩剑英、王青、徐春兰、翁国生等等,同样因为有从事表演的经历,在从事多剧种导演时显得得心应手。当然,确实也有出身话剧导演专业而常有优秀戏曲作品问世的导演,但他们在表演技术层面仍无法摆脱对“技术导演”的依赖,至少在排戏的某些阶段,要由戏曲界人士协助突破一些具体的舞台呈现难关。
20世纪50年代“戏改”时期建立导演制最直观的指标,即导演的职业化,终于在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得以实现。如今,导演由主要演员兼任的现象已经极为罕见,尤其是在新剧目创作中聘请职业导演已经成为惯例,而导演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也得到承认。若从这个角度看,在戏曲领域建立导演制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它所依赖的却并非既有的导演理论,反而是导演所具备的戏曲表演技能。
四、戏曲导演制的得与失
戏曲领域导演制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戏改”主管部门未曾想象到的路径完成的,然而正如当年的设想,这一全新的演剧制度确实深刻影响了戏曲创作与演出。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评估这一变化的得与失?
建立导演制这一目标终于达成的标志,是导演职业化及剧团内普遍设置专门的导演岗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导演行业的高度职业化已是无可怀疑的现实,除传统戏恢复演出外,由导演负责新剧目创作早就是常识。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导演制度的确立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在戏曲界成为普遍现象的。戏曲剧团导演岗位的设置此前之所以未能全面实现,部分是由于直到70年代剧团(包括国营剧团)仍是经营性文化企业,岗位设置与剧团开支直接相关,导演这种在演出中被认为非必需的岗位设置,自然难以为戏曲界普遍接受㊳。80年代后,政府资助在戏曲剧团支出中的比例急剧提高,戏曲界对导演工薪一事才不再敏感。当我们看到新剧目创作经费越来越依赖财政、导演费用同步上升时,就更可理解这一点了。
建立导演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完全确立了新剧目演出前的排演制度。如果说当年新中国京剧团初建时还因为一部新戏演出前排演半个月而遭到同行的嘲笑,那么七十年过去后,现在任何戏曲剧团在演出任何新剧目前,都要安排数月的排练,甚至连传统戏的演出通常也安排一段时间复排。除极少数经典剧目外,戏曲演出的合作者事先不经“对戏”、直接“台上见”的现象已经基本绝迹。戏曲演剧制度的这一重大变化,得益于两个外在因素:一是国营剧团的人事制度让所有戏曲演员都有了固定归属,流动性变得极小,因此演员可以方便地在一起排练;二是演出市场的萎缩与分配制度的彻底改变,让演职人员对时间的价值丧失了敏感性,即使长时间排练也不影响其收入,自然不复有抵触情绪。戏曲演出“台上见”的现象固然消失了,然而这两个原因听起来都并不令人欣喜。
戏曲是一种需要多人乃至群体合作创作的艺术,剧团演职员相对固定、长期合作,容易在演职员间产生默契,有助于提升艺术的整体性和规范化水平。即使在人员流动幅度最大、最自由的民国京剧界,名演员也经常聘请固定的琴师、鼓师,这足以说明稳定的合作者对表演艺术的重要性。所以,“戏改”中改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保新组建的剧团演职员相对稳定。但是,戏曲演职人员流动的优点在这里被忽视了。新的合作者之间能激发新的创作灵感、发展出不同的演绎方式,这是戏曲史上形成如此丰富多彩的剧目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优秀剧目常演常新、在经典化道路上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人员相对固定的剧团里,戏曲演员失去了不断寻求新的合作者的机会,这与仅演出事先经过严格排练的剧目所导致的凝固化演出样式产生叠加作用,使数十年来传统经典剧目很少变化,虽然戏曲艺术因此能得到较好的传承,但也不能不面临丧失更多发展空间与更多新的可能性的窘境。
新剧目创作是另一个问题。在戏曲演剧艺术层面上,剧目完全按定本演出,这是戏曲表演史上最大的变化,它与导演制或者说编导制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彻底改变了演员在舞台上自由发挥的现象,更不用说,确立导演制后,戏曲舞台上不仅“提纲戏”完全消失,“演活戏”现象也日渐绝迹。20世纪60年代戏剧界仍有对“提纲戏”和演员在台上“放水词”的批评,而在导演制实际确立后的当下,戏曲演员早就习惯于严格按照剧本和作曲设计的唱腔表演。尽管在舞台表演过程中,遇有突发情况时为遮掩而采取的应急救场行为仍然存在,但已是极偶然的特例。
新剧目在演出前经过长时间精心排练,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舞台事故及不合理的表演。从角色的安排与分配开始,所有演员对每个场景中自己的位置及变化、唱腔台词及唱念方法都反复练习,形成相对固定的舞台呈现方式,这就使得每次正式演出都是以同一剧目的同一形态面向观众的重复呈现。从这个角度说,导演制的戏剧意义是戏剧作品在正式公演前已经“创作完成”,所谓“公演”就是让剧目以“成品”方式呈现在舞台上。它比戏曲的定腔、定本演剧制度更进了一步,那就是不仅剧本和音乐是事先确定的,所有演员在每个场景中的所有行动也都是事先确定的。
从演剧制度角度看,“演活戏”和导演制是其两个极端。就戏曲剧目的形成过程而言,“演活戏”的剧目是在演出中完成的,它的存在方式是一次性的,同一剧目在下一次演出中会呈现出另一种形态,演出过程就是剧目的创作过程;而导演制的剧目创作是在演出之前完成的,在演出之前,对剧目的演绎形式就已设计好并固定下来,所以它的存在可以是多次性的,每次演出都是表演样式的重复。相对于“演活戏”每次演出都会因演员水平参差不齐或表演者状态好坏而导致演出质量不稳定的现象,导演制的优点显而易见,它使演出整齐、规范、有序,演出质量是可以预期和保证的。但是,定型化演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导演制的创作体制形成后,演员从舞台演出中的创造者变成一定意义上的现成模板的复制者,这窒息了他们在舞台上自由创造的欲望,使他们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设计动作唱腔的意愿迅速下降。多数演员、包括主要演员的自主创造能力难免因此退化,长此以往,对戏曲表演的整体水平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导演制并不意味着戏曲表达就不再有自由创造的空间了,只是这一空间被主要赋予了导演而非演员和乐师。换言之,在执导每个剧目时,导演可以且必须有自己独创性的设计,然而,由于演出形态在导演主导的排演过程中已然凝固化,实际演出时演员、乐师个性化的发挥,尤其是即兴的创造就受到极大的约束,至少在理论上,他们不被允许和鼓励即兴发挥。在戏曲发展史上,明清年间地方戏大量兴起时戏曲表演之所以获得重大发展,就是因为艺人和戏班在常年的经营性演出中不可能完全按照现成的剧本演绎,即使有现成的剧本在,多半不识字的艺人表演时也不得不大量地即兴发挥,表演与剧本呈现出明显的分离与多元状态。很多艺人在表演时并不完全以剧本为根据,唱词和含白、动作等等,都有自由驰骋的余地。但是,在建立导演制的过程中,在那些旧剧改造者眼中,民间戏剧特有的这些“演活戏”的即兴成分的弊病被无限放大了,而它的积极意义,包括对表演艺术发展、提高的刺激作用等等,却很少得到正面总结,在当时的环境下,甚至连这种理论意识都无从显现。
因此,无论是从传统剧目演出角度看,还是从新剧目创作角度看,导演制可谓得失兼备,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回到“戏改”时期,众多文化部门的管理者推动建立导演制的努力,对戏曲演剧制度和艺术的影响,本不限于有更多具有新思想内容的剧目出现,它所改变的也不只是晚清民国商业化剧场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名角制。导演制真正改变的是戏曲的演剧样式,甚至戏曲的整体生态。从整体上看,“戏改”主导者秉持的基本观念是不喜欢个性化表达,更倾向于追求群体秩序;同时,他们亦是精英主义的,在内心深处对戏曲的民间形态有种出于本能的抵触与鄙视。“戏改”所倡导的制度,包括导演制在内,无不如此。评估导演制的得与失,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维度。在所有艺术领域,规范与自由都是一对反义词。戏曲表演亦不例外。戏曲导演制的建立对戏曲演剧制度最大的冲击与改变,就是使戏曲表演从自由的、充满活力的、每次演出都有即兴的舞台艺术,变成了相对凝固的、规范化的、每次演出都在重复的舞台艺术,与此同时,戏曲的民间性被迅速消解。对这一变化的得失亦无法做简单的是非判断。在一个由众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组成的高水平的演出环境里,自由与活力是促使艺术不断有新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伟大的艺术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出现。在一个相对缺少杰出艺术家的低水平的演出环境里,凝固与规范才能确保艺术艰难地维持在一定水准上,它是在其衰落不可避免时有效的缓冲阀。但是,这个结论最好不要被引申为替导演制在当下中国戏曲语境中的合理性背书,因为假如将时序前置,建立导演制的努力是否应该为戏曲表演艺术水平的下降承担部分责任,恐怕是个无法回避的疑问。
① 参见海兰·契诺伊:《导演者的出现》,杜定宇译,《戏剧艺术》1981年第1期。
② 如孙百璋编译的《俄国演剧法择要》(通俗教育研究会1918年版)就是国内较早的涉及戏剧导演的著作。
③ 马少波:《关于戏曲导演》,《人民戏剧》创刊号,1950年4月1日。
④⑤⑩⑪⑫⑬⑭⑮⑯⑳㉑㉒㉓㉖㉗ 《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记录》,《新戏曲》第1卷第2期,1950年10月。
⑥ 参见《皖南戏曲改革工作总结》,《新戏曲》第1卷第1期,1950年9月。
⑦ 王仲元:《太原市戏曲人员的收获和缺点》,《新戏曲》第1卷第1期,1950年9月。
⑧ 《苏南区戏曲改革工作总结》,《新戏曲》第1卷第1期,1950年9月。
⑨ 参见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的新戏曲而奋斗》,《人民戏剧》第二卷第六期,1951年3月。
⑰⑱⑲㉔㉕参见《如何建立新的导演制度座谈会记录》。
㉘ 在笔记小说里,有戏班演出时乡村老者将剧本放在桌前,戏班如不按剧本演出就要责罚的记载,虽是极端现象,倒也并非不可能。按我的田野考察经验,戏班演戏最为主家忌讳的是“偷戏”,即删减剧情,至于戏班在某部戏里演得多一点,加唱或多些身段,是不会挨罚的。
㉙ 当然,名角在演出中故意加点戏外的词以考验甚至戏弄配演的现象也是难免的。在这样的场合下,配演就要有“接得住”的本领。如果没有随机应变的本事,窘在台上,那这碗戏饭也是很难吃下去的。
㉚ 也有相反的例子。有文章这样写道:“谭鑫培六次赴沪演出,多是张阿牛充当鼓师。他第一次为谭打鼓时,夏月润担心他与谭配合不好,在临演之前请他去与谭对戏,免得临场出差子。张阿牛认为夏月润轻视他,生气没有去。等演出时,他的鼓点与谭鑫培的演唱无一处不是严丝合缝的,甚至连谭也佩服。”(宋学琦:《记与谭鑫培合作过的鼓师》,戴淑娟等编:《谭鑫培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
㉛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第六章很具体地回忆了他当年改编演出《霸王别姬》的过程。他演这出戏是简单排练过的。扮演霸王的杨小楼是前辈,不可能请他一起来排戏,所以首场演出实际上是他们第一次按梅兰芳的新本子走,演出中他甚至建议“九里山大战”后就结束(反正是新戏,第一次演,观众也不知道戏到哪里为止)。演出后,梅兰芳在冯幼伟、姚玉芙等人陪同下去杨府,说是道乏,应该还包含向杨提一点表演上的建议的意思,希望他在念“力拔山兮……”时加一些必要的身段。当然,他们要顾忌礼数,不能明着说,而杨小楼心里也明白得很。几天后,杨小楼就约梅兰芳到他家,因为他想好了这段表演的设计,他把想好的演法说给梅兰芳听。“当时我们来了几遍”,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排练了。参见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五册,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352页。
㉜ 名角的“私房戏”,剧本是专门请人为他写的,为防剧本外泄,所有配演演出前拿到的都不是完整的剧本,而是只涉及该位配演的唱腔与台词部分,俗称“单片”。合格的配演仅凭这些“单片”就能知悉他的戏,然后就是“台上见”。《锁麟囊》是全新剧目,事先当然需要稍加排练,负责排戏的是程砚秋的管事,俗称“抱总讲”,他手头有完整的剧本,负责除主演外所有演员的“对戏”。《锁麟囊》中扮演女二号赵守贞的是程剧团中和他长期合作的吴富琴,“春秋亭”一场赵守贞和主角薛湘灵有大段非常紧凑的对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机会与程砚秋排练,通常是请教程砚秋的管事,由管事来帮忙“对戏”。按扮演梅香的名丑刘斌昆的回忆,上海首演的正式演出前,他们一共走排三次,程砚秋最后一次才到场。因为只是简单地走了走位,上场时他才知道程砚秋扮演薛湘灵,一个简单的“看囊”水袖要三次翻动,美极了。(参见刘斌昆:《情深谊长忆砚秋》,《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3页。)传统戏曲演出前很难安排排练还有经济上的原因。演员搭班拿戏份,每场演出的收入都与当场演出的总收入有关,一天是一天的钱。名角给自己排新戏,如果老是让配角演员来排练,不给钱不合适。如果都要给钱,排戏的时候又没有收入,负担既重,又很难确定如何开戏份,这也是传统戏曲班社不可能经常排戏的原因。当然,昆曲家班例外,既是家班,本来就无须给演员发工资。值得玩味的是,此前程砚秋在他著名的“赴欧考察报告书”里曾经建议戏曲实施导演制。“导演者权力要高于一切。”他说,“说到导演问题,更使我们惭愧”,因为戏曲排一部新戏只要排一两次,“至多三次,大家就说不会砸了”,“更不堪的是连剧本也不分发给演员”(程砚秋:《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1933年版,第77、49页)。然而,这些他激烈批评的现象,又全都出现在他七年后排《锁麟囊》的过程中。他明明在赴欧考察时理解了导演的重要性,并且呼吁戏曲界仿效,为什么不带头实践呢?程砚秋是一个“窗口”,它告诉了我们戏曲导演制与传统戏曲演出制度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也间接地说明了要从上至下地强行推行导演制,很容易伤及戏曲之根本。
㉝ 李曦华:《论导演技术》,《戏曲报》第5期,1950年3月25日。
㉞ 流泽:《上海市戏曲编导学习班总结》,《戏曲报》第四卷第10期,1951年7月5日。
㉟马彦祥:《巩固并扩大戏曲改革工作的成绩——在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发言》,《剧本》1953年第10期。
㊱ 吴琛:《艺术室工作总结》,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华东戏曲研究院文件资料汇编》,1955年3月印行,第66页。
㊲ 拙著《当代中国戏剧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介绍了这段时间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体系“指导”戏曲的各种“洋教条”,此处不赘。参见该书第80—91页。
㊳ “戏改”初期政府欲向剧团派驻干部时,只要让戏班负担其工资,就必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抵制,这算是一个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