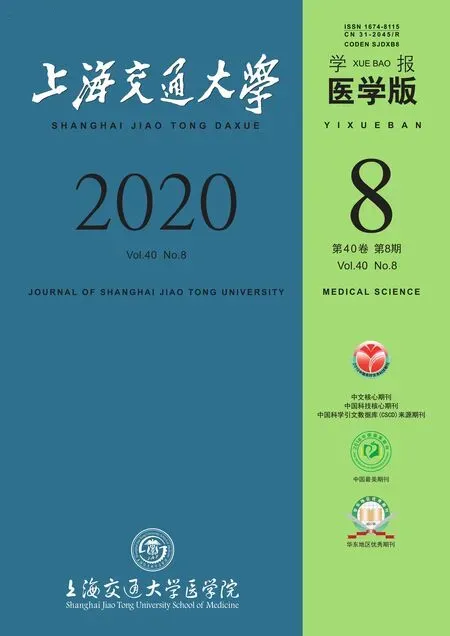人格障碍诊断与评估的研究进展
胡 佳,仇剑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200030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fifth edition of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5),人格障碍是一种与个体文化背景明显不符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的持久模式。该模式使个体感到痛苦或导致个体功能损害,泛化到个体各个方面并且缺乏弹性[1]。
美国的一项全国流行病学调查(n=43 093)发现,14.79%(95%CI 14.08%~15.50%)的成年美国人至少有1种人格障碍;较常见的是强迫型人格障碍 (7.88%,95%CI 7.43%~8.33%),其次依次是偏执型人格障碍(4.41%,95%CI 4.12% ~4.70%)、反社会型人格障碍(3.63%,95%CI 3.34% ~3.92%)、 分裂型人格障碍(3.13%,95%CI 2.89% ~3.37%)、 回避型人格障碍(2.36%,95%CI 2.14%~2.58%)、表演型人格障碍 (1.84%,95%CI 1.66% ~2.02%)、 依赖型人格障碍(0.49%,95%CI 0.40%~0.58%)[2]。英国的一项研究[3]采用结构化临床访谈的方法,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共计626 名16 ~74 岁的社区人群调查发现,人格障碍患病率为4.4%(95%CI 2.9%~6.7%),在城市地区的男性、失业者、分居者中该比例更高。流行病学数据[4]显示人群中普遍存在人格障碍,该现象值得关注与研究。
1 DSM 系统中人格障碍诊断的发展
人格障碍诊断的变迁,反映出对人格障碍临床诊断的认知和发展轨迹。根据DSM 系统,可看出人格障碍诊断的发展。在其早期阶段,DSM-1 的出版标志着人格障碍诊断有了正式的开端;DSM-2 的出版补充了人格障碍的起病时间,但该阶段的人格障碍诊断理论支撑不足、可操作性和临床实用性都较差。1980 年DSM-3 的出版标志着人格障碍诊断进入了后期阶段。DSM-3 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来理解人格障碍,代表了人格障碍诊断和分类的重大进展[5];此后出版的DSM-Ⅳ及其修订版DSM-Ⅳ-TR,均沿用了DSM-3 的多轴诊断策略、类别诊断标准。各典型类别人格障碍有明确独立的、操作化的诊断标准。人格障碍被划分为3 种类型,分别是奇特或古怪型(A 型),戏剧化、情绪化或不稳定型(B 型),焦虑或恐慌型(C型)。总体来说处于后期阶段的人格障碍诊断有了突破性发展,目前的临床诊断沿用了该阶段的诊断标准。但是因为各类型人格障碍具有相互独立的诊断标准,并且满足规定条目数就可以诊断为某种人格障碍类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对人格障碍的病理性严重程度进行评估[6],同时存在异质性和高共病问题以及诊断标准多元的问题[7]。2013 年出版的DSM-5 在其第三部分提出了人格障碍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s,AMPD),标志着人格障碍诊断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DSM-5 中人格障碍诊断发展的新方向
2.1 AMPD 的主要内容
DSM-5 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人格障碍诊断新的发展方向。DSM-5 的第二部分仍然使用类别诊断标准来评估人格障碍,但DSM-5 的第三部分提出了AMPD[1]。AMPD替代了传统的分类诊断模式,既克服了分类诊断模式的弊端,又能评估人格障碍的严重程度,能够更全面地描述个体的病理性人格特质。
2.1.1 人格障碍一般诊断标准 在 AMPD 中人格障碍的一般诊断标准涉及人格功能损害、病理性人格特质、损害的广泛性、损害的时间稳定性、与其他精神疾病的鉴别、与物质或其他躯体疾病引起的生理异变的鉴别、文化环境7 个方面。其中对人格障碍的诊断起决定因素的2 个标准是:标准A,中度及以上的人格功能损害;标准B,一种及以上病理性人格特质。标准 A 中的人格功能损害,包括自我功能(身份和自我引导)和人际功能(共情和亲密感)2 个方面(4 个因素)[1],构成了病理性人格障碍的核心[6]。标准 B 中的病理性人格特质包括5 个维度:负性情感、分离、对抗、脱抑制以及精神质,且这5 个维度包含更为具体的25 个病理性人格特质[1]。
2.1.2 人格障碍类型 AMPD 中在典型的人格障碍类型方面有较大变化,精简为6 个典型类型:反社会型、回避型、边缘型、自恋型、强迫型和分裂型。此外,符合人格障碍一般诊断标准但不符合6 个典型类型中的任何一种人格障碍,被划分为特定特质人格障碍。特定特质人格障碍不需要再划分亚型,而是根据标准A 和标准B 提供构成人格的描述性元素。不同的描述构成不同的案例。因此,在AMPD 中,个体即使不被诊断为某一类型人格障碍,也可以有该类型人格障碍阈值下的临床表现,即可以有满足该类型人格障碍的某几条诊断标准的临床表现,但尚达不到诊断标准[1]。
2.2 AMPD 的理论与研究支撑
DSM 系统人格障碍部分的一个持久讨论主题就是隐藏在不同症状下的共同因素是什么,目前还未能解释,因为不同人格障碍的一些症状表现似乎有相似性[8]。许多观点都在尝试解释不同类型人格障碍的共病问题[9]。这些解释指出,一个共同的潜在因素的存在导致不同类型人格障碍具有相似特征,该潜在因素涉及人格病理的严重性[10]。AMPD 强调了所有类型人格障碍的一个共同因素:人格障碍的病理性水平,即人格功能的损害程度。文献[11]表明,各类型人格障碍之间的变异往往高度相关。Sharp 等[12]对966 例成年患者使用人格障碍诊断问卷(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Ⅳ Axis Ⅱ Personality Disorders,SCID-Ⅱ)第2版进行评估,发现存在1 个人格病理性的一般因素(G 因素)和若干特殊因素(S 因素)能够解释各类型人格障碍之间的协方差。值得注意的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条目倾向于负荷于一般因素。Sharp 等[12]的研究结果表明DSM-5 第二部分按照独立的标准将人格障碍分为10 种显著类型,而制定独立的特殊治疗计划可能不合理。评估和治疗计划应该聚焦于人格病理性的一般因素。上述研究[12]指出,虽然定义该一般因素还存在几种可能性,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该一般因素反映了人格病理性的严重程度,即人格功能损害程度。该研究支持了AMPD 将中度及以上人格功能损害纳入诊断标准。
AMPD 的标准A 将人格功能分为自我与人际2 个维度。该划分方式可以追溯到心理动力学概念,比如Kernberg 的人格组织模型[13]。Kernbergr 人格组织模型包括真实性检验、自体与客体的区分及整合 (身份认同)、防御机制3 个维度[14]。其中自体与客体的区分及整合维度,可以为AMPD 用自我和人际2 个维度来评估人格功能水平提供理论证据。
AMPD 的标准B 将人格特质分为五大维度。Hentschel 等[15]指出基于证据的人格障碍分类应纳入维度诊断。AMPD 采用多维特质模型来评估个体的病理性人格特质,并且被证明与大五人格模型有良好的对应性[16]。
3 新的人格障碍评估工具的开发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人格障碍诊断量表是SCID-Ⅱ和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16]。近年来,随着强调人格障碍的一般因素以及人格障碍诊断的维度化,新的评估工具相继被开发出来。以下主要介绍APMD 中提出的评估工具,以及基于Kernberg 人格组织模型的评估工具。
3.1 AMPD 下的评估工具
3.1.1 PID-5 Krueger 等[17]开发的DSM-5 人格量表(Personality Inventory for DSM-5,PID-5)在AMPD 中被提出,是用来评估病理性人格特质的自评量表。PID-5 共220道题,使用李克特四级评分,范围为0 ~3 分,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PID-5 按照AMPD 的标准B 将个体的人格特质划分为5 个方面、25 个人格特质[18]。PID-5 的5 个方面可以看作是五因素模型的非适应性变异[19]。
关于PID-5 的效度研究,Hopwood 等[8]招募了1 001 名正常被试,发现PID-5 的特征与人格评定量表(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PAI)之间有广泛的收敛性,可以有效地组织五因素结构。这些因素被认为反映了广泛的心理系统,将人格、精神病理学和临床相关行为联系起来。Zimmerman 等[19]的研究表明PID-5 与16 项人格组织问卷(Inventory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16 Item Version,IPO-16)的平均得分呈正相关,其中负性情感和精神质方面的得分与其相关性较强,脱抑制方面的得分与其相关性较小。眭爱萍等[18]对439 名正常被试的研究表明PID-5 的结果能较好地预测基于DSM-Ⅳ筛查出的人格障碍个体。
而在 PID-5 的信度研究中,Krueger 等[17]发现25个人格特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值范围为0.72 ~0.96,中值为0.86。有学者进行了PID-5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的研究。Zimmermann 等[19]对577 名正常被试进行德文版PID-5 研究,发现德文版PID-5 的25 个人格特质的Cronbach's α 值范围为0.73 ~0.95,中值为0.86。这与Krueger 等[17]的研究结果几乎一致,但是该研究指出情绪易变、操控、敌意3 个特质可能还有更复杂的结构,而不是简单地被划分为单一的维度。Zimmermann等[19]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了212 例住院患者样本的研究,表明PID-5 可能适用于其他语言和文化,为PID-5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一项丹麦的混合样本(n=1 119)研究[20]表明,25 个人格特质的Cronbach's α 值范围为0.75 ~0.95,一致性系数最低的人格特质是不负责任,一致性系数最高的人格特质是古怪,表明PID-5 量表总体上可靠、有效;但是该研究结果认为机械的完美主义特质可能应属于负性情感维度,而不是AMPD 中提出的脱抑制维度。眭爱萍[21]对正常被试(n=539)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PID-5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该研究发现量表中负荷于分离维度下的受限制的情感特质,实际上更倾向负荷于负性情感维度。
总的来说,PID-5 的人格特质与临床症状有良好的相关性,可以依据个体的人格特质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PID-5 是以人格特质为特征的诊断,时间稳定性优于DSM-Ⅳ的分类[15]。多项研究证明了PID-5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可推广性。但PID-5 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220道题的题量以及操作的相对困难性限制了临床应用;一些特质在实际维度上的负荷与原来维度不一致等。
3.1.2 LPFS 人格功能水平量表(Level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Scale,LPFS)根据AMPD 提出,用于评估人格功能损害程度[22]。LPFS 使用诊断标准A 中提及的人格共同相关的4 个因素来区分5 级损害:0 级,没有损害;1级,一些损害;2 级,中度损害;3 级,重度损害;4 级,极严重损害。
LPF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0]。Morey 等[23]发现在337 例患者中,248 例符合DSM-Ⅳ人格障碍典型类型中的至少1 种标准。LPFS 在测量符合典型人格障碍标准的患者时显示出72.7%的特异度和84.6%的敏感度。LPFS 与对其他人格病理学的测量,以及对人格功能、风险、预后和最佳治疗强度的临床判断有显著相关性[23]。Zimmermann 等[24-25]在正常人和患者间进行的2 个研究也证明了LPFS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Preti 等[22]的研究证明即使使用者没有足够的经验,LPFS 在评估患者时也显示较好的准确性。综上,LPFS 弥补了DSM 系统在评估人格功能损害方面的空缺,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3.2 基于Kernberg 人格组织模型的人格障碍评估工具
Kernberg 阐述了基于客体关系理论的人格组织模型。Kernberg 认为,在人格障碍外显的行为下还有潜在的人格组织的问题,可以从现实检验力、身份认同、防御机制3个维度的不同表现来划分不同的人格组织[14]。人格组织围绕身份认同这一核心概念,被划分为不同水平。有统一身份认同的个体,人格组织可以分为正常人格组织和神经症性人格组织,二者主要是防御机制上的差异。身份认同不稳定、肤浅的个体可以被划分为边缘人格组织和精神病性人格组织,二者主要是防御机制和现实检验力的区别。其中边缘人格组织可以划分为高、中、低3 个水平[14,26]。
常用的基于Kernberg 人格组织模型的评估工具有人格组织量表(Inventory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IPO)和人格组织诊断表(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Diagnostic Form,PODF)。比较前沿的评估工具主要有人格组织结构化访谈问卷(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STIPO)及其修订版(STIPO-R)。
Clarkin 等[26]编写的 STIPO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旨在通过评估个体不同维度的人格功能的水平来判断人格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STIPO 有身份认同、防御机制、现实检验力、客体关系质量、应对与僵化、攻击性、道德价值7个维度。2016 年Clarkin 等[26]修订的STIPO-R 将其精简为5 个维度:身份认同、防御机制、客体关系的质量、攻击性和道德价值观,并且在每个维度的项目中嵌入了自恋维度的项目。
评估者首先对受试者的回答进行单项评分再得出每个维度的总分,该得分提供了每个维度的病理学指标。再综合每个维度,得出总体临床评分,评分范围1 ~5 分,代表人格组织水平从正常的人格组织到非常严重的病理人格组织[14,26]。
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版本的STIPO 显示出良好的评分者信度、同时效度和区分效度,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范围分别为0.72 ~0.97[27]、0.89 ~1.00[28]、0.82 ~0.97[29]。因此,对STIPO 维度的评定被证明是可靠的。在DSM 系统中,STIPO 表现出良好的结构效度:人格障碍患者在各个维度的人格组织水平均明显低于非人格障碍者[28]。同时,STIPO 被证明与LPFS 有良好相关性[22]。此外,STIPO是一个有理论基础的评估工具,提供了一个全面的人格功能评估[29]。但STIPO 的题量大、评估用时长,Clarkin等[26]新开发的STIPO-R 在题量上进行了精简。英文版STIPO-R 的信度、效度研究已经完成,中文版本STIPO-R正在研究中。
4 总结
回顾DSM 系统关于人格障碍的评估与诊断发展历程,DSM-1 正式提出人格障碍的诊断;DSM-3 提出多轴诊断策略、类别诊断标准;DSM-5 提出AMPD。AMPD强调了人格障碍的共同因素(人格功能损害水平)和病理性人格特质,表明了人格障碍诊断和评估新的发展方向。AMPD 提出的对人格功能损害水平的评估,弥补了此前DSM 系统在这方面的空缺,对应的评估工具为LPFS。APMD 在多维特质模型的基础上,强调了病理性人格特质的5 个维度。这5 个维度与正常人格特质具有连续性,可以看作其负性变异。AMPD 中针对人格特质的评估工具为PID-5。基于Kernberg 人格组织模型的人格障碍评估工具STIPO 被证明与LPFS 有良好的相关性,能较为准确、全面地评估个体人格功能水平。这些新的模式与评估工具与目前DSM 系统中人格障碍分类诊断标准相比,已经有本质上的变化。如何在应用新模式的同时保持诊断的连续性无疑会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目前开发的人格障碍评估工具,如PID-5、LPFS、STIPO 等,在中国标准化的研究还有进一步的空间,值得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M]. 张道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35-766.
[2] Grant BF, Hasin DS, Stinson FS, et al. 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disabilit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J]. J Clin Psychiatry, 2004, 65(7): 948-958.
[3] Coid J, Yang M, Tyrer P, 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in Great Britain[J]. Br J Psychiatry, 2006, 188: 423-431.
[4] Lenzenweger MF, Lane MC, Loranger AW, et al. DSM- Ⅳ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J]. Biol Psychiatry, 2007, 62(6): 553-564.
[5] Piedmont RL, Sherman MF, Sherman NC, et al. Using the five-factor model to identify a new personality disorder domain: the case for experiential permeability[J]. J Pers Soc Psychol, 2009, 96(6): 1245-1258.
[6] Morey LC, Berghuis H, Bender DS, et al. Toward a model for assessing level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in DSM-5, part Ⅱ : empirical articulation of a core dimension of personality pathology[J]. J Pers Assess, 2011, 93(4): 347-353.
[7] 孙青青, 丁锐, 陈图农. DSM 系统中人格障碍诊断的新进展[J]. 医学与哲学(B), 2018, 39(11): 75-79.
[8] Hopwood CJ, Wright AG, Krueger RF, et al. DSM-5 pathological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J]. Assessment, 2013, 20(3): 269-285.
[9] Hopwood CJ, Good EW, Morey LC. Validity of the DSM-5 levels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scale-self report[J]. J Pers Assess, 2018, 100(6): 650-659.
[10] Bender DS, Morey LC, Skodol AE. Toward a model for assessing level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in DSM-5, part Ⅰ : a review of theory and methods[J]. J Pers Assess, 2011, 93(4): 332-346.
[11] Wright AG, Thomas KM, Hopwood CJ, et al.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SM-5 pathological personality traits[J]. J Abnorm Psychol, 2012, 121(4): 951-957.
[12] Sharp C, Wright AG, Fowler JC, et al. The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pathology: both general (‘g’) and specific (‘s’) factors?[J]. J Abnorm Psychol, 2015, 124(2): 387-398.
[13] Ferrer M, Andión Ó, Calvo N, et al. Clinical components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personality functioning[J]. Psychopathology, 2018, 51(1): 57-64.
[14] 李雄, 吴明霞, 张爱华. 基于克恩伯格人格组织理论的心理测量工具的述评[J]. 中国校外教育, 2014(3): 46-48.
[15] Hentschel AG, Livesley WJ. The General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GAPD): factor structure, incremental validity of self-pathology, and relations to DSM-Ⅳ personality disorders[J]. J Pers Assess, 2013, 95(5): 479-485.
[16] 丁锐, 陈图农, 孙青青. PID-5 人格问卷与大五模型的关系及其应用[J]. 医学综述, 2018, 24(24): 4894-4898.
[17] Krueger RF, Derringer J, Markon KE, et al.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a maladaptive personality trait model and inventory for DSM-5[J]. Psychol Med, 2012, 42(9): 1879-1890.
[18] 眭爱萍, 陈图农, 韩瑜. DSM-5 人格问卷(PID-5)在中国大学生样本中的初步应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 25(4): 560-565.
[19] Zimmermann J, Altenstein D, Krieger T, et al. The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of self-reported DSM-5 maladaptive personality traits: findings from two Germanspeaking samples[J]. J Pers Disord, 2014, 28(4): 518-540.
[20] Bo SN, Bach B, Mortensen EL, et al. Reliability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DSM-5 pathological traits in a Danish mixed sample[J]. J Pers Disord, 2016, 30(1): 112-129.
[21] 眭爱萍. DSM-5 人格障碍多维特质模型在中国样本中的应用:信效度和临床应用[D]. 南京: 南京医科大学, 2017.
[22] Preti E, Di Pierro R, Costantini G, et al. Using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for DSM-5 level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rating performed by inexperienced raters[J]. J Pers Assess, 2018, 100(6): 621-629.
[23] Morey LC, Bender DS, Skodol AE. Validating the proposed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severity indicator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J]. J Nerv Ment Dis, 2013, 201(9): 729-735.
[24] Zimmermann J, Benecke C, Bender DS, et al. Assessing DSM-5 level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from videotaped clinical interviews: a pilot study with untrained and clinically inexperienced students[J]. J Pers Assess, 2014, 96(4): 397-409.
[25] Zimmermann J, Böhnke JR, Eschstruth R, et al.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investigating criterion a from the alternative model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DSM-5[J]. J Abnorm Psychol, 2015, 124(3): 532- 548.
[26] Clarkin JF, Caligor E, Stern B, et al. Manual for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Revised (STIPO-R) [EB/OL]. [2019-08-04]. http: //www.borderlinedisorders.com/structured-interview-of-personality-organization.php.
[27] Stern BL, Caligor E, Clarkin JF, et al.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STIPO):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s in a clinical sample[J]. J Pers Assess, 2010, 92(1): 35-44.
[28] Doering S, Burgmer M, Heuft G,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STIPO)[J]. BMC Psychiatry, 2013, 13: 210.
[29] Hörz-Sagstetter S, Caligor E, Preti E, et al. Clinician-guided assessment of personality using the structural interview and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of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STIPO)[J]. J Pers Assess, 2018, 100(1): 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