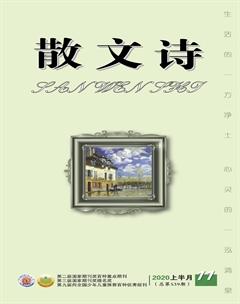时间的渡口(外二章)
张永波
时间像一个渡口,总有一些船只来来往往。
那些越聚越多的人群,仿佛最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的道理,井然有序,为生活让出了通道。
船开了,渡口人流散去……
海阔天蓝间,一心向善的人们,站在风浪中,扬起信仰的白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安放着宽容的钟声。一缕缕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目光,喜欢观赏冲浪的风、弄潮的波涛。
也有人在岸边垂钓,时间的线越放越长,有时收回一个惊喜,有时收回一朵涟漪,有时收回一天晚霞。
时间偶尔狡黠,时常会脱钩。有人岸边闲坐,看春水拉高时间的腰际线。转眼秋水一瘦,就露出了时间的伤疤。白云苍狗,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
也有人闲云野鹤,独坐舟头,把斜阳余晖披在身上,任一条鱼穿梭梦中。还有人卷起裤腿和袖子,摸著石头过河。时间回旋,多少人,将在彼岸再一次碰头。
时间有声也无声。转瞬间,人生这块水漂石在河面跳跃了几下,就不见了身影。
一条河流淌的不都是传说
请允许一朵迟到的百合花,赶上春天。允许一棵狼毒草,举着草原的火把,照亮蛮荒的彊域。逐草而居的部族深知点燃一堆篝火,不仅仅是为了取暖,他们被烘烤的苦乐年华,会像篝火一样浪漫,像叮叮咚咚的额尔古纳河水,学会了浪迹天涯……
在此其间,我循规蹈矩,凡事小心再小心。我喜欢和风习习,喜欢暴风之后的片刻宁静,喜欢和空中大雁一起保持队形,用身体书写的“人”字,召唤远方。
允许漫山遍野的韭菜花,演绎飞天的情愫。它们有决心登上兴安岭,哪怕化作冷硬的石头。当从山巅溢过来的霞光,像一棵棵倒立的樟子松,将身影投在河流里,惊起三两声狗吠,炊烟就从毯房上,弯弯曲曲地爬到空中。牧归的汉子打马奔来,把套马杆举过头顶,像轻轻举起的命运……
允许一只苍鹰说出草原的辽阔。允许羊群细细咀嚼芳草的风情。允许我把岸柳深藏胸中,清晰地阅读着,为大地记录一段小小的光阴。
落 日
只有水在流,风在吹。
群山苍茫。晚霞满布。
远方。落日。风起云卷,离别时的辉煌。苍林如海,背影沧海桑田。
浑圆。一种恩宠。
有人喊山,有人喊水。
有人喊朝阳,有人喊落日吗?
云水之上,苍茫之外,落日像一口井,挂在故乡村头,拎上来,落下去。落下去,又拎上来。
多少年了,日子也是这样,拎来拎去。
人,漂着的浮萍。
想起浮萍,总想起小时候受到惊吓后,那个替我喊魂的人。想起唢呐、锣鼓和哭声。
山冈上。所有声音消逝后,仍有人,与落日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