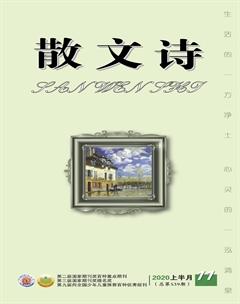草木人间
蔡兴乐
菜 花
常走进娘的菜地,渐渐地发现,蔬菜们大多会开着黄色的小花小朵。
比如西红柿、小白菜,比如浑身带着刺的黄瓜、棚架上正荡着秋千的丝瓜,还有大朵大朵花开金黄的南瓜。
还有一些蔬菜的花虽不是黄色,骨朵的形状却如会飞的蝴蝶。
比如紫蝶般的豆角花、豌豆花、萝卜花。
娘说,那耀目的黄色和彩蝶一样的形状,为的是尽可能多地吸引蜜蜂和蝴蝶光顾,那这小小菜地该是多么热闹呀。
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还是半大小子的我信以为真。
后来从课本上得知,吸引更多的蜜蜂和蝴蝶来,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传花授粉,以便更好地坐果和繁衍后代。
娘那时当然也知道这些,只是故意逗我玩罢了。
真可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野麦子
野麦子虽然头顶一个野字,却不与那些狗尾巴草、铁链草、马齿苋们同流合污。
好像自家身体里流淌着的,也是那青青麦子的正宗血统。
有麦苗茂盛的地方,笃定也会有野麦子的身影。
一株野麦子,只把自己的家,小心翼翼地,选择在一片朝阳的麦地里。
刚出苗的野麦子,与大麦小麦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即便经验丰富,娘也很难区分。
直至到了快要抽穗灌浆的时节,差不多一夜工夫,野麦子们,就会蹿出麦苗一大截来。
鹤立鸡群的野麦子,总是尽可能多地,享用雨露的滋润与阳光的抚摸。
当那些籽粒饱满的大麦小麦们,高昂着骄傲的头颅时,野麦子却只能垂下松散干瘪而又细长的穗子。
像是在感恩,更像是在表达某种难以言说的愧疚。
桐 花
泡桐花开了,开在这人间的四月天。
泡桐花开了,满树满枝淡紫色的小喇叭,鲜亮地挂在老屋的前后,让这春夏之交的分水岭,仿佛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早起的姐姐,正对镜梳妆,粉粉的脸蛋,比那一朵泡桐花还要妩媚。
原来,她要去约会心仪的恋人。
泡桐花落了,每一朵仿佛都是无奈的叹息。
得了绝症的善祥老爹,要用这棵百年老桐树,好给自己打一口寿棺。
泡桐花落了,再也不见满树满枝淡紫色的骨朵。
我花开花落的分水岭,也再次回归本该属于它的平静。
爱与恨,都该珍视,或者予以宽恕;生与死,也要泰然处之,或坦然接受。
艾 草
姐姐大我五岁,出生時恰逢十年不遇天灾。老屋外正茂盛着的几株艾草,也便顺手成为了姐姐的乳名。
娘说姐姐是花朵的香气、青草的命。
如同草字头姓氏的我,本也就是一株草,一株艾一样的草,开不出红硕的花,结不出金黄的果。
而一旦离开家乡分水岭,无论走到哪里,仿佛都是无根的浮萍,一辈子流浪他乡。
也罢。
就用这握笔的手,握住一柄锄头,握住瓦蓝铮亮的镰刀。
与艾草般苦命的姐姐一道,把农历里的小日子,打理得既风调雨顺,又宠辱不惊。
芝 麻
由于土地稀少,产量又不高,在家乡分水岭,芝麻便成为极少见而又金贵的作物。
娘往往会在岭坡朝阳的菜地旁,专门给芝麻划上一块领地。
得到娘的悉心呵护,一株青青的芝麻苗,在不经意间,就超过了白菜的高度。
芝麻开花的季节,清风拂面,阳光正好。三两朵白云,总会把分水岭的蓝天,给擦拭得一尘不染。
几只蝴蝶也会赶在我的前头,飞临娘的芝麻地。
芝麻们则会用小小的洁白的喇叭花,完成一句闪亮的农谚。
在不大的分水岭,在娘的菜地旁,一株芝麻的小小幸福,总是如此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