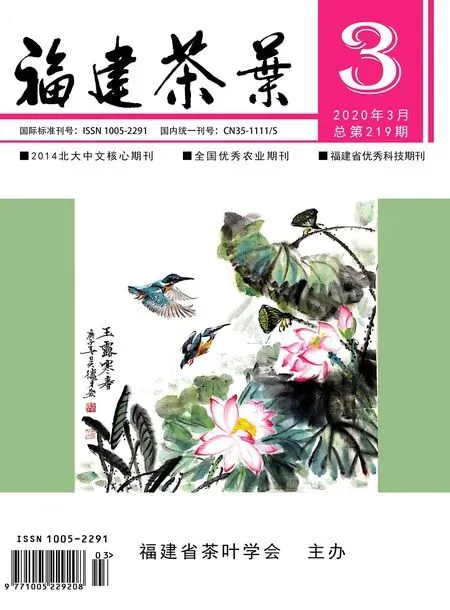中外BIT在港澳特区的适用问题
——以“谢业深案”和“世能案”为视角
沈奕灵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1 问题的提出
“一国两制”之下,港澳特区经中央政府授权可以在某些领域单独对外缔结条约1,由此产生了在港澳特区单独对外缔结条约的领域内,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条约是否可以适用于港澳特区的问题2。对此,港澳《基本法》做了原则性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港澳特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港澳特区”。3简单来说,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国际条约不应当适用于港澳特区,除非有特别情况。然而,香港“谢业深案”和澳门“世能案”未采纳上述规定,前者仲裁庭通过扩大中国-秘鲁BIT中“投资者”的适用范围,认定了中国-秘鲁BIT适用于香港特区4;后者仲裁庭则依据“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5,认定中国-老挝BIT适用于澳门特区6。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认定与中国国内法预期相悖,加上BIT本身适用的特殊性,这引发了中外BIT应如何适用于港澳特区的问题。
2 国际条约在港澳特区适用的基本制度
中国根据“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对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条约在港澳特区的适用做了特别规定,既有坚实的法理依据作支持,也有在不同层面的国内法上制定相互照应的规则制度。讨论这些基本制度有助于更好地分析中外BIT在港澳特区的适用问题。
2.1 港澳特区的对外缔约权
一个地方实体能否成为国际条约的缔结主体,或者说是否有对外缔约权,从根本上讲应该看国内法是否给予其必要的授权,因为条约的缔结适用国际法,但缔约机关的资格则取决于有关国家的国内法。7香港、澳门回归后,其对外缔约权主要是通过《宪法》、港澳《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葡联合声明》)授权和确立的。
首先,中国政府是以1982年《宪法》第31条为依据谈判和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第31条确定了特别行政区的设立8;其次,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分别在1984年和1987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两个声明确立了港澳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以独立名义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外签订协议9;再次,在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之后,全国人大分别在1990年和1993年分别通过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重申并进一步说明了港澳特区的对外缔约权10。由此可见,关于港澳缔约权现行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宪法》;第二,《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第三,《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11因此,在讨论港澳特区对外缔约和国际条约适用的问题时,应当从其法律渊源入手。
2.2 国际条约在港澳特区的适用规则
香港、澳门的回归方式和特区的高度自治性,决定了国际条约在港澳特区适用的特殊性,结合历史进程,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12:
首先,多边条约在特区的适用。中国政府分别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夕照会联合国秘书长,阐明可适用于特区的多边条约,照会中涉及的国际条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为条约当事方可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条约的当事方、并决定于回归之日起适用于特区的条约,包括三种情况:一、回归之日前适用于港、澳的;二、属于外交、国防类或根据条约的性质和规定必须适用于国家全部领土;三、回归之日前未适用于港、澳,但已决定自该日起适用于特区。第二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澳回归时尚不是条约的当事方,但已于回归前适用于港、澳,并决定于回归日起继续适用于特区的条约。13
其次,过渡期缔结的双边条约在特区的适用。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分别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其职责涉及对适用条约的制度安排。14关于双边条约,原英国延伸适用于香港的双边条约全部停止适用;在过渡期间,中英两国政府通过联合小组协商同意,香港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同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谈判和缔结相关领域的双边协定,这些协定于回归之日起可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区,关于澳门也有类似规定。15
最后,港澳回归后,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在特区的适用。核心问题是,中央政府和港澳特区平行行使对外缔约权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是否能适用于港澳特区。对此,港澳《基本法》做了规定16,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没有排除在特区适用中央政府缔结的双边条约的可能性,但决定权在中央政府;第二,中央政府须在征询特区的意见后,才决定是否将双边条约适用于特区;在征求特区政府意见之前,中国缔结的双边条约不适用于特区,而非自动适用于特区。17因此,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不当然地适用于港澳特区,除非经过特别程序。
此外,中外BIT作为双边国际条约的一种,也应当遵从上述规定。但是,国际投资协定有其特殊性,通常具有非常明确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受保护的“投资”或被保护的“投资者”必须位于其中一个缔约国的领域内,被保护的自然人也需要缔约国一方的国籍。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港澳特区的投资者拥有中国国籍,符合大多数BIT中投资者的定义,但实际上中外BIT不是当然适用于港澳特区,这又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3 “谢业深案”和“世能案”带来的司法实践冲击
3.1 案情简介
3.1.1 “谢业深案”
“香港居民谢业深诉秘鲁政府案”是第一个涉及中外BIT是否能适用于香港的ICSID案件。谢业深是一位香港特区居民,出生于中国福建,父母均为中国公民。谢业深在秘鲁投资了一家工厂,2007年他向ICSID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声称秘鲁当局征收了他在秘鲁的工厂,依据1995年中国-秘鲁BIT请求赔偿。2009年仲裁庭做出管辖权裁决,认为中国-秘鲁BIT适用于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居民。
3.1.2 “世能案”
世能公司是一家在澳门特区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在老挝进行投资。2012年世能公司依据1994年中国-老挝BIT,以老挝政府违反了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征收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等为理由,向荷兰海牙常设仲裁庭提起仲裁。当事双方协商后,将仲裁地点设在新加坡并适用2010年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
老挝政府认为中国-老挝BIT不适用于澳门特区,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2013年仲裁庭作出有关管辖权的裁决,认定中国-老挝BIT适用于澳门特区。2014年老挝政府依据新加坡《国际仲裁法》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请求撤销仲裁庭裁决,并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表明中国-老挝BIT不适用于澳门投资者的新证据:两封信函。第一封是2014年1月7日老挝外交部致中国驻万象大使馆的函件,内容为老挝政府主张中国-老挝BIT不适用澳门特区,并寻求中国政府意见;第二封2014年1月9日中国驻万象大使馆的回函,大使馆肯定了老挝政府的主张,认定中国-老挝BIT不适用于澳门特区。2015年新加坡高等法院一审裁定,撤销“世能案”仲裁庭的裁决,认为中国-老挝BIT不适用于澳门特区。但2016年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判决认为,中国-老挝BIT适用于澳门特区并决定撤销高等法院的判决。
以上两个案子有其共同点,第一,申请人都来自于港澳特区;第二,作为仲裁基础的BIT均为港澳回归前中央政府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第三,都认定中外BIT适用于特区。其不同点在于认定适用的路径有所不同,“谢业深案”仲裁庭首先考虑的是BIT本身对投资者的定义,认为申请者具有中国国籍,属于合格投资者,因而适用该BIT;“世能案”仲裁庭则通过解释BIT的空间适用效力来确定其是否适用于澳门特区。18下面会重点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认定适用路径。
3.2 争议分析
这部分将紧密围绕“中外BIT在港澳特区的适用问题”,选取案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3.2.1 “谢业深案”
仲裁庭认为,当前需要作出决定的是申请人是否有资格依据中国-秘鲁BIT,将其在秘鲁的纠纷提交到ICSID中心进行仲裁,为此,判断该BIT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是没有必要,也是仲裁庭不会分析的。19仲裁庭根据中国《国籍法》第4条20和中国-秘鲁BIT中对投资者定义21,认定谢业深符合该BIT的合格投资者。此外,仲裁庭还发现,《ICSID公约》和中国-秘鲁BIT中并没有排除该BIT对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特区居民的适用。22最终裁定谢业深可以援引中国-秘鲁BIT。
仲裁庭认为没有必要判断中国-秘鲁BIT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是因为本案的投资在秘鲁,这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只需要判断投资者是否符合该BIT的要求即可;其逻辑在于,某一投资者能否援引某一BIT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该投资者是否具有母国的国籍;二是该投资者所在地是否在该BIT的领土适用范围内。23笔者认为,仲裁庭回避了中国-秘鲁BIT适用香港特区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一国两制”制度的复杂性,通过解释BIT的空间适用效力难以信服。
有学者认为,条约中“投资者”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存在“条约边界移动规则”,因此,1995年中国-秘鲁BIT中有关投资者的定义并没有包括香港特区居民的意思,彼时的《国籍法》并不适用于香港,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并不包括香港居民。24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谢业深并非中国-秘鲁BIT中的“投资者”。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这种解释方法太过于机械化,“条约边界移动规则”本来就是适用于条约的,所以按照上述思路,考虑条约中“投资者”所包含的内容应首先考虑《国籍法》中的规定,再考虑《国籍法》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区。实际上,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8条和附件3的规定,《国籍法》自回归之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区25,那么最终结果依然是谢业深属于中国-秘鲁BIT中的“投资者”。
3.2.2 “世能案”
本案的核心是解释中国-老挝BIT的空间适用效力,即是否适用于澳门特区这一领域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中国-老挝BIT文本并没有对协定的领土适用范围作出任何规定。
第二,中国国内法的角度,主要涉及《中澳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前者属于双边条约,仅拘束于缔约双方;后者属于国内法,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当事国不得援用其国内法的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中国中央政府在信函中援引《澳门基本法》是不相关和不可接受的26。
对此,有学者进行反驳。第一,解释条约并不等同于履行条约。中国作为双边条约的缔约一方表达自己对条约意思的理解,这一理解与其国内法相一致,并且得到缔约对方的明确肯定和接受,这是条约解释的正常状态,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条约的顺利履行,但解释本身不是履行。第二,第27条在此处并不适用,因为在本案中需要履行条约的是老挝而非中国,老挝并未试图援引其国内法来规避条约义务。
第三,条约法的角度,主要涉及“条约边界移动规则”。仲裁庭和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9条关于条约的领土范围的规定,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条约边界移动规则”是隐含在第29条中的一个规则,也被认为是国际习惯法规则。同时,第29条中的例外情况,即“条约表示不同意思”和“另行确定”,本案中不存在。此外《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15条关于条约的国家间继承,也有类似规定。
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首先,澳门的回归不属于领土继承。基于不平等条约的领土割让自始无效,中国一直拥有对澳门的主权;其次,“条约边界移动规则”是否属于习惯国际法不确定。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以“争议各方共同认为”27以及“所有专家均接受”28来证明条约边界移动属于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完全不满足法律确信和一贯的国家实践这两个条件;最后,存在第29条中的例外情况,老挝政府提交的两封信函作为双方的嗣后协定,即“另经确定”。
关于两封信函,上诉庭认为老挝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中所表达的立场与在所谓关键日期之前的立场相冲突,故不可接受。29有学者认为,老挝政府自始主张中国-老挝BIT不适用于澳门,这一立场从未改变,提交的所有证据皆为证明这一立场,并不存在冲突。
3.3 成因探索
中外BIT适用于港澳特区的争议原因有三个。
3.3.1 直接原因是中外BIT文本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港澳特区
大多数中外BIT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港澳特区,也没有意图显示其不适用于港澳地区。再者,也未在BIT审查的第一个10年到来之前对该问题进行明确。30
3.3.2 中国关于国际条约的适用缺少统一标准
我国没有对条约在国内适用方式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样,我国也未对在国内予以直接适用的条约的判断标准做出一般性指导规定,而是针对不同的条约和不同的领域,由相关法律分别作出规定。这样的缺陷在于,各部门法各自为政,规定互不统一。由于没有统一的原则性标准用以判断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中国各部门法的规定实质上构成了对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情形的罗列,无法穷尽所有情况。
3.3.3 中国关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缺少宪法性规范
中国没有对国际条约的适用进行统一规范,《宪法》也未对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等级效力作出说明,因而在冲突发生时缺少明确规定。
3.3.4 国际投资仲裁庭优先适用国际法规则
国内法与国际法在港澳特区适用中外BIT问题上有所冲突,中国《宪法》、港澳《基本法》及《联合声明》均对此明确了态度及立场,但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国内法的两部《基本法》并不具有修改或者优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在近些年的国际仲裁案例中,仲裁庭已近乎形成一种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共识。
4 中外BIT在港澳特区适用的思考
4.1 中外BIT的空间适用效力
首先应当明确,中外BIT是否适用于港澳特区和港澳特区投资者能否援引中外BIT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世能案”涉及的是第一个问题,即中外BIT在港澳的空间适用效力,“谢业深案”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投资者和投资所在地的适格。从上述讨论中可以发现,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复杂,更加难以说明;但仅讨论投资者和投资所在地的适格,又可能产生中外BIT可以被港澳投资者援引的结果,这实际上是违背中国国内法的规定。因此,中外BIT在港澳特区适用的问题仍存有较大争议,可能会继续带来相关司法实践的问题。
4.2 中外BIT的解释
4.2.1 解释顺序和方法
中外BIT也应当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1)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即条约用语、上下文、目的和宗旨、通常意义以及善意解释,来解释条约。另外,该公约第32条对条约解释的补充资料作了规定,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由此推断,应当先考察条约约文,文本不清楚时,再联系上下文。该公约第32(2)条规定,“上下文”除包括条约约文外,还包括条约序言及附件、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以及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的任何文书。因此,两国间就有关BIT所发出的外交信函可作为条约用语的上下文部分,其对于条约的解释也是有帮助的。“世能案”中上诉庭否认了中国-老挝外交信函的作用,此做法是不可取的。之后,再考虑目的和宗旨、通常意义以及善意解释。
4.2.2 第三方的解释权
“谢业深案”和“世能案”均涉及到第三方机构对另外两方缔约的条约进行解释,在投资条约条款的解释过程中,可能未虑及缔约国对投资仲裁的“同意”,或者违背缔约国国内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31“世能案”中,上诉庭无视中老外交信函对中国-老挝BIT的作为嗣后协定的说明,剥夺了缔约方在BIT下的解释权,这可能违反了中国法律(包括中国宪法、法律和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第三方机构在对BIT进行解释时,应严格遵循上述条约法有关条约解释的规定,审慎行使自己的解释权,并应对BIT缔约方的解释权予以充分的尊重。缔约方也应尽可能地提供相关材料,例如嗣后协定和实践、条约的筹备工作和缔约情况等,以此充分地支持自身的解释内容。另外,第三方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属于投资仲裁审查的问题,本文不予以讨论。
4.2.3 对投资者的保护
国际投资仲裁庭倾向于投资者的保护,并优先适用国际法。外国投资者了解外国有关投资的国内法是比较困难的,要求外国投资者依据一国国内法来判断BIT的适用似乎也是不合理的。BIT文本作为最重要的规则内容,应当予以首要考虑。对BIT文本不明确的地方,在选择国际法来解释的基础上,也应当合理考虑国内法的规定。但目前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投资者的保护,优先适用国际法的方式来看,东道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防止仲裁庭进行扩大解释,应尽量在BIT文本中明确重要规则,形成统一、系统的BIT文本。即使BIT文本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BIT缔约国应加强国际法层面的依据,例如上文提到的嗣后协定和实践。
4.3 重新审视中外BIT适用的国内法规定
“谢业深案”和“世能案”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考,进一步要求重新审视中外BIT适用的国内法规则。第一,国内法预期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不一致,可能会有更多司法上的冲击;第二,两案的申请人为港澳特区居民,援引中外BIT维护自己的权利,证明了中外BIT确实有利于维护港澳特区居民的权利;第三,虽然港澳特区有权对外缔结BIT,但实际上的数量很少。因此,需要修改中外BIT部分条款,明确其在港澳特区适用的规则。
5 总结
中外BIT文本对港澳特区的适用是不明确的,其中,BIT的适用问题分为BIT的空间适用效力和对“投资者”、“投资”的定义来确定BIT的适用对象和范围,这是应当区分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较为复杂,但通过分析中国国内法可以确定,除非有特别情况,中外BIT不适用于港澳特区。这种认定规则与国际法上对条约适用的解释,即“条约适用于一国全部领域内,除非有特别情况”,相违背。在中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不明、国际法适用缺乏统一规则的情况下,难以援引上述国内法来确定中外BIT在港澳特区的空间效力;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仲裁庭保护投资者,优先适用国际法。此外,中外BIT的繁多和港澳对外缔结BIT的稀少,不利于港澳投资者的保护,更加需要重新审视中外BIT文本对适用港澳特区的规定,建议应明确其适用。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6条,单独对外缔结条约的领域包括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
2.本文所称条约的“适用”专指相关国际条约在特区是否具有可适用性,是否约束特区,而非指国际条约如何在特区得到具体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或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澳门的需要,在征询澳门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澳门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情况和需要授权或协助澳门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与其有关的国际协议适用于澳门。
4.Tza Yap Shum v.The 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
5.《维也纳条约法》第29条
6.Sanum Investments Ltd v.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PCA Case No.2013-13).
7.邓中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及有关问题》,《法学评论》1993年第2期。
8.1982 年《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9.《中英联合声明》第3条第2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10款进一步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中葡联合声明》第2条第2款和第2条第7款做出了类似的规定。
10.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3条和第14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香港基本法》第151条进一步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澳门基本法》第13条、第14条以及第136条做出了类似的定。
11.张磊,《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 —以修订我国〈缔约条约程序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
12.戴瑞君,《中国缔结的双边条约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 —兼评“世能诉老挝案”上诉判决》,《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就多边国际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事项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7年第39号,第1688-1718页。另见https://treaties.un.org/pages/HistoricalInfo.aspx?clang=_en#China Note 2 and Note 3
14.《中英联合声明》第5条及附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声明:为求本联合声明得以有效执行,并保证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中葡联合声明》第4条及附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为保证本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一九九九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在本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将根据本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15.戴瑞君,《中国缔结的双边条约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兼评“世能诉老挝案”上诉判决》,《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
16.《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或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有关国际协议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和澳门的需要,在征询澳门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澳门的国际协议仍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情况和需要授权或协助澳门政府作出适当安排,使其他与其有关的国际协议适用于澳门。
17.戴瑞君,《双边国际条约适用于港澳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1月10日第005版。
18.别良辉,《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对港澳投资者的适用——从“世能案”和“谢业深案”两起投资仲裁案谈起》,《仲裁与法律》第135辑。
19.Tza Yap Shum v.The 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Spanish)(previously posted un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removed for inaccuracies),para.68
20.中国《国籍法》第4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
21.“投资者”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是指: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拥有其国际的自然人;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22.Tza Yap Shum v.The Republic of Peru(ICSID Case No.ARB/07/6),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Competence(Spanish)(previously posted unofficial English translation removed for inaccuracies),para.69
23.别良辉,《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对港澳投资者的适用——从“世能案”和“谢业深案”两起投资仲裁案谈起》,《仲裁与法律》第135辑。
24.别良辉,《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对港澳投资者的适用——从“世能案”和“谢业深案”两起投资仲裁案谈起》,《仲裁与法律》第135辑。
25.香港《基本法》第18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附件3: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下列全国性法律,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
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命令》附:国徽图案、说明、使用办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26.Sanum v.Laos,[2016]SGCA 57,Judgment,para.114.
27.Sanum v.Laos,[2016]SGCA 57,Judgment,para.47.
28.Sanum v.Laos,[2016]SGCA 57,Judgment,para.58.
29.Sanum v.Laos,[2016]SGCA 57,Judgment,para.112,114.
30.易在成,朱怡然,《港澳投资者适用中外BITs问题研究——以“谢业深案”与“世能案”为视角》,《际商务研究》2018年第2期。
31.黄世席,《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及投资条约解释的公正性——基于“Sanum案”和“Yuko案”判决的考察》,《法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