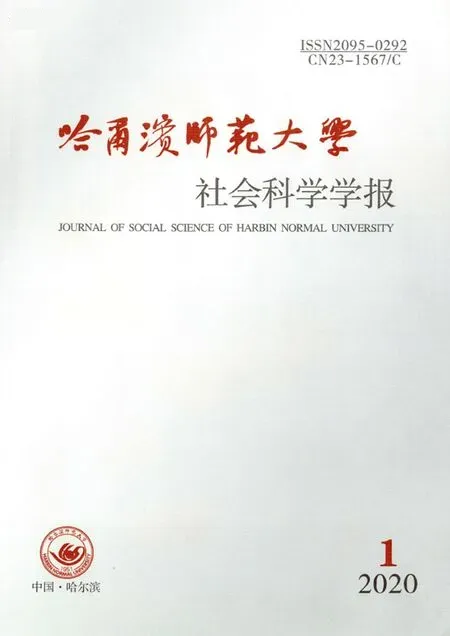《曹植甄后传》与日本学界的“古诗”及建安文学
[日]栗山雅央
(西南学院大学,日本 福冈 814-8511)
① 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其“甄皇后”项只收录《塘上行》一篇而已。
一
木斋教授最近出版的新著《曹植甄后传》,根据曹植与甄后相恋的立场来分析各种作品,提出了对“建安文学”的新见解。如他在序文中所言:“可以说,到这一本诗传,才是这一研究的总结和最后果实——写完这本书之后,关于十九首和曹植甄后恋情关系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可以宣告完成。”[1](P18)可见这部著作是作者本人相关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曹植甄后传》基于木斋教授所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2],重新考察了建安诗,尤其是作者认定为曹植与甄后二人所创作的那些作品。据于他的看法,曹植的诗、赋、乐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属于与甄后相恋制作;而后代视为徐幹所作的《室思诗》、班固所作的《咏史诗》等,也都是曹植所创作的。一般认为,甄后留下的作品仅有《塘上行》一篇①,但木斋教授把许多无名氏诗歌或“古诗”都看作甄后之作,又将若干种“古诗”看作曹植之作来加以考察。木斋教授持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
《曹植甄后传》的内容构成,是采用“传记”方式来分析每个阶段曹植所处的地位、个人境遇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据此考察曹植所作诗歌的内容旨趣。本书共十八章,从“曹植的青少年时代”(第一章)开始,叙述了曹植与甄后的相恋过程(第二至第六章)、他们度过“幸福时光”(第七章)而终于迎来“离别时光”(第八章)。其后则叙述从东汉建安末年到曹魏黄初四年这四年间的事情(第九至第十六章),包括“甄后赐死,曹植待罪”情节。最后叙述太和年间曹植去世及其后曹植集的编撰情形(第十七、十八章)。从这一结构可以看出,本书最注重的就是从建安末年到黄初四年这一时期,焦点则在于曹植与甄后之间的恋爱关系。
在本书中所写曹植生平的每一阶段,包括青少年时期(第一章)、建安九年(第二章)、十六年(第三章)、十七年(第四、五章)、十八年(第六章)、二十一年(第七章)、二十四年(第八章),公元220年(第九至第十一章)、黄初二年(第十二至第十四章)、三年(第十五章)、四年(第十六章)、太和六年(第十七章)、直到死后(第十八章),都以大量文学作品来考察曹植甄后之间的相恋情形。而值得注意的就是作者将向来不归于曹植、甄后名下的作品认定为他们二人所作,以此来描绘出他们之间恋情的发生、成立与终结。其所论及的此类作品如下:
曹植的作品:《今日良宴会》(第四章)、《涉江采芙蓉》、《上邪》(第五章)、《西北有高楼》(第七章)、《回车驾言迈》(第十章)、《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第十一章)、《兰若生春阳》《庭中有奇树》(第十二章)、李陵《有鸟西南飞》(第十四章)、《青青陵上柏》(第十七章)
甄后的作品:《全汉诗》所收入的无名氏《古歌》(第三章)、《步出城东门》《江南可采莲》《有所思》(第五章)、《上山采蘼芜》(第六章)、《陌上柏》、宋子侯《董娇娆》、班婕妤《怨歌行》(第七章)、张衡《同声歌》、李陵《陟彼南山隅》、李充《嘲友人》、李陵《良时不再至》、苏武《黄鹄一远别》《结发为夫妻》《烛烛晨明月》《双凫俱北飞》(第八章)、李陵《晨风鸣北林》、李延年《羽林郎》《古八变歌·章华台》《迢迢牵牛星》《明月皎夜光》、曹丕《燕歌行》(第十章)、李陵《烁烁三星列》《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第十一章)、苏武《童童孤生柳》、曹植《闺情》、徐幹《室思诗》《冉冉孤生竹》《种瓜东井上》《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第十二章)、曹植《西北有织妇》《古绝句》(第十三章)、《行行重行行》(第十四章)、《孔雀东南飞》(第十六章)
一览可知,这些作品包括《古诗十九首》及李陵、苏武诗等脍炙人口的名作。例如,作者对所谓“苏李诗”的理解如下:“苏李诗应始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二月,终结于黄初元年岁末,其中具有双重之政治背景和情爱背景。其政治背景,主要是曹操临终前后所带来的政治变局,由此带来曹植、甄后之间关系的巨变。此一组诗写作于曹操死前的送别之作情意绵绵,而写作于翌年秋季之后的诗作,则透露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1](P155)这一看法,完全是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来展开的。作者对其他作品的研究,也是采用同样的逻辑。另外,作者将大量诗歌都归为甄后所作,这点尤其令人瞩目。如其所自言:“首先震惊我的,是甄后居然写了如此之多的五言诗,而且,写的如此精彩,如此感人!与其说,古诗‘旧疑是建安陈王所制’,不如说,主要是甄后的作品。曹植是甄后五言诗写作的开蒙者和指导者,甄后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自己的生命呼喊,化作了五言诗饱浸血泪的诗。”[1](P340)可见作者对甄后诗歌的评价相当高,这一点与向来的建安文学研究完全不同。
另外,木斋教授对曹植辞赋的理解也十分特殊。《洛神赋》隐喻曹植对甄后的爱恋之情,这是已为人所熟知的一种说法。木斋教授也在第六、第八章中做了全面的分析。然而不仅如此,木斋教授还把其他辞赋作品也都纳入了曹植、甄后的恋爱话语中。在他看来,《感婚赋》与《愍志赋》等作品系作于建安九年曹丕与甄后举行大婚之际,抒发了曹植对甄后婚礼的感慨(第二章);《离思赋》诗曹植在建安十六年“写给甄后而无从奉达的内心表白”[1](P56)(第三章);《登台赋》是曹植在建安十七年登上铜雀台时表现对父亲曹操的敬爱之作,而《橘颂》同样是写给甄后的作品(第四章);《九咏》是“曹植首次向甄氏挑明心迹的细节记录”[1](P76),表现出“历经大苦之后的痛彻心新扉的伤痛”[1](P78)。此外,从曹植、甄后相恋的视角出发,作者特别注意到《芙蓉赋》,认为:“曹植一生赋作甚多,咏物之作也甚多,但歌咏花树之作,仅有《芙蓉》一篇而已……即可知道此赋并非真正歌咏芙蓉,而是歌咏喜爱芙蓉的人——甄氏。……这应该是两个人之间首次身体上的突破。”[1](P79)将《芙蓉赋》理解为隐喻曹植与甄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作品(第五章)。《神龟赋》以乌龟为例,表现曹植对曹操的孺慕之情(第六章)。《蝉赋》是“到建安二十二年春天,经过醉生梦死的疯狂之后,曹植开始产生沉重的负罪感”[1](P137)之际所作,而《节游赋》也是通过邺城出游情形来展现曹植本人内心的苦恼(第七章)。《蝙蝠赋》与《鹞雀赋》两篇都是黄初二年“甄后赐死,曹植待罪”时的作品,因为甄后被赐死与文帝曹丕的皇后郭氏有关,所以前一篇是“诅咒郭后,发泄怒火的寓言体作品”[1](P253),而后一篇则是“暗喻曹植死里逃生的事情”[1](P254)之作。从木斋教授的这些观点,可知他是把曹植的种种赋作都看作透露出曹植本身某种情感的“抒情赋”之作。虽然《离思赋》《登台赋》确是“抒情赋”,但《芙蓉赋》《蝙蝠赋》《鹞雀赋》一般认为是“咏物赋”,因此从来很少人试图从中窥探曹植的情感。作者这种希望从作品中积极探寻曹植个人情感的尝试,值得我们注意。
最后,笔者希望提出的一个疑问点是,木斋教授把《北堂书钞》的记载看作“铁证”之一,这似乎仍可商榷。的确,在《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乐部可以看到“曹植诗云弹筝奋逸响,新声好入神”的说法;不过这在同卷八十二礼仪不中的表述却是“古诗,今日良燕会……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把《今日良宴会》的句子看作曹植诗的材料仅有《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而完全不见于其他文献,故这一点似乎仍有慎重考虑的必要。
二
那么,最近日本学界对“古诗”及“建安文学”的研究情况如何呢?特别值得介绍的一部著作,就是柳川顺子的《汉代五言诗歌史的研究》[3]。作者对“古诗”同样提出了十分独特的新说,与今年的“古诗、建安文学”研究多有不同。一般认为,《古诗十九首》的成立时期是东汉后期,包括建安时期。上文已经提及,木斋教授对“古诗、建安诗歌”的看法十分特殊,不过他对此也是部分认同的。而柳川的看法却与此完全不同,她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部分是较早形成的,她把它叫作“第一古诗群”,这批古诗早在东汉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理由在于,《诗品》所言“陆机所拟”的“古诗”,以及见于《玉台新咏》的枚乘《杂诗》都十分特殊,其篇目大多重合;而东汉前期傅毅的《舞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东城高且长》诗句的影响。据此,她进一步推断“第一古诗群”的命名人就是傅毅。
将成立比较早的一批古诗看作“第一古诗群”来进行考察,这一点是柳川顺子的研究中最为独特之处。不过追根溯源,清末的吴汝纶就曾经于《古诗钞》中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柳川顺子实际上是基于他的观点来展开了进一步论述的。
那么,柳川顺子所说的“第一古诗群”包括《古诗十九首》中的哪些呢?在她看来,“陆机所拟”的十三首就是“第一古诗群”,篇目如下:《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会》《迢迢牵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兰若生春阳》《青青陵上柏》《冬城高且长》《西北有高楼》《庭中有奇树》《明月皎夜光》《驱车上东门》。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今日良宴会》《迢迢牵牛星》《青青河畔草》等木斋教授认定为曹植与甄后所作的作品。柳川顺子基于“第一古诗群”这一概念,认为这批作品中也有早晚之别。最早期的几首有如下特征:在内容上,并没有涉及宴席本身,但诗中所描绘的离别悲哀之情,却能给宴席增添离愁别绪的气氛;在形式上,诗歌句数也很有规律,要么就是八句或十句,要么就是其两倍的十六句或二十句,这是因为,古诗最早应该与音乐节奏有密切的关系,其诗歌句数受到音乐的限制。她认为,八句、十句的古诗是一种基本模型,而其两倍句数则是节奏重复的形态。另外,笔者认为这反映出“第一古诗群”中最早的一批作品,其作者应是西汉后宫中的宫女。
与此相对,成立比较晚的几首则有如下特征:在内容上,诗中大抵描写对人生无常的慨叹,还出现了对东汉首都洛阳的描写。此外,诗中直接描绘了“宴席”的场面,而且受到“死亡”意识的影响,所以后期的“古诗”里可以看到陵墓等关于死亡的意象。在形式上,这批诗作没有句数的规定,作者认为这反映出这批诗作已经脱离了音乐的影响;其作者则是参加宴席的男性文人。
从各种方面来看,柳川顺子的看法都跟以前对《古诗十九首》的看法截然有异。柳川顺子认为从最早几首到最后几首之间,经历过几个阶段,她把最早几首看作“原初的古诗”,包括如下六首: 《兰若生朝阳》(描写失去爱情的郁闷)、《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这两首都描写守寡女人的寂寞)、《迢迢牵牛星》(描写牵牛织女的悲恋)、《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这两首的主题都是折下植物送给远方的情人以示爱)。“原初的古诗”的特征包括如下三点:一是音乐性,原初的古诗与音乐的节奏相关。这一点在诗歌句数的规律里可以看到。二是娱乐性,古诗是在宴席的轻松气氛中成立的。因为“原初的古诗”就在宴席中被创作的,所以没必要再在诗歌里直接描写出宴席的情形。三是女性性,她认为“原初的古诗”作者的后宫中宫女与男性知识分子同处于宴会之间,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诗歌素养。
在“原初的古诗”产生后,受到“原初的古诗”影响的诗歌群也逐渐发展形成了,就是《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上两首都描写对人生短促的慨叹或对现实生活的焦躁感)以及《明月皎夜光》(描写友情的崩坏)等三首。这三首都表现对时间逐渐推移的慨叹,明确表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悲哀感,这意味着这群诗歌的作者不是女性而是男性。而且,柳川顺子认为这些“古诗”质变的背景跟宴席有关,因为这些男性在宴席间与她们相处,也很容易接触到“原初的古诗”。
最后,产生了“第一古诗群”的最后一批作品,就是《青青陵上柏》(描写人生短暂与洛阳街区、酒宴与参加酒宴的人的心情)、《今日良宴会》(描写为了摆脱不得意处境而参加宴席的人)、《驱车上东门》(通过描写陵墓表现人与死后世界之间的关系)等三首。这三首都直接描写宴席本身,这一点跟“原初的古诗”完全不一样。
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柳川顺子认为,从东汉中期以后,才开始产生并非由“无名氏”,而是由当时的知识分子(张衡、崔瑗等)所创作的五言诗。东汉前期的五言诗大部分都有匿名性,而东汉中期以后,五言诗的匿名性渐渐消失了,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特殊的情况,就是“第一古诗群”的成立。另外,她认为所谓“苏李诗”也在东汉中期才出现。过去一般认为“苏李诗”的成立时期与建安年间很接近,但柳川顺子的看法比较新鲜。因为曹植《送应氏》、徐幹《室思》等都受到“苏李诗”中不止一首的影响,所以她认为,再比建安年间要早不少的某一时期,“苏李诗”就已经成立而流传下来了。
那么,柳川顺子对“建安文坛”的理解又如何呢?她认为“建安文坛”就是汉代五言诗的真正嫡派。这是因为,汉代五言诗本来就是在宴席间产生的娱乐性文艺,而建安文坛也是在宴席间进行了他们的创作活动,但到了建安时期,已经摆脱了汉代五言诗所有的“匿名性”。汉代五言诗与建安诗歌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它们的主要题材都是“宴会诗”与“闺怨诗”。最后,她对“五言诗”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五言诗之所以被视为文人的文学形式,乃是东汉末期,特别是建安时代的发展,尤其曹操的个人存在使然。
此外,柳川顺子还提到陆机与阮籍的创作活动,因为跟本文内容无关,此不赘述。
三
如上两节所述,木斋教授与柳川顺子的看法都十分特殊,不过他们之间只有一部分共通,而其他部分则多有不同。他们对所谓“古诗”等“汉代五言诗”与“建安文坛”之间的关系,看法就不一样。如柳川顺子在其著作的序章中所论:“五言诗的开端就是个谜。距其源头还比较接近的六朝末期(六世纪)人,就已经对其情形含糊不详了。此外,对于汉末(三世纪初)建安文坛所主导的五言诗潮流,向来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可是在建安诗之前,还有所谓《古诗十九首》等汉代无名氏所写的五言诗群。建安诗人当然是基于对这些诗群的意识才创作出了新的文学,如此看来,这一文学的新潮流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建安文坛的位置,是其后延续一千数百年的五言诗史的开端;然而其本质,却必须要立足于这一汉代五言诗歌史才能理解。”[3](P4)而木斋教授却有如下理解:“其次,使我震惊的事情,是我将汉魏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乐府诗、连同曹植诗赋、甄后诗,将这些诗作几乎是一网打尽式地整合在一处,并将这些作品依照其作品本身显露出来的诸多信息,安置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位置、背景位置,这些作品几乎是严丝合缝地站立了起来,组合成为一个完整、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就像是一个历史拼图,它们回到了自己凹凸不平的位置上,展示了曹植甄后的一生行踪。”[1](P340)可知柳川认为“汉代五言诗”与“建安文坛”之间具有前后继承的关系,而木斋教授却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同时关系,这是他们最大差异所在。具体来说,他们对李陵、苏武等所谓“苏李诗”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柳川顺子认为“苏李诗”在东汉中期已经成立了,这是因为“苏李诗”受到“第一古诗群”等“古诗”的影响,而对建安文坛有显著的影响。比如,曹植《送应氏》其二,“愿得展嬿婉”的“嬿婉”受到苏武诗“欢娱在今昔,嬿婉及良时”的影响,她认为“嬿婉”二字本来是对女性的形容,在受苏武诗句的影响之后,《送应氏》中的“嬿婉”才开始有宴会气氛的内涵。而“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得“嘉会”二字,在李陵诗“嘉会难再遇”与苏武诗“嘉会难两遇”里也可以看到。这个词语几乎不见于其他作品。另外,徐幹《室思》的“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应该受到苏武诗的“相见未有期”与“中心怆且摧”两句的影响,但是木斋教授的看法不同。如上文所述,所谓“苏李诗”的大部分都是曹植与甄后在建安二十四年到黄初元年间所写的,因为这些诗歌的种种内容跟当时的曹植、甄后的情况可以相互印证。
虽然木斋教授与柳川顺子的看法似乎完全不同,不过他们的观点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女性。木斋教授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为甄后所作,而柳川顺子也认为“第一古诗群”中的最早一批作品是西汉的后宫女性所作。他们的思路完全不同,但这一共同点值得注意。在木斋教授对《古诗十九首》的分类中,曹植的诗歌有《今日良宴会》《涉江采芙蓉》《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兰若生春阳》《庭中有奇树》《青青陵上柏》,甄后的诗歌有《迢迢牵牛星》《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來》《冉冉孤生竹》《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行行重行行》。而柳川顺子认为后宫女性所作的诗歌如下:《兰若生朝阳》《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其中的《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青青河畔草》等三首,他们都看作女性之作。关于《迢迢牵牛星》,木斋教授是从“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迢迢”来判断,“远貌,则牵牛为远,而织女为近,自然是应该女人写给男人,这是从这一句来看,从全诗语气来说,更应为女性所作”[1](P196)。而柳川顺子依据东汉班固《西都赋》中的“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判断西汉时期的后宫内有牵牛织女之像,当时的后宫女性应当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像。因此,她认为这些女性能够理解牵牛织女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写作。此外,木斋教授认为,《明月何皎皎》“语气分明,应为甄后劝告曹植早些返回之作。全诗皆近似口语,吻合于甄氏口吻”[1](P241),《青青河畔草》“为甄后黄初二年暮春初夏之际思念曹植所作。《青》诗与甄氏之死的背景吻合”[1](P242)。而柳川注意到其中“纤纤”二字在燕赵之地流行(《韩诗》),而“娥娥”二字在长安一带流行(杨雄《方言》),而当时燕赵佳人频繁入到后宫,故认为汉代后宫是这两者发生联系的一个节点。他们都看重女性作者的存在,这是过去的研究中罕见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探讨。
总而言之,尽管木斋教授在其著作中宣称“关于十九首和曹植甄后恋情关系的研究,就我个人而言,可以宣告完成”[1](P18);但从日本的最近“汉代五言诗”以及“建安文学”的研究进展来看,汉代以前“古诗”研究非但不是“完成”,反而可以说,将基于这些新鲜的看法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余论
最后,介绍日本学界“建安文学”研究中特别值得参考的两部著作。一部是铃木修次的《汉魏诗研究》[4],另一部是伊藤正文的《建安诗人及其传统》[5]。这两位学者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受到吉川幸次郎的影响。《汉魏诗研究》虽然已是大约半世纪以前的著作,但至今仍未失去其高度的学术价值。下面通过目录来简单介绍其内容:第一章“楚歌、新声考”,从《楚辞》开始进行分析“楚风”诗歌的特征,特别是《安世房中歌》、西汉皇帝所作诗歌、西汉贵族所作诗歌、东汉文人(梁鸿、班固、崔骃、王逸、徐淑等)所作诗歌等,并以《郊祀歌十九章》、李延年《歌》为中心,对“新声”诗歌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乐府、古歌、古诗考”,第一部分主要围绕“乐府”机关、“乐府”作品、“短箫铙歌”与“相和歌”等对“乐府”加以考察;第二部分则针对“古诗、古歌”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木斋教授与柳川所论的《古诗十九首》及所谓“苏李诗”。他对《古诗十九首》的理解如下:“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成立,最稳妥的观点应该是如刘勰早已指出的,认为其乃‘两汉之作乎’吧。我们并没有证据足以声称其中完全不包含西汉之作。不过同时也有必要考虑,这些作品果真是在某个时期,由某个作者进行的特定创作吗?这些作品作为活的文艺而流行于民间,又是在哪个时期呢?如果对作品的各种要素加以分析,说不定有些部分确实反映出了西汉时代的因素。然而,如果《古诗十九首》并非由特定诗人所特定创作的作品,而是由非特定的诗人创作,流动性地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定型了的话,那么,要将这些作品的形成时期推定为某一特定时期的这种思考方式,就多少是有些无理的了。”[4](P316)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生成,他的这种见解应该说是比较稳妥的。此外,铃木修次还谈到“汉魏民间诗歌中反映的文学感情问题”,主要从“无常感”“享乐感”“非情感”“流氓的悲哀”“别离的哀愁”等视角分析。第三章“建安诗考”,则从“建安诗”的评价及具体时代的分析开始,考察建安诗的具体题材与赋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从“集团性创作活动”视角比较诗赋之间的差异。最后,他讨论了三曹七子及其他作家的创作活动情况,而最详细的就是与木斋著作有关的曹植的创作活动。总之,铃木修次是从先秦到三国、从《楚辞》到建安诗的脉络上,展开了他独到的研究。
此外,伊藤正文的《建安诗人及其传统》,则是在作者去世后,由其弟子编纂的一部论文集。因此,虽然这部著作出版于2002年,但其中大部分论述却与《汉魏诗研究》撰写时期大致相当,同样至今保有其学术价值。这部著作的关注角度与铃木修次完全不同;铃木修次是从先秦开始讲到建安,而伊藤正文则是从建安开始讲到唐代,故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建安文学给南朝诗歌、唐代诗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一篇“建安诗”,主要对《岩岩钟山首》及王粲、刘桢、魏武帝乐府还有曹植进行了分析。其研究手法是首先通过作品来考察诗人传记,包括“王粲传论”“王粲诗论”以及“刘桢传论”“刘桢诗论”等,然后又基于诗人传记来分析其诗歌作品,二者相辅相成。他对曹植的理解大致如下:第一,曹植诗歌极其复杂多彩而规模庞大;第二,其诗歌细致入微而颇有流动感;第三,曹植用“兴”的手法来创作诗歌[5](P212-214)。第二篇“南朝诗”,包括对鲍照与陶渊明的考论。对鲍照进行分析时,也采用上述“传论、诗论”的方式来进行详细的考察。第三篇“杜甫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通过分析杜甫诗,指出到了盛唐时期才开始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出现对建安诗人、鲍照及谢灵运等的文学价值的评论。第四篇“盛唐诗”,则是基于上述分析,考察盛唐诗人对汉魏六朝至初唐时期作品的评价。伊藤正文认为,在唐代文学批评史上,盛唐时期一向较受忽视,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较少。因此,他主张重视作品的资料性,以补充散文资料的不足。此外,他还指出杜甫的诗论与其他盛唐诗人的诗论有所不同,反而与盛唐中唐之际文人所展开的诗论有契合之处,将杜甫看作跨越两个时期的文人。
铃木修次、伊藤正文二人都是日本学界汉唐诗研究的名家,惜乎其研究在中国学界尚未得到充分了解,故本文特作介绍,希望有助于学界的参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