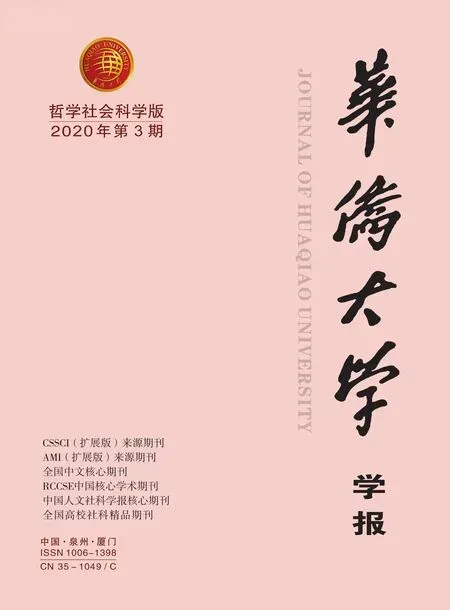权威主义的深层透视:弗洛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诊断
○许秩嘉 姜延军
犹太裔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宗教思想遵循着“应然—异化—健全”的理论逻辑框架。与传统的宗教概念的范畴不同,弗洛姆对宗教作了广义的界定,即认为凡是对人的“存在两歧性”(1)在弗洛姆看来,人的理性打破了动物生存性存在的“前自然和谐”,使人自诞生以来就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远离动物的生存形式,不断获得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另一种是返回子宫,回归原始和谐,寻求动物性的踏实安全。弗洛姆扬弃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人性论,将之从狭义的性角度发展为广义的社会文化角度,将人性定义为自由与孤独交织的矛盾存在,即“存在两歧性”矛盾。问题予以回答、给个体以定向框架和信仰目标的思想行为体系即是宗教。弗洛姆考察了历史上的多种宗教形态,并根据不同宗教的内在精神中是否潜藏着人道主义的宗教情感与救世精神、是否符合人性发展规律而将之区分为健全的宗教和异化的宗教,即“人本主义宗教”(2)在广义的宗教界定下,“人本主义宗教”的界定标准也与传统的有神论宗教不同。在弗洛姆看来,早期的佛教、道教,以赛亚、苏格拉底、斯宾诺莎的教导,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种倾向,近代西方的“理神论”等都是“人本主义宗教”的例证,它们会拓展人的生命力量,使人摆脱外在的异化力量而回归自身、摆脱虚幻而回归现实、摆脱奴役而回归自治。“人本主义宗教”强调宗教救世精神,反对迷恋教条礼仪、权威神明等宗教形式,其本质是一种指向主观宗教态度而非客观宗教实体的人道主义文化信仰体系。与“权威主义宗教”(3)在广义的宗教界定下,“权威主义宗教”不仅包含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有神论宗教,也包含国家崇拜、种族崇拜、领袖崇拜、技术崇拜等“世俗宗教”,因为它们都试图以异化的方式回应人的“存在两歧性”矛盾,都有着让人逃避自由、丧失自我的虚幻特质,在心理学上拥有着与权威神明同样的迷幻作用。。作为“宗教异化”的必然结果,“权威主义宗教”的本质是人对“存在两歧性”矛盾的异化回应,它使人否定其内在的生命力量而将之投射于外在强力,在逃避自由的救赎等待中体验着受虐快感,牺牲自由来换取安全。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弗洛姆对“宗教异化”的审视与批判同样遵循着疾病诊断逻辑。通过对“宗教异化”的逻辑起点、病症表现及病理因由的诊断分析,弗洛姆系统掌握了“权威主义宗教”的生成演变路径,完成了对异化宗教的三维批判,为其进一步开展对“宗教异化”的人本主义救治奠定了基础。
一 “宗教异化”的逻辑起点
弗洛姆坚持“共同的人性”的客观存在,即认为人有一种按照其本性的要求发展的倾向。由于人性有其天然的客观需求,健康的人格不单单体现在人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社会,更在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性的客观发展规律。这种对客观人性的悬设决定了其对宗教的理想原型与应然状态的设定——理想的宗教必然符合客观的人性发展规律,促进人的生命的拓展与生长;相反,异化了的宗教必然是人性的天然需求实现受阻的产物,违背人性的发展规律。因此,人性论是弗洛姆批判“宗教异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宗教变革思想的逻辑归宿;正确地认识人性是其开展宗教批判、进行宗教变革的前提。
在弗洛姆的理论视野中,人性不是善恶本体,但它具有或善或恶两种潜能。其中,善作为“第一潜能”展现了人的自发创造性,构成了人的“生命力量”;恶是人的“第二潜能”,第一潜能实现受阻时才会激发人的第二潜能:“破坏性是丧失生命力的结果。”(4)[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冯川主编,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第233页。唯有生长条件无法满足善的潜能的需求、无法实现生命的成长发展,邪恶才会产生。弗洛姆否定人性的善恶实体论,而选择从人类面临的“存在两歧性”矛盾出发来理解人性。面对自由与安全不可得兼的“存在两歧性”矛盾,人需要不断了解和思考自己及所处的世界,将自己置于一个定向体系中寻求自我的生命位置,找到新的安全形式来补偿因自由而丧失的原始安全。这种人性的天然需求构成了形形色色情感的重要根源与人的精神动力源泉。作为一种定向献身体系,宗教信仰即是人对解决“存在两歧性”困惑的努力,人有着克服与自然分裂感的强烈宗教愿望:“宗教信仰的需求深植于人类的生存条件之中。”(5)[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44页。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一神论宗教,无论是“权威主义宗教”还是“人本主义宗教”,本质上都是解答“存在两歧性”问题的努力,所不同的仅仅是答案是否符合人性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有助于“第一潜能”的顺利实现,是否实现了自由与安全内在统一的“新和谐”。异化了的宗教,无论是神圣权威还是世俗权威,本质上讲是都以逃避自由的方式来回应“存在两歧性”问题,都以牺牲自由、退回“原始和谐”的方式换取安全,都是“第一潜能”受异化社会现实阻碍所激发的“第二潜能”的产物。弗洛姆将是否遵循人性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性“第一潜能”的实现作为判定宗教异化与否的唯一标准,在人性层面上展开了对“宗教异化”现象的初批判。
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抽象的人性论阶段,而是选择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分析人性的现实需要与人性异化的根源,实现了抽象矛盾的具体化与现实化,使人性成为了一个既受潜在本能牵引又受社会环境及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动态实现过程——由于具体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人性现实地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性格”,它是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中间环节。这种“社会—心理—存在本体结构”的人性论实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统一,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善恶人性论”与“反映人性论”的弱点。以此为基点,弗洛姆掌握了“宗教异化”的病症源头,进而在逻辑起点上建构起批判“宗教异化”的坚实基础,但也从根源上埋下了其理论的深层缺陷——从存在本体论结构出发的人性悬设将科学性从其历史观中剥离,造成了“人本—科学”天平的失衡。
二 “宗教异化”的病症表现
弗洛姆全方位地批判揭示了“权威主义宗教”使人在奴役与压迫中远离真实、丧失自我的人性异化现实,“宗教异化”的病症表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偶像神明让人在权威朝拜中丧失爱与理性
在弗洛姆的视野中,早期的基督教虽然是人本主义的,但随着教会组织经济与社会构成的变化,自其诞生一百多年后,基督教便丧失了为底层人民服务的性质,成为为罗马统治者服务的宗教。“教条发展了,一个变成神的人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个变成人的神的观念。父亲不应当再被推翻了;有罪过的不是统治者而倒是受苦的群众。攻击不再指向当局,而倒是指向受苦者本身。满足就在于父亲为他听话的儿子提供的宽恕和爱恋,同时也在于受苦的耶稣在继续作为受苦群众的代表的同时所具有的庄严的、父亲般的地位。”(6)[美]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页。随着父权原则的加强和母权原则的势弱,一神论宗教中的权威主义倾向不断增强,上帝作为偶像神明具有全知全能的绝对权威,信仰者的心理态度由爱与平等转变为畏惧与服从,“宗教异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通过对新教中的加尔文宗(7)加尔文宗,亦称“长老会”“加尔文派”,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是新教三个原始宗派之一。的分析与批判,弗洛姆具体剖析了异化宗教的精神特质。加尔文宗认为,人为了正视自己,必须彻底地鄙视自身的每一种品性,必须时刻保持谦逊才能抱有对上帝的真诚屈服:“加尔文在这里描述的那种经验:鄙视自己的每一种品性,由于为自身的贫乏所压倒而屈服于一种精神,乃是所有‘权威主义宗教’的本质,无论它是用世俗语言表达的,还是用神学语言表达的。”(8)[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孙向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此外,他还对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9)路德宗,又称信义宗,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于德国,标志着基督教新教的诞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路德宗的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王公贵族,其本质特征仍然是对家长式权威的屈服:“人不再得到教会和圣母的慈母般的爱,他必须独自一人面对严厉的上帝,只有完全顺从,他才能得到上帝的慈悲。”(10)[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5页。在路德宗的教义中,人是上帝的附庸,他的生死皆服务于上帝;人是否能够获得恩惠与膏泽取决于其以悲惨无能之感屈从于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程度。
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表层批判,而是以心理学视角剖析了人在崇拜偶像神明中丧失自我的深层心理动力过程。“权威主义宗教”使人将自己的爱与理性力量投射到具有神圣权威光环的上帝身上,进而使自己变得空虚赤贫:“偶像代表着以异己形式呈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11)[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第98页。此时,人只有通过上帝才能接近他自己,在崇拜上帝中与失去的自己相联系,在上帝的荣耀中寻回他丧失的丰富人性。然而,为了得到上帝的爱,人必须歌颂上帝的全能、贬低自己的无能、展现自身的无助。于是,人愈是称赞上帝就愈加空虚赤贫,愈是空虚赤贫就愈加感到罪恶,愈是感到罪恶就愈加朝拜上帝,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在“人本主义宗教”中,罪恶起源于反对自己而非反对上帝,罪恶的反应是接纳、包容与理解,罪恶的救赎是通过爱与理性摒弃对权威力量的虚幻依赖,获得自我实现;而在“权威主义宗教”中,罪恶起源于不服从权威而非违背伦理规范,罪恶的反应是堕落感、自责感与憎恶感,罪恶的救赎是通过完全的臣服和胆怯式的悔罪来获取权威的宽恕。在这种臣服中,人不再相信自己拥有理性与爱的力量,人与自己为敌并丧失了自我:“人真正的堕落是他的自我异化,他对权力的屈服,他对自己采取敌对的态度,即使是在崇拜上帝的外衣下。”(12)[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孙向晨译,第42页。
(二)世俗权威导致了人的感性狂热与理性瘫痪
“现今的偶像崇拜已经不是崇拜巴力(Baal,太阳丰饶之神)和阿斯塔蒂(Astarte,生育和爱情女神)的问题了,而是国家及其专制权力的神化、机器的神化、对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功的神化,而这个文明竟威胁着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13)[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孙向晨译,第88页。在弗洛姆眼中,国家及其专制权力的神化是权威主义世俗宗教根本表现,而法西斯主义又是这种神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它造成了现代人感性的狂热与理性的瘫痪:“如果我们想理解像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体系怎么会支配成千上万的群众,准备为‘我的国家,不管是对还是错’这个原则,牺牲他们的正直和理智,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定向中的这种图腾的宗教性质。”(14)[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第27—28页。在弗洛姆看来,法西斯主义是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中下阶层、失业官员和学生的造反运动,它以反犹主义的方式迎合并释放了中下阶层在潜意识中的嫉妒与义愤情绪,以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傲慢方式医治了德国群众在一战后受挫的民族自尊心;它虽然标榜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但其实质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通过分析古罗马皇帝凯撒的权威生成路径,弗洛姆进一步展现了权威主义世俗宗教形成的心理机制:“一个拥有至高无上势力的人是受到尊敬和崇拜的。尽管他奴役着我们,但他仍被认为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因为我们宁可‘自觉自愿’地顺从‘善良’和‘聪明’的人,而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无能为力地拒绝对那些邪恶的人的服从。”(15)[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4—165页。权力往往决定着人的自由和生死,奴役着人的肉体与精神。人虽然受权力的奴役,但出于维护自尊的合理化机制,人往往习惯于美化权力,对世俗权威产生半催眠式幻觉。在对国家、政党、领袖等强权的臣服中,个人将自己的内在力量投射给外在权力,于其中体验着施虐与受虐“共生关系”的快感,补偿了自由带来的孤独无依,却也丧失了主体意志。
弗洛姆反对国家崇拜,但并非反对爱国主义。事实上,爱国与国家崇拜的区别正如其在《爱的艺术》中所言的自私与自爱的区别一样。自爱与爱他人具有内在机理的融通性,自爱者必然具有爱人的勇气与能力,爱人者也必然懂得自爱。如果一个人只对自己或某个特定的对象付出爱与热情,而对其他人消极冷漠,那么这种爱不过是一种根植于依恋情愫的、泛化了的利己主义。相反,自私则公开排斥对他人的爱,自私者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竭尽全力从外界摄取利益与关爱,填补内心匮乏的自爱。因此,真正的爱国正如自爱一样,并不排斥对其他国家、对全人类的爱,反而会促进人类博爱情感的增长;但对国家的狂热崇拜却只会促使人贬低、排斥甚至憎恨其他国家与民族,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自我优越感,激发狂热的民族情绪,进而有利于集权专制领袖迅速建立起个人的畸形政治威信。
毫无疑问,弗洛姆对权威的批判是鞭辟入里的,但这种对权威一概而论的激进否定显然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忽视了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权威在凝聚国家意志、抵御外族入侵、提高社会组织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人类社会越来越高效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决定了权威主义生成的历史必要性与必然性。对权威主义“一棍子打死”的姿态本质上是人道主义学者们无力改变异化现实的幼稚呼唤,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言:“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三)“工业时代的宗教”将人降为资本与机器的奴仆
在广义宗教的框架下,技术与机器等人造之物成为了弗洛姆语境中现代人狂热崇拜的“工业时代的宗教”,它们作为“新的偶像”反过来奴役人、控制人甚至毁灭人:“这种新宗教的危害也就昭然若揭。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而成了技术的奴隶。一度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技术向我们展现出另一幅嘴脸,技术就像印度宗教里的迦梨女神,是毁灭之神,不分男女老幼都将成为贡献给她的牺牲品。”(17)[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162页。人将机器与科技奉为圣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作为机器操纵者的人类获得了像上帝般无所不能的虚幻满足。最终,被人创造且朝拜的机器和技术获得了自治性,脱离了人的控制,使人沦为自己亲手所造之物的奴仆。
对资本与消费的狂热崇拜也是“工业时代的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偶像崇拜的一种集体的、强有力的形式,我们发现了对权力、成功和市场权威的崇拜。”(18)[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第25页。消费方式与使用方式相匹配是符合人性的占有方式,然而,现实中二者却形成了完全分离的局面。消费往往带有了攀比财富、显示身份、填补空虚感等功能,使人对消费的渴求远远超出了其真实的需求。消费本应是具体的、有感情的,现在却失去了创造性与人情味,失去了作为一种过程体验的感性美;消费本应是人实现幸福的一种手段,现在却同样获得了自治性,成为了目的本身;消费成为了一种与真实自我相疏离的幻想活动,为人提供“幻想的满足”。人们贪婪地占有、无尽地吞噬,在对资本与消费的崇拜中丧失了美感与丰富性,朝着超出生命真实需求的虚幻方向越走越远:“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像一个大苹果,一大瓶饮料,一个硕大丰腴的乳头,我们则是吸乳者,永远在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在失望。”(19)[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第398页。
此外,毒品、酒精、性狂欢等都作为一种诱发短暂的狂喜甚至癫狂状态而成为“工业时代的宗教”的一种新仪式。人类在原始社会时虽已开始从自然中分离,但二者的距离并不遥远。人的视野仍局限于土地江河、动物植物的范畴内,因而只能通过动物图腾崇拜、佩戴动物面具等仪式来逃避自由,满足退回自然的欲望。随着人类与自然分裂的程度逐渐加深,“癫狂状态”作为一种逃避自由的新仪式也在现代社会得以普遍形成。人往往寄希望于毒品、酒精、性狂欢所带来的狂喜状态来消除与世界的分离感,获得合一的体验,但在短暂的狂喜体验消逝后,分离感却会更猛烈地袭来。此时,人不得不更高频率地求助于狂喜状态,因而陷入了无底洞般的恶性循环之中:“性融合蜕变成人为了摆脱分离强施于他的焦虑而做出的绝望挣扎,但结果却是分离感与日俱增,愈演愈烈,因为,除了在极短暂的时刻,没有爱情的性行为根本不可能填补人与人之间的鸿沟。”(20)[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第343—344页。
与对偶像神明与世俗权威的崇拜类似,“工业时代的宗教”同样让人依赖外在力量而非内在的本体力量来消除与世界的分裂感,因而使人最终沦为外在力量的奴仆,丧失了主体地位,离真正的自由越来越远。“工业时代的宗教”是“宗教异化”现象的当代病症。
(四)功利取向使宗教信仰在权力欲求中有名无实
弗洛姆认为,虽然基督教已成为西方普遍的宗教信仰,但这种信仰与皈依并没有深入人的精神内里,实现实质上的“基督教化”。因为,西方人的社会性格结构并没有因为对基督教的信仰而发生反现代性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情感依然是对教会与权力的屈服。他提出了“基督教英雄”和“非基督教英雄”两个概念。“基督教英雄”的典型代表是耶稣,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力的英雄。耶稣不使用暴力,不愿意去统治与占有,其最高目标是为人类献出生命。相反,“非基督教英雄”以统治、制胜、消灭、掳掠为价值指向,对他们而言,男人的价值就在于保持强力和获取权力的能力。由于“非基督教英雄”和人类的“男性理想”相吻合,西方的历史仍然是征服、贪婪和傲慢的历史,征服他人、战胜他人的欲望仍深植于现代人的社会性格之中。然而,在人类野蛮征服掠夺的过程中,在人类追随“非基督教英雄”的脚步之中,对“基督教英雄”的“信仰”可以缓解作恶的道德焦虑,进而纵容杀烧抢掠无尽剥削的行为:“人们有一种无意识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是为我们去爱的;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拯救,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对基督的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模仿。’”(21)[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第151—152页。对神的“信仰”成为了现实功利欲望的庇佑工具与世俗人心的安抚工具,缓解着人在掠夺征服中的道德罪恶感,纵容着人的现实欲望。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敬畏神灵,但他实际崇拜的却可能是神灵庇佑的现实利益。宗教成为了一件廉价的外衣,遮蔽着人对权力与征服的贪欲。
信仰本应源自心灵深处的信念,而非出于自我保护、祈求拯救或祝福的功利目的。信仰动机的功利化往往会使人失去内心的坚守与力量,将自己置于精神上的脆弱境地。功利取向使宗教信仰在权力欲求中丧失了作为信仰的核心要素,这成为了“宗教异化”的又一个突出的病症表现。
三 “宗教异化”的病理分析
在展示了“权威主义宗教”奴役人、压迫人的残酷现实后,弗洛姆进一步剖析了“宗教异化”形成的多种原因,找到了“宗教异化”的深层病理。“宗教异化”的生成原因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奠定了“宗教异化”的精神根基
“有太多的人害怕自由而宁愿选择幻觉。”(22)[美]弗洛姆:《生命之爱》,王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29页。偶像崇拜的基础不是特定的偶像,而是特定的人性态度;“宗教异化”的根源不在于被朝拜的对象,而在于朝拜者的性格结构中天然存在的渴望被统治、虐待、征服的潜意识。人在最初保持着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他不自由却拥有着天然的安全,正如未出生的婴儿与母亲的合一状态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婴儿逐渐从母体中分离出来,都开始了追寻自由却也难逃孤独的生命旅程。与自然、与母亲分离虽然为人带来了自由,却也使人丧失了曾有的温暖与无条件的安全。自由使人感到孤独、焦虑、茫然、无助,人在自由中失去了曾有的确定感和存在感。于是,人通过权威主义倾向、破坏性、机械化趋同等机制来逃避自由,以异化的方式来回应“存在两歧性”问题:“另有许多人在他们的生命的道路上继续推进,但他们依然不能把脐带完全剪断;他们对母亲、父亲、家庭、种族、国家、地位、金钱、神祗等仍有着共生性的依附;他们从未完全成为他们自己,从而也就从未完全诞生。”(23)[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第477页。人在特殊历史境遇下形成的逃避自由天性奠定了“宗教异化”的精神根基。
权威主义倾向是逃避自由的机制之一,它具有两种模式,即“受虐—施虐”共生关系:一是羡慕权威,通过臣服于权威来获取存在感,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焦虑和恐惧。在这种共生关系中,施虐者全知全能,受虐者渺小卑微;借助对施虐者的依附,受虐者无须做出选择、担当风险和责任;受虐者像仍未完全脱离母体的胎儿般残缺不全,但他不必忍受自由与孤独,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二是使自身成为权威,通过奴役他人的肉体与精神来展现自我力量,强迫他人变为自己的一部分,借此加强与外界的紧密联系,降低幽闭感,获得存在感,消除自由带来的孤独与不安:“虐待狂动力的本质便是由完全主宰他人而得到的快感。”(24)[美]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我相信人有实现自己的权利》,第76页。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上卑躬屈膝、对下耀武杨威,对外毕恭毕敬、对内欺凌施虐,他们通过这种两极反差来获得平衡感和存在感;有的人通过虐待动物或是虐恋、性虐待等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消解自己的无力感。在“施虐—受虐”共生关系的作用下,皈依宗教不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逃避困惑与焦虑;不是出于献身,而是为了寻求安全。
逃避自由的固恋情结深植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它与国家、种族、政党、市场法则等社会控制力量相结合,交织出一张包围孤独个体的巨大的网,使人在对安全与归属的渴求中被轻易地支配与奴役。“权威主义宗教”即是人类固恋情结在宗教领域的表达,人渴望通过狂热的偶像崇拜与权威依附来摆脱自由带来的不安,寻求生命的确定感。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构筑了“宗教异化”的精神根源。
(二)社会结构的父系转向注入了“宗教异化”的历史基因
约翰·巴赫芬(25)Johann Jakob Bachofen,瑞士人类学家和法学家,其最出名的著作为《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认为,人在进入父系社会前经历了一个母系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与母亲的互动关联在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对人类的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母权制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却依然可以在社会的很多方面发现其留下的深刻印记。弗洛姆继承和发展了巴赫芬的母权制社会思想,认为母权制社会的“母爱原则”与父权制社会的“父爱原则”在宗教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对立性地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母爱原则”的积极方面在于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与包容,消极方面在于无法培养人的独立性、责任感和纪律性;“父爱原则”的积极方面在于培养个体的纪律性、责任感与理性,消极方面在于钳制、服从与等级不公。健全的人应是“母爱原则”与“父爱原则”的统一,健全的宗教亦是如此——只沉溺于母亲的“无条件之爱”或只依赖于父亲的“奖惩之爱”,宗教就会只停留在早期,神就只是庇护一切的母亲,或是施行赏罚的父亲。
母系社会中女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神因而往往是保护一切、养育一切的伟大母亲形象。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结构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发展演变,宗教中的母爱原则逐渐被父爱原则替代,二者间越来越严重的失衡状态使人信奉的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从自然中拔根离去,摆脱了对慈母形象的神的依赖,开始崇拜代表理性、原则和法律的父亲形象的神。在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年间,在巴勒斯坦的摩西教形成之时、埃及的伊克拉顿宗教改革之时、印度和希腊的北方部族入侵之时,父权宗教得以普遍形成,进入权威主义与偶像崇拜的窠臼。但母爱原则没有彻底消亡,其始终以人道主义为表现形式与“权威主义宗教”进行着顽强斗争。
(三)合理化机制与社会无意识强化了“宗教异化”的心理动力
“精神分析探究的是思想体系是不是表达了它描述的感情,或者是不是隐含着相反态度的合理化。”(26)[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第48页。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认为,某人对某种陈述的真诚信念并非其信念真实性的充分证明;唯有借助对人的无意识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知晓,真诚信念的背后究竟是在追求“合理化”还是在诉说真实。弗洛姆同样用“合理化”概念来分析“宗教异化”的心理原因,并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发展为“社会无意识”理论。
在他看来,人们往往认为自己对权威的狂热膜拜是因为其认同偶像神明的光辉真理,但事实却往往相反,狂热崇拜不是其理性认同的结果,而是原因。人往往并不明晓其真正追随与笃信的究竟是什么,“自我”经常声称其“正式信仰”是对权威的理性认同与爱戴,却意识不到“本我”对权威的狂热依附情愫才是其真实的“秘密信仰”。合理化机制阻碍着潜意识真实的意识化,让人充分地相信自己的意识与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使人看不清自身宗教信仰的真实动机,因而强化了权威主义偶像崇拜的形成动力。而合理化机制生成的重要原因,是受奴役者自我安慰的主观意愿。在专制社会中,受压迫群众处于弱势的地位而充满恐惧,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为缓解自身潜意识中的愤恨感、无助感和屈辱感,必然倾向于将剥削者美化和神圣化。剥削者的形象越是高大神圣,自己所受到的专制和压迫越是容易得到释然。合理化机制使受压迫群众的自卑感在对神圣领袖的朝拜之中得到转移与消减,却造成了理性的瘫痪,使人在自我麻醉、自我欺骗中丧失了感知真实的勇气。
合理化机制导致了信仰者的无意识自欺,“社会无意识”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我们置身于黑暗中,我们之所以保持我们的勇气,是因为听见每个人和我们一样吹着口哨。”(27)[美]弗洛姆:《自我的追寻》,孙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在弗洛姆的理论中,“认同需求”是人性中固有的五种需求之一。认同需求既可以来自于实现创造性潜能所带来“自体感”,也可以来自于群体依附所带来的虚幻身份认同。人性中的“认同需求”与面对群体时的一致性压力让人不得不顺从权威,形成共同的盲从与迷失。人为了能够成为群体的一员,为了获得虚妄的身份认同,往往愿意冒生命的危险,放弃其爱与自由的权利。当个体的“白日梦”作为“共同幻想”而得到满足时,也就成为了真实:“但是,即使最不合理的定向,一旦为许多人共享,就会给个体一种与他人一致的感受和一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而这正是精神病人(28)在弗洛姆的理论语境中,“精神病人”往往泛指精神异化的现代人。丧失的。”(29)[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第28页。
(四)社会性格结构异化构成了“宗教异化”的核心要素
弗洛姆将精神分析的微观视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角相结合,在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机理之中引入了“社会性格”的中介概念。社会性格是力比多结构与社会经济形态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制约着意识形态的走向:“社会—经济结构、性格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三者是不可分的。”(30)[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第146页。因此,社会经济形态与人的力比多结构相互交织作用,共同塑造了人的社会性格,社会性格又决定了包含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异化了的宗教顺应了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结构,它既是社会性格异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加深了性格结构异化的程度,加重了人的精神残缺。
从社会性格理论出发,弗洛姆提出了“市场人格”的概念,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异化”的核心原因。市场人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在市场人格中,人将自身体验为一种“人格市场”中的商品;人关心的不是是否运用力量实现自我、增加生命价值,而是是否获得外界认同、增加交换价值;人的自尊不是基于稳定的“自体感”,而是基于不断变化的可卖性;人的最高目标就是全面适应,以便能够在人格市场中成为“抢手货”;人不再关心生活的意义,在商品化的自我售卖中丧失了自我体验的一致性,沦为外界目的的工具。
市场人格对人的精神异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交换突破了其作为经济手段的框架定位,成了目的本身。喜爱交换代替了喜爱囤积,交换本身即是一种目的,由此形成了现代人对商品与消费的依赖和崇拜,形成了“工业时代的宗教”。另一方面,交换式思维逐渐从非经济领域泛化到经济领域:恋爱成为了两个价码相当的人之间的利益互惠互换;参加晚会不是为了享受过程,而是为了同更高价值的“商品”交往,以便接近博得收益的机会;清晨的散步被视为一种健康的抽象投资,而非令人愉悦的具体活动;听一场音乐会常常被用是否“值得”他所付的钱来抽象地衡量……“市场人格”使现代人无法与具体的现实世界产生“普遍联系”,人们关心抽象的理性价值甚于具体的感性存在本身。“普遍联系”能力的丧失造成了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使人丧失了对生活、对生命的热情,人的生命越来越空虚。然而,人越是空虚越是沉迷于交换,越沉迷于交换越是空虚,因而日益陷入了孤立无援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情感淡漠、空虚无助的状态进一步提升了人在“存在两歧性”矛盾中的孤立无依感,增强了“逃避自由”的心理动力,扩大了“权威主义宗教”的生存市场,强化了“宗教异化”的心理基础。
(五)宗教与世俗权力交织构筑了“宗教异化”的现实力量
“所有伟大宗教的悲剧在于,一旦他们成为由一个宗教机构统治的巨大组织,就违背和败坏了自由原则。”(31)[美]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第65页。庞大的组织机构容易使宗教产生官僚主义倾向,迫使宗教向违背宗教理想精神的世俗利益一次次地妥协与投降,构成了“宗教异化”的现实原因。弗洛姆以基督教为例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早期的基督教是穷人们的精神革命。《旧约》中的先知质疑自己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早期的基督徒则质疑罗马帝国的道德合法性,因为它违背了爱和正义的原则。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封建秩序,随着天主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教会不再鼓励人们批判违反了爱和正义的世俗力量,转而号召人们接纳自己的现实处境、不加区别地支持现存政权。基督教日益成为了剥削阶级消除受压迫阶级反抗意志、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中,物质生产始终无法充分满足所有人的合理需要。由于资源有限,能够享受充足资源的人不愿同其他人分享资源,因而寻求暴力等物质力量来压制那些威胁其特权的人。然而,暴力并不能真正地使反抗者在内心臣服,为了让受剥削者不再使用武力反抗,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处境,必须有精神力量去压制他们的心灵。“权威主义宗教”即是剥削者进行精神控制的非暴力统治工具,它借助虚幻的希望来麻醉化地满足被压迫者的心灵与情感,阻碍受剥削阶层的心理独立,抚平他们的反抗斗志,使其对权威保持孩子般的温顺姿态,进而维持少数人的特权。由于在社会中得不到现实的满足,“幻想的满足”便成为了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补偿,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幻想的满足具有为每一种麻醉剂所特有的双重功能:对积极的现实变化,它们既是镇痛剂,又是障碍物。”(32)[美]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第14页。在世俗利益的诱导下,扩大了的宗教组织机构往往成为协助世俗权力安抚受剥削群众反抗情绪的思想武器。庞大的宗教组织和它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家庭、部落、国家的位置,人崇拜的不再是上帝而是宣称奉了上帝之名的团体。
四 弗洛姆“宗教异化”批判的批判性审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基础上,弗洛姆把异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体因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感到与自我疏离,形成了长期的精神病态化。“宗教异化”的本质即是偶像崇拜造成的人的精神异化,是人因偶像崇拜丧失主体地位而感到与自我疏离的精神状态。
在弗洛姆的宗教批判中,人的实践能动性及人的价值地位得到了高度凸显,但科学的物的逻辑却难以寻觅。虽然弗洛姆对权威主义的批判犀利深刻、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一针见血,但不难发现的是,这种激进的批判往往忽视了对权威主义存在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考量。如前所言,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权威不仅具有由生产组织方式集约化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具有提升社会组织效率与社会向心力的历史必要性:“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3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37页。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必须在个体与集体、自由与必然中寻求平衡,不能脱离相对谈绝对、脱离集体谈个体、脱离必然谈自由。弗洛姆为了矫正“左”的错误,为了挽救被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物的逻辑所压制的人的价值,无疑走向了将人道主义等同于个体至上的自由主义并视之为价值判断唯一标准的极端,无视科学的客观性维度的意义。弗洛姆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后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引导与戕害,但事实是,他本人也未能逃脱误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样命运,未能平衡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能动性逻辑与科学的客观性逻辑的关系,最终将“双重逻辑”割裂疏离,走上了右的道路,走向了乌托邦。“双重逻辑”的单向缺失决定了其历史观中科学性的缺失,致使其悬设了一个先于具体历史条件而存在的永恒理想人性模型——这种理想人性的存在构成了其“宗教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孕育着其思想的独特魅力,也埋下了其理论的根源性缺陷。
虽然弗洛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诊断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但也有值得我们汲取的养分。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始终用“应然—病态—健全”的逻辑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心理学视角使其实现了异化概念内涵的主观化与微观化转向。借助“社会性格”概念,弗洛姆力图在对社会经济形态与人的本能结构的相互作用中阐明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进而完成了对“宗教异化”路径的深层透视。心理学为弗洛姆理解宗教、理解人类社会开辟了全新视角,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宗教现状的内在本质提供了新的支点。
当前国际宗教世俗化进程浩浩荡荡,宗教极端主义风起云涌,宗教的网络化如火如荼,原教旨主义迅猛异常。纵然当代宗教现状千变万化,我们依然能够透过弗洛姆的理论框架把握这变化中的不变——宗教的持续复杂化从根本上讲是扩大了的精神异化与人性异化,它反映出现代人越来越严重的内在空虚与病态性格结构,反映出社会生产方式远远没有实现人道化的客观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异化现实加速了权威主义人格在更广泛人群中的落地生根,进而扩大了异化宗教的生存市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宗教现状。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亦是如此。不可否认,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已有极大的不同: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淡化,工人阶层收入大幅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看似极权主义及高压剥削的阴云逐渐散去,人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与解放。然而,借助弗洛姆的社会精神分析法我们依然不难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与劳动境遇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人依然处于各种外在力量的奴役之中,依然承受着性格结构异化的精神病态苦痛,权威主义人格与市场人格依然是现代人典型的性格特征。人虽然摆脱了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极权主义统治,但却陷入了新的“匿名的权威”的统治之中,依然难以对抗外在力量的奴役,无从主宰自己命运。因此,虽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在形式上产生了许多新的改变,但其高度异化的、极权主义的内在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日得不到实质的改变,权威人格就会持续生成,进而为各种新形式的奴役创造生存空间。日趋尖锐的性格结构异化与人的精神异化充分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远未达到其所标榜的健全与人道化。
弗洛姆批判了种种有神或无神形式的权威崇拜,批判了异化宗教对人的压迫与奴役,但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加速宗教的消亡,而是要在改变现代人的异化性格结构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合乎人性的“人本主义宗教”,挽救被启蒙运动全面抹杀了的宗教人本关怀。对弗洛姆“人本主义宗教”的理论蓝图与构建路径,笔者将另外行文阐释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