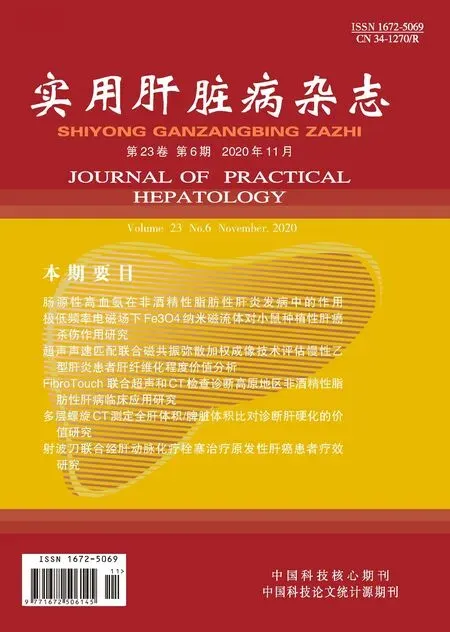胆汁酸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发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何胜夫 综述,汪余勤 审校
胆汁淤积是指肝内外各种原因导致的胆汁形成、分泌和排泄障碍进而导致胆汁不能正常进入十二指肠而反流入血的病理状态[1,2]。病程早期可无明显症状而仅仅表现为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GGT)水平升高。在4660例慢性肝病患者中,胆汁淤积发生率高达10.3%[3]。胆汁酸在该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胆汁酸是由胆固醇在肝脏内经过一系列生化反应而合成的两性分子,初级胆汁酸在肝脏合成后经胆管分泌入肠道,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合成次级胆汁酸[4],胆汁酸作为一种信号分子广泛参与人体内多种代谢及激素信号通路[5,6]。研究发现,将体外培养的肝细胞置于高浓度具有潜在毒性的胆汁酸中培养会诱导肝细胞凋亡[7]。在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升高[8]。在胆管结扎(bile duct ligation, BDL)小鼠,也能够检测到中性粒细胞的活化及其在肝脏的聚集[9],表明炎症反应是胆汁酸淤积时导致肝损害的重要因素。
1 胆汁酸循环及胆汁酸转运体
胆汁酸合成包括经典通路和非经典通路两种途径。经典通路是以肝细胞内质网中的胆固醇7-羟化酶(cholesterol 7-hydroxylase, CYP7A1)为主要限速酶催化发生;非经典通路则发生在巨噬细胞及其他组织中,以定位于线粒体的甾醇27A羟化酶(sterol 27A-hydroxylase, CYP27A1)和定位于内质网的氧甾醇和类固醇7-羟化酶(oxysterol and steroid 7-hydroxylase, CYP7B1)为主要限速酶发生的。在经典通路中,胆汁酸的合成受法尼醇受体X(farnesoid X receptor, FXR)负反馈调控[10]。胆汁酸在肝脏合成之后大部分通过肝细胞表面的胆汁酸转运蛋白-胆盐输出泵(bile salt export pump, BSEP)运输至胆小管,小部分胆汁酸可以通过分布在肝细胞的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MRP2)排泌至胆小管然后储存于胆囊之中。当进食过后,胆囊收缩将胆汁酸排泄至肠道,其中95%胆汁酸在回肠中通过小肠刷状缘细胞表面的Na+依赖的胆汁酸转运体(apical sodium 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 ASBT)以及位于小肠上皮细胞基底膜的有机溶质转运体和异源二聚体(organic solute transporter and Hhterdimer, OSTα/β)主动吸收至门静脉[6,11]。胆汁酸经血液循环到达肝脏后被肝细胞基底膜的胆汁酸转运体主动摄取,包括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a+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NTCP)、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OATP)家族[12]。其中,NTCP几乎负责摄取所有的结合性胆汁酸,并受核受体法尼醇受体X以及SHP(FXR/SHP)调控[13]。OATP主要负责摄取非结合性胆汁酸,其主要受核受体FXR、孕固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 PXR)等调节。胆汁酸循环中任一环节受损均可能导致胆汁淤积性肝损伤的发生。
2 胆汁酸并非通过其毒性直接诱导肝细胞凋亡
既往的观点认为,各种因素导致胆汁淤积时,高浓度胆汁酸是通过其固有的溶解细胞膜毒性作用而直接导致肝细胞调亡。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是将肝细胞置于高浓度次级胆汁酸中培养,然而在胆汁淤积患者体内,这些次级胆汁酸浓度很难达到上述实验水平[14]。随后,有学者提出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患者中,是由于胆汁酸诱导肝细胞凋亡[15],但是在BDL小鼠模型以及胆汁酸培养的体外人肝细胞,尚未发现肝细胞凋亡[16,17],表明胆汁酸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过程中可能是通过其他机制发挥作用的。
3 胆汁酸通过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损害
3.1 胆汁酸介导相关炎症因子表达进而诱导中性粒细胞浸润 在小鼠模型中可以观察到在BDL 6小时后肝实质坏死区域有中性粒细胞大量聚集,与肝细胞损伤的起始时间一致,并且该研究还发现中性粒细胞的浸润持续整个胆汁淤积病理过程[14,18]。相关实验发现将小鼠肝细胞置于200μM的牛黄胆酸(TCA,小鼠主要内源性胆汁酸)中体外培养,可显著刺激一系列细胞因子和黏附分子mRNA水平升高,包括CD1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MCP-1)、巨噬细胞炎性蛋白2(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2,MIP-2)等[18-21],并且有发现,胆汁酸诱导的炎症因子表达增加与NTCP有关,因此认为胆汁酸通过NTCP介导进一步诱导炎症因子表达上调[21],而在胆汁酸转运体NTCP缺乏的胆汁淤积患者中发现,尽管患者血清胆汁酸浓度很高,但其肝损伤却很轻[13]。将人肝细胞置于病理浓度(>50μM)的甘氨鹅脱氧胆酸(GCDCA)中体外培养,炎症因子,诸如MCP-1、CCL15、CCL20、CXCL1、IL-8等表达上调[7]。此外,在敲除炎症因子CD18或MCP-1基因后,研究者观察到虽然BDL小鼠血清胆汁酸浓度极高,但其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较对照组小鼠降低,并且肝细胞损伤也明显减轻[9,21,22]。同样的,研究者在TCA中培养的小鼠肝细胞中发现早期生长反映因子-1(early growth response protein 1 EGR-1)表达上调,EGR-1是一种转录因子,其可调节包括炎症因子在内许多基因的表达,并且当EGR-1缺陷时,胆汁酸介导的炎症因子及细胞黏附分子释放减少,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下降,肝细胞损伤明显减轻[7,23]。此外,研究者发现在BDL小鼠模型中,小鼠肝内皮细胞以及肝实质细胞中细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的表达明显上调,ICAM-1作为一种细胞黏附分子可以促进中性粒细胞向病变区域迁移,因此可诱导中性粒细胞在肝脏受损区域大量浸润,并且其表达上调强度与肝损伤程度相关[24]。细胞黏附分子ICAM-1和ERM蛋白(ezrin/radixin/moesin,埃兹蛋白/根蛋白/膜突蛋白)以及Na+/H+转换调节因子-1(NHERF-1,可以影响ERM以及ICAM-1的表达[25,26])形成的大分子复合物(ICAM-1/ERM/NHERF-1)在BDL小鼠肝脏中表达增加,他们认为该大分子复合物与BDL小鼠肝脏中性粒细胞浸润有关,而且在NHERF-1缺陷的BDL小鼠模型中,小鼠肝脏内中性粒细胞浸润显著减轻。并且他们证实NHERF-1缺陷的BDL小鼠较对照组小鼠的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低70%,并且其肝细胞损伤也明显减轻[26]。通过上述一系列实验证明,胆汁酸可通过诱导BDL动物模型中一系列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促进中性粒细胞在肝脏聚集,进而导致肝损伤。
3.2 其他免疫细胞的作用 除了中性粒细胞之外,其他免疫细胞也同样参与胆汁淤积过程中胆汁酸介导的肝损伤。库普弗细胞(Kupffer cell)—是肝脏中的巨噬细胞,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过程中同样发挥作用。既往将巨噬细胞分为两型—M1和M2[27],其中M1型Kupffer细胞为促炎表型,能被某些病理因素如细菌脂多糖、毒素等诱导释放炎症因子如IL-6、TNF-α等,从而导致肝脏损伤。而M2型Kupffer细胞为抗炎表型,其可选择性被IL-4以及IL-13激活,并且释放IL-4、IL-10、IL-13以及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而促进损伤修复并且抑制肝纤维化,从而减轻肝脏损伤[28]。Kupffer细胞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在病理过程中能够整合多种信号进而根据肝脏微环境的变化迅速改变其表型[29]。TGR5是一种G蛋白偶连胆汁酸受体,其广泛表达于Kupffer细胞、胆管上皮细胞以及肝窦内皮细胞,可被胆汁酸如石胆酸(LCA)、脱氧胆酸(DCA)、鹅脱氧胆酸(CDCA)等激活[30]。巨噬细胞中TGR5被胆汁酸激活后,可以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而加强抗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进而影响Kupffer细胞表型的转变[31]。在肝脏受损病理过程中,Kupffer细胞还能够通过吞噬凋亡细胞和细胞碎片,抗原呈递以及招募其他免疫细胞发挥其作用[28,32]。除巨噬细胞外,T细胞同样在胆汁淤积性肝病过程中发挥作用,IL-17是一种促炎以及成纤维细胞因子,由Th17细胞分泌,在BDL动物模型中已经证实可见Th17细胞以及IL-17的增加[33]。既往有研究表明,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小鼠模型中,自然杀伤T细胞(NKT Cell)能够加重肝损伤[34],而随后相关研究表明,NKT细胞可通过刺激抗炎因子IL-6或抑制Kupffer细胞释放的促炎因子而减轻胆汁淤积性肝损害[35]。近期,研究者发现,在恒定自然杀伤细胞(iNKT Cell)缺陷的小鼠模型中,炎症因子CXCL-10、ICAM-1释放减少,EGR-1表达下调而胆汁酸转运体MRP2和NTCP的表达上调进而导致在BDL动物模型中胆汁酸介导的肝损伤明显减轻,证明NKT细胞在胆汁酸介导的肝损伤病理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
3.3 胆汁酸介导的炎症信号通路 如前文所述,在胆汁淤积性肝病过程中胆汁酸通过诱导相关炎症反应导致肝损伤,而胆汁酸是如何诱导炎症反应发生的呢?Woolbright et al就此提出炎症信号通路假说,他们认为胆汁酸可诱导一系列促炎信号级联反[18]。既往已有研究证实,TCA可以通过一系列信号通路上调EGR-1的表达进一步促进炎症因子MCP-1、MIP-2以及ICAM-1的 释放,而这一过程并不需要FXR参与,这证实胆汁酸介导炎症反应过程中部分是依赖EGR-1进行的,而这一过程涉及特定炎症信号通路的激活。鞘氨醇1-磷酸受体2(sphingosine1-phosphate2 S1PR2)是胆管细胞中主要表达的鞘氨醇1-磷酸受体,Wang et al 研究人员发现在BDL动物模型中,TCA可以通过S1PR2激活ERK1/2/AKT-NF-κB信号通路进而诱导诸如MIP-2等炎症因子释放以及一系列炎症反应进而加重肝损伤。Toll样受体9(Toll-like receptor9 TLR-9)是细胞内的一种DNA受体,相关学者研究发现胆汁酸可以损伤线粒体,线粒体损伤后释放的线粒体DNA(mtDNA)可激活TLR-9,而在敲除TLR-9的小鼠肝脏细胞中,胆汁酸诱导趋化因子MIP-2的作用明显减弱。而且在敲除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及Trif因子的小鼠模型中,胆汁酸诱导炎症因子表达的作用同样也会减弱[14],而MyD88以及Trif是TLR-9的下游信号分子,因此可以推测在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中,胆汁酸诱导肝细胞损伤释放mtDNA后激活TLR-9信号通路,进而导致下游信号分子激活增加炎症因子的释放从而加重肝损伤。综合上述研究证明,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过程中,胆汁酸可通过多种促炎信号通路介导肝细胞损伤。然而目前许多炎症信号通路尚不清楚,仍需进一步研究发现。
4 胆管上皮细胞的参与
胆管上皮细胞是排列在胆管管壁内的上皮细胞,其同样在胆汁酸介导的胆汁淤积性肝损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胆管上皮细胞上存在许多胆汁酸转运体(如TGR5、ASBT、OSTα、OSTβ等)。如前所述,TGR5可在胆管上皮细胞细胞中表达,研究发现胆汁酸浓度升高时可诱导胆管上皮细胞中TGR5被激活并促进胆管细胞增殖并且可以抑制胆汁酸介导的细胞损伤。胆汁酸转运体ASBT同样在胆管上皮细胞中表达,当发生胆汁淤积时,胆管上皮细胞中ASBT表达上调,导致胆汁酸摄取增多进而导致肝脏内胆汁酸浓度上升,而近年来研究发现当发生胆汁淤积时抑制胆管上皮细胞中ASBT可显著降低胆汁酸浓度并减轻肝细胞损伤。此外,胆管上皮细胞还能表达和分泌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OPN是一种多功能蛋白,它能够与炎症细胞上的整合素受体结合成为许多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NKT细胞、Kupffer细胞)的趋化因子。当发生胆汁淤积时,胆管上皮细胞中骨桥蛋白表达水平增高,而且对于敲除OPN的BDL小鼠模型中中性粒细胞浸润明显减轻,炎症反应也明显减轻。
5 胆汁淤积性肝损伤的治疗
对于胆汁淤积性肝病尚无特别有效治疗措施,熊去氧胆酸(ursodesoxycholic acid,UDCA)和S-腺苷蛋氨酸(S-adenosyl-L-methionine,SAMe)仍是目前治疗胆汁淤积性肝病主要药物[2]。奥贝胆酸(obeticholic,OCA)—主要用于治疗临床UDCA应答不敏感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患者,已于2016年由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上市。而中草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近年来已被多项实验发现对于胆汁淤积性肝病的治疗具有一定效果。胆汁淤积时小檗碱(berberine,BBR)已被证实可通过增加NTCP表达促进胆汁酸的摄取进而恢复胆汁酸循环稳态。薯蓣皂苷(dioscin)则能增加胆汁淤积过程中胆汁酸转运体MRP2、BSEP、NTCP的表达维持胆汁酸循环稳定从而减轻肝细胞损伤,并且它可以减轻肝脏炎症反应,减轻氧化应激以及发挥抗纤维化作用。柯里拉京(corilagin)可抑制EGR-1的表达进而抑制炎症反应并降低胆汁淤积动物模型血清中总胆汁酸以及ALP水平,并且它还可以抑制NF-κB的表达进而减轻胆汁淤积性肝病中肝脏炎症反应,这可能与抑制前文所述的炎症信号通路相关。此外,橙皮油素、五味子乙素等均被发现对于胆汁酸介导的肝损伤有一定治疗作用[3],但这些中草药的临床应用仍需要进一步的实验验证。除传统中草药以外,还有许多新型药物正处于研究当中,比如Tropifexor,它是一种高效的FXR受体激动剂,其可通过激活肝细胞中FXR表达进一步激活下游SHP表达进而诱导BESP表达从而降低胆汁酸的蓄积。非诺贝特(fenofibrate)是过氧化物酶体增值剂激活受体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α,PPARα)激动剂,其可通过激活PPARα进一步抑制CYP7A1活性从而降低胆汁淤积时胆汁酸的合成,并且它可降低PBC患者血清ALP以及体内多种炎症因子水平,这些新型药物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中,有望在将来为胆汁淤积性肝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