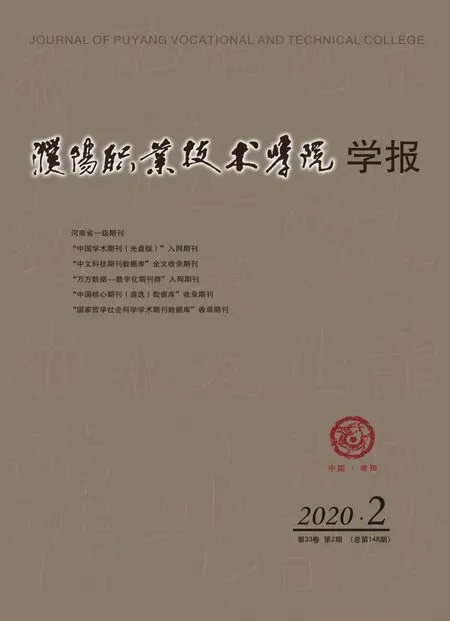春秋时期鲁国与济水之戎的关系
刘一麟
(青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济水之戎,顾名思义,即春秋时期活跃在济水流域的一支戎族。近代学者顾颉刚在 《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中称其为鲁西之戎,盖因其活动地域在鲁国西部[1](87)。另有当代学者孙战伟称其为楚丘戎,乃因其常据楚丘为据点之故[2](60)。春秋之时,戎族分支繁多,并且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此前,学界多认为戎族的活动地域当为中国西部或西北部,其实不然。童书业先生就认为:“戎,并不限于西方,东方、南方、北方都有戎。 ”[3](12)故所谓济水之戎,便是活跃在当时中国东部之戎,而与其交往密切的,则是当时的东方大国——鲁国。
一、鲁隐公摄政与济水之戎请盟
公元前723年,鲁惠公卒,因太子允年幼,鲁人便推举庶长子息姑摄政当国,是为鲁隐公。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4](1529)摄政当国的行为,在鲁国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鲁国的始祖周公旦就曾在周武王去世后摄政称王。然而,即便实力强大如周公,在摄政称王时仍受人非议,甚至为此引发叛乱。同理,效仿周公摄政当国的鲁隐公所受到的压力亦是可想而知。故在鲁隐公执政的十一年间,低调谨慎成为其主要的行事作风,睦邻友好则成为其主要的外交政策。而毗邻鲁国的济水之戎,便在此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据《左传》记载,济水之戎的活动地域当在鲁、曹、宋等国之间,盖今豫东鲁西的济水流域[5](74)。 当时,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领土国家,国与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大片的空隙,而戎族便在这些空隙中生产和活动。故《后汉书·西羌传》中总结道,诸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6](2872)。 由此可知,在实行国野制度的周代,济水之戎主要活动于华夏诸国之间的野地。他们和其他地区的戎族一样,依托山地而聚,同时又逐水草而居,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并与该区域聚于平原的华夏族交错杂居。正是因为这样的戎夏分布格局,加之鲁隐公的外交需求,使得济水之戎与鲁国的交往成为必然。而双方交往最主要的形式,便是会盟。
根据《左传》的记载,鲁隐公与济水之戎先后进行了两次会盟。第一次为潜之盟,《左传》隐公二年记载:“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7](23)据杨伯峻先生考证,潜为鲁地,当在今济宁市西南。隐公二年,即公元前721年,鲁隐公与济水之戎在潜地会盟,其原因乃是为了重温鲁惠公时的旧好。由此可知,鲁国与济水之戎,至少在惠公时期就有和平友好之传统。重温旧好在当时应是一种惯例,新君即位之初要和友好国家进行会盟,彼此联络感情,就像我们现在的新任领导人去各国进行访问一样。故鲁隐公即位之初,便先在三月“及邾仪父盟于蔑”[7](7),又在九月“及宋人盟于宿”[7](8)。 同时,由于鲁隐公乃是代替鲁桓公摄政当国,故其积极与周边国家会盟更有稳定政权的深层次意义。而与济水之戎的潜之盟,则是鲁隐公即位之后所举行的第三次会盟。这次会盟的结果,是济水之戎请求与鲁国结盟,却被鲁隐公推辞掉了。笔者以为,鲁隐公的辞盟,乃是其欲擒故纵的外交技巧的体现,而非同盟时机与条件的不成熟。故仅仅半年后,鲁国与济水之戎便展开了第二次会盟。《左传》隐公二年云:“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7](24)据杨伯峻先生考证,唐亦为鲁地,在今山东省鱼台县旧治东北十二里武唐亭,与潜相距不远。这次会盟的结果,乃是终隐公一世,鲁国与济水之戎未有摩擦与冲突,可见唐之盟效果之显著。
二、鲁桓公即位与济水之戎的修好
公元前712年,鲁隐公在鲁大夫蒍氏家中,被羽父弑杀。 由于羽父曾“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7](86),故弑杀鲁隐公的幕后主使,其实就是鲁惠公时的太子允,即后来的鲁桓公。《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立桓公,而讨蒍氏,有死者。 不书葬,不成丧也。 ”[7](86)意思是说,鲁桓公即位后,为了掩盖其弑君的罪行,将无辜的蒍氏当成了替罪羊。同时,鲁桓公还不以国君的规格安葬鲁隐公,致使《春秋》的作者“不书葬”。笔者以为,鲁桓公此举,是为了强调鲁隐公只是一个摄政的臣子,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君,并以此来证明其内乱行为的正当性和政权的合法性。然而,这种行为仅仅只能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真正能为其稳定政权起到帮助的,还应是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及寻求外部的支持。故《左传》桓公元年载:“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7](88)紧接着,“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7](89)可见鲁桓公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当时的中原第一大国郑国会盟,以此来稳定其政权。越之盟结束后,鲁桓公随即又在唐与济水之戎会盟,亦可见当时鲁国对济水之戎的重视程度。《左传》桓公二年载:“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7](98)由此可见鲁桓公的即位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鲁国的内乱,并没有影响到其与济水之戎的友好关系。于是终桓公一世,亦未见双方交恶之记载,可见双方同盟之根深蒂固。
在当时“贵华夏而贱戎狄”的历史背景下,鲁国能三番两次地与济水之戎会盟,并在隐、桓两代都产生了和平友好的积极效果,堪称难能可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历史传统之影响和现实利益之需要两个方面。首先,鲁国乃周公之子伯禽所建之邦,自古以来就是周礼的推崇者和维护者。《左传》定公四年周公分封伯禽为鲁公时要求他治国要“疆以周索”便是明证,而这更是与分封唐叔到晋国时要求他“疆以戎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1715-1716)。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用了三年的时间,“变其俗,革其礼”[4](1524)。笔者认为,周公所创之周礼,其实就是指周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置于内即是宗法制,置于外便是分封制,置于行为规范及文化思想层面,即是所谓的礼乐制度,而置于国家权力运行以及邦国外交上,则应是先秦时期极为重要的盟誓制度。李健胜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十分频繁,借盟誓调节各国关系乃至华夏与诸戎关系的做法,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9](51)。正因如此,无论是鲁隐公还是鲁桓公,在即位之初就积极与济水之戎会盟,盖因历代鲁公都是周礼的推崇者与维护者,故需借盟誓制度来维护其与济水之戎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实现国家权力的平稳运行。
当然,这一时期的鲁国与济水之戎交往频繁,并且积极会盟保持友好关系,除受历史传统影响以外,更多的是因现实利益之需要。潜之盟时鲁隐公之所以要展现一定的外交技巧,其实就是双方在实力上的博弈。鲁国乃是周王朝极为倚重的诸侯国,之后虽日渐衰落,但在春秋初期仍然算得上是大国,实力不可小觑。然而鲁隐公与鲁桓公即位时,鲁国国内均有能够导致内乱发生的不安定因素存在,因此二人都急切需要国外势力的支持,故实力强大的济水之戎便成了他们双双争取的对象。关于济水之戎的实力,史书中亦无明确记载。但《左传》隐公七年载:“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7](57)可见济水之戎不仅能朝觐周王室,还能随意讨伐和扣押王室公卿,其实力亦不容小觑。而能与如此强援为盟,无论是对摄政当国的鲁隐公,还是弑君即位的鲁桓公,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推测,济水之戎对于隐、桓二公平息国内动乱和抬高国际地位,必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理,济水之戎作为异族,却能够觐见王室甚至扣押公卿,除自身实力强大以外,恐怕也少不了鲁国在其背后的支持。另外,除政治上的互助,经济上的互利与文化上的互通,当亦是鲁国与济水之戎同盟的主要原因。总之,双方能在春秋时期长时间地维持和平友好关系,除受历史传统影响以外,更多的是因现实利益之需要。
三、鲁庄公讨伐与济水之戎的消亡
如前文所述,春秋时期的鲁国与济水之戎能在长时间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盟誓制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相争、夷夏之防被打破的大背景下,盟誓制度所依靠的盟誓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和双方出于道义所达成的契约精神,便显得异常脆弱。因此,当双方的利益追求出现分歧,彼此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节,会盟时所达成的契约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谈或一张废纸。故所谓的弃盟与背盟现象,也在此时接连出现,成为春秋时期一种普遍的政治乱象。而鲁国与济水之戎世代所维持的和平友好关系,终于也在弃盟与背盟中走向了尽头。而为这段关系画上句号的,则是鲁庄公。
公元前693年,鲁庄公即位,鲁国并没有出现因为权力更迭而产生的动乱。相反,由于鲁桓公在齐国的冤死,鲁庄公在即位之初,鲁国便展现出了一股励精图治的崭新气象,国家实力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在此背景下,鲁庄公并没有继续与济水之戎会盟,而是直接放弃了与济水之戎所保持的世代友好传统,其政治意图显露无疑。紧接着,鲁庄公先是参与了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的储君之争,之后又在长勺之战中大败齐军,后来更是在柯之盟中胁迫齐桓公归还了齐国之前侵占鲁国的土地,其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就在此时,济水之戎却主动侵略鲁国。《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7](226)所谓“追”,郑玄注为“逐寇也”;所谓“讳之”,杜预注为“戎来而鲁不知”。由此可见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676年,济水之戎主动偷袭鲁国,至于其发动袭击之原因,未见史书记载。笔者推测,此次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当是鲁庄公放弃了与济水之戎的同盟后,济水之戎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依靠而被周边的华夏国家所孤立,其经济生活必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故其偷袭鲁国,乃是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生存资源。然而令济水之戎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鲁军训练有素且战斗力极强,不仅成功地抵御了戎军的偷袭,还在鲁庄公的率领下将其追逐到了鲁、曹边界上的济西之地。鲁庄公伐戎之雄心由此初现。
之后,在鲁国这个曾经的盟友身上吃了亏的济水之戎,将侵略的矛头转向了实力弱小的曹国。《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云:“冬,戎侵曹。 ”[7](248)曹国乃西周初年就被分封的嫡系诸侯国,乃鲁国西部之友邦,且同为姬姓。故两年后鲁庄公征讨济水之戎,除了报当年济水之戎偷袭之仇,当亦有为曹国复仇之意。而这也与当时齐桓公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相符合,可见不仅仅只是鲁国与济水之戎,华夏各国均在此时展开了对戎族的讨伐。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管仲所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7](280)。 于是,《左传》庄公二十六年记载:“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7](254)此役乃鲁国与济水之戎的最终决战。庄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668年,鲁庄公亲自率军讨伐济水之戎,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可见讨伐战争之艰难。之后,史书中再无关于济水之戎的记载,笔者认为,其或被鲁庄公完全消灭,或在遭遇重创后被迫迁徙,又或者是被征服后逐渐融入华夏族。总之,春秋时期的鲁国与济水之戎的关系,最终被鲁庄公的一场大战画上了句号。
四、结语
春秋时期鲁国与济水之戎的交往,开始于隐公二年,即公元前721年,终止于庄公二十六年,即公元前668年,共计五十四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鲁国曾与济水之戎先后进行了三次会盟与两次战争,共同书写了一段载之史册的戎夏关系史,这对研究春秋时期整体的戎夏关系,乃至对中国早期民族与国家形成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春秋时期鲁国与济水之戎的和与战,在无形中打破了存在已久的戎夏间的民族壁垒,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民族大融合,同时为中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另外,基于盟誓制度的衰落与“尊王攘夷”政策的实行来研究春秋时期的戎夏关系,也为先秦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更为笔者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