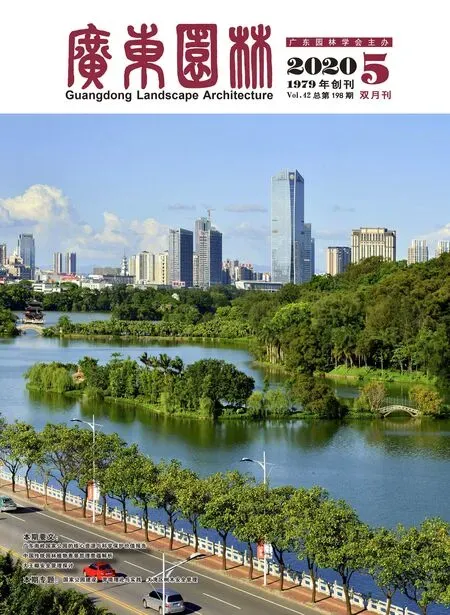星球时代下的专业认同与设计文化:对话查尔斯·瓦尔德海姆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esign Culture in Global Age: Dialogue with Charles Waldheim
嘉宾介绍:查尔斯·瓦尔德海
姆(Charles Waldheim),美 国-加拿大籍建筑师与都市主义者。瓦尔德海姆探索景观、生态及当代都市之间的关系,同时是多部被广泛翻译与出版的著作作者与主编人。他是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约翰·E·欧文教席教授,兼任城市化办公室主任,是罗马美国学院会员,加拿大建筑研究中心访学基金获得者,莱斯大学库利南主席,及密歇根大学桑德斯基金会员。
导读:广东园林杂志海外风景园林思想专栏的首篇访谈有幸请到了哈佛大学风景园林系前系主任,同时也是景观都市主义理论的提出者与主要倡导者的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教授。星球城市化与景观都市主义都是以城市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在对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瓦尔德海姆作为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研究者,对星球化议题同样有着深刻的见解。本次访谈集中探讨了星球化与在地性的并存性及其关系、风景园林学科自身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性、景观都市主义者的身份与责任、多学科协作中风景园林的角色与潜力,以及学科内核从生态规划往设计文化转向的趋势等。
蔡淦东:最近出版的一期《New Geographies》(新地理)杂志取名“Extraterrestrial”(地球之外)①《New Geographies》是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出版的设计研究刊物,自2008年创办至今,主要关注设计学科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反映了设计学科的关注点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学术思潮。伴随着星球化研究的进行,一系列以星球为设计尺度的竞赛也盛行起来,例如设计人类在火星上的栖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议题对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来自设计学科的多位学者,包括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风景园林师,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全球或星球议题。20世纪展开了来自规划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球城市”讨论,这可以认为是对星球城市化批判性讨论的开端。全球城市理论关注的是作为社会与经济网络核心的大城市,而星球城市化则认为整个星球都已城市化。近年来对星球城市化探讨得最深入的当属追随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研究成果的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他的研究与资本经济网络、气候变化、物理环境构成等议题相关,同样认为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已经城市化。关于你问题里提到的另一个话题—地球以外,我认为这需要追溯到1968年阿波罗8号太空船的宇航员拍摄的“地出”(Earthrise)照片。在那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意识与星球意识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回到过去十年设计学科的讨论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Hashim Sarkis、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Toshiko Mori以及布伦纳都提出了诸多有关全球性和星球化的探讨②Hashim Sarkis,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规划学院院长。Toshiko Mori,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教授。。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学科善于为特定场地输出知识,而建筑与城市学科则在思考全球问题上更得心应手。这样的情况随着风景园林逐步地适应以星球化为核心的理论框架而得到改善。
蔡淦东:这与您提出的景观都市主义者的概念相符,即风景园林师在更大的星球尺度上实践,而非仅仅关注于场地尺度。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对的,这与风景园林师如何看到他们自身的工作,以及谁来委任工作有关。在过去,相比起由工程师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师进行城市规划,建筑师提出城市设计构想,风景园林师往往是最后被委任的,而这个情况因环境保护思潮的盛行而有所扭转,越来越多风景园林师得以介入到场地组织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
蔡淦东:而另一方面,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基金会(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最近公布了本年度“研究与领导力奖”的6位获得者,其中至少有3份获奖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问题:深入地区与场地,与当地居民互动且倾听其声音,用设计的方法尝试解决明确存在的本地问题。尽管设计地球乃至太空的热情高涨,与之相对的对在地性议题的深入关注似乎也是当下的一大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两个看似背道而驰,但同时出现在我们专业讨论热潮当中的议题?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你提到的两个趋势的确是并行的。我认为启蒙运动是不完整的,它具有全球的影响力,但却没有体现出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及地理上的迁移,这两者往往需要依靠教育来实现人与人的连接①启蒙运动一般指发生在欧洲17到18世纪的一场涉及哲学、文化、科学等方面的运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欧洲。瓦尔德海姆这里提及的启蒙运动也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我成长于一种不依靠出生地而是迁移地来定义自我的文化,在这里你作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的居民身份无关种族,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充满问题的历史。得益于启蒙运动我们才能跨语言和文化地进行全球性的连接,但它同样带来了地方文化与认同感的丢失。我坚信只有通过教育、交流与分享,人文精神才能跨越种族得以延续。我们正在向自己—既是作为哈佛设计学院也是作为风景园林学科,提出一个艰难的问题,不仅关乎在地性,也关乎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毫无疑问,风景园林、城市规划、都市设计与建筑学自古就是权力表达的工具。设计并建造世界本身即是权力的表达。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能产生种族主义的设计,一个种族主义的学校则会延续这状况。回溯在北美大陆上发生的对原住民的屠杀以及黑奴历史,我们仍然在寻求方法应对这种状况。问题是风景园林学科如何向这一段种族主义历史作出回应,以及如何提出具有批判精神的问题。这同时也塑造了另一个有关我们学科未来的问题:依靠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产物的现代风景园林解决上述困境是难以想象的,又或者说,我们该如何为学科进行去殖民化,才能以一种后帝国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学科姿态出现?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很多。而这也是我们目前最感兴趣的议题之一。
我不认为星球化与在地性之间存在矛盾,这两者只关乎我们的工作对象和方向。我们学科的历史建立在特定的国家与地区认同感之上,或为特定文化所服务,在整个工作生涯当中我都致力于超越这种族群主义。我们用教学作为媒介,通过知识的教育与环境的营造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谈到个体认同,我认为我在哈佛设计学院的同事提出了诸如新人种学(New Ethnography)或新人类学(New Anthropology)的研究课题,皮埃尔•比朗格尔(Pierre Belanger)和加雷斯•多尔蒂(Gareth Doherty)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关于风景园林学科建构人类主体性的新思考②皮埃尔·比朗格尔成立了非盈利设计研究工作室OPSYS,长期关注于设计学科与社会生态学、地缘政治学的关系。加雷斯·多尔蒂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与人类学,并深入研究伊斯兰地区、西非及拉丁美洲的风景园林发展。。谁是土地的拥有者?如果说西方现代景观是精英群体通过资本主义把自我表达于建成环境、花园、庄园或公园,那么这些建成空间的主体性该如何理解?又该如何被用于对学科进行批判性思考?这些正是当下最有趣的学科议题。
蔡淦东:我们已经谈到了系统性种族主义,我想进一步跟您探讨关于不公平性的话题。我注意到最近哈佛设计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Architecture, Design,Action”(建筑、设计、行动)的访谈,您也参与其中。尽管访谈内容是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我认为其中同样涉及到了全球与本地的问题,例如访谈中有关“美国建立于窃取而来的土地之上”,“我们应更多地向少数族裔建筑师学习”,“我们建造的世界是以系统性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为基础”等讨论。您认为系统性的不公平性跟星球化与在地性之间的鸿沟有关吗?风景园林又是否可以充当二者间的调和者?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这是可能的,但我更想听听你如何思考它的可能性。最近围绕不公平性以及学校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等讨论,与美国的原住民群体问题息息相关,这部分源自白人优越性思维作为定义“美国梦”的标准已渗透到各个族群当中。我完全赞成我们应重新思考自身的历史,并承认黑人景观一直被低估、被忽视、缺乏理论化与系统记录。因此,在我想象风景园林能解决什么问题之前,我们应首要思考的问题是风景园林在上述问题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方面,我通过历史和理论课程上向学生介绍风景园林在过去如何通过建成作品与学科建设巩固了白人阶级的权力,另一方面,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倘若风景园林的内核是白人优越性,我们该如何克服它而前进?也许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一个新的领域以及创造新的词汇。当现代风景园林学科的概念在19世纪被发明时,倡导者们正是宣称着当时的专业分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的变化。我们正面临着类似的时刻,人们向建筑与风景园林提出了是否可以做到去殖民化的质疑。
从这点出发,我们现在的讨论应该是全球化议题如何符合并促进解决以上问题。刚才提到的群体认同感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学术圈中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即这是由经济系统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意外或危机。如果将所有事物摆在一起,无论是族群认同、帝国主义、去殖民化还是资本主义,毫无疑问一切都是相互连接的。全球化就是一个人类在全球尺度互相连接的概念,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延伸。把全球与本土联系在一起思考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我们可能会因此丧失了对资本主义及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政治批判力。
蔡淦东:在《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新景观宣言)①《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于2017年出版,收录了2016年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基金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的重要发言。2016年是由麦克哈格为首撰写的景观宣言发布的50周年。一书中,理查德•韦勒(Richard Weller)提醒我们在1966年宣言的第一个版本是由5名白人撰写,关注点仅在北美,也没有涉及社会公正问题、物种濒危问题以及气候变化问题。50年后的新宣言有超过600名参与者以及32名演讲者,涉及的专业议题也比当年广泛得多。然而当我翻阅所有演讲者背景的时候发现,其中仅有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两位来自中国,还有一位来自印度。剩余的演讲者都来自西方国家。不难想象,仍然有许多声音未被聆听,许多实践与想法没被发现和重视。您认为如果要撰写2066年版的景观宣言的话,它应当包含哪些内容?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把时间线拉长是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尤其考虑到气候问题的时间性。我不清楚我能否看到那一天,但我拭目以待。我认同你说的投入更多注意力到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②Global South属于社会经济学与政治学范畴,国际上使用该词一般泛指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并非指代地理学中赤道以南区域。,并且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上述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学科的发展而解决吗?尽管现代风景园林是一个西方世界的概念,但它从欧洲出发输送到世界各地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东亚地区的快速成长是令人惊叹的。然而风景园林学科作为一种媒介可以一直向不同的观念和声音保持开放吗?抑或是我们该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工作或描述方式?我坚信依靠教育与文化分享,大学作为一种机制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贫困,实现阶级跃升,并融入到全球网络之中,这也是我来到哈佛设计学院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人持反对意见并认为我们需抵制全球化以捍卫当地文化。我认为两者兼得是可能的,这并非简单的零和游戏。拓展风景园林学科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不过我对是否需要新的词汇这一观点依然保持开放态度。
蔡淦东:这与专业身份认同有关。在您的著作《Landscape as Urbanism》(景观都市主义)中,您提出了风景园林师作为时代的都市主义者的口号。在2016年的新景观宣言会议上您也提到了这一点。景观都市主义者(Landscape Urbanist)的专业身份与责任是什么?它与风景园林师(landscape Architect)的区别又是什么?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我的观点是,西方的风景园林学科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像音乐剧一样为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服务的城市化副产物。从未有人期待或渴望风景园林成为人人都能享有的资源。从绘画题材、花园形式到公园发展模式,作为媒介的风景园林一直改变着自身的出现形式。当我在25年前第一次创造“景观都市主义”这一术语时,我希望凭借这一修辞行动提醒人们,我们必须调整实践的方向。我一直使用这样的观点尝试引起更多人思考我们学科究竟能做些什么。在我第一次接触风景园林时,它是关于植物材料以及如何利用植物进行设计的。这在某一时期是正确的理解,但我认为对我们学科而言完全不够。因此,景观都市主义所倡导的是风景园林师取代规划师、城市设计师以及建筑师而被雇佣,因为后三者还未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环境应对策略。在北美,大多数的风景园林项目并非建立在设计学院之内,而是在林学院、农学院以及自然科学学院,这使得许多人依然认为风景园林是关于花园设计以及环境管治、保育及林学的。我尊重这一观点但我不认为它是我们学科的未来。景观都市主义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宣称风景园林师应重新武装自身并如一名都市主义者般工作,这恰恰是当年学科被创立时奥姆斯特德的想法。奥姆斯特德深知我们学科是关于如何塑造城市、整合基础设施与自然系统的。最近我们更频繁地使用生态都市主义(Ecological Urbanism)一词③生态都市主义可以被看作景观都市主义的批判性延伸。相关理论著作包括莫森·莫斯塔法维与加雷斯·多尔蒂于2010年合著的《Ecological Urbanism》(生态都市主义)。,因为我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它具有更好的精确性。
有一个有趣的争论:一方面,如果你从不质疑、批判或重命名自己的专业或学位,你将无法对外部情况进行回应并与社会脱钩。另一方面,我不建议每次遇到一个新议题便更换学科的名字,例如一次飓风、一场流行病,或一场大火灾。已被认可达数个世纪的知识突然被认为并不完善的例子屡见不鲜,19世纪下半叶的风景园林学科就是针对已有的建筑、工程、花园设计与艺术等学科不完善而被发明的。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学科逐渐变得热衷于怀旧,而丧失了原有的激进性。20世纪第一个10年创立的城市规划学科,50年代创立的城市设计学科以及25年前创立的景观都市主义,都是试图通过重塑专业实践与讨论,来为风景园林学科带来相关性的尝试。关于风景园林师是否有足够的社会身份认同以面对今日的挑战,我认为仍没有明确答案。
蔡淦东:我认同我们应努力保持专业的灵活性并使之能更好地应对世界变化。风景园林在20世纪中期曾受到生态规划与环境科学学科的深刻影响,20世纪末则是建筑师产生了对风景园林的兴趣,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竞赛带来了建筑理论与策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减少对外部学科的吸纳,而是通过自身技术提升与理论发展以建设更明确的专业身份?又或者我们应保持风景园林的“模糊身份”,以更好地发挥风景园林学科的综合性特点,从而更好地粘合各个学科?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我认为将“模糊性”解读为一种潜在的“灵活性”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个有趣的角度。我注意到许多人都认为我们专业缺乏强有力的地位,实践中也有不少人提出工程师在20世纪占据了风景园林师的地位。我认为在这样的挑战下风景园林才能显示出最有趣和价值的一面。景观都市主义思想的出现并非因为我,而是主要因为一系列的机遇、空缺被证明与风景园林息息相关,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最有价值的技能上。我要额外提到几点:首先,我不认为整合所有知识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决定该吸取多少的科学知识、植物知识、历史理论知识以及城市知识以塑造我们的专业领域。学校里关于此的争论每天都在进行,而我个人反对风景园林师融合一切知识的想法。我认为最首要的是设计文化的问题,即景观都市主义者该如何扮演引领建筑师及城市设计师的角色问题。这与我们上一代同行有根本性的区别,他们是提倡运用科学知识到规划而摒弃设计的一代生态规划师。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景观都市主义者需在设计场地尺度而非区域规划尺度上熟悉生态系统策略。第三,景观都市主义者需要具备与多种应用型学科协作的能力。
在我看来把风景园林或景观都市主义看作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是错误的,它必须是一个关于文化、想象力,以及对新生活与工作概念思考的活动。如果把我们的工作降低到纯技术性的程度,我们将在与其他领域的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包括房地产、市政工程,以及其他相关领域。有鉴于此,设计文化以及风景园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概念是我的思想核心。因此,我在书中与教学中提出的建议是减少对技术层面的过度关注,而更关心风景园林师的价值。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将越发与技术无关,而与想象力、提出构想的能力以及描绘世界的能力有关。从这点来看,风景园林学科正在变得越发强大与备受瞩目,并且这一切并非发生在某个具体的地区,而是通过风景园林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因此可以认为,景观都市主义者作为全球性设计师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对传统风景园林师定位的批判上。
蔡淦东:您刚刚反复提到了“设计文化”这一概念。在《景观都市主义》一书中,您认为与当代风景园林更密切相关的是设计文化,而非科学导向型的环境规划。在另一本著作《Cartographic Ground》(土地的表达)中您同样提到了空间精确性与文化想象力的问题。我认为设计文化是您的学术思想中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这让我想起最近一个流产了的Sidewalk Toronto城市设计项目①Sidewalk Toronto是由美国Sidewalk Labs负责的位于多伦多滨水区的城市设计项目,因在城市设计中大量引入技术创新而备受业界瞩目,但于2020年5月宣布项目终止。。尽管项目遇到的问题很多,如新冠病毒的爆发,而一个无法被忽视的问题是项目过度强调技术导向与智慧城市概念而非文化概念。人们的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到对信息安全和全球共享系统的讨论中,本土文化与认同却遭到忽视。您怎么看这一项目?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毫无疑问,多伦多是全球范围内一座重要的城市,也是北美少数的几个实践景观都市主义的城市。他们聘请一流的风景园林师重塑城市的滨水区,WEST 8、MVVA、JCFO等事务所在那里实践着由风景园林引领的城市项目。Sidewalk Labs的失败之处部分来自于对公众想象力的忽视,以及对当地文化的错误理解。作为一名移民到加拿大的美国人,我生活在两个国家,我认为Sidewalk Labs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与放任主义的产物,即由技术方和私人企业完全接管数据。这引起了所有关于公共领域隐私权的尖锐问题。我把这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错误理解,一种把美国思考公共空间的政治模型移植到一个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环境中的错误操作。我同意你说的缺乏空间想象力和高水平的设计同样是这个项目失败的症结所在。
蔡淦东:非常感谢您在今年特殊背景下的繁忙开学季抽空接受了这一次的采访!
查尔斯•瓦尔德海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