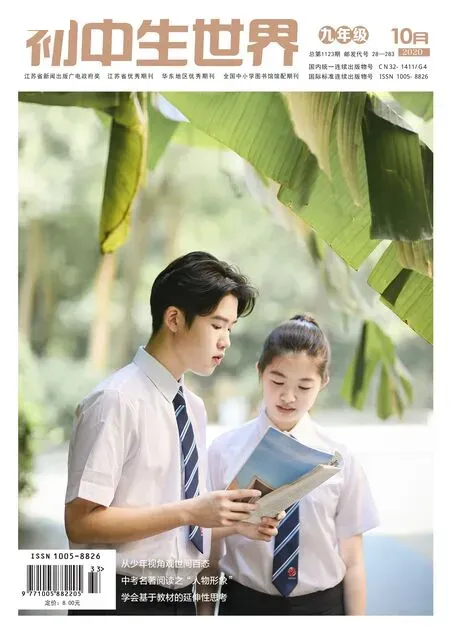八百米故乡
文 苏 童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存在,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1982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八百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对我来说,八百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词,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1982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与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八百米,不算很远,但也不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只好放弃腌菜了。搬家也给我造成了麻烦,且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都是扬中县(现为扬中市),改写成苏州是80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长辈们常常用家乡方言交流,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恐惧,就像一个隐私,唯恐给外人听到,可惜的是,这隐私无法藏匿,因为长辈们从不以他们的家乡为耻。扬中岛的方言听起来接近苏北话,而苏州这个城市的市民文化与上海相仿,地域歧视从来都是存在的,苏北话历来被众人不齿。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们,一旦与别的女孩子发生口水仗,必然会因为长辈们的口音受牵连。通常她们得到的回答是:不管你们的老家在江南还是江北,反正你们不是苏州人,是苏北人!
失散,团聚,再失散,是我母亲的家族在扬中、苏州两地迁徙生息的结局,没有土地的家族将永远难逃失散的命运……我童年时代热闹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缩了,家族对于我来说,仅仅是由直系亲属组成。每次回到苏州,我的足迹仅限于我父亲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们都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每两家之间的距离都很遥远,远远超过八百米。对我来说,超过八百米,故乡便开始模糊,开始隐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乡已经飘忽不见了。
所以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我去了我父母的故乡扬中,满眼生疏,父辈在此留下的痕迹已经无从追寻。我回到苏州,回到苏州城北,我曾经有过的八百米故乡,什么都不见了,只留下两座清代同治年间的石拱桥,一南一北,供人们凭吊。我发现在拆除了古旧的房屋之后,城北地区变得很空旷,同时也很小,那两座桥之间,现在看起来连八百米也不到!
所以,我怀疑我的八百米故乡也仅仅是错觉。我的内心需要一个多大的故乡?我需要的故乡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吗?
(选自2017年第4期《文学少年》,本刊有删改)
鉴赏空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苏童以自己的故乡的变迁为题材,以时间为序,叙写了对于“故乡”的认知过程;融入了对童年往事以及过往生活的体验与沉淀,既有婉约入微的生活细节,又有淡淡的乡愁之思,更有富有生命哲理的思索和感悟。
从空间距离来看,八百米很短;从时间坐标来看,岁月漫长。作者巧妙地将自己对故乡的复杂情感交织在这一时空轴中,抒写了自我的独特感受——“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文章真切自然,平实却有细致的韵味,犹如一幅白描,波澜不惊而又蕴藏着浓郁的思绪。
文章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是作者内心的宣言和个性的表达。要使自己的文章产生迷人的魅力,就要把自己的独特感受写出来。
读有所思
1.文章叙写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对故乡的不同感受,联系全文,看看作者对故乡的情感经历了什么样的认知历程。
2.作者说,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请说说“很短”和“很长”各有什么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