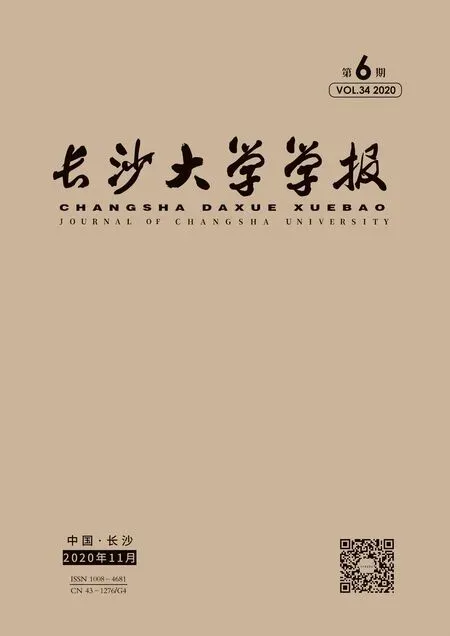从空间角度解读扎迪·史密斯“伦敦三部曲”的可行性
熊 丽
(九江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东亚大学人文学院,韩国 釜山 612022)
一 引言
扎迪·史密斯是英国当代作家,她从小热爱阅读和写作。在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时,她的第一部小说《白牙》就轰动了整个文学界。截至2016年,她已经出版了六部小说:《白牙》《签名收藏家》《论美》《使馆楼》《西北》和《摇摆时光》。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已经20年了,也许我国还有很多读者对她比较陌生,但国外许多读者和学者都给予她很高的评价,比如Maria Cristina Paganoni评价她是一位“广受赞誉的作家,因为她独创性地描绘了时代新主题”,“她描绘的从未有过的新联系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人类和文化交织带来了光明”[1]。
身份和种族认同问题一直都是后殖民小说的热点问题。同样,正如Maria Cristina Paganoni所说:“实际上,史密斯的小说研究了多元文化的英国的杂糅问题,试图从某种意义上展示文化混血的所有可能的延伸。”[1]扎迪·史密斯就是以其对当代英国移民生活的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吸引了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注意。学者们从叙事技巧、女性主义、民族认同、全球化等不同角度解读扎迪·史密斯的小说,其中也不乏批判之说,比如在写作特点上,Tracey L. Walter批评道:“扎迪·史密斯对黑人女性的刻画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史密斯很难创作出不同角色类型的女性角色(黑人和白人)。史密斯笔下的女性角色缺乏发展,因为她们会被白人男性主人公所遮蔽。”[2]无论褒贬,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当代小说家,扎迪·史密斯及其作品都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从空间角度这一视角来解读她的作品及主题的研究目前仍然非常匮乏。
二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伦敦空间
《白牙》《西北》和《摇摆时光》这三部小说都是以伦敦西北部郊区——威尔斯登为背景展开的。扎迪·史密斯在被采访时说,威尔斯登正是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把这三本书视为一个系列,称为“伦敦三部曲”。这三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对史密斯小说的另一种解读。Audrey Golden认为:“阅读史密斯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伦敦之旅,不受著名地标建筑的限制,而是由当代大都市中虚构的伦敦人所限定。”[3]在这三部小说中,扎迪·史密斯向读者展示了21世纪伦敦城市生活的全景,小说体现了强烈的空间感。她以伦敦的城市空间为切入点和视角,反映了英国社会潜在的危机,记录和再现了伦敦居民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困难,为我们在后现代语境下理解伦敦提供了新的思路。
“空间”一词来源于地理学,虽然地理学是一门涉及空间、地域、景观和场所的学科,但地理学家不应将空间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隔离开来,历史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在人们对人物、环境、事件和现象的解读中不可或缺。Emmanuelle Peraldo在《文学与地理》一书中指出:“在一个以 ‘空间转向’为标志的时期,时间不再是分析的主要范畴,而空间是。它现在被认为是文学中的一个中心隐喻和传统主题,而文学批评则作为一种新的工具和标杆占领了空间。”[4]1史密斯小说中伦敦城市空间曲折的伦理选择,反映了英国第二代移民对自我伦理认同、他者伦理认同和公共伦理认同的新思考。可以说,扎迪·史密斯利用中心与边缘的动态空间关系,建构了人类的“差异”与“他者性”,从而再现了21世纪英国人尤其是第二代英国移民伦理身份选择的复杂性。在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断裂过程中,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二元对立不断被颠覆。
文学是作者世界观的表达。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文学创作不仅反映了作者的主观空间体验和建构,而且反映了客观的空间变化和社会现实。同时,文学本身也是话语协商和思想碰撞的空间。在扎迪·史密斯的小说《白牙》《西北》和《摇摆年代》中,世界呈现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一样的巨大变化:不同族裔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前更为频繁,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地的人口流动在增加,在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不同文化背景和种族的人正在大量增加;尽管在一些地方存在种族和地区的误解和冲突,人们还是渴望了解彼此;移民、旅游和经济合作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交流。另外,对于西方社会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后代,即二代移民基本已经融入主流文化,对祖先的文化记忆已经褪去。一些白人和移民已经接受了种族和文化融合的事实,并习惯了他们的共存。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虽然在文化差异的建构上还存在一些冲突,但年轻一代的非白人移民中也会有人逐渐接受他们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作为现实,当然更多的仍是在进行多途径的身份协商。史密斯作品中的伦敦受到全球移民和后现代文化及社会力量的分散效应的深刻影响,并“强调了界定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自何方的巨大的当代问题”[5]168。
三 相关空间理论
Massy指出“空间是社会维度,不是单纯的人类社会性,而是在多样性中的参与。它是各种形式的异质性不断产生和重新配置的领域——多样性、从属性和利益冲突”[6]61。从空间角度去解读作品,除了可以了解故事发生的地点、地理嵌入性和知识生产本身的空间性以外,还可以“通过空间化/全球化重述现代性的故事,揭示现代性在暴力、种族主义和压迫中的先决条件和影响”[6]64。现代性的影响之一是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知识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权力地理(殖民权力/殖民地空间)上,是一种具有交叉轨迹的权力几何学。
Lefebvre延续了马克思的空间观,即空间是不断参与社会生产,并由社会生产的。“社会空间是与生产力量(以及生产关系)相联系而产生和再生产的。空间的产生是由于财富增加,因此剩余生产也在增加,这反过来又对初始条件产生了追溯作用。”[7]79与马克思的空间思想不同的是,Lefebvre从哲学的角度建构了空间生产理论,并将空间提升到认识世界的核心维度。Harvey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Lefebvre的空间生产思想,提出“空间的恰当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实践来解决的”[8]13。一方面,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对空间生产影响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同意Lefebvre对空间的理解,即不同的社会产生不同的空间。由此,“什么是空间”这个哲学问题被“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和利用独特的空间概念”所取代。“社会空间辩证法”是Edward Soja在总结Lefebvre空间观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的,其理论内涵包括两个维度:空间是社会过程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产品”[9]79;社会不能脱离空间,社会关系是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因此采用空间理论,特别是Lefebvre和Soja的“第三空间”理论来探讨空间与民族认同及自我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有着特殊的研究意义。正如Soja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第三空间”是他思考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一种新方式。他借鉴Lefebvre的“三元辩证法”,提出了“他者化——第三化”的批判策略,认为“第三空间概念具有列斐伏尔始终要赋予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它既是一个区别于其他空间(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或者说第一个空间和第二空间)的空间,又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10]79。 这是一个更为开放和动态的空间。
四 城市空间理论下的“伦敦三部曲”
我们可以在Lefebvre和Soja的空间理论的指导下去探讨扎迪·史密斯的“伦敦三部曲”中人物的空间体验。生存空间是在资本与权力话语下建构的,引发了“自我—他者”“压迫—反抗”“中心—边缘”的体验。城市新空间的产生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生存体验和身份认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扎迪·史密斯“伦敦三部曲”中的威尔斯登既是旧殖民地中心的一部分,同时又保留了普通和日常的生活化元素。正是这种地方性和世界性的混合体反映了大多数人在多元文化中的英国生活方式,虽然看似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发生在这个具有有限范围的地方,但其实与世界各地都有着历史和文化的联系。
讨论伦敦城市空间的混乱,我们不能忽视英国的殖民主义及其长期影响。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英国是许多殖民地的母国,过去的社会环境主要由白人主导并深受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然而,二战后,英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当时许多来自前殖民地的人移民并定居到那里。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人怀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大量涌入英国,成为英国的劳动力,后来成为英国的公民。从空间上讲,伦敦城是前大英帝国的心脏,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当不同的民族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后,他们必须处理错综复杂的种族关系,这些关系中夹杂着根深蒂固的殖民记忆,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伦敦并不像之前所宣传的那样去欢迎和接受多元文化,相反,这个城市充满了混乱与不安。这种混乱与不安来自文化的异质性;公共空间,如地铁、学校、街道等存在的各种暴力以及伦敦城市空间里巨大的等级差异。这个多元化的城市成为一个“中心——边缘”空间。这三部小说模糊了社会认可的界限,重新审视了各种伦敦人对本地人和移民的反思。小说中的人物审视自身面对的现实,审视冲击他们的观念和自我意识的外力,然后转向内心,试图解决他们的文化局限性。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各方面都感受到孤立和歧视,并逐渐被边缘化。从空间角度来看,伦敦的混乱空间与非白人移民的边缘空间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那么边缘空间需要被消除吗?Bell Hooks认为不需要,她主张应该在边缘构建自己的身份,少数族裔应该将边缘空间中心化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空间。换句话说,只有在边缘,他者才能抵抗霸权,并使第三空间呈现更多的可能性[11]145。Soja 提出的“第三空间”正是提供了这样可能性的动态开放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选择躲避冲突,也可以去进行直接反抗,或者不断进行身份协商。在这里,身份同样是流动和不确定的。
扎迪·史密斯观察了不同宗教、历史、传统和流行文化中人物的身份冲突,其小说也涵盖了伦敦移民的身份建构、空间和生活条件等诸多主题。小说中所描写的这些移民的身份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边缘化,他们都急需或者试图去建构自己独特的身份。《白牙》作为史密斯的处女作,讲述了琼斯、伊克巴尔和查尔芬这三个人的家庭的经历,为我们呈现了移民带来的社会及家庭问题。多元文化在英国的表现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将多元文化国家融入其中,通过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和背景的人物的个人经历来体现。小说对伦敦的边缘空间进行了描述,在当代伦敦,主流空间仍然由白人控制,而黑人只占据了一些边缘和外围区域。空间分布表明,后者位于从属地位。当伊克巴尔一家第一次搬到伦敦时,他们的住所位于伦敦的边缘地带,那里是穷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居住的东伦敦位于伦敦的底部,是一个主要的移民居住中心,犯罪率高、安全问题严重。尽管移民家庭寻求迁入主流社会,但他们的肤色决定了他们在当地人眼中是不正常的。移民是被边缘化的他者,他们的空间则是与主导空间分离的种族异化空间。除了居住隔离,这种边缘化现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例如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种族歧视。阿桑娜来自孟加拉国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庭,然而在伦敦,她原来的背景变得毫无意义,她的种族在英国被视为低人一等。这三个家庭都有移民的历史,他们或他们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尽力在这片新土地上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但他们只被当作陌生人看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不得不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努力在这片土地上认同自己。《西北》则更为直接地在小说名中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地点。小说从空间角度让我们看到城市生活的万花筒,听到它混乱的节奏,这是扎迪·史密斯对伦敦繁华街道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巷的刻画,在这种环境下小说讲述了四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的悲惨故事,他们的愿望和梦想被残酷的现实压倒,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喻的心酸和强烈的焦虑。《西北》这部小说可以从文化空间的异质性、公共空间的暴力、城市空间的阶级分化、空间归属的缺失等几个方面来反映。伦敦杂乱无章的空间让我们不禁要问:英国政府所倡导的要让不同声音被听到、不同思想能表达出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时代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呢?就像James Wood在《纽约人》中写道:“《西北》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想象中的、活生生的、悲喜交加的、多重奏的伦敦现实——它的口音、尘土飞扬的人行道、呜呜作响的公共汽车、阴暗的办公室、潮湿的公园……以及阴森的住宅区。”[12]《摇摆时光》里呈现出来的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威尔斯登的阴暗凄凉,是精神和物质极度缺乏的贫民窟。由于社会的偏见,住在简陋房屋里的移民在堕落和暴力的绝望中挣扎,而住在豪宅里的富人则在虚伪、身份丧失和道德败坏中成为精神贫民。小说使用了非线性叙述手法,看似只是一个“时间层”的叙述处理,但在时光穿梭中也让我们注意到空间的转换。无论是叙述者童年时期居住于威尔斯登,还是成年后辗转于伦敦、非洲以及纽约之间,无不体现出空间转换所要表达的对立的种族、阶级、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小说以舞蹈为媒介,展示了非洲裔英国女孩与非洲本土女孩在外貌和才华上的异同,并对英国黑人移民的身份进行了定位。像叙述者这样的人被称为“椰子人”,即在白人眼中,他们是外来人,同样,在非洲人眼里,他们也是“他者”, 这就揭示了叙述者身份困惑的原因,即身份不是稳定的、单一的,而是相对的、多样的。
五 结语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和城市经验的探索者,扎迪·史密斯对这座养育她的城市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伦敦,除了作为这部小说的地理背景之外,还是一个积极参与创造文化和塑造社会的城市空间。她在小说中对这种城市空间的特殊介入在众多主题中脱颖而出,值得我们去探究。“伦敦三部曲”通过文化空间的异质性、公共空间的动荡与暴力、家庭空间的分裂与隔阂,分析了英国目前面临的多民族性导致的城市空间混乱。扎迪·史密斯否认多元文化主义是对当前混乱局面的补救,相反,她建议,鉴于种族问题的复杂性,族裔身份问题还需要在作为城市空间的伦敦地区进行不断协商,以寻找到一种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