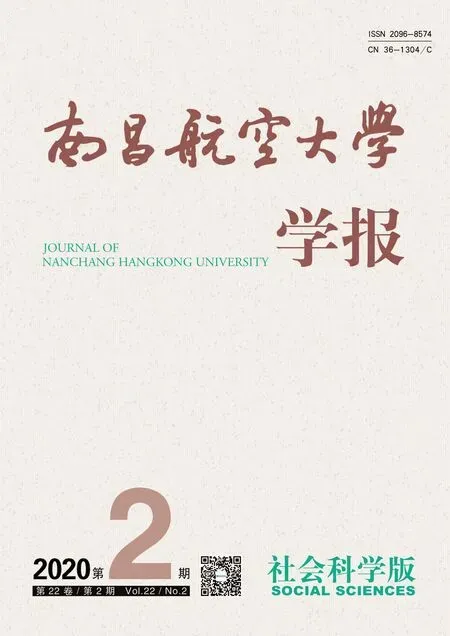弗洛姆自由观下的女性自我重建
——以《野草在歌唱》和《使女的故事》为例
谢 华,巩文文
(1. 南昌航空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南昌 330063;2.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63)
引 言
弗洛姆师从弗洛伊德,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创新,形成了弗洛姆自由观,并著有专著《逃避自由》和《爱的艺术》。在不同生活时期,自由一词承载着不同的意义。原始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分离促成了人类理性的开端。最初自由的获取是对自然力量反抗的同时对个体的认知[1]。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受到始发纽带约束下狭窄的自由。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人越来越自由的同时,伴随的是利益至上原则、关系距离的疏远以及极度的空虚感和寂寞感。如果选择屈从于这种心理机制,则是弗洛姆所说的消极自由,特点是摆脱束缚,即 Free from[2](69)。逃避自由正是逃脱这种令人无力的消极自由;相反,在上述的心理机制下,人们如果选择与外界的人或事建立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和爱,寻求自我救赎办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以摆脱不安全感,此之为积极自由。
近几年,对作品《野草在歌唱》和《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多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利等视角出发。Wang J[3]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探讨了白人玛丽和黑人摩西之间的扭曲关系。易妮[4]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野草在歌唱》中男性对自然和女性压迫以及他们的反抗。Misugi K[5]认为《使女的故事》所传达的女性主义思想固然重要,但是更要重视这部作品的文学和美学价值。王苹和张建颖[6]结合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理论,探讨了《使女的故事》中基列国的权力策略。但鲜有学者研究两部作品中涉及的弗洛姆自由观,因此本文将两部作品与弗洛姆自由观相结合,研究女性自我重建有一定新颖性和创新性。
虽然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属于不同国籍、生活在不同时期,但纵观这两位女性作家的成长经历以及代表作品,不难发现她们在刻画女性形象时笔触犀利,并且她们的作品都格外关注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生存命运以及她们的自我重建历程。本文用弗洛姆自由观解读《野草在歌唱》和《使女的故事》中两位女主人公在父权制社会下的生存状态,探讨她们的自我救赎方式,给陷于困境中的女性完成自我重建提供有效方法。
一、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生存状态
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都生活在父权制的笼罩下。幼年的玛丽由于父亲的男权思想,导致玛丽童年生活在沉闷狭隘的房子中,压抑着玛丽的自我意识。玛丽单身时期,带她出去玩的男性数也数不清[7](29)。婚后的玛丽在逼仄的房子里受到丈夫的压迫与摧残。由于玛丽童年时期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父权思想,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因此婚后的玛丽并没有得到婚前幻想的伊甸园,却是一个无尽的深渊。小说中多次提到玛丽的生活状态,比如沉闷的铁皮屋,用水困难等问题。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生育权是女性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也在丈夫迪克的怒吼中泯灭,玛丽的话语权也被剥夺。玛丽另一方面遭到黑人摩西的控制,种族肤色并没有影响男性优越感,摩西在某种情况下牵引着玛丽。比如,摩西用着半诙谐半责备的语调说:“夫人认为我来照顾老板有什么不妥吗?”玛丽屈服了[7](153)。白人中心主义是反对黑人以此种口吻和白人说话的。因此玛丽在自我形塑期在“家”这个空间里所接受的男性中心和白人中心主义预示了她日后自我的扭曲、分裂走向[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控诉基列国的专制体制和对妇女的残害。基列国一方面是由大主教充当的宗教极权分子设想的美好理想国度,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女性的人间地狱。在基列国,女性不再是与男性平等或者傲视群雄的形象,而是变成统治阶级的统治对象。她们被迫失去工作,经济财产由丈夫保管,活动空间由工作退居家中,连高高在上的大主教夫人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度,女性被分为三六九等,分别为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穷人家的)经济太太,荡妇(妓女),其身份由不同颜色的衣服判断[9]。小说中游离于正常女性与妓女之间的使女们更是被剥夺了各种权利,甚至是自杀的权利,因为她们被看作国家的生育资源,行走的子宫。她们的名字是OF 加上她们服务的大主教的名字(比如OFFRED,意为福瑞德家的),女性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成为基列国的生育资源被大主教们分享着。语言承载并传达思想,但使女们的话语也要受到限制。在基列国里,使女们的语言被一板一眼地限制着,连使女们的见面寒暄用语也是由大主教们精心策划的。例如:一个使女说“祈神保佑生养”,另一个则回答“愿主开恩赐予”[10](20)。
综上所述,虽处于不同时期,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总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体与财产等方面受到男性的摆布和剥削,话语权缺失,处于边缘和“他者”的地位。
二、自我重建方式对比
玛丽和奥芙福瑞德都处于父权制社会下,失去话语权、成为男性的附庸品,但两人的自我重建方式却完全不同。
(一)追求消极自由的玛丽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指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包括极权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玛丽失败的自我救赎之路。
1.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主要通过施虐和受虐的方式来获得自由的假象,两者的根源皆是内心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施虐指主要通过控制和操纵他人来获得快感,目的是让他人产生痛苦感和依赖感[2](97)。受虐指由于自身的无力感产生的想要依赖权威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感。碰巧玛丽正是施虐狂和受虐狂的结合体,拥有支配欲和服从欲的双重变态心理,这也是玛丽的失败自我救赎的一个重要原因。
玛丽的施虐对象主要是家中的仆人。在后殖民主义时期,黑人主要为高高在上的白人输出劳力来维持生活,这也增加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玛丽刚到迪克的农场后,对周遭的一切感到无能为力,在压抑逼仄的房子里惶惶度日,孤独,无助。在受到丈夫迪克的压迫后,玛丽将自身的愤怒感发泄在了家中的仆人身上。她竟然因为浴缸的长时间使用导致浴缸发霉和附着的污渍,让仆人从十一点不停歇地刷到了下午三点多,她竟然忘了仆人要吃饭的需求[7](67)。玛丽的施虐倾向使得为她服务的仆人痛苦不堪。根据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分析,玛丽的施虐倾向是由于农场的恶劣环境使她有种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因此通过施虐来掩盖情绪,逃避孤独。玛丽在施虐的同时还伴有受虐倾向,其施虐者主要为丈夫迪克·特纳。农场的生活环境相较于城市差距甚大,在玛丽的积蓄在布置房间上用完后,没有多余的积蓄装天花板,甚至对周遭的一切无能为力时,便将希望寄予迪克身上,却等到了迪克的吼叫,甚至责骂玛丽用水过度的行为[7](65)。秦丹丹[11]指出女性成为附庸品后,容易把男性概念里的真理当作天经地义,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和独立人格。此时的玛丽孤独无助,认为摩西是能给她安全感的个体,以为依附摩西能够获得救赎,因此发生不伦之恋。由于当时白人和黑人呈二元对立的状态,直接导致了玛丽的悲剧。朱迪思·巴特勒认为在父权制下的女性仅仅充当了男人欲望发泄的工具和生儿育女的机器,是一个“无生命的、无形的、无法被命名的非物体(nothing) ”[12],因此玛丽的此种自我救赎方式显然是不成功的。
2.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机械趋同
弗洛姆指出,机械趋同是指在面对孤独感和恐惧感时,个体选择麻木自己或封闭自己来获得自由的假象,放弃自身的特性以与大众趋同,让自己与大众处在同一个群体中以驱逐孤独感,这是大多数人在困境中选择的出路,而且相对于极权主义,这种方式较为温和[2](123)。在城里上班的玛丽有着可人的工资,经济独立,快三十岁的她依然梳着少女的头发,而且未曾想过结婚,这是玛丽本我的体现,但是玛丽偶然听到朋友们的议论后,为了和大家看起来一样,她将头发上的缎带取下,并且开始寻找可以将自己嫁出去的男人[7](33),这也预示着玛丽日后自我救赎的失败。迪克在经营农场方面的能力欠佳,使得农场频繁处于破产的边缘,玛丽偶然看了农场帐单后,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但每次在农场稍微有点起色后便退出经营。究其原因,是玛丽骨子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祟。玛丽自幼生活在父亲挣钱养家、母亲操持家务的家庭里,到了农场后,他们的朋友斯莱特夫妇的生活也是如此,可以说,玛丽的父权思想坚不可摧。因此即使是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刻,舍弃自己的能力和棱角的玛丽依然选择回归“群体”。玛丽的机械趋同思想使其经济上更加贫困,其精神生活便可想而知,这又会使玛丽陷入新的孤独感和恐惧感中,注定了自我救赎的失败。
3.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破坏欲
破坏欲是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的内在冲动,它旨在消灭一切必须抗衡的对象[2](119)。弗洛姆认为,由于长期积压在内心的孤独感和无力感无法释放,主体就会采取破坏行为来释放自我内心的消极情绪,与极权主义不同,破坏行为具有时间持续短,破坏力大的特点,破坏欲后果严重,比如当今社会的仇富、自残、吸毒等行为。因迪克生病,玛丽不得不去田地照看。她拿着鞭子训斥黑人,甚至用鞭子在黑人摩西的脸上留下了伤疤,在闷热狭隘的空间里积蓄的孤独感和焦虑感终于在广阔的田地爆发,此时的玛丽充当着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她厉声斥责黑人,甚至要克扣黑人的工资,其口气与她的父亲没什么两样。在父权制社会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玛丽的孤独感终于在男性的身上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当玛丽又回到属于女性的空间-狭隘的铁皮屋时,孤独感和无力感重新袭来。
因此,在父权制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情况下,陷于困境的玛丽并未采取创造性的劳动和爱,相反,采取逃避自由机制使自我愈加分裂,也为自身的悲剧埋下祸根。
(二)追求积极自由的奥芙福瑞德
沦为基列国使女的奥芙福瑞德同样生活在父权制性别二元对立的社会中,以奥芙福瑞德为代表的使女们的生存地位则更加的低微。奥芙福瑞德被迫与丈夫和孩子分离,充斥着孤独感和焦虑感,在基列国充当生育的工具。同样是陷入以父权制为背景的困境中,奥芙福瑞德却选择了爱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化解困境,完成自我救赎。
弗洛姆认为唯有积极的自由才能实现个体的统一,即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劳动获得[2](175)。弗洛姆在其专著《爱的艺术》中教会人们如何用爱化解孤独,包括爱自己和爱他人。弗洛姆强调爱的本质是给予,给予本身能带来快乐[13]。基列国严密的权力运作机制仅仅规训了奥芙福瑞德的身体,她的精神是属于自己的。首先,奥芙福瑞德爱自己,身处困境中的她时刻保护着自己。在采购路上与同伴窃窃私语,假装被嬷嬷驯服等行为都保护了她个人的人身安全。其次,奥芙福瑞德也爱他人。虽处于“边缘”地位,奥芙福瑞德依然关心他人,在红色感化中心安慰帮助崩溃的珍妮,甚至帮助具有反抗精神的好友莫伊拉逃离基列国的控制,并且请求去“荡妇俱乐部”作为五月花(反基列国的救助组织)的信息运输者[10](235),为自己的逃离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父权制的基列国内,奥芙福瑞德通过爱自己和爱他人完成自我救赎,最终脱离困境。
三、相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
多丽丝·莱辛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虽未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不可否认,她们都是伟大的女性主义作家。多丽丝·莱辛笔下《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虽意识到自身处于困境,并且曾经有过逃离农场回到城市的经历,终因拗不过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重返铁皮屋内得过且过,怨天尤人,对于外界的压迫既无心理反抗,更无行动觉醒,最终难逃厄运,落得被自己的情夫所杀的下场。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将《使女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奥芙福瑞德塑造成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沦为使女后的奥芙福瑞德在心理上进行反抗,仇视基列国的种种不公。并且行动觉醒,比如与五月天的联合,与司机尼克密谋逃跑路线等。最终奥芙福瑞德在他人帮助下完成了自我救赎,逃到了加拿大,重获自由,将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作为对基列国的残暴以及种种变态行径的指控。
结 论
本文从弗洛姆的自由观视角出发,结合作品《野草在歌唱》和《使女的故事》研究了女性的自我重建,得出以下结论:父权制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品,孤独感和无力感充斥身心,在这种困境下,如果追求弗洛姆自由观中的消极自由,屈从此种心理机制,得过且过,试图躲避束缚,只会给自身造成更大的困扰;相反,弗洛姆自由观中的积极自由启发人们利用爱和创造性的劳动来驱逐孤独感和无力感,追求积极自由使自身与外界取得联系,重新唤醒自身生活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最终完成自我救赎。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体制不断完善,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在这同时,个体反而容易陷入孤独感和无力感,此时我们更要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劳动完善自我,追求积极自由,学会爱自己和爱他人,在困境中完成自我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