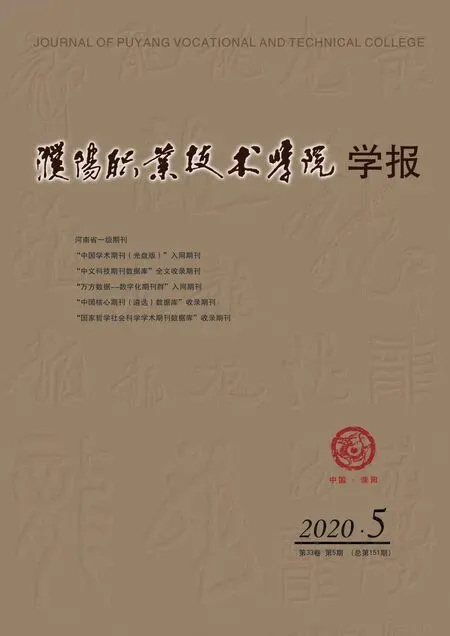清华简《系年》中的晋吴邦交
李 殊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晋、 吴两国的邦交是关系春秋中后期全局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与第二十章的内容主要讲述了晋吴、 晋楚邦交关系的变化过程,弥足珍贵。 关于巫臣使吴的时间,《系年》与传世文献《左传》记载不一,本文第一部分尝试对此做一探讨。 自晋景公始, 晋主动与吴建立邦交关系,确立 “联吴制楚” 的战略方针,至吴国灭亡,晋吴邦交随之结束,期间历经一百多年。本文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从晋景公至晋定公期间各个阶段晋吴邦交的内容与变化,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
一、吴伐郯与巫臣使吴时间
史籍多载巫臣使吴在鲁成公七年, 但早有学者对此存疑。 杨伯峻先生就提出巫臣使吴或在鲁成公六年,他推测:“当年使吴,当年教之车战,吴当年伐楚、入州来,使楚七奔命,未必见效如此之快。或巫臣使吴在去年。 ”[1](912)碍于史料短缺,无法得到进一步佐证。
清华简《系年》的出版,使这一问题被重新探讨。《系年》第二十章曰:“晋景公立十又五年,申公屈巫自晋之吴,焉始通吴晋之路,二邦为好。 ”[2](186)晋景公十五年,为鲁成公六年(楚共王六年、吴王寿梦元年)。 《系年》的不同记载,使近年许多学者都支持杨伯峻先生的观点,认为巫臣使吴在鲁成公六年,而吴对楚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鲁成公七年。
但笔者认为, 杨伯峻先生言吴国军事崛起速度太快,这是因为吴国自身的实力本就不容小觑。早在春秋前期,吴国在与齐桓公的对抗过程中,已展现出相当的实力。即使是在楚国实力强大的楚庄王时期,也未能将吴国完全收服。 所以,巫臣使吴当年,吴国攻楚便势如破竹,是有前期的实力作支撑的,吴国勃兴绝非单纯倚靠晋国的这次援助。 而且,吴国伐楚,只是挑衅,并非大规模与楚作战。加之楚国此时正陷入两面战争的泥潭,无暇抗吴,这是此时吴国得以成功伐楚的一个重要因素。故笔者认为,巫臣使吴与吴伐楚、入州来等军事行动发生在同年也并非不可能。
鲁成公六年为寿梦即位元年,据《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记载,这年,寿梦 “朝周。 适楚。 观诸侯礼乐”[3](10)。又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3](10)。
鲁成公七年,吴始见于《春秋》,即言其伐郯之事。吴国之势至伐郯始渐张。鲁季文子忧愤疾呼:“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1](909)
史籍记郯国之事甚少。 郯,已姓国,子爵。 杨伯峻先生言:“郯国故城在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二十里。 ”[1](739)鲁宣公四年作为鲁的属国始见于经传。 其时鲁、齐欲平莒、郯二国之怨,因莒不肯,鲁用兵于莒。 鲁成公七年,吴伐郯,郯与吴成。 鲁成公八年,晋士燮会齐、鲁、邾之师伐郯,“以其事吴故”[1](918)。 可见,郯在服吴之前随鲁从属于晋。 鲁昭公十六年,郯与徐、莒参加齐国的蒲隧之盟,则郯又从齐。 鲁哀公十年,吴会鲁、邾、郯伐齐。郯从属于吴。吴灭后,郯又服于越,最终为越所灭。
巫臣使吴的时间,关系到吴伐郯动机的不同。若其通晋吴之交在鲁成公六年, 吴于次年伐晋之盟国郯国是何原因?
张志鹏猜想吴伐郯 “大概为检验用新方法训练的军队的战斗力”[4](83), 从而为接下来对楚展开军事行动作准备。他进一步推测巫臣假道于莒入吴,也是为交涉伐郯事宜。 交涉无果,故而伐郯。 该理由未免有些牵强。若事前已与晋建交,并接受了来自晋的恩惠,郯国此时又无叛晋之迹象,吴国为何要选择晋之弱小盟国作为练手对象呢? 不过,鲁成公八年,晋虽与吴继续建交,晋大夫士燮仍联合齐、鲁、邾之师征伐新与吴成的郯国。可见,吴伐郯是与晋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 晋国在联吴的同时,又抑制吴国北上,这是晋国维护霸权的表现。
更多的观点认为,吴伐郯是为楚国助威。在吴伐郯的同年秋,楚子重伐郑,晋楚战争一触即发。 故吴恩培先生言:“此举,吴国显为受楚指使,北进以威胁鲁国,从而牵制整个晋国集团。”[5](38)则此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又为吴作为楚的属国牵制晋的属国, 为楚伐郑助攻。吴在与晋建交前一直作为楚之盟国,但说这次军事行动是受楚指使,为楚伐郑的前奏,则有待商榷。 因为自楚庄王盟吴、越而还之后,并没有吴国参与楚国军事行动的记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吴伐郯是其北进战略的一次实践。 童书业先生认为,晋、齐、鲁、邾四国伐郯,《左传》“以其事吴故”[1](918)之说自相矛盾。 吴国伐郯是其主动打通晋吴通道的一次行动。 在原通道莒道被楚国切断后, 晋主动伐郯,“盖欲以郯为通吴之路耳(或是时郯畏楚,不肯为吴、晋之通路)”[6](79)。 吴恩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采取了童书业先生的观点,其云:“关于吴伐郯的原因,或系晋、楚争霸政治格局下代理人战争的延续; 也可能是吴国为打通与中原国家的联系通道。 ”[7](32)王晖先生推断吴伐郯是为巩固北方领地,“郯国与柤邑接近, 吴寿梦这次伐郯国后,结盟而退,大概只是为了胁服郯国以巩固吴北方柤邑一带的领地罢了”[8](66)。
吴伐郯是为北进,这种观点是笔者所认同的。寿梦是一个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君主,其即位之初便赴中原考察礼乐,正是其渴望摆脱蛮夷之邦的身份,进入中原政治舞台的体现。 吴、郯国土接壤,吴欲北上,郯国本就容易作为其首要攻击目标。 而此时,鲁正奉晋令伐宋,又会师救郑,给吴伐郯造就了一个绝佳时机,吴攻鲁不备,而使郯服,尝试迈开北进的第一步。
故笔者认为, 吴伐郯是寿梦在先辈奠定的基础上,将吴国势力范围逐渐向北扩展的初步尝试。巫臣使吴应在吴伐郯之后较为合理。 寿梦于此次伐郯初露锋芒后, 这一新兴势力立即引起了巫臣及晋国的注意。晋国自然不愿意再多一个敌手。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吴国有发展强大的愿望与实力,巫臣顺势使吴,复仇之余,帮助晋国实践 “联吴制楚” 的战略方针,造就了吴楚相争、吴晋为好的新格局,吴国也由此进入大发展时期。
若巫臣使吴在鲁成公六年, 那吴伐郯之事暂时还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系年》应有其他的史料来源,也不可轻易忽视。
二、晋吴邦交关系的内容与变化
(一)巫臣使吴,晋吴建交
晋景公时期,晋楚争战胶着,在巫臣的推动下,晋国确立 “联吴制楚” 的战略方针,吴晋始通。《系年》第十五章云巫臣 “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叛楚”[2](170)。 晋景公为促进晋吴友好,接连两次派巫臣使吴,留巫臣之子狐雍在吴国任行人一职。 《系年》第二十章载:“二邦为好,以至晋悼公。 ”[2](186)
吴国此时本就渴望与中原国家加强联系, 故晋国推行 “联吴制楚” 战略时,寿梦即作出积极反应。一个国家要发展强大, 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方针。吴国在面临北上还是西进的战略选择时,欣然接受晋国的橄榄枝, 既北上与晋及其所领导的中原诸侯为盟,进入中原文化圈,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又南下在晋国的帮助下与楚为敌,扩大自身的势力。不难理解,此时的吴楚、晋吴,就如同先前秦晋、秦楚的邦交走向一样,都是远交近攻之策的实践。吴楚边界东西相接,吴国要想强大,首先面临的阻碍就是楚国。若此时选择北上,与中原为敌,不仅对发展无益,反而易使自己陷入两面为敌的困境。
吴国在晋国的帮助下伐楚大捷,令楚令尹子重、子反 “一岁七奔命”[1](912),晋国 “联吴制楚” 初见成效。巫臣使吴次年,双方初始建交,晋士燮却会合齐、鲁、邾之师伐郯。借伐郯之事,晋国向吴国传达了一个信息, 即双方的联合是以吴不得北上侵犯晋国的势力范围为前提的。 晋召集诸侯会盟于蒲, 始邀吴来参盟,而 “吴人不至”[1](921)。 此后,吴晋联系骤然减少,两国再次会见竟在六年之后。
这一阶段吴晋联系中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晋寻求与楚弭兵。 晋自景公晚年,在开启吴楚第二战场的同时, 也在积极寻求与楚国的和平邦交。 晋楚息兵,晋吴联盟之事故然先行放置。
第二,道路难通。 楚国意识到吴国对自身的牵制,开始着力切断晋吴联系的通道。 鲁成公九年,楚伐莒, 切断晋吴之间的首条通道, 晋吴联系受到阻碍。
第三,吴国修养生息的需要。吴接连伐楚、伐巢、伐徐,逼入州来,在使楚国遭受打击的同时,对自身也是一种消耗。如何巩固胜利成果,是吴国此时面临的一大要事,故吴国没有继续对楚展开攻势,也无暇与晋会盟。
晋厉公即位之后,也没有与吴加强联系。晋继续派使与楚弭兵媾和, 成功弭兵之后, 又忙于与秦交战。 直至鄢陵之战爆发前,方合鲁、宋、郑、卫等诸侯会吴于钟离,吴国与会,正式加入中原伐楚同盟,这也是吴与中原国家正式相会的开始。 《左传》成公十五年记载为 “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1](958),晋吴双方的交往由此得以重新密切起来。
鄢陵之战,楚国战败。舒庸趁机叛楚,“道吴人围巢,伐驾,围釐、虺”[1](989),晋国 “联吴制楚” 再见成效。楚灭舒庸而没有伐吴,吴楚之间虽未因此爆发战争,楚却开始将目标盯紧至宋彭城,再度反制晋、吴,而新理政的晋悼公则将晋吴联盟推至一个高峰。
(二)悼公复霸,晋吴联盟
联吴政策是悼公复霸的关键一环。晋悼公时期,吴晋联系空前紧密。晋国继续拉拢吴国,吴改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会盟。 晋吴联系紧密之时,正是晋楚争霸、吴楚争强之时。 楚国切断晋吴联系的通道,对吴化守为攻。 晋国则将吴国纳入以晋为盟主的中原集团,先后举行鸡泽之会、戚之会、柤之会、向之会以修吴好,把楚国作为共同防范对象。
楚伐莒之后,彭城成为吴晋往来的必经通道。晋悼公初即位,楚国便抓住机遇,攻宋彭城,置五大夫,驻守三百乘。晋楚之间因宋、郑再起争端,互不退让。晋卿韩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1](1000)楚在令郑制宋的同时,又抽出手来简师攻吴。 鲁襄公三年,楚子重帅师伐吴。这是楚经过精心准备,首次对吴展开战略攻势。 钟离—州来—群舒是楚国固守的一条重要弧形防线,而现在吴国正逐渐突破这条防线,继灭舒庸之后,楚国最终将利剑直指吴国。
面对共同的敌人,晋吴双方结成战略联盟。鸡泽之会,悼公专派荀会逆寿梦于淮上,可见晋国对吴国的重视。但此时正逢楚吴相战,故寿梦未至。但后来,吴又专门派使者解释道歉,“且请听诸侯之好”[1](1034)。于是,晋使鲁、卫先会吴于善道,继而合诸侯会吴于戚,吴国成为晋与楚争陈的得力盟友。 鲁襄公十年,晋再次组织柤之会,《系年》第二十章则记载柤之会同年,即 “悼公立十又一年,公会诸侯,以与吴王寿梦相见于虢”[2](186)。 整理者以 “虢”“柤” 为一地。
晋此次会盟,欲灭偪阳予宋,实是为反制楚国,继续加强晋吴联系。正如晁岳佩先生所言,晋国此举是 “为了确保北方集团东南屏障的安全和吴、晋联系的畅通采取的重要举措, 它对晋国实现战略反攻计划和悼公重新取得霸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8](79)。
晋国在悼公时期,一面多次与吴国会盟,紧紧将吴团结于中原反楚联盟;一面在知罃的建议下,采取疲楚服郑的战术。 楚接连失利,不敌于晋,晋国得以复兴霸业,吴国在此期间既通于上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又在伐楚战争中占得优势,逐步振兴强大。
(三)晋楚弭兵,晋吴疏离
悼公之后,晋吴联系明显减少,吴国鲜有参与以晋为主导的中原会盟的记载。晋楚弭兵之会,吴国没有出席。 弭兵之后,吴国则开始主动拉拢晋国,但晋国对 “联吴制楚” 显然已不如从前热心。
晋平公即位初期,晋吴双方仍以婚姻巩固邦交关系。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晋嫁女于吴的记载[1](1182)。之后,晋国对吴国不再热情拉拢。吴晋关系疏离的原因,笔者分析有以下四点:
第一,吴王寿梦死后,诸樊即位,自身还未除丧便趁楚共王之丧而侵楚,反遭败师。 吴与晋会于向,告败于晋,谋求合作。晋正重刑修德,以睦诸侯,吴伐楚丧,师出无礼,故晋借此没有帮吴敌楚,而是合诸侯伐秦。 此事或许伤害了诸樊对晋的感情,此后,吴与晋疏远。
第二,晋忧在齐。 平公即位前期,晋齐关系极为紧张,晋患在东夏。 悼公晚年,齐人已有叛迹,邾、莒并有二心,中原同盟开始离析。平阴之战,齐患暂定。栾盈之乱而齐患又起。 齐不服于晋,征战不断。 晋国多次盟会都为谋齐,故不召吴国与会。
第三,楚不敌晋。 楚康王在位前期,息兵整顿内政,晋楚、楚吴皆未起大的争端。 康王曾自言:“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 不谷即位,于今五年, 师徒不出, 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1](1145)楚国短暂息兵,于中原事务参与度降低。后虽有湛阪之役,又趁晋齐交战,与齐亲善,共同抗晋,但皆失利,未对晋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吴楚之间也暂时守平,十余年没有爆发战争。故晋 “联吴制楚” 之策暂时有所放缓。
第四,晋楚弭兵。宋之盟后,晋楚争霸战争消减,晋对 “联吴制楚” 更不热心。 如此则 “晋君少安,不在诸侯。 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1](1381)。晋平公耽于享乐,晋政多门,忙于倾扎争邑。 正如子产所言:“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1](1508)晋国执政卿赵文子、 韩宣子处事柔和, 不热衷于霸业斗争,务求 “诸侯无烦”[1](1334),对楚国会盟诸侯放之任之,与楚邦交中多处退让。晋将重心放置于对付北方戎狄,对 “联吴制楚” 已不热心。
而弭兵前后, 吴国对晋国的态度则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早在弭兵之前,吴王诸樊在位期间,于对楚战争中,吴已多处败势。 吴召舒鸠叛楚,最终落败。 诸樊攻巢被射杀,死于对楚战争之中。 吴国在对楚战争中的失利, 与其没有得到晋国的援助与牵制有莫大的关联。 由于晋吴久未同盟,二次弭兵之时,吴国未作为晋的盟国参会。“其政治地位成为了既不朝晋、又不朝楚的被边缘化的特殊国家。”[7](32)国际地位孤立。 弭兵之后, 战争的硝烟很快弥漫在吴楚之间,楚灵王新即位便迫不及待地合诸侯攻吴。《系年》第十五章云:“以至灵王,灵王伐吴,为南怀之行,执吴王子蹶由,吴人焉或服于楚。 ”[2](170)自鲁昭公四年起,吴楚之间针锋相对,连年征伐,互有胜负。至鲁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自杀,吴楚之间依然没有停战。这一阶段吴楚相争,晋国对楚国连年伐吴、灭陈、灭蔡等,不作干涉, 期间还与楚继续巩固宋盟关系, 续以婚姻,这些都不得不使吴国预感到危机。
吴王余昧即位后,迅速调整邦交政策,派贤公子季札出使,主动与中原诸国建交。 随后,又主动派使狐庸与晋互通,改变吴国所处的孤立地位。《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载:“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 ”[1](1315)而后,晋平公也派叔向作为专使至吴,受到吴国的热情接待。这是吴晋再度亲善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由吴国主动促成。
晋昭公在位期间,晋国依旧忙于连年伐戎。楚平王一改楚灵王好战作风,改革内政,息民养兵,改善内外关系。晋楚维持弭兵,吴楚同样暂时息兵。期间,鲁昭公十三年,也许是感到楚国国势渐兴,晋曾欲召吴与会,与吴国有所联系。平丘之会前,“晋侯会吴子于良”[1](1501),奈何道路不通,双方会盟失败。
晋顷公即位之后,其时,楚平王作茧自缚,致使内乱严重。鸡父之战,吴国战果辉煌,接连夺取州来、居巢及钟离三大重镇,楚国只有被动防守的余地,此事《系年》第十五章也有所记载。楚平王死后,吴欲趁丧伐楚。这次,吴国主动向晋报告。吴王僚 “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潛,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1](1649),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终晋平、昭、顷三世,晋吴交往多以吴国为主动。二次弭兵之后,晋对与楚争霸,以及经营 “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已显得极不热心,晋吴关系疏离。而吴国则为国家利益考虑,主动与晋亲善。在接下来吴与楚连年征战的过程中,晋吴有过互通,但未会盟。 晋对吴楚战争显得莫不关心,处于中立,未施援手,也未施障碍。总体来看,依旧不失为 “联吴制楚” 策略的成功之处。 一方面,使得晋国得以专注国内斗争,征伐鲜虞、陆浑之戎,靖齐、鲁诸侯,无南楚之忧。同时,又使吴国国际地位得以继续提升, 全力攻楚而无中原干扰、夹击之患。
(四)黄池之会,晋吴争盟
晋定公在位时期,晋、楚、吴三国的均势被打破,与晋国衰败成鲜明对比的是吴国霸业的奠基。 晋吴邦交关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晋吴争强。 这一切都以鲁定公四年的召陵之盟为转折。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其时,蔡昭侯受辱于楚,以其子及大夫之子为质,诚请晋国伐楚。 晋召盟于召陵,却出尔反尔,因求贿未得而拒绝了蔡国的请求, 由伐楚而转伐中山。 晋国在召陵之盟中无威无信,再无霸主雄风。 召陵之盟后,中原各国竞相掀起反抗晋国霸权的斗争,晋国霸业迅速坍塌:“晋因赵、范内哄,同盟解体,于是齐、郑、卫、鲁四国之好逐渐形成,晋遂失诸侯。”[1](1767)对此,《系年》第十八章云:“晋人且有范氏与中行氏之祸,七岁不解甲。诸侯同盟于鹹泉以反晋,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 ”[2](180)
值得注意的是,召陵共谋伐楚,却未见吴国的身影,且《左传》中也没有晋吴联合伐楚的记载。 而《系年》中则明确记载晋国参与了战争。《系年》第十八章曰:“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 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 晋师大疫且饥,食人。 ”[2](180)《系年》第二十章曰:“晋柬(简)公五年,与吴王阖盧伐楚。 ”[2](180)则在召陵之盟前,晋吴联军一直打到楚国方城之外,但晋国中途退出了伐楚战争。荀寅分析局势,指出晋国此时伐楚对自身不利。首先,晋国困于内灾,“水潦方降,疾虐方起”[1](1710)。 《系年》云晋伐中山时出现了“大疫且饥,食人” 的悲惨状况也可证此。 其次,国际形势也不利于晋。 晋国连年征伐鲜虞还未取胜,此时伐楚容易导致南北两面受敌,最终 “无损于楚,而失中山”[1](1710),齐国也会趁机对晋不利。 再次,自弭兵于宋之后,晋国自身一直坚决维护弭兵成果,避免与楚国正面冲突。 此时若继续伐楚,破坏弭兵局面,责任皆将归咎于晋,晋国 “弃盟取怨”[1](1710),于自身无利。最后,晋国已对争霸战争不再热忱,而吴国则相反。若晋吴联合成功打击楚国,得利者为吴而非晋。吴之厚,晋之薄,吴国在淮域独大,接下来必然会北上威胁中原,这是晋国不愿意看到的。
这次会盟是吴晋关系破裂的前奏。 蔡国投晋无望,便又奉吴为主,与吴结盟。 吴国本就一直在等待时机,遂即与蔡、唐联军迅速伐楚,《系年》第十九章云:“陈、蔡、胡反楚,与吴人伐楚。”[2](184)柏举之战,吴入郢都,楚几亡国,诸国震惊。伐楚大捷之后,吴又伐越,取得夫椒之胜,吴国国力达到全盛。蔡忠心事吴,越臣服于吴,陈国背楚亲吴,吴国取代楚国成为淮河流域的新霸主。 淮域得志之后,吴北上寻盟诸小国,不服者则攻伐,相继使鲁、邾、宋、卫归服于吴。 紧接着,吴又与齐争强,实现 “将有大志于齐”[1](595)的既定目标。
同时期, 晋国正由赵简子掌政。 在先前赵氏与范、中行氏内斗时,齐、鲁、郑、卫都曾站到赵氏的对立面。 在吴北上攻伐诸国时,赵简子不予干涉,并且也有侵伐齐、卫的军事行动。 一方面是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也与赵氏确立 “北进战略”,无暇顾及有关。晋吴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暂时还未站到对立面。
吴国所向披靡, 大败齐师于艾陵之后, 几已成霸。诸国之中只剩晋国是其霸业的最后阻碍。双方并未通过战争一决雌雄,而是在黄池之会中,争歃血先后。 《系年》第二十章记载:“阖庐即世,夫差王即位,晋简(定)公会诸侯,以与夫差王相见于黄池。 ”[2](186)并未记载盟会细节。传世文献中则记载黄池之会中,吴晋兵戈相向,赵简子代表晋国与吴争长,并与吴王订立盟质。 但关于主盟者最终为谁,文献记载不一。《左传》记 “乃先晋人”[1](1873),但有使晋先、先吴于晋的异议。《吴语》言 “吴公先歃”[10](615)。《史记》的记载自相抵牾。 《吴太伯世家》言晋先,但《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皆言吴先。 千百年来,悬而未决。
黄池之会并没有稳固吴国的霸业, 其连年北上征伐使越国得以喘息再起, 最终吴国于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 年)被越所灭。越灭吴时,远在晋国的赵襄子听闻,为吴降丧食,并派使者对夫差言吴晋黄池之会虽有盟誓, 但今吴国处于危难之中,“非晋国之所能及也”[1](1917),不予相救。 在越灭吴后,晋吴邦交走向终点,并为晋越邦交所代替。《系年》第二十章云:“越公句践克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 ”[2](186)
晋吴邦交始于巫臣使吴,大体经历建交始通、亲密会盟、各自疏离、争强争盟这四个阶段,双方交往以 “制楚” 为核心,以互聘、会盟的和平方式为主。 前期,在晋楚争霸战争激烈之时,晋吴邦交以晋国为主动,是为与楚争霸服务。中期,在晋楚弭兵之后,晋国不再热忱于争霸,晋吴邦交反以吴国为主动,吴国积极与晋国为首的中原联盟保持交往, 为与楚争战做外交保证。 晚期,召陵之盟、柏举之战后,晋、楚衰败而吴国独强。 吴北上争霸,虽未与晋爆发军事冲突,但双方邦交关系已经破裂。 黄池之会,吴与晋争先,但双方依旧订立 “好恶同之”[1](1917)的 “友好” 盟约。 越国灭吴,晋未助援,而后与越为好,晋吴邦交为晋越邦交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