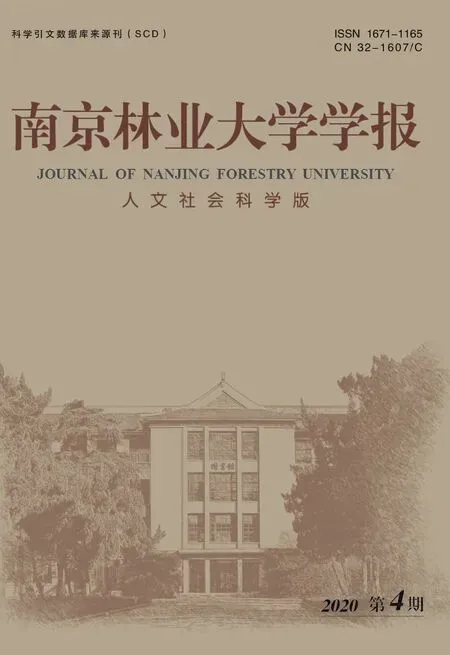论后疫情时代全球生态政治的现实主义转向*
刘 魁,李 玉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当前正在影响全人类生存的新冠疫情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由诸多因素引发的全球生态危机。基于不同的国家政治、经济、伦理与生态立场,国际社会围绕其应对策略产生了严重分歧,形成了生命主义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主义与生态主义之争的困境。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治理方式的弊端在新冠疫情面前尽管已经暴露无遗,然而西方社会对于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霸权主义的国家政治以及经济主义的发展政治的追求并未减弱。鉴于此,我们认为,20世纪后半叶基于全球生态危机而形成的后现代生态政治,盲目消解国家主权与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忽略了启蒙精神的巨大现实影响,实际上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政治。经历此次疫情的冲击,21世纪的全球生态政治将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即转向一种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又具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与国家主权意识的生态政治。至于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所期待与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态政治设想能否成为现实,还有待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一、当前疫情频发的生态学反思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一方面在科技创新与生物医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另一方面也不断遭遇新的疫情,例如,2002年的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9年的“僵尸鹿”以及2019年末发展至今的新冠肺炎等疫情。在这些疫情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最大,波及全球。各国政府、科学界与社会公众纷纷从不同角度探讨疫情产生的根源,寻求对策。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未就其产生的原因达成共识。从生态学视角来看,目前影响最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野生动物滥食说、自然报复说、气候变暖说和自然节律说。应该承认,这四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存在证据不充分的问题,以致难以形成有效的防治对策,因此需要认真反思,综合应对。
(一)野生动物滥食说
这是目前社会上最为流行的看法。它认为,此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滥食野生动物,特别是滥食蝙蝠或穿山甲、果子狸而引起的。据医学研究,蝙蝠体内存在数百种病毒,是病毒的自然界原宿主,而其他野生动物如穿山甲、果子狸等在与蝙蝠的接触过程中或通过其他途径会感染病毒,成为病毒的中间宿主。通常情况下,与病毒和谐相处的野生动物不可能主动将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但是“如果人类不当地对待野生动物”,如人类捕杀、食用蝙蝠、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则很可能会导致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最终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有证据表明,具有地域性的疫情,如“2002年暴发的SARS、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均“与蝙蝠有关”。[2]蝙蝠很可能也是此次新冠疫情的自然界原宿主,中间宿主则可能是穿山甲或者果子狸。
应当承认,野生动物滥食说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然而不可否认,这种观点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并没有找到新冠病毒从蝙蝠到穿山甲以及传染到人类的完整、清晰而明确的路线图;其二,在新冠疫情流行之前,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吃过蝙蝠、穿山甲或者果子狸等野生动物,但是,并没有暴发严峻的新冠疫情;其三,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此次新冠疫情危机是有多个源头的,自去年夏天以来,各种不明肺炎就开始在各地流行,亚洲与欧洲、非洲、美洲的疫情源头也不尽相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地区环境保护与动物保护意识较强,并不普遍存在滥食动物的问题,但是仍然出现了疫情大流行问题,这些令人难以理解。
(二)自然报复说
这种观点在哲学界颇为流行。它认为,此次疫情是大自然以病毒为工具向人类展开的报复。自然生态系统由人类、灵长类等高等动物、其他动植物、微生物等组成,事实证明,作为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病毒先于人类在地球上广泛存在,“在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3]。在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有限的前工业革命时代,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人类、其他动植物等各自生活在独立的领域,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中。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人类为追求利益、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拓展其生存空间,无休止地开发自然地域,侵犯动物、病毒的独立生活空间,导致野生动物向人类生活空间迁徙,人类的生活空间里出现更多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就是大自然对人类无休止开采行为进行报复的产物。
法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明确指出,新冠病毒并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由于“资本改造了自身再生产的周边环境”导致的人为灾害,是“大自然对四十多年来所遭受的粗暴而残忍的虐待给出的报复”[4]。处于失衡状态的大自然为维持自身的平衡,发动病毒向人类展开报复。因此,为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性、稳定性,许多人主张应当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减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给予野生动植物应有的独立生存空间,将人类的活动、经济发展的速度限制在自然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保持经济发展与自然系统的平衡、稳定。
不可否认,自然报复说虽然也有一定的根据,但它是建立在人类大胆的猜测基础上的,只能算是一个隐喻。大自然毕竟是非生命存在物,没有情感,没有意志,何来报复?即使新冠病毒是因为人类的行为侵犯,为什么是在2019年冬天这个时间段暴发,为什么有些国家与地区疫情严重,有的地方疫情轻微,对此,自然报复说也难以解释。
(三)气候变化说
这是气候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气候界认为,新冠疫情与全球气候变化有一定关系。王琦院士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为病毒的生存、繁衍、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不仅“为病毒的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提供了良好环境”,如传播疾病的蚊虫、携带病毒的鹿鼠等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存活时间更久、繁殖速度更快,而且也引起许多动物的迁徙,导致这些动物将所“携带的微生物传播至其他地带”,进一步扩大病原体与传播媒介的分布区域。[2]赵斌教授指出,“病原体、宿主和传播环境”是大多数传染病的三种不可缺少的因素,气候变暖“可能通过影响病原体、媒介生物、宿主及其生存环境来影响传染病”,进而影响“疾病暴发的时间和强度”[5]。此外,气候变暖不仅有利于病毒的生存,同时也为其发生基因突变提供了条件。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也认为,这场流行病与当前的气候危机具有相关性,此次疫情的防治“正在预备、劝导和鼓动我们为气候变化做准备”[6]。因此,从人类生存的长远角度考虑,我们在进行防治新冠疫情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气候变暖,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节能减排,开发清洁能源。
毋庸讳言,这种看法的优点在于注意到了新冠疫情暴发的气候条件,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全球气候变暖并非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新冠肺炎要到2019年暴发呢?为什么各国情况不一呢?对此,气候变暖说也难以给予圆满解释。
(四)自然节律说
这是中医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它认为,所谓SARS、新冠疫情之类疫病是在一个气候周期内发生的自然现象,与异常的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地理环境有关,五运与六气之间的相辅相成与制约关系能自动调节气候变化,应对疫情。自然界具有自稳定机制,可以自动调节气候演变中出现的不稳定状态,如冠状疫情表现为三年化疫,其间出现的相关流行病三年内也会在自然的调节下自行消失。根据这种自然节律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瘟疫的一种,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变化现象。从整体层面上讲,它与一个甲子气候周期的“天时气化规律”有关,局部地区的“异常气候条件”[7],如湿、热等,也为疫病的暴发提供适宜的条件。换句话说,自然环境的非时之气乖戾等是疫病发生的重要外因,因此,我们在医学上可以运用三年化疫机制预测疫情的发生、发展趋势,做到科学防治。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医学根据与气候学根据,但这种类型的自然节律说是针对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而建立的本土性医学理论,具有本土的局限性,能否突破地域限制推广至国外,还面临很大的质疑。此外,根据这种以古代中医为基础的自然节律说,新冠疫情属于寒湿疫,按照气候演变的规律,应该在5月中下旬结束,可是目前到了6月份,美国乃至全球的疫情还没有被控制住,令人困惑。
一句话,上述四种假说都面临一定的理论困境,难以完全解释当前的新冠疫情,需要拓宽思路,系统考虑,综合应对。从人类文明史视角看,当前疫情频发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大发展而导致的生态失衡的结果。正如法国医学教授让-路易·维尔代指出的,传染病的流行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人与周围微生物环境关系的结果”,无论是微生物,还是人类、气候条件等,都处于不停发展变化之中,导致人与其周围微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建立起新的平衡”[2]。当前频发的疫情,除病毒本身的因素外,也与洪涝等自然灾害、极端异常的气候、过分开发土地、城市化建设等因素破坏了生态平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病毒或者病原微生物是导致当前疫情暴发的直接原因,气候变化及其周期性为疫情的频发提供了温床与机遇,而人类的活动,如为发展经济入侵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以及人类滥食野生生物则是疫情频发的间接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当前的疫情危机,现在许多人一味谴责工业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工业文明的发展也是基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而发展的,不可遏制,各种病毒也不会因人类停止工业发展而不再产生,对此,我们只能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由于当前的全球疫情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引发的生态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生态政治的视角寻求对策。
二、启蒙精神与当代生态政治面临的三大冲击
面对当前严峻的全球疫情危机,各国需要的是团结协作、共渡难关,建立在命运共同体意识上的平等合作意识和超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全球政治合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于全球抗击疫情不仅不给予积极合作,反而制造种种障碍,对当前的生态政治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究其根源,还在于启蒙运动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巨大历史影响,以致当前的全球生态政治遭遇霸权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主义的发展政治以及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的巨大冲击。
(一)霸权主义国家政治的冲击
由于启蒙运动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遗产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机构与人士,为了维护本国乃至西方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与文化霸权,对于全球疫情抗击不仅不给予积极合作,反而设置种种障碍:其一,对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全球抗疫斗争不仅不给予经费与道义上的支持与合作,反而进行各种不公正的霸权主义政治指责,甚至断绝经费支持、直至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致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其二,面对严峻的疫情,不仅不关心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反而公然提出“反对全球化”“美国至上”“去中国化”等霸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口号,反对全球合作,大力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政治,在政治、经济、技术发展与文化交流方面对他国设置种种障碍,对俄罗斯、欧盟、中东进行打压,迫使他国和盟友国在中美之间选择站队,甚至不顾盟友关系与外交准则,哄抢豪夺他国防疫物资;其三,对于最先面临严峻疫情危机的中国不仅不给予支持,反而落井下石,进行“政治污名”与民族歧视,甚至进行霸权主义的“法律滥讼”,引起各国正义人士的巨大愤慨;其四,在当前疫情危机的关键时期,不断从联合国的各种组织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公然倡导核威胁与外星空间战争,破坏全球和平。
(二)经济主义发展政治的冲击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社会从由宗教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走向了世俗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占统治地位的头等大事。
在疫情期间,一些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有意忽视严峻的疫情危机,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比如美国、英国、意大利、巴西等西方国家政府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不及时采用已被证实有效的防范措施阻挡病毒传播,导致疫情日趋严重。此外,为了发展经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顾气候变暖的严峻形势,有意放松过去的环境保护政策,鼓励开采石油、页岩气等化石能源,以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局势严峻。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甚至削减卫生医疗保健的资金预算,将这部分预算用于生产化石燃料,其环境保护署甚至“暂停了美国本土的环境法规申请,尤其是针对拯救重度页岩气污染工业的相关法规”[8],由此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三)自由主义生命政治的冲击
新冠疫情危机涉及个人自由与政府管制的关系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为了对抗政府等社会强势组织的独裁威胁,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成为西方国家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圣经”。即使政府与医疗机构为了防治新冠疫情扩散,保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也遭到了多方抵制与质疑。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就认为,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政治贯穿于个体生物性生命的生命政治,而最近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则是政府的阴谋。政府通过此次疫情试图将“例外状态”常态化,通过限制人们的自由,让人们长期生活在没有自由、令人恐惧、不安全的紧急状态之下,人们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追求所谓的生命安全,成为仅有赤裸生命的“神圣人”。政府所提出的保护法令会导致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政府让人们产生限制个人自由以追求人身安全的需求。[9]实际上,正如著名学者巴迪欧(Alain Badiou)指出的,管控措施是控制疫情传染的有效途径,因为除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等到病毒因缺少传染目标而消失”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人们遵守政府的要求和纪律不仅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同时也是对“所有易感人群提供了支持和基本保护”[10]。从人类整体所处的状况出发,“例外状态”并非国家的阴谋,实际上,政府只是病毒性例外的可悲执行者,政府所提出的隔离措施是对个人生命的保护,尽管个人会觉得隔离是一种对人身自由权利的限制。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这种对个人主权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生存在社会中的个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实,个人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干涉他人的权利为前提条件。而西方人们不自觉地“将自由、个人自治的权利和隐私置于社会和谐之上”[11],以牺牲个人生命安全为代价追求自由的行为实际上是置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无视社会集体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西方疫情泛滥的一个重要文化根源。
追根溯源,上述的霸权主义的国家政治、经济主义的发展政治和自由主义的生命政治之所以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巨大的市场,是因为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力。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已经从传统社会进入具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等特征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固然具有种种弊端,但是已经把人类带进了新的时代。虽然现代社会存在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分化和信仰危机等严重的问题,但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文化霸权对于经济发展的无尽追求以及对个体的主体身份自由的保护,一直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护身符,并且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疫情猖獗的全球危机时代,西方社会也不愿意放弃这种建立于启蒙精神基础上的护身符,除非有更合理的替代选择。问题在于全球目前仍然处于现代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时代,具有生态启蒙性质的后工业文明或曰生态文明还在建构与展望过程中,难以撼动工业文明的根本。可是,自20世纪60年代爆发全球生态危机以来,为了拯救人类,一些学者盲目倡导与追求全球多元化,反对国家主权政治,削弱国家主权,片面强调生态意识与生态责任,贬低个人的主体意识与身份自由,陷入了浪漫主义的政治冲动,忽视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意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冲动与公民对身份自由的极端重视,忽视了启蒙精神对个人身份自由的盲目崇拜,导致西方共同体意识、个人责任意识以及超越经济发展的信仰追求的削弱,从而促使夸夸其谈的全球生态政治在严酷的疫情危机面前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处境。
三、疫情危机与全球生态政治的现实主义转向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有许多学者设想,未来会出现长期稳定的跨国合作以应对生态问题,国家主权地位下降。然而,现实发展非常复杂。
首先,从国际组织对于疫情的应对效果来看,国际间的委托授权运转不良,不仅欧盟等国际组织在应对疫情中表现较差,无法调动各国达成一致行动,暴露出其能力不足,而且国际合作也变得支离破碎。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协调地缘政治的“世界政府”,“那些认为这场危机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被解决的信念,纯粹是异想天开”[12]。
其次,疫情危机之下依靠自由市场或个人主权无法有效维护国民的安全,而真正有效的途径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此可知,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即使是倡导市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也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行使政府权力,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正如巴迪欧所指出的,当前局势在社会秩序上会使国家“威权主义干预”[10]应运而生,迫使国家不得不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国家权力在保护国民生命安全中表现出其高效性。
再次,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来看,依赖科学技术进行生产要素全球性分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会适度放慢,欧美等国家认识到本国生产医疗设备能力不足,将其跨国企业迁至本国,并进行产业重组,这实际上是增强了国家的经济主权。因此,疫情危机呈现出的国际组织的软弱性、自由市场与个人主权的无序性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足都在提升国家主权,西方国家的主权意识可能会不断增强,但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自由主义的地位。
最后,国家主权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局限性。个人自由权并非不受约束与限制,在紧急情况下,个人主权表现出无序性,需要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个人行使自由权时也需要考虑适用范围,不能以危害社会集体利益为代价。同时,在衡量个人自由权与生命权时,西方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政府为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采取的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已经表明其对生命权与自由权的衡量,认可生命权高于自由权。尽管新冠疫情影响了自由主义国家的稳定性,西方国家对于自由主义与市场意识的迷恋并未减弱,如著名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的,可以通过“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13]关系的方式缓解新自由主义危机。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不会因生态危机而受到阻碍,也不会因国家主权的提升而动摇,而是会在新的约束框架内追求自由主义。
鉴于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国家主权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自由主义的现代价值追求,我们认为,未来的全球生态政治将会以生命共同体意识、国家主权意识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为基础,形成具有全球意识但不放弃国家主权,行使国家主权但不干涉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追求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不影响生命共同体意识,这样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达到三者稳定、平衡的新型生态政治。
首先,未来的全球生态政治必定是建立在生态学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基础上,倡导环境保护与生态和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主权与个体自由意识及其相关制度体系必须有助于拯救人类、保护人类,否则,就会违背人类的生存本能,就会因不符合时代需求而被抛弃。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国家是阶级政治的产物,在阶级存在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主权的核心地位还将存在很长的时间,只有当人类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国家才有可能慢慢被历史淘汰。虽然国家主权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国家主权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仍然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最后,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虽然不利于人类的生态拯救,但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毕竟是现代性的思想根基。只要现代性的价值追求还没有被历史淘汰,自由主义就难以被取代。不过,为了拯救人类的集体生存,个体的自由主义价值追求会受到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价值链的束缚与约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遭受了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思潮等的猛烈抨击与批判,在学术界有人断言现代性的危机,宣称后现代的来临。实际上,只要启蒙精神与工业化还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现代性就会继续存在。现代性的危机实际上只意味着现代性受到了来自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等方面危机的严重挑战,意味着人类进入了现代性的反思与探索阶段。
近来,有部分西方左翼思想家提出,面对全球新冠疫情,新自由主义由于其所具有的自由市场的无序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资金短缺等诸多弊端,在持续性的紧急状态下无法生存,很可能会灭亡,全球生态政治将会走向基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型生态政治。大卫·哈维明确指出,新冠疫情危机导致“资本无休止的螺旋式积累正从其内部的某个角落四面崩塌开来”,导致资本主义陷入严重危机状态,不仅美国将“整个经济进行社会化改造”[4],并出现逆新自由主义潮流而上的大规模政府干预,而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前所未有的干预政策,而这些政府干预措施实际上超越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权限。因此,哈维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措施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这场危机“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社会主义的想象力来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14]。齐泽克也指出,新冠疫情加速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进程,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世界秩序会走向更加温和、平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因为,“危机之下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新冠疫情将人们团结起来,增强人们的个人责任感,在地方也会出现以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为模型的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15]
我们认为,以哈维与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预言过于乐观。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目前采取的这些所谓反自由主义的措施,只是意味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在新冠预防对策问题上的严重失利,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还有一定存在空间与文化土壤,但是,目前毕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占据主导地位,能否出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生态政治仍是个未知数。况且,哈维以政府干预界限为根据划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齐泽克则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紧急状态下的“战时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解释。无论何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它们都是建立在颠覆或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革命基础上的。在目前的危急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诸如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措施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应对疫情的紧急策略,不可过于拔高。从短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新型冠状病毒也不会带来“病毒革命”。或许疫情危机为西方左翼思想家提供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实验场所,未来能否出现基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型生态政治,仍需要历史的进一步检验。
总之,21世纪生态政治的使命固然是克服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拯救人类,实现全球生态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新冠疫情危机给我们的巨大启示是:21世纪的未来生态政治将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将是一种基于全球生态威胁与启蒙精神的现实主义的生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