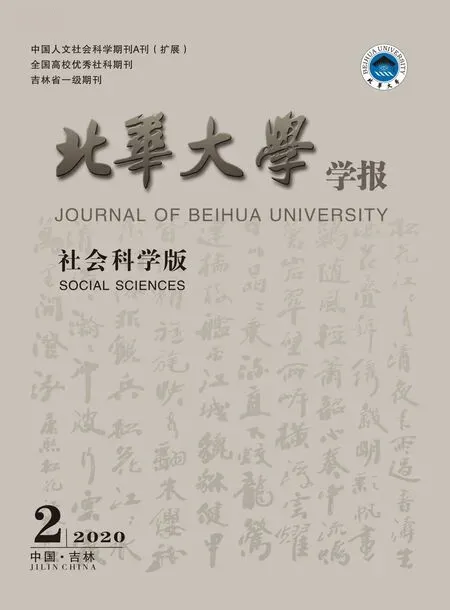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的理论与实践
王 奔
地方本科院校音乐专业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方向标和立足点,是培养未来音乐教育从业者正确艺术理论观点,进而指导他们的音乐教育实践活动。音乐学科特殊的审美视域定位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切入点,它既影响音乐教育从业者的世界观,又是他们的方法论。音乐艺术特殊的审美属性有抒情性、形像性、想像性、隐喻性、时间流动性,以及与其他艺术种类的结合性,等等。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紧密联系着音乐艺术特殊的审美属性来进行。音乐艺术所表现的所有审美属性都基于它固有的本质特征,这些审美属性只是音乐艺术内在本质特征的外化表象,而音乐艺术更有其深刻的本质内涵。音乐教育实施课程思政的改革如果没有深入触碰到音乐艺术的特殊本质内涵,就相当于失去了进行此项事业具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结果会导致课程思政实施的路径迂回曲折。只要正确认识音乐艺术的特殊本质内涵,就能解释音乐艺术所具有的审美属性和审美表象,也会使课程思政实施的路径变得方向明确。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里的一切理论与实践必须遵循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与规律。
音乐艺术的特殊审美视域包括:审美创造、审美呈现、审美欣赏。在音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中,这三者互相依托、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有着极为丰富的表现形式。音乐教育实施课程思政的目的,就是要深刻揭示这三者的本质内涵和客观艺术规律,按照客观艺术规律从事音乐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进步,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审美创造
审美创造是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审美环节。音乐艺术审美创造过程就是音乐作品的创作过程,它包含着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最关键的内容。音乐家富于高度情感智慧的审美创造,是课程思政教育活动重要的基础性内容。在探讨音乐艺术的审美属性以及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时,对音乐作品创作过程特殊性的研究至关重要。音乐创作规律同其他艺术门类创作的普遍规律一样,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创作方法与思维方式、创作灵感与情感积淀、创作逻辑与表达方式。但不容忽视的是,在音乐作品创作的过程中,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带有音乐艺术特殊的审美属性,即抒情性、形象性、想像性、隐喻性、时间流动性以及与其他艺术种类的结合性,等等。
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创作过程为例,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张藜(1)张藜(1933—2016),中国著名词作家。代表作品《我和我的祖国》《亚洲雄风》《山不转水转》等。,曲作者是秦咏诚(2)秦咏诚(1933—2015),中国著名作曲家。代表作品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我和我的祖国》等。。据词作者张藜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介绍:这首歌曲是先有曲调后填的歌词。张藜非常喜爱曲作者秦咏诚于1962年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一直有为其填上适当歌词的愿望。1984年初,词作者向曲作者提出按照《海滨音诗》的情绪基调重新创作一首适合填词和演唱的歌曲。(3)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创作过程参见李周立著,张藜注释《久别的人:张藜歌诗人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这首歌曲音乐部分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课程思政教育的重点内容。
虽然没有歌词的提示和表述,但是6—8节拍和直线式旋律线条,都具有畅快表白、直抒胸臆的特质。其欢乐活泼、真挚热爱的形象性特征,已经为审美受众界定了情感指向——这是形象思维的结果,用于表达对祖国、对家乡无比眷恋的深情。而乐曲发展所选择的“同头换尾”、重复、变奏的作曲手法,则是抽象思维的结果,用于保持乐曲情绪基调不变。这两种思维方式往往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讨论音乐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的目的,是要在音乐艺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改革的方式、方法。因为音乐家在创作中所使用的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与其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世界观和艺术观密不可分,所以音乐家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取决于其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时所选择的立场和角度。音乐教育课程体系中,无论是器乐、声乐、合唱、合奏等专业技能课,还是歌曲创作法、音乐欣赏、中外音乐史等基础理论课都包含异常丰富的课程思政内容。教师在课堂授课时理应深入讲解、挖掘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使用的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借以了解作曲家先进的艺术观,提高学生对音乐艺术本质内涵的认知能力和对音乐作品的鉴赏能力。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音乐部分的创作,是作曲家秦咏诚长达22年(1962—1984)情感积淀的外化表现,情绪基调早在创作《海滨音诗》时就已经形成,而这种对祖国、对家乡真挚热爱的情感,正是课程思政所实施的具体内容。相比之下,词作家张藜创作的歌词朴实无华、热情真挚,准确表达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热爱。虽然歌词以文字为载体,具有文学性,但是歌曲具有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审美属性:歌词通过文字表述使音乐旋律的审美取向更加明晰,音乐曲调则使歌词的文学语境更加具有抒情性。音乐与其他艺术种类的结合性这一审美属性,为音乐学科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歌曲这个音乐形式审美效果更加直接。歌曲作为一种体裁,在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里具有极强的大众性与广泛性。古人云“歌者,乐(le)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迴居诸乐(yue)之上。”[1]这深刻阐释了声乐作品最能够直接触动人的心灵! 课程思政研究重心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影响音乐家创作的艺术思维活动上,是因为艺术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刻体现在其艺术创作之中。音乐教育的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的实践里,全面分析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内容的责任重大。认真深入研究教育教学内容中音乐作品创作过程的艺术规律、特殊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这可以作为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路径之一。
二、审美呈现
审美呈现是表演性艺术门类(音乐、戏剧、电影等)特有的审美环节。课程思政教育实施需要在音乐作品与欣赏者之间,有音乐表演者(演奏或演唱)作为从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两者之间的媒介。英国著名音乐家亨利·伍德曾经在他的《论指挥》一书里写到:“音乐是写下来的没有生命的音符,需要通过表演给予它生命。”[2]音乐表演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课程思政实施中审美呈现的效果,进而影响审美欣赏的质量。仍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为例,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4)李谷一,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曾经首唱歌曲《乡恋》《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知音》《我和我的祖国》等。。歌唱家李谷一之所以能成功演唱这首歌曲,当然得益于她甜美的嗓音条件和高水平的演唱技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深厚的音乐修养和扎实的艺术功底。那么深厚的音乐修养和扎实的艺术功底从何而来?这主要来自于多年音乐艺术实践,来自于多年音乐艺术实践过程中对所演唱的歌曲作品思想内涵和情感类型的深入体会与研究。对音乐作品思想内涵和情感类型的深入体会和研究,能否与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相结合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音乐教育培养的目标是音乐基础教育的从业者,对受教者专业能力和文化素质有全面的要求。基础音乐教育从业者不一定是专业的音乐家,但却应该是一个富有爱心和人文素质的音乐教育受教者,同时他(她)又具备合格的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
音乐教育的教育目标虽然并非使每一个受教者都达到德艺双馨,但作为歌唱家,李谷一在音乐艺术审美呈现环节中所做的歌曲思想内涵和情感类型的深入体会和研究,却值得音乐教育在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探索中予以重视和借鉴。李谷一在考虑如何诠释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时,曾就歌词中个别语句的表达方式提出过具体意见,她与词作者反复讨论“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这句歌词是否应该改为“你用你那母亲的温情和我诉说”更合适一些?李谷一认为后者在实际演唱的艺术实践中效果更好。这说明在音乐艺术审美呈现环节里李谷一已经达到了“二度创作”的高度了。在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的审美呈现中达到“二度创作”的高度——当然是符合原作在审美创造中创作思想和理念的二度创作,是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的另外一条路径。在音乐艺术审美呈现中追求音乐表演二度创作的过程就是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的过程,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二度创作必须符合音乐作品原作的创作思想和创作理念,演唱(演奏)者必须深入触碰到音乐作品创作者内心的创作动机,才能体会和研究出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类型。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中的本质规律是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音乐创作者内心的创作动机必然是想要表现社会生活中感动他的事物。正所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3]225其二,二度创作是对音乐作品创作思想和价值评价的再一次升华,演唱(演奏)者从自身认知角度对音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加入自己的审美判断,丰富和完善了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二度创作的个性化特点使演唱(演奏)者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使音乐作品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其三,进行音乐作品的二度创作需要表演者以能够主动学习音乐艺术本质规律为前提,甚至是主动向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请教演唱(演奏)该作品时,应该如何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与情绪类型。二度创作是以表演者对音乐作品学习领会为基础,以表演者独立艺术见解和独特艺术处理为标志的音乐作品审美呈现。
三、审美欣赏
审美欣赏是音乐教育课程体系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课程思政教育各个环节中最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音乐教育专业技能课和专业理论课的教学实践首先以审美欣赏为前提。音乐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理念应该是首先学会欣赏美,然后学会表演美,最后才懂得如何去创造美。审美欣赏在音乐教育课程中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使之成为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受教者参与程度最高的审美环节。
在审美欣赏活动中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首先要符合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客观艺术规律,遵循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独特属性;其次要在整体艺术规律大视野内观照音乐欣赏的特殊性,利用整体艺术规律中普适性原理解释音乐欣赏中的个别审美现象;最后,在音乐欣赏活动中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要充分发挥艺术作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功能,使受教者在审美欣赏中获得审美愉悦。
第一,音乐艺术审美欣赏是因人而异的审美体验。关于审美欣赏中因人而异的审美体验,有一句西方谚语说得特别恰当:“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审美个体由于生活阅历、知识积累、个人观点和艺术理解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审美体验各不相同,这是审美欣赏环节中非常普遍的现象。音乐欣赏作为艺术作品审美欣赏的一部分,在审美体验中不啻也会有这种现象,而且还要更复杂一些: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里具有审美呈现的特殊环节,这使得同一个欣赏者在欣赏同一部音乐作品时,因为演唱(演奏)者不同的艺术处理会有不同的审美体验。音乐艺术联想性和隐喻性的审美属性,甚至使欣赏者在不同时期因为心境和情绪的不同,即使欣赏同一个表演者演唱(演奏)同一部音乐作品,其审美体验也会不同。所以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在审美欣赏环节中要正视因人而异的审美体验规律,既给予受教者极大的音乐联想和想像空间,以提高音乐欣赏活动的主动性、趣味性;又要界定音乐作品宏观的情绪基调和思想内容,以保证准确领会音乐作品的思想意义。例如在德国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5)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德国伟大作曲家,欧洲音乐史上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者,其《第九交响曲(合唱)》作于1823年。音乐欣赏活动中,音乐教育的任何教育阶段(从本科各年级、硕士到博士)都可以将其作为审美对象。因为这是一部堪称人类音乐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作品既有音乐形象的抒情性和戏剧性,又有音乐内容的思想性和深刻性。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恢弘的世界性命题出发,这部音乐作品则更有其深奥的哲学意义。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的路径要从不同的审美效果和审美体验入手,以期在音乐欣赏审美体验中找到审美主体的审美个性与审美共性的结合点。
第二,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抒情性特征。抒情性特征是音乐艺术最重要的审美属性,是音乐艺术“以情感人”审美效果的源泉,在课程思政教育实施中毫无疑问地成为重要途径之一。音乐艺术的抒情性特征潜移默化地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古人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60从这个角度上说,音乐既然是表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中突出高尚的人类普遍情感就要成为重点。在俄国著名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6)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俄国著名作曲家,其《第四交响曲》作于1877年。审美欣赏活动中,音乐艺术抒情性审美特征体现的极为完美。欣赏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时必须提到冯·梅克夫人(7)冯·梅克夫人(1831—1894),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庇护人,曾和柴科夫斯基保持多年的友好通讯。见逸文译《柴科夫斯基论音乐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他在1878年2月17日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谈到他的《第四交响曲》时说:“这纯粹是个抒情的过程。这是用音乐来倾诉激动的心灵。从本质来说,内心的感受借音响而流露,就像抒情诗人以诗句抒怀一样。区别仅仅在于,音乐具有更加无比强大的手段和细致的语言去表现千百种不同的内心情绪因素。”[4]1因为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特殊的感情,他把他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并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音乐艺术的抒情性特征能塑造人们高尚的品格,这极大丰富了课程思政教育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于高尚道德情操之上,而音乐艺术的抒情性特征表达的就是人类普遍的高尚道德情感。世界上极少有像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这样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微妙又非常复杂,微妙复杂到似乎只有深刻理解柴科夫斯基的交响音乐,才能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极其富于感染力,它触动着人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而无法用语言文字去表达。柴科夫斯基的交响音乐作品大都具有很强的抒情性特征,而其中以《第四交响曲》最具代表性。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在音乐欣赏活动中的实施,应以音乐艺术最基本审美属性——抒情性为路径,以人类社会中崇高的普遍情感作为审美欣赏对象。
音乐艺术抒情性的实际表现有多个角度和侧面——除以上论述的“以情感人”,抒情性特征还表现在“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再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为例:词作者张藜对曲作者秦咏诚表现眷恋和热爱家乡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有“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进而要求曲作者再创作一首与其音乐情感相同的《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曲调。欣赏者在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审美欣赏活动中,“感同身受”的是对家乡、对祖国无限热爱的崇高情感,这种情感也是无数古今中外艺术经典所表现的人类普遍情感。当欣赏某部音乐作品时被音乐情感所打动,就说明在欣赏者内心深处早已隐藏有这种情感。“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感情共鸣。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的又一条路径就是:在音乐艺术审美欣赏活动中用高尚的人类普遍情感使受教者达到感情的共鸣。
第三,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形象性与思辨性。实施课程思政的最终结果是通过音乐艺术美的熏陶,塑造完美的人格、提高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进而完善人们的社会行为。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3]60阐述的正是音乐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由于在音乐艺术本质规律中与生俱来的审美属性,使得它在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里探索出音乐教育课程思政的最佳实施路径,这些路径要既能够达到教育方针的美育效果,又要遵循“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原则。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按照音乐艺术固有的本质规律和普遍原理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教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引领与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特殊审美属性结合起来,使得课程思政教育的理论观点在音乐艺术审美欣赏中体现得合情合理、入情入理,发挥音乐艺术抒情性的表达优势,把人生观、价值观通过音乐艺术的特殊艺术手段,变成自然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之中的“不说之理”。这个潜移默化的审美过程,就是音乐艺术审美欣赏形象性与思辨性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过程。
综上所述,音乐艺术审美创造所使用的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使音乐作品的内容既有形象性又有思辨性。音乐艺术审美欣赏活动中审美主体最先感受到的就是音乐形象。仍旧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为例,歌曲6—8拍子的节奏、直线式下行的旋律线条,使得音乐形象特点鲜明,非常有音乐个性。加之以直抒胸臆、感情炽热的歌词内容,欣赏者立刻就会被歌曲独具特色的音乐形象所吸引,达到脍炙人口、反复吟唱、竞相传唱的审美效果。在音乐教育环境氛围里还会出现学习或模仿首唱者的音乐处理方式、演唱特点的音乐实践活动,即审美呈现。接下来音乐艺术审美欣赏就应该是作品分析,即思辨性环节。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的思辨性环节是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的有效路径之一: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从审美创造到审美呈现都充盈着饱满的爱国热忱。无论音乐创作,还是歌词创作,最后到首唱者的二度创作,都表现出对家乡和祖国热爱的真情实感。音乐艺术审美欣赏活动最终需要具有思辨性的观点来概括和总结。在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整体音乐实践最后的审美欣赏阶段,只有使用具有思辨性的观点概括出这首歌曲的人文主义情怀,点出热爱家乡和祖国是全人类的普遍情感,也是包括音乐在内所有艺术作品永恒的创作主题,才能保证这首歌曲音乐实践活动的完整性。
音乐教育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蕴藏于音乐艺术特殊的审美视域之中,蕴藏于音乐艺术审美创造、审美呈现、审美欣赏三个音乐实践活动的板块之中。找到这些有效途径,依赖于对音乐艺术本质内涵的认知和对客观艺术规律的遵循,以及把音乐艺术审美创造、审美呈现、审美欣赏的艺术原理,灵活、合理地应用于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首先,在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入讲解、挖掘音乐作品的创作方法和思维方式。包括音乐作品在内的所有艺术作品,无论它的创作者承认与否,没有不打上时代烙印的艺术作品,因为在作品里都有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即使是什么态度都没有,也是一种对待生活和艺术的态度)。柴科夫斯基在1878年3月27日写给塔涅耶夫的信中说:“我可不愿意自己笔下出现一些不表现任何内容而无谓地耍弄和弦、节奏和转调的交响乐作品。我的《第四交响曲》当然是标题性的,但这个标题却绝不可能形诸文字……交响乐——一切音乐形式中最抒情的一种——不是正该如此吗?交响乐不是应该表现难以言传的、出于内心而要求一吐为快的那一切吗?”[4]2由此可见,要在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中,使受教者通过世界经典音乐作品,学习伟大音乐家的人生态度、崇高信仰,获得积极向上的人生经验的教育目的,关键的出发点就是坚信所有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次,在审美呈现环节中准确把握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类型,以完美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进行二度创作。音乐教育课程思政的实施,如果与音乐作品二度创作结合在一起,既能培养受教者的政治思想素质又可以提高受教者的音乐表现能力。最后,音乐艺术审美欣赏环节在音乐教育课程思政的实施中具有非常重要而广泛的作用。音乐艺术特殊的审美属性使得音乐欣赏中的审美体验多种多样,为音乐教育课程思政实施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内容:因人而异的审美体验、以情感人和感同身受的抒情性、寓教于乐的形象性和思辨性,等等。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引领,在音乐欣赏审美体验环节的重要指导作用,应正确处理审美体验个性化与共性化两者的关系,使受教者准确认知音乐作品的思想内容。古人总结道:“乐(yue)者,乐(le)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le)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le)。”[3]236这段话指出了正确审美导向的作用,说明音乐欣赏活动应该达到既有趣味性同时又有思想性的审美效果。
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的理论与实践,全方位地与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契合点。在音乐艺术特殊审美视域的理论与实践中,探索实施音乐教育课程思政有效的、最佳的路径,是音乐教育从业者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