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南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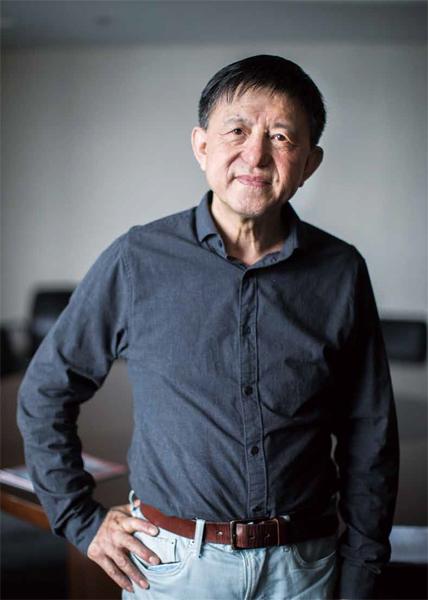
赵鼎新在8月末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他常年生活在芝加哥,居住在一栋有四百多户居民的高楼里,他戏称“一栋楼就是一座村庄”。
赵鼎新身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点在于,他在昆虫学领域学习了12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到博士最后一年时,决定转入社会学领域,“我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
浸入社会学研究后,赵鼎新認为自己首先要克服的是“一种弃医从文的鲁迅情怀”,即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改变中国。“社会需要多样化思想,无论我提出的理论再好,如果一个国家只按照我的理论来发展,肯定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1996年起,赵鼎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他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此后,赵鼎新在国内先后出版《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等书。2012年,赵鼎新出版《民主的限制》,他在序言中描述自己关心中国前途,有很强的现实感,童年生活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又在宁夏当过8年工人。因此,他“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同时对民粹主义保持警惕。
回国后,赵鼎新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赵鼎新在芝加哥时,一直阅读国内外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与身边的人聊美国的防控措施,关心同事所主持的新冠疫情相关研究。在曲折的抗疫过程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他认为怀有各种政治目的的谣言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不实信息的背后是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即使是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我们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强大与困境,谈到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在许多国家的上升,始终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当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世俗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下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如何审视西方近代思想体系,特别是它的生命力及局限性,在避免走向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道路的同时走出自己的道路?”
人:人民周刊 赵:赵鼎新
防疫成功的国家的特点推翻了以前许多理论
人:经过今年的新冠疫情,你对公共卫生和政府运作体系等方面有什么思考吗?
赵:如果我是当时的武汉市长,我该怎么办。我想到这点就浑身冒冷汗:一千万人封城怎么得了。我把这个新冠疫情称为“贝叶斯弥散性灾害”。弥散性是指灾害一旦发生,马上就会散开,而不像地震一样仅仅局限于一地。这类疫情会给决策带来四个非常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难:事后的影响很清楚,而前期对后果难判断;决策者在前期会有很强的投鼠忌器心态,因为从严决策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从严决策一旦成功可能成为众人眼中的错误决策,因为成功的早期控制反而让一些人以为决策者过度反应;为了早期决策的自主性和不给社会带来恐慌,保密是必须的,但是一旦消息传出或者疫情扩散,前期的保密在大家眼里就是隐瞒信息和渎职。
另外,在当时这是个新病,其感染率到底有多高,病症到底有多严重难以确定:低了就是感冒,高了就是SARS。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很难决策,或者说当官会犯当官的错误,专家可能也会犯专家的错误。后来像英国这些国家还搞什么群体免疫,说明专家也会犯错误。
人:你对各国不同的防疫策略怎么看?
赵:我们社会学系有教授领导了一个涉及26个国家、160多人的研究新冠的团队。他们的第一篇文章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的防疫能做得非常成功。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理论,比如国家能力强的国家防疫搞得好、女总统的国家防疫搞得好、西方民主国家防疫搞不好、宗教在社会中影响很大的地方疫情更难控制等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以下这些国家在疫情的第一波中表现都非常出色:中国、越南、韩国、蒙古、约旦、斯洛伐克、新西兰。就这些国家而言,这就把以前所有的理论给否定了,因为这些国家在国家能力、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领导的性别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方面都有巨大不同,但是他们的防疫都成功了。总结他们搞得好的原因无非两点:要么追踪,要么封锁,采取这两个模式都会成功。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则是双保险,追踪和隔离都实施。
这次新冠疫情,哪怕是新加坡、韩国这些抗疫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在贫富得病差异、不同族群得病差异、不同宗教得病差异这三个方面都很明显。而从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的患者这三方面差异不大。这其实是不得了的成就。
封锁是长痛不如短痛,社会代价很大,但可以把病毒捂死,追踪就需要很强的国家能力。这个研究也发现很多西方国家失败的原因不完全是体制问题。他们失败在于两点,第一是认为自己手上的牌很多。他们公共卫生体系很发达,但其实没几张牌——这样的国家反而只能搞封锁,因为他们追踪需要突破个人隐私等等,西方式民主国家比较难做到。第二是意识形态误导。疫情早期不少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信息和防疫经验不但不给予重视,往往还会带着否定态度。结果是延误了时机。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在疫情防治上做得更为有力有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很难争论清楚,但疫情防控的好坏大家都能看得见。
如果不实信息有某种宏大价值观支撑,就成了不可证伪的大谎
人:在美国,核酸检测的结果由疾控部门掌握,但是不会透露给被检测者的公司、邻居等等,因为这涉及个人隐私。疫情防控运用了很多大数据的功能,你认为个人隐私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让渡给政府?
赵:我在芝加哥住的那栋大楼很高,里面有四百多户人家,一个大楼就是一个村庄。早期楼中有一人感染,虽然没说是哪户,但还是通知了大家。后来因为隐私问题就什么都不公布了。这个问题我和不少人美国聊过,很多美国人脑子很清醒,有一个人说美国政府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数据还少吗,每天都在悄悄获取,并且用作各种不同目的,现在却以保护为名不用这些信息,简直就是在愚弄我们。

10月17日,武汉,演员演出抗疫题材歌剧《天使日记》
美国政府能悄悄利用获取到的各种个人信息,却很难公开这么做,因为这与他们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不符。所以当疫情来到时,虽然西方国家有很强的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但他们不敢用追踪来作为防疫的一个手段。
人:疫情和舆情的扩散是同步的,这次疫情中全球都扩散着一些怀有各种政治目的的谣言。
赵:美国政客散布不实信息并且能得到不少支持,背后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首先,不实信息背后是否有一个该信息的主要受众所共享的宏大价值观的支持?如果不实信息背后有某种宏大价值观支撑,该信息其实就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大谎,因为相信这套价值观的人,或者会对该信息的真假不在乎,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分辨能力。即使是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他们对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不实信息也更容易采取体谅的态度。
美国有一套以西方式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和西方国家民众, 对这套话语体系仍然有很强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政客散布的有关中国疫情的各种不实信息,成了一个有话语体系支持的“大谎”。
另外,美国是两党政治、三权分立的体制。在该体制下,虽然特朗普和蓬佩奥等人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人的病毒”“武汉病毒”,并且在病毒的起源地上做了许多不靠谱的文章,但这些言论同时也受到美国反对党领袖、许多主流媒体以及各界人士的公开反对。这些都使得特朗普的言论成了美国的一种声音,而不是全部声音。但外界往往会把中国某些人的个人声音等同于甚至故意曲解为政府的声音。也就是说同样是不真实的声音,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世俗化与启蒙的困境
人:你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负面后果导致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消退,它的消退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
赵:对中国来说现在尚不清楚。世界范围来说,对欧洲的影响让欧洲不知所措,毕竟欧洲自由要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这几十年的移民还有因劳工短缺造成的在地化等等,很多国家像法国完全没能力消化。父母在当地已经是中产阶级了,儿女加入ISIS要去打圣战。自由主义者往往会认为民主是个平台,他们有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如果各种思想能在这个平台上自由竞争的话,那最好的思想最终肯定会占上风。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目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衰落在不同地方的影响不一样。在许多伊斯兰教地区其表现形式是一种与原教旨主义宗教势力结合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中东宗教民族主义全面崛起有几个原因。第一是美国带着打偏架的中东政策,明显偏袒以色列很多。第二就是美国由于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原因,改变了间接帝国传统,原来是间接控制,现在则是包括了军事占领在内的更为直接的干涉。第三是美国在和苏联斗的时候,不管你是民主还是专制,只要反苏联反共他都支持,但是民主化浪潮出来之后,美国有一个阶段是对任何争取民选的团体都支持,导致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不少带着很强的保守宗教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的壮大。现在CIA又回来了,想办法压制他们、反民主。目前美国从过去舆论和政策一致的传统,转到了舆论还是支持民主自由、但政策层面却越来越现实主义。
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却很分裂,不同伊斯兰教教派之间有冲突、不同部落之间有冲突,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伊朗和土耳其都不是阿拉伯国家,却是中东穆斯林地区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大国。但这两个国家也搞不到一起去。土耳其最近拍了几个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关于奥斯曼帝国早期建国历史的系列电视剧,这些剧在东南亚的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民众中很受欢迎,但是在叙利亚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却被禁止,因为中东许多国家原来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尽管如此,ISIS还是能在中東很快地发展起来,甚至像一个新兴“国家”,“疆域”最大的时候据说比英国都大。ISIS领袖自称“哈里发”,号召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都参与大圣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召集到美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穆斯林加入(注: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象征,从原则上说,哈里发不仅对哈里发国拥有统治权,也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自土耳其的凯末尔政府废黜并流放奥斯曼末代哈里发以后,“哈里发”这个称呼已消失近百年。“伊斯兰国”及其“哈里发”并不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或绝大多数穆斯林所承认——见澎湃新闻《消失近百年的“哈里发”为何在“伊斯兰国”复生》)。
人:你在2014年提到,许多人对启蒙运动之后的世俗思想体系失去兴趣,宗教领袖和宗教意识开始抬头。
赵:17世纪以后人类所产生的主要的世俗思想体系的影响力都走了下坡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并且重新开始和政治产生紧密结合。比如,许多国家原来都施行政教分离政策,但现在某些国家政教却逐渐开始合流。大量宗教人士开始参与到政治中,在基层层面就是社会运动,比如反对堕胎;在选举层面就是进入体制。随着宗教人数增多,总统就不得不“假装”,民主社会就是哪些人多,就有人会设法抓住这个票仓。
人:你怎么看待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影响力不断减弱的现象?
赵: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自己拍拍脑袋就能设计出一个理想社会,并且他们的理性设计要比“上帝”的安排还要好,我这儿说的就是自由主义,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其他各种“主义”。但是在今天的世界,这些“主义”的影响力都在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影响力减弱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目前遇到自启蒙运动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1月3日,美国波士顿,美国大选选举日投票正式开始,选民排长队等待投票时洗手消毒
人:你多次提到过马克斯·韦伯,第一次读到韦伯是什么时候?
赵: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当时是走向未来丛书,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80年代出国之后又读了一遍,还是不能认可他的具体解释,但却开始能把此书当成一本经典来欣赏,并且开始理解宗教的巨大力量。第三次是读韦伯的《中国的宗教》,此书具体史实上有不少错误,却提供了史学专家完全没有能力提供的insights(洞察力或原创性论点),让我领略到了比较视角的魅力。
开始读懂韦伯还是进入社会学领域若干年后。当我开始寻找我的理论工具时,我发现韦伯的合法性分析、理想类型方法等等相对来说要比别的方法好用很多。
人:你怎么看待海外学者对儒学和现代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你认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赵:没有冲突的。你不能搞传统的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式的儒学,那是和现代民主很难相融的,但我们可以对儒学文本做出新的、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解读。你从传统儒学本身去寻找现代民主,那是没有的,但是改造成为现代化思想的一部分那是可能的。
但是儒学在当前只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拥有多种资源并且能整合社会方方面面的组织和制度。任何思想,没有组织、资源和制度,它就很难取得深入的影响。这其实是当代儒学发展最大的困境。
启蒙运动之后产生了不少线性历史观,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真知灼见,以及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原理,因此产生了大量思想家。就像我之前分析过的波兰尼和哈耶克,他们的论点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像是盲人摸象,但是他们都是好学者,各自都做到了一種片面深刻。总之,虽然启蒙以来的哲学和思想有许多问题,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启蒙后产生的知识分子分析问题的方式、他们的理性精神,以及给我们留下的大量具有原理性的遗产却是我们在目前所必须坚持的。
人:人需要启蒙吗?
赵:我青年时候见过很多悲剧。当时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道,什么叫同情,同样也不能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声音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启蒙之后我们获得的并不是一种玫瑰色的自由,而只是一种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后果的新的生存条件。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实习记者李丽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