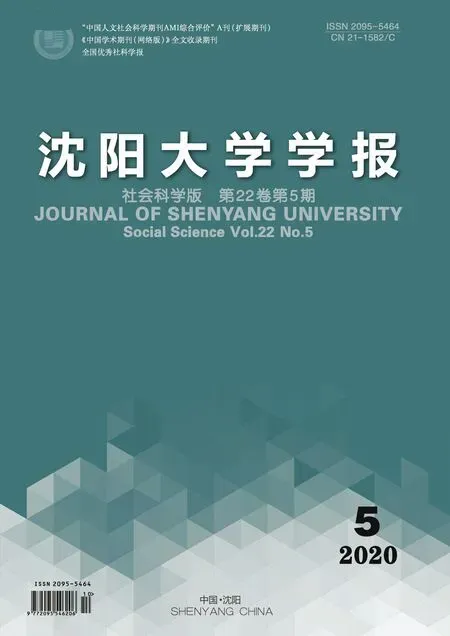古斯特少尉“双重危机”形象的表现方式及时代意义
田 思 悦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从19世纪末向20世纪初过渡的时期常被称为“世纪之交”,此时,欧洲社会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变革之中。在技术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欧洲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在科学方面,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提供以生物学理论解释世界的新视角,颠覆了传统的世界观;在哲学方面,马克思《资本论》的出版扩大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力,扭转了长久以来西方唯心论哲学的传统。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思想文化的异常活跃,文学领域的关注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宏大的斗争主题、勇猛的仗剑英雄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回忆,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看到的是生活的贫困,是人的自私、贪婪、冷漠[1]。走下神坛的英雄人物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1900年,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在《新自由报》圣诞版上发表了《古斯特少尉》。主人公古斯特作为奥匈帝国军官,本该是英武果敢之人,但实际上却是胆小懦弱之徒。施尼茨勒用印象主义和内心独白等典型的现代派文学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世纪末奥匈帝国军官形象内在的矛盾和性格冲突,暗示了帝国内部不同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
一、 古斯特少尉人物角色的双重危机
从时代上看,古斯特少尉生活于充满变革的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身份上看,他隶属于一个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群体----奥匈帝国军队。因此,古斯特人物形象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双重影响。在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下,人物形象面临个人和阶级的双重危机。
1. 个人危机:神经质人格特征
古斯特少尉身上带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如百无聊赖、悲观厌世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神经质”人格特征。“神经”或“神经质”这样的词汇反复出现在主人公的思维中,可见他对自己的这一状态也有所察觉。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神经质可能有头痛、消化问题、眩晕、失眠等多种不同症状,可能在失落和希望、末日恐惧和热忱追求等矛盾中来回摇摆,但其核心特征在于混乱。在古斯特少尉身上,这种混乱首先体现为半梦半醒的思维状态。他的思维断断续续,似乎仍然处在理性的边缘,但又不完全合乎逻辑。即便是在与其他人发生对话的时候,他的思维也并不完全清晰。当他与面包师因为衣帽间拥挤而产生矛盾时,面包师要求古斯特少尉保持安静,甚至称其为“傻小子”,并威胁要折断其军刀。此时,古斯特少尉似乎并不处于清醒状态,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了真实威胁,也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离开衣帽间的。他的头脑中断断续续地出现下述想法:
“他说的是什么?我真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他在哪儿?他已经走开了……也许这只是一个梦……这是怎么回事儿?真的发生过这种事?真的有人这样对我说话?……怎么,我已经来到了大街上?”[2]120
混乱还体现为忽视因果关系、不断产生抱怨心理。罪责这个词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但无一例外,古斯特少尉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忍受无聊的音乐会而不能去赌钱,是因为前一天被别人赢了太多钱;他之所以遭到了面包师的“羞辱”,原因在于朋友送他音乐会的票,但他喜欢的姑娘拒绝和他约会;他没能够去骑兵团,是因为父亲认为去骑兵团“是一种太昂贵的娱乐”[2]125。这些想法并不符合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主人公仅仅是为了将自己从失败的境遇中解脱出来,才屡次将罪责推脱给外界。此外,古斯特少尉面对死亡、婚姻等问题的态度也是混乱的。面对死亡,少尉有时觉得为了捍卫荣誉必须慷慨赴死,有时觉得自己如果失去生命颇为可惜。他情绪低落时就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决斗,心情大好时又觉得自己可以将对手“剁成肉糜”[2]131。面对女性,一方面,他思考是否应当结婚,以使家里有个“漂亮女人”[2]119;另一方面,又对长久地和同一位女性约会感到厌倦。可见,古斯特少尉缺乏稳定而理性的判断,对事物的态度往往随着个人主观感受的变化而变化。“神经症”会使人遭受“精神不安”之苦。在音乐会上,古斯特少尉便显示出极大的不安。尽管反复暗示自己要更加耐心,但却始终不能奏效。他甚至将自己的不安和暴躁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他担心自己向旁人借用望远镜或把钱夹子从衣服里拿出来,可能会让对方想要“吃掉自己”[2]117。音乐会结束以后,古斯特少尉与面包师的冲突也是由不安和烦躁引发的。少尉因着急而做出的插队行为及其表现出的暴躁态度,让面包师感到愤怒。发生冲突以后,少尉在街上游走时,不安的情绪已经上升到“焦躁、抓狂”的程度。这种焦虑和躁动不断引发冲突,让古斯特少尉反复产生自杀和决斗的念头。上述“神经质”人格特征让古斯特少尉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也使其生命遭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以上种种是其在个人层面产生的危机。
2. 阶级危机:奥匈帝国军官阶级的没落
“军官”这个职业身份也给古斯特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匈帝国军官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按照社会角色期待,军官应当是绅士群体,应当严格遵守道德和社会规范,而不能展现任何个人的、个性化的特征。与同时代的许多军官一样,古斯特少尉的身份认同主要来自军队,因此荣誉惯例和部队准则是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在施尼茨勒笔下,古斯特少尉习惯于压抑个人的情绪和感觉,用以迎合社会对军官的要求和期待。面对与面包师的冲突,与其说古斯特少尉害怕失去荣誉,不如说他是害怕沦为别人的谈资和笑柄。他一路都在担心面包师会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而不确定的结果造成了他极大的心理焦虑,个人情绪和其身份所要求的理性不断交锋。当个人情绪占据上风时,他就展现出面对死亡的真实恐惧:“怎么?牙齿在格格打颤吗?哎呀!那就让它格格打颤一会儿吧……”[2]123,“古斯特,你对自己可得真诚坦率!你感到害怕了”[2]128但当理性占据上风时,他又对自己讲:“丧失名誉,就是丧失一切!”[2]122于古斯特而言,真实情绪只有在极少数独处的时刻才可能出现。大多数时候,他只会选择服从于社会、部队、上级的期待和要求。主人公还反复产生自杀和决斗的念头,以期用死亡弥补被面包师玷污的荣誉,这正是积极迎合军队规则的表现。从个人层面上看,古斯特少尉并不想承担自杀和决斗带来的死亡风险。在他的记忆中,第一次决斗时的心情既激动又害怕,最后他战胜了实力不凡的毕桑茨中卫。相比之下,此次的决斗对象----医生,似乎不具有任何威胁,少尉却并未因此获得平静与信心。尽管古斯特对即将到来的决斗充满焦虑和担忧,但军官的身份要求他压抑个人求生的本能,将军官的“荣誉”置于生命之上。他心中始终有“为荣誉而死”和“为自己苟活”的较量。对于奥匈帝国的军官而言,决斗本应该是捍卫荣誉的高尚举动;若荣誉受损而又不愿意决斗,就只能放弃军籍。在古斯特身边,不乏为了求生存而放弃军籍的人,古斯特对这样的人十分厌恶。但事实上,古斯特本人也在两个选择之中犹豫不决。他似乎没有“捍卫荣誉”的强烈欲望,同时又对放弃军籍的后果感到恐惧。他不断权衡,试图找到一个万无一失、自我保全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对古斯特而言,决斗和自杀都已经失去了在“荣誉”层面的意义,不过是一条强制性的、不得不服从的规则而已。甚至在最为痛苦的时刻,古斯特少尉想到的也不是捍卫“荣誉”的信念,而是外部的规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最后的时刻,举止要大方,像个男子汉,像一个军官”,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上校能够说他“是一个勇敢的人”[2]122。可见,古斯特少尉认为自己的价值并不来自于对荣誉的捍卫,却来自于上级的评判。然而,古斯特少尉身为军官而产生的身份认同也岌岌可危。随着帝国军队不断吸纳来自市民阶级的年轻人,军官作为贵族的地位面临威胁,军官阶级的特权和荣誉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军队森严的制度和规则不断失去效用。古斯特少尉这样的军官开始怀疑自身价值并失去信念,在“遵从内心”和“遵守规则”的两极矛盾之间不停摇摆。作为军队里的底层人物,整个军官阶级的没落趋势构成了古斯特少尉的第二重危机。
3. 奥匈帝国新旧价值观的更替
与施尼茨勒的不少作品相似,小说《古斯特少尉》发表之后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施尼茨勒笔下的古斯特少尉是否损害了奥匈帝国军队和军官的形象。在当时的维也纳市民群体中,《新自由报》的影响力较大,也正因为如此,官方对这部小说的反应极其强烈。小说发表仅仅三天,《国防军》日报就刊发匿名文章,措辞严厉地批评施尼茨勒。1901年6月,施尼茨勒不得不放弃军籍,原因之一便是他在《古斯特少尉》中对军官进行了“不当”描述。《古斯特少尉》的情节并非由作家凭空捏造。早在1896年,施尼茨勒便记录下这部小说的创作红线:“一个人挨了一耳光;没人知道这件事。打他的人死了,他平静下来,他似乎不是因为被损害的荣誉而痛苦,而是因为害怕别人会知道这件事而痛苦。”[3]12这一素材可能来源于奥匈帝国作家、外交官利安德里安与某位面包师进行的一次决斗。可见,小说与奥匈帝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施尼茨勒选择古斯特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并非偶然,其背后潜藏着作家对时代动向的思考。一方面,这个姓氏让读者联想起马戏团小丑的名字----笨蛋奥古斯特;另一方面,又与伍斯特非常相近,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传统喜剧形象----汉斯伍斯特,一位充满欲望的鄙俗农夫。借助这个语言游戏,施尼茨勒暗指古斯特少尉不再符合社会对军官的期待,他不过是世纪之交时期一个浅薄粗俗、神经质的普通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傀儡、代表,其背后是整个帝国军队。1871年德意志统一,官僚、军人和容克贵族逐渐成长为支配欧洲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服从上级、自我克制则被美化为荣誉和良心[4]。军官一度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因而不具有个体性。到了作家施尼茨勒所处的19世纪末期,市民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社会对个体、个性的关注日益加强,强调纪律、规则、统一性的军队价值观必然随之没落,古斯特少尉的危机状态正是军队没落的一个缩影。与之相对的是作为个体商人的面包师勇猛强悍,他的强硬态度代表了个体和市民阶级的崛起。二者的对比展示了不同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暗示了新旧价值观的交替。
二、 双重危机的文学表现形式
古斯特少尉呈现出的危机状态是世纪之交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状态, 施尼茨勒巧妙地采用了两种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手法: ①印象主义文学写作方法。 研究者往往关注施尼茨勒戏剧与印象主义的关联, 却忽略其小说中的印象主义文学特征; ②内心独白手法。 现代派作家认为传统叙述方法已经不能准确表达现代世界的真相, 内心独白手法则可以更好地表达人物内心。 施尼茨勒便是德语文学界使用内心独白手法的先驱。
1. 印象主义
首先,施尼茨勒选用的题材具有印象主义特色。主人公古斯特的身份是一名军官,本应该活跃于军事、政治等领域,但施尼茨勒却将这些领域完全排除在文本之外,转而聚焦一名军官的个人生活状态:在音乐会上的烦躁表现,对待女人的轻佻态度,出入酒馆、赌场、舞厅等场所的经历,以及神经质的思维特征等。即使是面对极其严肃的话题,古斯特少尉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他的思路常常被琐事或女人占据。如在设计自杀计划时,会忽然想到对待女人要“多献殷勤,多送鲜花,多多美言……”[2]124回避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事件,着墨于个人生活经历,这是印象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5]。从视角上看,小说以古斯特少尉的思维为核心,他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观察也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如在音乐会上,他有过这样一段独白:“那个家伙干嘛老看着我?我觉得,他是注意到我感到无聊乏味,根本没有在听……”[2]117在他的设想中,如果向上级汇报与面包师的冲突事件,温文尔雅的上校一定“回敬以谩骂和羞辱,然后引咎辞职!”[2]120。古斯特少尉不仅十分关注周围人的一举一动,还时常从自己的立场臆测这些举动背后潜藏的想法。这种强调个人主观感受、弱化客观事实的表现方式也具有印象主义作品的特征。从小说发生的空间来看,古斯特所处的环境由室内音乐会转向室外开放空间。他一直处于对“新鲜空气”的迫切需求当中。在听音乐会时,他便想道:“真热啊!怎么还没完?我真渴望清新的空气!”[2]117而到了普拉特公园以后,他也反复感叹道:“空气如此清新,周围如此静谧……”[2]123,“啊,空气真新鲜,它将离我而去……”[2]126对室外的向往是印象派画家最初的诉求之一,画家们会着重强调室外光线和色彩的对比变化。施尼茨勒在《古斯特少尉》中也描述了一个迫切向往室外环境的人,小说虽然没有刻意强调光线和色彩,但在环境描写中仍渗透了少量有关“天色”的词句,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印象主义绘画的主张。小说也不乏对主人公感官感受的描写,几乎所有相关描写都表现了古斯特的焦虑和慌乱。小说中首先出现了对视觉的描写,主人公通过视觉和听觉确认具体的时间。一开始便出现了古斯特看手表确定时间的细节;来到室外以后,古斯特又通过“天真黑啊!”[2]123“天色已经发亮了!”[2]126等光线和色彩的变化来确定时间。在此期间,古斯特还通过倾听钟声来确定时间,小说甚至完整地再现了他数钟声的过程。施尼茨勒对感官运用的描写还远不止于此,在室内场景中,古斯特通过视觉感受细致地观察周围人的举动、所携带的物品,以及他们的眼神;与面包师发生冲突前夕,听觉感受占据了上风,他先是听见嘈杂的声音和争吵,随后才通过视觉观察确定真实的情况、对方的身份,等等。到了室外,古斯特依然依靠视觉和听觉确定自己的处境,如:通过视觉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阿斯佩恩桥、普拉特公园、第二家咖啡馆;倾听钟声、车马声辨别周围的环境。施尼茨勒还加入了对嗅觉的描写:“这里有一股什么怪味?……这会儿还不可能开花吧?”[2]123,“今天真暖和,比昨天要暖和多了,有一股香气,一定是花开了……”[2]1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感官感受往往是彼此独立的,古斯特不会在同一时刻调动多种感官获取清晰明确的信息。如他听到了钟声,就不会再去看手表;闻到了香气,就不会用眼睛去追寻香气的来源。正如印象派艺术家所主张的那样,古斯特一直体验着当下的、彼此割裂的印象、感受、气氛。从语言层面上,整个小说具有口语化倾向和方言特征,使用了大量法语、英语和拉丁语词汇。德古意特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历史批评版《古斯特少尉》中,评论部分对文本中直接使用或化用的口语词汇及外文词汇进行了详细标注,数量总计超过50个[3]553-566。甚至最初版本的标题“Lieutnant Gustl”中也使用了法语词汇。1912年《施尼茨勒选集》出版以后,才改成了德语写法“Leutnant Gustl”,后续版本的标题多沿用此德文写法。语言的混用使得小说更加贴近事实的原貌,这同样是印象主义文学的特点之一。罗斯巴赫指出,一定程度上,古斯特少尉思维缺乏内核和缺乏连续性的特征借由印象主义手法得到了表达。作为世纪之交的文学潮流,印象主义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多关注人物的主观感受和思维。借此手法,古斯特少尉混乱而模糊的思维和感受跃然纸上,古斯特的人物特征也如同一幅印象派绘画若隐若现。
2. 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是以第一人称、用直接引语的形式来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叙事手法。它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叙述者在文章中消失,文本没有对情节发展的提示;文字直接反映人物的思维过程,可能有断续和跳跃,进而给读者造成阅读困难;小说故事性较弱等。尽管施尼茨勒早年作品中也出现过内心独白手法,但这一手法在《古斯特少尉》中所占篇幅之长可谓空前。这种全新的创作尝试直接来源于法国作家杜雅尔丹的启发。1887年,杜雅尔丹小说《月桂树已经砍尽》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和一名歌女某次约会的过程,时间跨度仅为几个小时,但主人公心理活动却有极大的时间跨度,缺乏传统小说的持续性、逻辑性、条理性、明晰性[6]。尽管这部小说销量并不算好,但却依然是最早利用长篇内心独白手法进行的文学实践。施尼茨勒认为,杜雅尔丹的作品之所以不甚成功,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这种创作形式的题材,而内心独白所适合的题材是一种边缘状态,一种存在危机,是一种向死亡倒塌的内化。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古斯特少尉个人,还是他代表的阶级,都处于这样一个走向衰亡的边缘状态。可见,这一题材与内心独白手法是一组堪称绝妙的搭配。施尼茨勒通篇使用了多个问句、感叹句和省略号,通过这些语言技巧,古斯特少尉的思维被成功地转换成了可以供人阅读的语言,生动地还原了其思想流动和情绪变化,这种形式让人联想到戏剧中的舞台说明。 施尼茨勒将主人公彻底的从叙述者视角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进而将这些最私密的个人的思想和情绪呈献给读者。 为了使古斯特少尉的内心独白不至于难以理解,施尼茨勒煞费苦心。首先,他安排古斯特少尉与面包师及咖啡馆服务员直接对话,两次真实对话打断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给小说构建一个牢固的事实根基,也给读者提供一个理解的抓手。其次,看似啰嗦、混乱的独白隐藏着很多明确的信息,如古斯特少尉正在一场演唱会上,时间是4月某日晚上9点多,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了戏票,但自己并不感兴趣。他前一天和一位医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即将决斗。 他喜欢的姑娘正在和一位犹太富人约会,等。 从古斯特少尉对其军旅生涯的回忆中,甚至可以推算出其年龄为23岁。 这些信息共同呈现了古斯特少尉的日常生活状态和个人真实情况, 为读者理解古斯特的心理和思维提供了充足的背景。 更为匠心独运的是,为了使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更加真实自然, 施尼茨勒在表达这些客观信息时, 有意使用主观性较强的语言。 完全从主人公的思维出发, 从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进而更加直观地表现古斯特少尉所处的生存边缘状态。
三、 结 语
《古斯特少尉》表现了主人公所面临的个人危机和阶级危机。而在表现这种危机状态时,作家施尼茨勒选用了印象主义和内心独白两种世纪之交时期兴起的现代派文学手法,细致刻画了主人公的个人感受和心理活动,也暗含了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判。当时的奥匈帝国虽然尚未有明显的衰落迹象,但欧洲大环境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展现影响,军官等曾经主宰社会命脉的阶级逐渐显露颓势。古斯特少尉这一人物所呈现出的“双重危机”体现了1900年前后奥匈帝国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新旧价值观的更替。